用故事講述云南民族團結進步的歷史經驗
——讀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之一
□ 文/龍成鵬
用故事講述云南民族團結進步的歷史經驗
——讀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之一
□ 文/龍成鵬
我們這期原著欄目,就僅從個人“歷史”的角度來介紹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憶》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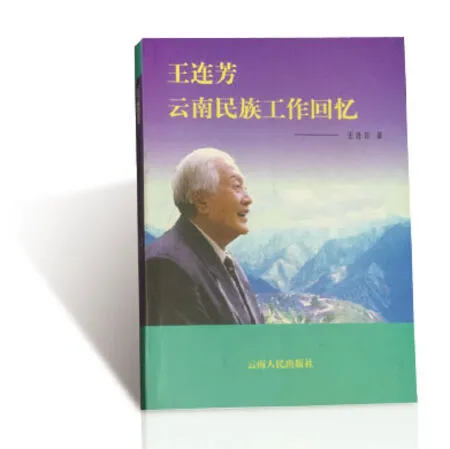
王連芳(1920-2000年),回族。河北省滄州市鹽山縣人。
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任冀魯邊區回民救國總會主任委員、
冀魯邊軍區回民支隊政委、渤海區回民協會總會主任委員。建國后,歷任國家民委處長,中共云南省委邊疆工委副書記、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長,云南省民委主任,
云南省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是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在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的語境下,回顧云南民族工作的歷程
1950年8月6日,作為中央民族訪問團第二分團的副團長,王連芳第一次到云南。1952年底,訪問團工作結束后,王連芳留在了昆明繼續從事民族工作。1988年離休后,他開始口述回憶這幾十年來的工作經歷。這些口述經過整理,匯集成一篇篇短小精悍充滿趣味性的文章,陸續發表在《云南日報》《民族團結》等媒體上。1999年,先后發表過的87篇文章被匯集成冊,以《王連芳云南民族工作回憶》為題出版,被省委領導稱為是“對云南民族工作的又一重大貢獻。”2012年,在云南民族工作者和媒體人的努力下,這本描述云南民族工作歷程的書再版。
今天的云南,正在努力建設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示范區建設是擺在民族工作者眼前的目標,從歷史看,云南民族團結進步的局面,是幾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云南民族工作回憶》就是這段歷史的記錄,它用生動感人的細節為我們繼續總結云南民族工作的經驗教訓,做了最好的示范。因此,在今天的語境下,我們更應該去讀這本書,去重溫這段光輝歲月。
民族工作者的回憶,可以構建三種歷史
云南民族工作者的回憶性文字,不止有王連芳的《云南民族工作回憶》,我印象深的還有云南文史資料選輯叢書里的《云南民族工作》(共三冊)。這些來自一線的民族工作者的回憶性文字,不同于一般的媒體報道,他們深入、細膩、感人,是我們介紹云南民族工作成就最直接的文獻材料,也是影響、教育我們年輕一代民族工作者的最佳教材。甚至可以說,這些優秀的回憶性文字構成了云南民族工作的“成功學”,它不應該跟我們這個急劇變遷中的社會,以及變化中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工作者割裂,而是要成為他們提高技巧,培養事業心的“成功學”教材。
王連芳的《云南民族工作回憶》和很多老一輩民族工作者的回憶一樣,它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成一個詞,就是“歷史”。歷史一詞,細分可以從三方面理解。
第一,這是個體的歷史,因此從中可以看到個人的成長,轉變。
第二,這也是民族工作的歷史,從中可以看到民族工作的曲折歷程,以及較大的歷史事件。
第三,這還是民族文化的變遷史。中央訪問團1950年到邊疆民族地區,其所見到的民族同胞,跟今天差別不可謂不大。但沒有比較,就看不出差異。而《云南民族工作回憶》這樣的書,就提供了一個歷史參照系。
讀歷史,可以明智。而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把歷史跟今天這條線聯系起來,把歷史的經驗融入到當下的實踐。
我們這期原著欄目,就僅從個人“歷史”的角度來介紹一下《云南民族工作回憶》這本書。
一個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煉
王連芳個人的成長,在《云南民族工作回憶》中并沒有專題討論。個中原因,可能跟王連芳寫作的立場和態度有關。顯然,他并不想寫成一本自傳,而是想描述民族工作者這個群體的經歷。
云南的民族工作,始于1950年的中央訪問團。
1950年春,在毛澤東主席的提議下,中央政府組織了中央民族訪問團。訪問團的工作任務主要是傳遞關于新中國的消息,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調查了解民族與邊疆社會的實際。中央訪問團先后組織了四個團,第一個啟動的是西南訪問團。
訪問團的成員結構復雜,分醫療組、文工隊、展覽組、放映隊和攝影組,團員中還有專門從事考古、民族語文、民族工作的專家、干部。從職業看,有藝術家、作家、記者等不同職業。
訪問團這一個群體的成長,王連芳在書里面有一節單獨描述。“來云南時,訪問團都是年輕人,團長夏康農40多歲,我30歲,秘書長聶運華27歲,其余的大多數20多歲,最小的才18歲,而且相當一部分來自大城市。”
這些人大多數沒有留在云南繼續從事民族工作,但他們回到各自的崗位后取得的成就,多少都跟訪問團的經歷有關。這些人,有歌唱家胡松華、郭淑珍、仲煒,舞蹈家張苛,作家李喬、鄧友梅……這些文藝人士,當年都還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訪問團經歷對他們的影響,可以從郭淑珍的一句話里看出來。若干年后重游云南時,她感慨道:“我一生的事業和世界觀,是在訪問團打下的基礎。”
王連芳,跟訪問團里的文藝人士不同。王連芳是河北人,回族,13歲(1933年)就在北方參加革命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被調到中央民委工作。盡管對黨的民族政策很熟悉,但直到1950年8月抵達云南時,這位年輕的民族工作者對云南民族復雜的情勢的了解,不會比今天同齡的民族工作者更多。
據王連芳在書中回憶,中央訪問團的領導干部主要是北方人,“很苦惱的問題就是不了解南方少數民族的情況”。
在進入云南的時候,盡管做了大量的功課(可參見附錄:《中央民族訪問團的任務、工作方法和守則》),但他們對于云南的了解,還只是集中在少數幾個民族上。這些知識,顯然是民國時代的積累,還有待進一步深度調查。因此,王連芳也特別提到,中央訪問團要求云南分團認真做好調查。
有一個故事,是王連芳對自己工作的反思,我們可以管窺訪問團當時的知識狀況。
1950冬,訪問團在麗江召集滇西北的各民族代表開會。會上王連芳要求民族代表一律穿自己的民族服裝。結果獨龍族代表只好穿裸露著雙臂的麻布褂子,蹲在寒風中瑟瑟發抖。“這一幕使我一直深感內疚”,所以一直想深入調查。1957年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深入獨龍族聚居區做調查,帶回來的資料讓王連芳對獨龍族的認識更進了一步。這一年,恰好貢山縣縣長孔志清(獨龍族)參加民族參觀團到昆明,所以王連芳跟孔志清又進行了一次深入的對話。對話讓王連芳再次覺得慚愧。
王連芳回憶,“我跟孔縣長說,你們生活很苦,有許多原始社會的風俗習慣,你給我講一講。”但聽到“原始”二字,孔縣長就“不太高興”,說要讓王連芳解釋一下,什么是原始社會。王連芳的解釋讓孔縣長更加不高興了。因為列舉的各種“原始”的東西,比如住的是低矮簡陋的房子,人口少,不會做買賣等等。這些解釋,孔縣長一一反駁。“昆明人的房子高,比我們的山崖高嗎?他們人多,比我們的大樹多嗎?”孔縣長還說,獨龍族在山上的生活,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差,他們想吃野雞,可以上山打,而這是昆明沒有的。
王連芳總結他和獨龍族縣長的談話時,頗為感慨:“孔志清的一席話,顯露了獨龍族兄弟獨特的民族心理。我深感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自豪感,從那以后我再不用‘民族落后’這個詞,改用‘先進’和‘后進’。在這一點上,孔志清同志是我的第一位老師。”
從不了解獨龍族的民族服飾和經濟狀況,得出獨龍族“落后”的結論,再到意識到獨龍族人有民族自尊心,并由此不再用“民族落后”這樣的詞匯,王連芳的自我反思為我們勾勒出一個民族工作者自我修煉的不同層次。
我們可以肯定,王連芳即使初到云南,對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平等、團結的主張也是十分熟悉的,當然也貫徹落實尊重民族傳統和文化這樣的基本要求(在麗江王連芳讓獨龍族代表穿自己的服裝,其初衷也是出于尊重),但在云南的具體工作中,還是會出問題。這個事例說明,讀懂民族政策,有民族團結的意識和觀念,并不意味著工作中就不會有錯誤。而老一輩民族工作者可貴的地方,是他們能及時發現問題,嚴格要求自己,自我反省。民族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思想工作,民族工作者的自我修煉,自我反思,不可謂不重要,而從老一輩云南民族工作者身上,我們已經看到最好的示范。
民族工作,需具備了解之同情
還有一個例子和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有關,同樣具有現實性。
王連芳留在云南工作后,經常深入少數民族村寨做調查,有時候,在一個寨子會住上幾十天,其認真的態度跟做學術研究沒有區別。1953年,王連芳在潞西縣的景頗族寨子住了一個月,期間有一次騎馬去一個景頗族寨子,到寨門外向導就急切地把王連芳從馬上叫下來。理由讓人有些難以置信。向導說,每個寨子都有一種專門咬騎馬人的鬼,要是他被咬死了,向導不好交代,所以趕緊勸誡。向導的話提醒了王連芳,“以后我到景頗族寨子,都尊重他們的風俗,徒步進去”。
尊重當地的文化、尊重各民族的風俗習慣,是黨的民族工作60多年來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經驗,也是今天民族工作者的基本常識和基本技能。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者開創歷史的角度看來,這個很小的事例告訴我們,云南民族工作的經驗,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這樣一步步建立起來的。而且今后還要繼承下去。各民族的風俗習慣,只要不違反國家法律,不危害其他人,無論跟其他人的生活常識有多么大差異,都應該被視為合理,進而得到尊重。
尊重民族文化是建立在了解基礎上的。王連芳回憶說,1958年受“左”傾影響,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的社會和諧穩定也受到破壞。有一次,由于“大躍進”的錯誤做法引起景頗族山官的反抗,為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地方干部把這些山官送去“學好隊”教育。臨走時老百姓來送行,每個人都朝那個山官的手心吐一口吐沫。外來的干部不了解景頗族文化,以為這是群眾“唾棄”山官。殊不知,恰恰相反,這是景頗族隆重的禮節,是大家出于關心山官,對他的遠行受苦的祝福。王連芳反思說,群眾這樣做就表示對當時的錯誤政策不滿,而這些干部完全會錯意。
客觀上講,對類似的文化做了錯誤解讀,當然也就不能準確理解老百姓的心聲,甚至還會加重錯誤情勢。
云南民族眾多,民族文化內涵豐富,民族工作乃至其他行政工作,都離不開對文化深入的學習和洞察。很多反面例子都是忽略文化造成的。今天在云南建設全國民族團結示范區進程中,政府的行政力量更加深入地觸及甚至改變著各民族社會,如何做好這些工作,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問題。我們能否讓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建設,不僅在我們的時代有“示范性”,也讓未來的民族工作者看到某種“示范性”,就像我們今天重新認識老一輩的民族工作者一樣?
(責任編輯 趙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