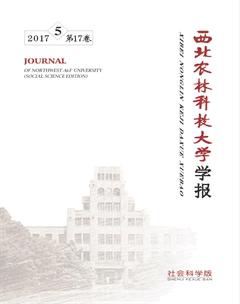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與社會資本的關聯效應測度
詹國輝+張新文
摘 要:農村水利設施的有效供給是實現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載體。通過梳理公共品整體性供給與社會資本的既有文獻,進而以博弈論詮釋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的行為選擇。同時建構出社會資本對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的Logit回歸模型,借助于CFPS中關于“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數據證據進行分析。研究發現,社會資本的存量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起到積極作用,其中社會網絡、社會參與以及農戶個體特征對整體性供給產生顯著影響。為此,通過營造農民整合參與的有利環境,增強農村社會資本的建設,有效培育和發展農村精英,以此來實現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的有效性。
關鍵詞: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社會資本;關聯效應
中圖分類號:F32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5-0098-06
一、問題的提出
具有公共品屬性的水利設施建設是農業發展的基石,也是國家糧食生產的核心保障。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引起的水資源短缺不同程度地抑制了農村區域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據國家防總統計,2013年全國因洪澇災害直接經濟損失3 146億元。截止2014年5月全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9.37億畝,僅占耕地面積的51.5%,仍然有近一半的耕地是“望天田”,基本灌溉條件比較缺乏。囿于水利基礎設施的不足,愈發加劇了區域性的整體貧困程度。水利基礎設施的供給現實以及供給的非有效性,反映出當下農村治理現代化的內生動力和長效續航力不足的問題 [1]。
而農村水利設施供給只憑借基層政府供給無法理順供給與治理過程,也未必能實現跨部門間的項目承接與轉移[2],表征出“整體性供給”有其存在的應然性。緣起于農村水利設施的碎片化現狀,單獨由政府或者是農村居民本身來實現水利設施供給不現實,因此施行農村公共品的整體性供給是必然的選擇。在當前農村仍是以親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境況下,通過整合農村居民與基層政府等力量實現農村公共品的整體性供給,不失為緩解當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供給非有效性的一種良治化模式。農村居民如何通過依托于以人際關系為核心的社會資本來實現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整體性供給已迫在眉睫。通過整合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主體,有效促進農村公共品供給,實現決策機制再整合,同時建立協同監督機制來協調縣鄉政府、村民以及第三方主體,最終形成城鄉均等化格局[3]。目前農村公共品的整體性供給與社會資本的關聯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社會資本不同程度會影響集體行動的規模和效應。社會資本的累積過程中勢必會形成信息交換與信息交流,并以此來促成集體行動[4]。Bhuyan認為社會資本在尊重對方農戶基礎上能及時、準確地提升對方農戶的整合與整體性供給意愿,可見社會資本是實現化解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之道[5]。(2)鄉村內部微觀主體的良性互動增強了人際網絡,能夠有效助推農村社會資本的提升,實現農村治理轉型的多元化,增強農村區域的開放性,最終促使農村傳統社會治理模式發生轉變[6]。(3)傳統自然村落在城鎮化、工業化的當下中國,也處于一個不斷消減的過程。我國的自然村2000年前有360萬個,到了2010年則只剩270萬個,每天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100個,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自然村的這種消亡速度還在加快[7]。(4)農村鄰里關系在“親市場”價值導向下的疏遠,宗族勢力的瓦解以及農村精英的流失,客觀上造成了部分農村區域內社會資本的衰退。新型農村整體性供給交易型的社會網絡尚未成型,勢必會影響到農村社會資本的有機整合,引致了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低效性[8]。
如何有效促進農戶的集體行動與相互整體性供給是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關鍵,亦是當前農村社會治理與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研究領域中亟待考究和解決的現實命題,更是基層政府化解農村公共品供給問題的重要手段[2]。然而,從目前調研資料來看,分散化經營土地的農戶對水利基礎設施的需求并未得到有效滿足,在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這種供給逐漸呈現出短缺加劇的趨勢。此外,僅僅通過村莊的自主性組織和社會網絡來促進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及維護可能會導致公共品供給過程中的偏向性問題,如村莊“能人”對于水利設施的投入相當程度上是具有個體偏好性的,而且分散化的水資源利用方式也無法實現對農戶的有效供給。以上的討論會產生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如何避免農村公共品供應中的不足,如水利設施的建設、運營以及維護需要什么樣的自主性網絡治理。二是如何避免分散化的公共品供應的不均以及低效問題。毫無疑問,農村社會資本的累積是實現村莊內部自主性網絡治理效用提升的重要手段,其依托的因素如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社會參與等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農戶整體性供給的外在關系紐帶。因此,核心農戶如何借助于社會資本進而發起供給行為的整體性供給,以及整合社會資本實現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長效性是農戶以自主性整合與整體性供給來達成公共品整體性供給的關鍵環節。本文擬基于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探討農村水利設施整體性供給過程中農戶行為的利益博弈,同時借助于實證研究來闡釋社會資本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影響,為我國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實施整體性供給路徑創新提供建議。
二、農村水利設施供給中的利益博弈和行為選擇
為了有效分析和厘清農村水利設施供給過程中各個行為主體間的利益博弈,為此提出了以下三方面假設:一是農戶雙方都是完全理性人;二是雙方都有兩種策略:參與公共品供給和不參與公共品供給;三是所有的變量取值均大于零。
在這里討論的農戶在經濟實力、資源、參與的積極性等方面是對稱的。α表示農戶A和農戶 B 不參與公共品供給時正常的收益,r是參與供給時的總收益,c是參與公共品供給的成本,雙方都參與時,農戶A和農戶B平分產生的額外凈收益,雙方收益均為r-c2(c
當p 為此,供給過程的利益博弈未能有效達成納什均衡,也就無法滿足農村水利設施有效性供給的薩繆爾森條件(所有消費者公共物品對私人物品的邊際替代率之和等于公共物品對私人物品的邊際轉換率),即:MRS1+MRS2+MRS3...MRSn=MRS(x,G),最終后果就會使得納什均衡的供給量遠遠小于本應帕累托最優的供給量,就是所謂農村水利設施的供給續航力不足。但是現實農村水利設施是在不確定和復雜性的場域下完成供給,同時這種博弈過程是多次往復的博弈,因此農村水利設施的供給成效就在博弈過程中慢慢被消耗一部分成效。這就從客觀上要求農村水利設施供給要施行整體性供給,以此突破固有供給模式的非均衡性。 三、模型建構與實證分析 現有水資源的短缺以及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日益老化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出現滯后,而農村水利基礎設施對農村灌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經濟形勢的轉變,設施建設的成本日益增高,一旦基層政府(縣鄉政府)并沒有加大財政投入資金,都將造成供給的非有效性。作為行動主體的個體農戶,依托于社會資本實現農村公共品的整體性供給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個體農戶以人際關系為紐帶,進而自發性地整合村莊力量供給農村水利基礎設施,這個過程中也促進了參與整體性供給的意愿,進而有效避免了傳統供給中的“搭便車”行為,有效緩解了村莊用水緊張的內在壓力[10]。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整體性供給過程是建立在多元化行動主體積極有效整合和協調集體行動基礎上的,不可否認的是,集體行動過程中勢必會出現精英農戶的角色,以其村莊內部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等因素動員和參與,并以此來實現其作為集體決策者的過程。因此本文主要將社會資本作為表征農戶的關鍵性變量,假定其對整體性供給過程存在行為選擇的外在影響。基于北京大學CFPS關于“農村水利基礎設施”2012年的農戶調查資料,對此進行 Logit分析,探索社會資本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外部影響,以期對農村公共品整體性供給提供借鑒性依據。 (一)模型建構以及樣本數據 本文嘗試采用研究二分類變量常用的方法——Logit回歸模型來考察社會資本及其不同維度對農戶參與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影響。具體的函數模型如下所示: 在(1)式中,α表示常數項;Xi是第 i 個農戶個體對整體性供給的參與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是除了社會資本以外的變量集合體;Zi則表示為社會資本,γi表示社會資本的影響強度;在總體關系模型中βi是關系模型中的偏回歸系數。所選擇的變量和變量分析主要是在表2中集中體現。 (二)實證結果分析 運用Stata 12.0 軟件對樣本進行Logit回歸分析農戶整體性供給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采用最大似然迭代法列出了最終納入全部變量的模型估計結果(見表3 )。在表3中,M1中主要是對社會資本指標的總體分析,而M2中則是將社會資本分解為4個維度內容(社會網絡、社會信任、社會聲望、社會參與)進行測定。為此,在對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影響分析過程中,主要是從個體、受灌溉面積、社會資本、用水環境等特征等進行多維度內容的分析。 1.農村居民個體特征對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影響。在M1、M2模型中,個體年齡A1和勞動人口A4都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性,與一開始預設表3中的結果是相互一致的。這說明了年齡和勞動人口規模與整體性供給是相互正向的關系。對農村水利設施的整體性供給的意愿一定程度是與個體對此設施的使用時間的長短相關,即說明農村居民對設施的依賴度大小。 同時基于農村居民的人口規模基數大所帶來的人口紅利,一旦其表示出對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勢必會形成人口整合力的影響。而對于農村居民的教育程度A2與收入狀況A3在統計學意義上尚未顯現出顯著性,與預期假設存在差異性,與調研區域的現實不相符的。實質反映出這兩個因素對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并未發生直接效應,需要經過間接環節才能促成整體性供給意愿。 2.灌溉面積的大小程度已然嚴重影響到整體性供給中各個農戶的整體性供給性意愿,并且這種影響是正相關的,在表3中M1、M2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75 3、0.067 2,足以證明以上論點。在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農戶需要擴大其農地的灌溉面積以此來增收,這就需要積極投入建設小型水利設施來實現廣灌溉,足見其對水利設施的依賴程度。而另一層面,倘若所獲得的受益又無法逆向回饋于水利設施建設以及灌溉參與過程,就會導致供給后管理出現“空心化”問題。因而作為理性選擇人的農村居民,勢必會以“整體性供給意愿”參與到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供給過程。 3.社會資本特征對整體性供給意愿的影響。在表3的M1中,社會資本對整體性供給的意愿影響相關系數為0.564 8>0.5,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得到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社會資本因子對農村居民有效參與到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影響非常大,且遠遠高于其他特征因子的影響程度。但是必須看到的是社會資本特征下的4個維度因子對參與意愿的影響程度差異性比較大。其中2個因子對此影響較大,囊括了社會網絡與社會參與,這二者在0.01置信水平下得到顯著性檢驗,此外社會參與的影響程度要高于社會網絡。與此同時社會信任與社會聲望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社會網絡是以“社會人際關系”為紐帶的,農村居民在村莊中的人緣好,社會交往能力強,有利于增加與他人信息共享頻數,增強村民參與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意愿,最終形成村莊場域內的整合力[11]。另一方面,社會網絡還能昭示出農村居民在場域內的社會動員和資源整合能力。農村社會網絡的大小,實質上反映了農村居民在村莊場域內所能占有的社會資源的多少。因而依據農村居民在社會網絡的區位與節點位。
對于社會參與因子而言,在1%置信水平下相關系數為0.310 4,社會資本4個因子中社會參與因子的影響程度最高。這也驗證了當前農村社會發展以及公共服務的供給有效性的現實情況。農村居民的社會參與集中表現了村民對村莊集體事務和集體行動的態度和偏好。基于課題調研組的訪談資料,所調研區域中村莊的集體事務與集體行動的客觀集聚點在于農村公共品的供給有效性問題。因此,對于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參與偏好程度客觀反映出了農村居民對待現行農村自治以及農村政治的自覺性,公共服務產品“偏好強”的農村居民,其在農村區域的社會參與度高,那么其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參與積極性必然會高漲。
4.用水環境變量對整體性供給意愿的影響。偷水狀況D1和用水糾紛D2等對水利設施的整體性供給是呈現出正向相關,在5%置信水平下得到了顯著性檢驗。其實這兩個因子的具體影響都能從制度經濟學中尋求到解釋。作為農村公共品的水利基礎設施尚無法界定和明晰出產權,一旦農戶受到機會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驅使下,就會滋生出“搭便車”的心理[11];同時基于水利設施歸屬基本農村公共品的范疇,最終會衍生出“公地悲劇”問題。正如奧斯特羅姆所言:“一個人只要不被排斥在分享他人努力所帶來的利益之外,就沒有動力為共同利益所作貢獻,而只會選擇做搭便車者。倘若每個人都選擇做搭便車者,就不會產生集體利益[12]。”本文核心在于農村基礎水利設施的產權并不明晰,易造成農村水權在村莊分配過程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現象。而這種分配機制的模糊化就會進一步地加劇村莊利益格局劃分的混亂,最終致使“偷水以及用水糾紛”等現象的增加,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整體性供給有效性也隨之大幅度下降[13]。對水利基礎設施的滿意度在表3中尚未得到顯著性檢驗,而其系數呈現出負值,說明了滿意度對整體性供給的影響在統計學上無意義。之所以出現上述的狀況,原因在于現行整體性供給的滿意度越強烈,必然會弱化現行制度安排的改革意愿。按照制度變遷理論,只有對制度安排的轉變或替代過程的預期收益大于成本時,才會實現制度的變遷過程[14]。因而,滿足于現行的制度安排勢必對新制度需求意愿不強烈,這就足以佐證上述統計學意義的現實分析。
四、結論與討論
基于上文的實證分析,有力地證明通過社會資本的研究視角可以探求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供給有效性。同時也驗證了社會資本是影響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關鍵性變量,其中社會資本的不同維度中,社會網絡、社會參與均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存在顯著性正相關,而其余兩變量(社會信任、社會聲望)對整體性供給的行為和過程尚未體現出統計學意義的影響。同時,還發現個體特征與用水環境特征對整體性供給的存在正向影響。
為此,在積極發展農村社會背景下厘清社會資本對整體性供給的互動影響,將農村居民個體與社會資本相互嵌入,并通過這種嵌入的視角來建構整體性供給的政策路徑,以此來解決當下農村水利基礎設施供給非有效性的困境:
1.要營造出有利環境以此來勸導農民整合參與。農村居民參與整體性供給的意愿主要取決于農村水利基礎設施的供給有效性,而供給有效性來源于財政資金的投入,責任主體的明晰以及整體性供給與整合的參與力度等。有利環境的核心要素是要產權制度的明晰化,也就是說確立村莊成員對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主體地位,防止因搭便車而產生的委托代理成本。同時基層政府以“專項資金、低息貸款”等方式提供必要的財政資金支持,為整體性供給營造有利的外在環境。
2.增強農村社會資本的建設和培育。在村莊中通過策劃和組織多樣化聯誼活動,以此來改善本村農民之間以及其與外界的社會交流,進而建構出互動交流型小型社會,拓寬社會關系網。同時可以依托于“一事一議、民主參與以及社會融合”等方式增加農村居民的社會資本存量,從而有效規范村莊內部整體性供給的參與行為。此外可以利用社會資本來規制農村居民的行為,并以良性價值觀和行為觀念來規制農村社會,通過村莊內部凝聚力的整合來保障整體性供給的有效性。
3.有效培育和發展農村精英居民。農村精英居民在農村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甚至在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中起到核心作用[15]。要培育和發展精英農民的關鍵舉措在于,一方面要加大村莊內部教育培訓力度,引入外部專業性人才,從而充實農村精英建設的基礎柱石,提升意愿的貢獻度;另一方面通過設計農村政治參與的流程實現對農村精英的外部嵌入,優化農村水利基礎設施整體性供給的政策設計,提升農村精英的參與自覺性。
參考文獻:
[1]賀雪峰,譚林麗.內生性利益密集型農村地區的治理[J].政治學研究,2015(3):67-79.
[2]張新文,詹國輝. 整體性治理框架下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3):40-50.
[3]曲延春. 差序格局、碎片化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整體性治理[J].中國行政管理,2015(5):70-73.
[4]杜春林,張新文.鄉村公共服務供給:從“碎片化”到“整體性”[J].農業經濟問題,2015(7):9-19.
[5]Bhuyan S. The “People” Factor in Cooperatives: An Analysis of Memb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7, 55(3):275-298.
[6]Uphoff N.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 Learning From th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M].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0:215-249.
[7]中國經營網.中國城鎮化10年90萬個自然村銷聲匿跡[EB/OL].[2015-12-6].http://www.cb.com.cn/economy/2013-0809/1007960.html.
[8]李冰冰,王曙光. 社會資本、鄉村公共品供給與鄉村治理——基于10省17村農戶調查[J].經濟科學,2013(3):61-71.
[9]陳潭,劉建義. 農村公共服務的自主供給困境及其治理路徑[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9-16.
[10]黃瑞芹. 中國貧困地區農村居民社會網絡資本——基于三個貧困縣的農戶調查[J].中國農村觀察,2009(1):14-21.
[11]詹國輝,張新文. 轉型期公共服務的志愿性供給——一個新的解釋框架[J]. 湖北社會科學,2016(3):35-42.
[12]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18.
[13]Gene M Grossman,Elhanan Helpman.利益集團與貿易政策[M].李增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16-20.
[14]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上的結構和變革[M].厲以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228-229.
[15]楊龍,仝志輝,李萌.農村精英對整體性供給社非線性發展的影響機制研究——基于北京郊區四個農民專業整體性供給社的案例分析[J]. 探索,2013(6):159-16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