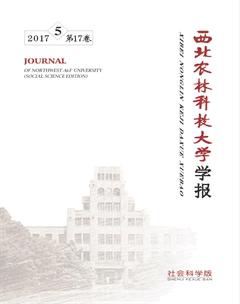產業結構變遷促進了經濟增長嗎?
馮學良+聶強
摘 要:基于中國29個省市1993-2014年的數據建立空間自回歸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分析產業結構變遷、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1)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遷過程均存在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并與空間分布格局和空間集聚類型密切相關。(2)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有顯著正向影響,且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型和空間異質性。(3)資本存量、勞動投入與基礎設施建設依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關鍵詞:產業結構變遷;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空間計量
中圖分類號:F3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7)05-0104-09
引 言
產業結構變遷是理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區別的重要變量,也是后發國家加快經濟發展的關鍵[1]。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背后一直伴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生產要素不斷從農業產業部門向非農業產業部門流動,產業結構變遷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2]。從全國范圍看,1978年的三次產業比重為0.277∶0.477∶0.246,而到2014年,該比重變為0.091∶0.431∶0.478。產業結構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隨時間推移發生了較大變化,1978年以來第一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81年達到最高值40.5%,到2014年則降至4.7%,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1978年的61.8%下降至2014年的41.8%,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978年的28.4%上升至2014年的47.5%[3]。隨著時間的推移,產業結構轉變的同時各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是一個動態變化過程,且呈現一定的空間分布特征。例如,假定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比重簡單反映產業變遷過程,1993年至2014年,長三角地區(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蘇省)該比重從19.77%上升到40.70%。而全國的情況是,1993年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比重為19.70%,與長三角地區的產業層次幾乎相同,但2014年,該比重為37.70%,比長三角2014年低了3個百分點。在這20多年里,產業結構變遷過程所表現出來的空間異質性和關聯性是否具有偶然性?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普遍存在空間關聯效應?一個地區的產業結構變遷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同時是否也會拉動或抑制周邊區域經濟增長?甚至在考慮技術進步的情況下,產業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否會加強?這些都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在既有的相關研究中,多數文獻都支持產業結構變遷會促進經濟增長[4-12]。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具體可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影響維度[13],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相對穩定[14]。進一步考慮技術進步的因素后,技術選擇和合理的資本深化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提高生產效率,加快經濟增長[15-16]。而且無論是技術創新、模仿創新還是技術引進都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變遷的過程[17],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經濟增長[18]。然而,另有學者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并未呈現出促進作用。至少,這種作用效果不是恒定的,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一定的周期性[19-20]。李小平和盧現祥對制造業結構變動的研究發現,制造業的結構變動并沒有導致顯著的“結構紅利”現象[21]。甚至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會逐漸讓位于技術進步[22]。
此外,李獻波等發現無論是城市群尺度還是城市尺度,產業結構動態變化對經濟增長具有相似的空間差異[23]。空間溢出效應是考察產業結構調整與生產率提升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24]。例如,從經濟增長的視角看,中國各省市人均GDP空間分布格局存在著全域范圍內的正的空間自相關性,且這種空間相關性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大[25]。徐春華和劉力[26]、武曉霞[27]、張翠菊和張宗益[28]研究影響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因素時也發現,產業結構變遷過程存在空間異質性和空間關聯性。
基于此,本文將空間計量模型引入經濟增長函數,考察不同區域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空間協同效應與空間關聯性。在當前研究中,有大量文獻探討過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同時考慮區域關聯和空間溢出效應的文獻并不多見。本文在考慮技術進步的情況下,考察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正如上文所述,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變遷進而加速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二者屬于遞進還是并列的作用機制并不十分明確。因此,本文將使用中國29省市1993-2014年的數據建立空間面板模型,同時把產業變遷與技術進步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繼續探討技術進步和產業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理論假設、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一)理論假設
按照費歇爾和克拉克對三次產業的劃分,國民經濟的增長取決于3個產業部門的增長,三次產業的結構變動會改變經濟增長的速度。這里,我們借鑒黃茂興和李軍軍[16]的分析方法,假設經濟中有N個產業部門,國民經濟的增長可以表示為:
兩邊對時間t求導,則有:
其中,git和g′it 分別表示經濟增長速度及其增長速度的變化,下標i表示各產業部門,φi 和φ′i表示各產業部門所占比重及其變化。一國經濟增長要同時受各產業部門經濟增長及結構變動的影響,因此,產業變遷會通過轉移資金、人才流動等方式重新分配產業部門間的基礎要素投入,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分析產業變遷我們借鑒干春暉的做法[14],使用重新定義的泰爾指數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公式如下:
其中,Y和L分別表示產值與就業,i表示各產業,n表示部門數。當TL=0時,經濟體系處于均衡狀態,TL值越大,經濟發展越容易偏離均衡狀態,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幅度越大。
基于此,我們得出本文的假設H1:產業結構變遷直接促進了經濟增長。
分析各產業部門經濟增長,我們引入包含技術進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如下:endprint
其中,K和L表示資本和勞動,A代表全要素生產率,i和t分別表示不同地區和時期。進一步,兩邊取對數可得:
進一步將全要素生產率Ait 分解為產業結構合理化Acit 、技術進步Atit和其他因素Xoit,即: lnAit=Acit+Atit+Xoit (6)
將(6)代入(5)式可得到C-D生產函數的計量模型:
此時,我們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H2:經濟增長過程,技術進步獨立于產業變遷。
(二)空間計量模型構建
在使用面板數據分析各省市產業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一個不能忽視的客觀現實就是省市之間的空間聯系,幾乎全部的空間數據都存在空間依賴性和空間自相關的特點[29]。而空間計量方法在計量分析的基礎上,加入地理位置和空間關聯因素,可以更好地識別和度量經濟現象之間的空間變化規律和決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傳統計量估計結果可能忽略的偏誤。目前,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有空間自回歸模型(SAR)和空間誤差模型(SEM)。
模型(8)為空間自回歸模型,模型(9)為空間誤差模型。其中,yit 為被解釋變量,指的是地區i在t時期的人均GDP,用來測度區域經濟增長;λ為空間自回歸系數,衡量了相鄰區域的經濟活動對本區域經濟活動的影響程度;Σnj=1wit yij為空間滯后因變量,指的是在第t年除地區i外其他區域人均GDP的加權平均值;β 為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ui為區域i的個體效應;εit 為隨機擾動項。ρ為空間誤差系數,衡量了相鄰區域由于經濟觀察值的誤差沖擊對本區域經濟觀察值的影響程度;Σnj=1Wijujt為空間滯后誤差變量,度量的是在第t年除區域i外,其他相鄰區域觀測值的誤差沖擊的加權平均值。
本文選用兩種不同的空間權重矩陣:一是使用地理相鄰(0-1)標準來定義的空間相鄰權重矩陣,若兩個空間區域相鄰,則認為存在空間相關關系,記為1;若兩個空間區域不相鄰,則認為不存在空間相關關系,記為0。二是空間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即通過地理距離構造權重矩陣,具體來說,以各省會城市的直線距離(d)的平方的倒數來設定。
空間相鄰標準假定空間單元之間的聯系僅取決于二者是否相鄰,這種空間鄰接標準設定的空間權重矩陣雖然簡單易行,準確率極高,但卻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只要兩個空間單元相鄰接,即存在相同的影響程度;另一方面,只要兩個空間單元不相鄰接,便不存在任何經濟聯系,這明顯不符合事實。因此,作為對比,本文同時使用空間地理距離權重矩陣。
經濟增長的過程不僅受當前值的影響,而且前期的經濟活動也會影響當期經濟增長的過程,也就是說,用一個動態的經濟模型來反映經濟增長可能更為現實。因此,本文建立包含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的更為一般的空間計量模型為:
其中,yi,t-1為被解釋變量yit的一階滯后,若τ≠0,該模型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若τ=0,該模型為靜態空間面板模型;ρΣnj=1w′i yt和δΣnj=1d′i xt分別為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w′i和d′i分別為相應空間權重矩陣的第i行;γt 為時間效應;而m′i為擾動項空間權重的第i行。
(三)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1.變量選取。本研究涉及的變量包括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具體見表1。
2.變量統計性描述。由表2數據可知,本文所用數據為平衡面板數據。從變量的各項指標看,中位數與均值在數值上十分接近,數據有較好的分布特征。各變量的標準差除產業結構變遷與技術進步的交互項偏大外,其他變量的標準差較小,數據未出現太大幅度的波動。對比最小值與最大值,發現二者極差在合理范圍內。
二、實證分析
(一)空間自相關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Morans I (莫蘭指數)[31]測算以人均GDP表示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變遷過程是否存在空間關聯性。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S2=1nΣni=1(xi-)2為樣本方差,ωij為空間權重矩陣(i,j)元素(用來度量區域i與j之間的距離),而Σni=1Σnj=1ωij 為所有空間權重之和。
Mordans I 的取值一般介于-1到1之間,大于0表示正自相關,即高值與高值相鄰、低值與低值相鄰;小于0表示負自相關,即高值與低值相鄰。一般來說,正自相關與負自相關更為常見。如果Mordans I接近于0,則表明空間分布是隨機的,不存在空間自相關。使用Mordans I 對人均GDP與產業結構變遷進行全局空間相關性檢驗,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從近10年的狀況看,中國各省市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空間相關性,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也存在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從Mordans I 看,2010年以前產業結構變遷的Mordans I 值大于0,即空間關系為正自相關,即高值與高值相鄰、低值與低值相鄰;而2010年后,Mordans I值小于0,空間關系變為負自相關。這也充分說明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不但存在空間依賴型與關聯性,甚至表現為負的空間溢出效應。一個地區的產業變遷過程可能并不利于鄰近地區的產業變遷,存在空間“掠奪”現象。
為進一步分析不同地區經濟增長是否存在空間異質性,我們做出29省市(不包含重慶和西藏)2014年人均GDP的局域Mordans I散點圖,見圖1。
Mordans I的4個象限分別對應于空間單元與鄰近單元之間的4種局部空間聯系形式,其中第一象限代表高高,包含的省市有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和山東;第二象限代表低高,包含的省市有河北、山西、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第三象限代表低低,包含的省市有湖北、湖南、廣西、海南、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第四象限代表高低,包括內蒙古和廣東。由圖1可以看出,處于“高高”和“高低”的大都是東部沿海省市,而處于“低低”和“低高”的則為中西部省市。大部分省市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前者為東部發達省份,后者為西部經濟落后省份,這充分說明,經濟增長在地理空間分布上存在明顯的空間依賴型與異質性,見表4。endprint
(二)實證結果分析
在進行空間計量模型估計時,如果仍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OLS),則會導致估計結果有偏差或不一致,而極大似然估計(MLE)可有效解決這一問題[29]。本文使用人均GDP作為被解釋變量(lnAG),泰爾指數(TL)和技術市場成交額(lnTE)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資本存量(lnZB)、人力資本(ED)、對外貿易(WM)、政府支出(ZC)、基礎設施(GL)作為控制變量,同時引入產業變遷與技術進步的交互項(TLTE),分別使用空間自回歸模型和空間誤差模型進行回歸,結果如表5。
在表5中的ρ、調整的R2、LogL以及F值等統計量來看,無論使用空間相鄰權重矩陣還是空間地理距離權重矩陣,空間自回歸的結果均具有較好的擬合度,表明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空間自回歸模型能較為準確地反映產業變遷、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其中,模型1與模型3為靜態空間面板模型,模型2與模型4為動態空間面板模型。整體來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但影響系數會因地理空間關系(空間相鄰權重還是空間地理距離權重)和經濟增長的滯后作用(是否考慮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而存在細小差異。具體來說,若忽略空間地理因素或只假定各省市的空間關聯度僅在于是否相鄰,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的促進效果會偏小。如模型1中產業結構每改變1個單位,會引起0.014個單位人均GDP的變動,小于模型3中產業結構改變1個單位,人均GDP增加0.026個單位,且二者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這說明,隨著貿易開放程度、交通設施建設等不斷加快,各省市之間的經濟活動及生產要素之間的流動越來越密切,不再局限于空間地理位置是否相鄰,而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產生了更為廣泛的聯系。
相較于模型1與模型3,模型2與模型4為考慮被解釋變量一階滯后項的動態空間滯后模型。由估計結果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可以看出,經濟增長盡管存在明顯的空間效應,但各省市當前的經濟增長也會受前期的影響,即存在一定的經濟慣性。對比估計結果的具體系數不難發現,不考慮經濟增長的時間滯后因素時,各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如模型3中產業結構變遷的估計系數為0.26)明顯大于考慮經濟增長滯后因素時的估計效果(如模型4中產業結構變遷的估計系數為0.006),這恰好說明了,忽略經濟增長的時間滯后性時,滯后項對當期值的影響會分配到各解釋變量,從而使解釋變量的估計結果偏大。而經濟增長的一階滯后項能將影響經濟增長的潛在因素(如政策環境、要素稟賦)從空間結構因素中分離出來,從而使靜態空間模型可能存在的偏差得到糾正,這也是克服模型可能會存在的內生性較好的方法之一。
模型5與模型6分別為考慮空間相鄰權重矩陣和地理距離權重矩陣情形下的估計結果,由δ2、LogL以及F值等統計量可以看出模型有較好的擬合效果,誤差項的空間自回歸系數(記為λ)的估計值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存在一定的空間誤差效應,但該效應并不穩定,這也說明本文采用空間滯后模型能較好地反映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的空間關聯性。此外,根據表5的估計結果,若不考慮經濟增長的滯后性時,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在模型5中的效果最為明顯,即技術進步每增加1%,對人均GDP的貢獻為12.4%,這遠低于美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29.1%[32],這一結果也符合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遞增的規律。而考慮經濟增長的滯后性時,該變量的估計結果為負,說明在生產函數中同時引入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可能會引起同一個模型中解釋變量間的獨立性發生改變,導致內在的傳遞機制出現紊亂。
在控制變量中,人力資本、資本存量和基礎設施建設的估計結果整體上顯著為正,即均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而對外貿易和政府支出的估計結果并不穩定,系數的大小也跟預期有較大偏差,這說明對外貿易與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非單向的因果關系,即對外貿易與政府支出的增加會影響產出,而產出的增加反過來也會影響對外貿易與政府支出。若要深究三者的影響關系,需建立多方程聯立模型,篇幅所限,這里不再深入探究。
由表6中的ρ、F值、調整的R2以及LogL可知,無論是普通面板模型還是空間面板模型,均較好地擬合了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經過Hausman檢驗后發現,采用固定效應進行估計會更合適。模型7為考慮異方差穩健性(Robust)的固定效應估計結果,模型8為工具變量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結果,模型9~12均為空間滯后模型。對比上述模型發現,產業結構變遷的系數大小基本一致,產業結構變遷均能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模型具有較好地穩健性。但普通面板模型估計結果在顯著性方面不及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說明考慮空間因素后的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具體分析模型9~12可以看出,是否考慮技術進步的因素并未對產業結構變遷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產生明顯差別,且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而忽略產業變遷的因素時,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要略大于考慮產業變遷時的作用效果,這說明產業變遷和技術進步之間可能存在內在的關聯,技術進步雖然可以“獨當一面”(此時的估計系數為0.006大于同時考慮產業變遷時的估計系數0.003),但技術進步潛在地加速了產業結構變遷,再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三、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結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不同地區的產品與要素的自由流動提升了地區間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為產業結構變遷提供了物質及人力資本的積累,經濟增長的區域差異十分明顯。地區經濟發展不僅依靠本區域內勞動力、資本以及人力資本的投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一個地區及相鄰區域產業結構變遷和技術進步的影響。
1.本文基于1993-2014年的相關數據,建立空間計量模型,分析產業結構變遷及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在考察期內,各省市經濟增長過程存在全域范圍的正的空間自相關性,而且相關性的大小基本保持不變。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也呈現一定的相關性,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關性逐漸增大,甚至在2010年前后,由正的空間相關性轉變為負相關。地區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遷過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資源掠奪”現象。而從局域空間相關性上看,東部發展較快的省份和西部落后的省份屬于同一種空間集聚現象,但集聚類型完全相反,這種空間分布的異質性是地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基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