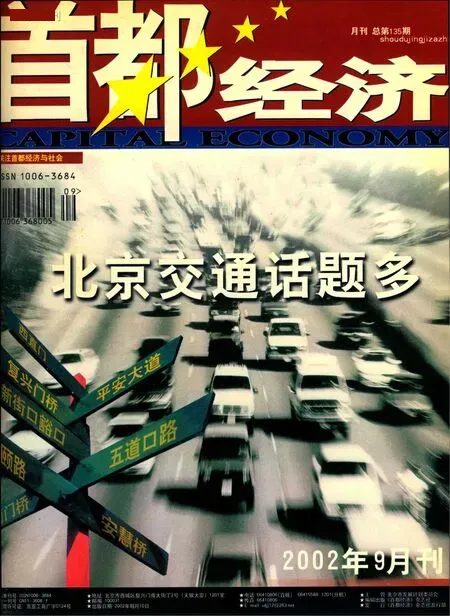京城剪影 之百年笑聲
徐文龍
導語
在北京,每個人都和這座城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一定帶給過你或喜悅或悲傷的過往。北京像個巨大的記錄儀,記錄著這座城市中每個人的剪影。從5月開始,本刊“文化映像”欄目推出“京城剪影”系列文章,將與北京有關的方方面面,記錄并呈現給您。或記憶或共鳴,或發人深省或拋磚引玉。第五期,我們談“百年笑聲”。
相聲,這個留存逾百年的藝術形式,誕于京城,發于津城,為人們帶來了太多歡笑。不過,當代相聲和很多傳統藝術形式一樣,逐漸式微。雖然德云班主郭德綱為京城相聲打了一劑強心針,但其實京城相聲圈也還是不太景氣。這話從何說起呢?恐怕要從一百年前說起了。
談笑百年
談起一個行業,溯本求源大多都有一個“祖師爺”,相聲也不例外。
如果您有機會到相聲后臺去走一圈,大多會在上場門的地方發現四個字——“曼倩遺風”,這里的“曼倩”指的就是相聲門磕頭的祖師爺——東方朔。不過拜東方朔為祖師爺,更大層面上是藝人們對自己這門藝術和身份的包裝,相聲界另外一位實際意義上的祖師爺朱紹文先生,是為相聲這門語言藝術開山立宗的集大成者。
不過,這位朱先生推出“相聲”這門藝術的時候,恐怕也頂多是把它當成一門手藝,而并不是出于多大的“藝術追求”。相聲的原始狀態,就是藝人們撂地(在街市上賣藝)掙錢的手段,上升到藝術層面,恐怕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了。所以這種藝術可謂是求生的藝術,與音樂和繪畫等藝術類別不同,相聲的本質,就是求生的技能。而那時候的相聲演員,每天最耗費心思的事情,就是怎么才能讓觀眾笑出來。如果彼時把人撓癢癢撓笑了也能掙錢,恐怕相聲這門藝術現在的名字就是“撓癢癢”了。這無關藝術的高低,也無關藝術表現形式,藝人們需要讓金主們笑,讓顧客們笑,讓一切能掏錢的人笑著把錢掏出來,所以鉆研怎么能讓人笑出來,是舊時相聲藝人每天的課題,這關乎到他吃完早飯之后是不是能有午飯吃,關乎到他餓不餓肚子。說大了,關乎生存。
新中國成立以后,各地成立藝術團體,這些相聲藝人們被逐個“收編”,按照計劃進行演出,再也不用費盡心機地讓人發笑了。這樣的情況下,藝人們也失去了生活的緊迫和危機感,而在藝術上的精進,除去一部分以“相聲藝術”為追求的人們之外,似乎大部分都沒那么專注了。這樣的問題對于相聲這種舞臺藝術是致命的,這也是為什么當下大多數人在電視里看到相聲時,第一反應可能往往是“相聲啊,沒勁”。
所以相聲式微,源頭是這門藝術原動力的缺失,是它的“根”變了。
孤木不成林
相聲不令人發笑了,自然也就不再擁有金錢上的價值,那么相聲的從業者們自然也就失去了奮斗的根本目標與動力。在這樣的情況下,本就式微的相聲更加慘淡,然而就在此時,一個叫郭德綱的相聲藝人橫空出世,托了搖搖欲墜的相聲藝術一把,算是為它續了一口氣。
在眾人皆知的“德云班主”的振臂高呼之下,京城百姓乃至全國百姓對相聲又有了新的認知,人們發現相聲又變得“可笑”了,能夠再一次讓自己開懷了。于是“相聲中興”、“相聲繁榮”等字眼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及,只可惜這談不上真正的中興和繁榮。
沒人能否認因為德云社,因為郭德綱,京城一度出現了很多相聲學員和從業者,極致時能達到3000人,雖然對北京這座大城市而言,一個行業只有3000名從業者實在太少,但要知道的是相聲在建國之初恐怕全國從業者相加也不到3000。可見3000這個數字,已經相當繁榮了。
除去從業者的數量,班社的繁榮更是郭德綱這桿相聲界的大旗帶動起來的。從德云社到第二班,從嘻哈包袱鋪到大逗相聲,一個又一個的民間相聲班社忽然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但可惜的是這些班社沒有一個能再一次像德云社一樣,真的在京城站住腳。
德云社雖好,可惜孤木不成林,相聲還是不免式微之勢。
德云社的好與其它的不好
為什么德云社能活下來,別人就不行。這是相聲界乃至全體觀眾都想知道的問題,也是每一個打算成立個相聲班社的人想知道的問題。這問題不好回答,不過其實也不難。如果你透過德云班主的嬉笑怒罵,關注到他的相聲本身,其實這些問題都很容易回答。在這里,我們不妨切換成產品經理的邏輯,來看看德云社。
1.產品
德云社的產品大多數是非原創的,如果你看過早期的德云社你會注意到這點。不過相聲界是沒有所謂完全原創的,傳統段子為骨、新方法為枝葉,這是相聲界創作的基本法,誰都要遵守。除去這些非原創的作品,那些原創度比較高的如《我要幸福》、《我要上春晚》、《我要反三俗》等段子,則是德云社的“主推系列產品”了。這些產品是擁有題材和藝術共性的:它們都代表了普羅大眾的生活;它們都不會局限在小題材內(如聚焦某個行業或某個人),而是聚焦生活細節或生活現象。這些作品是具有強烈生活共鳴的,所以能夠被大眾所接受。而其它班社或相聲演員的作品,則過多地聚焦在一些新視點和新現象上,這就導致生活沉淀和共鳴缺失了,這是德云社火的原因,也是大部分班社沒火的原因之一。
2.運營方式
劇場深扎根是德云社的運營方式。即使是郭德綱大紅大紫、各處商演的當下,德云社在各個小劇場演出也一場沒有停過。其他相聲班社則不然,底角兒(最主要演員)出走全盤停演,再復演時觀眾已經不買賬了,這種情況也發生過。
3.推廣
在推廣上德云社深諳其道,在品牌初成時,采用大流量轟炸推廣。媒體錄播,電臺錄音,觀眾錄音錄像并傳播到網上,這樣通過互聯網大肆傳播是其它任意一個班社都沒做過的,同時也是人們不愿意做的。因為如果觀眾能從網上找到節目,就不會再花錢買票了。但他們遠遠低估了京城百姓的人口數量,也低估了人們的消費能力,和人們對娛樂的追求。而品牌中期,德云社則采用了部分流量付費的形式,讓人們更無所不用其極地費盡心機在網上搜索德云社的相聲。直到現在,德云社已經學會大面積的流量付費了,而人們也開始認可這種形式。于是德云社在線上線下獲得了雙重成功,扎根更深。
這就是德云社的策略,簡直不像是一個相聲藝人的手段,但如果你想在京城做好相聲,或者說你想在這個時代做好相聲,這么做是必然途徑。
不會?那你還有一條路,學學我們的鄰居。
在“哏都”,相聲活著
去天津干什么?吃包子,坐摩天輪,聽相聲。
似乎我們的鄰居對相聲有著更深的見解,也似乎是九河下梢的天津衛,父老鄉親們更捧這門藝術的場,不管如何,相聲在天津比在北京火。為什么?因為純粹,也因為堅持。
79歲的尹笑聲穿了大褂準備上臺,沒掀開門簾,叫好聲已經響成一片。他這一生除了說相聲沒再干過別的,而他的觀眾們也正因為此而期待著他,因為他是個相聲演員,逗笑兒。除了尹笑聲,天津有一批這樣的相聲從業者,老中青三代從事相聲,不因為德云社火了,更不因為這門藝術能掙錢,他們就為了這門藝術,只為了逗笑臺底下的觀眾。在他們身上,你能看到相聲的另一種原動力——喜愛。
可反觀北京的班社,立不住就是因為不夠純粹,或者用天津的這群相聲演員說,他們就不是說相聲的。“少馬爺”馬志明提過一句業內很著名的話:“不是干這個的,別往里湊,擠進來你也干不好,因為你不愛這個。”
而在天津,我們鄰居那里,在這些愛相聲的人懷里,相聲還活著,好好兒的。
在北京,喝茶、泡澡、遛鳥兒、聽相聲、聽評書、聽戲,算是老北京的幾個大愛好。而這其中最能逗人一笑的相聲,在當下的京城,似乎也只能默默地苦笑。時光悠揚婉轉,筆者愿意相信這一百年的笑聲不會就此絕響,而京城百姓們也期待著那批愛相聲的人們,再一次能挑逗這座城市“笑的神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