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認知隱喻學為視角分析甲骨文形意關系并由此詮釋文字的內在哲學
李筱竹
(啟德教育集團 北京 100020)
以認知隱喻學為視角分析甲骨文形意關系并由此詮釋文字的內在哲學
李筱竹
(啟德教育集團 北京 100020)
甲骨文是中國較為成熟的成體系文字,其構形特點可體現我國古人的語言思維與民族文化。以認知隱喻學理論分析甲骨文,可看出甲骨文的形意關系即為一個立象過程,是一種隱喻方法。“象意”即似“隱喻”,“象聲”即似“轉喻”。以甲骨文形意關系入手,可看出中國古人的隱喻性思維,由此進一步探究中國古代言意之辨與西方隱喻理論的相似之處,即二者都是在談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問題。本文嘗試發現二者的相似性,并分析隱喻式思維對語言的作用。從認知隱喻學角度分析甲骨文形意關系并由此詮釋言意之辯的內在哲學,從而反映其中所隱含的直覺性思維的作用。
言意之辯;語言;文象關系;隱喻;轉喻
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對探究漢字的形成有著重大意義。大部分的象形文字體現了漢民族非凡的形象思維與開創精神。從古至今,學者對甲骨文造字方法,尤其是形意關系的研究在不斷發展,由此而產生的理論也是多種多樣、層出不窮。漢代許慎的“六書說”可謂此研究領域的源頭,歷朝歷代的學者也多從此說。然而隨著研究的不斷跟進與更新,也隨著國人思想的逐漸開化,逐漸形成了“三書說”、“二書說”等理論。時至今日,隨著西方學科的引進與發展,國內的語言學已日趨成熟,由于《馬氏文通》的發表,人們逐漸開始拿西方的語言學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漢語。然而對于我國最為特殊的漢字理論的研究,若要生硬地照搬英語的語言系統理論,確實偏頗。
筆者雖然同樣質疑用西方理論來分析中國古代漢字的可行性,然而有一種西方理論,卻似乎較為合理。認知學科也是近世紀的新興學科,其中的認知隱喻學理論非常新穎,其結合了語言學、心理學與哲學等理論知識的精華,用以分析人類思維及語言的關系。筆者發現,該理論所探討的問題剛好與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言意之辯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言意之辯是中國古人關于思維及語言的論戰。其中的王弼的“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之論正如認知隱喻學中隱喻理論相似,都提出人類的圖像式思維,以隱喻來表達事物或圖像背后的真意。筆者認為,若用這種理論分析甲骨文的形意關系,則不為一種新義,也可啟發后來學者。其實我國關于認知隱喻學的研究已逐漸興起。以徐通鏘、孟華等人為代表的文字學界已開始研究此理論對漢字的作用。孟華在《文字論》里就將漢字的形意關系分析為一種“文象關系”,并多次提及認知隱喻學理論與此密不可分的關系。胡壯麟在《認知隱喻學》中也認為此種理論對于創新我國漢字理論有著重要作用。筆者只是管中窺豹,將幾位學者的認知結合起來,做一次文字理論的中西合璧。
想要用認知隱喻學理論來分析甲骨文形意關系,首先要討論的不是如何來分析甲骨文字形,而是先要將認知隱喻學的由來以及它與中國古代語言哲學的聯系搞清楚。因為只有貫通了理論,用它來分析甲骨文才不顯得生硬,也能夠使讀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義。所以本文先要從認知隱喻學與中國古代“言意之辯”理論講起。再而用認知隱喻學理論分析甲骨文字形,最后對文字本身進行哲學上的闡釋。
1 認知隱喻學理論概述
從古至今,人類都在不斷研究語言的奧妙。“軸心時代”的孔夫子已開始了對語言的分析,隨后逐漸形成“言意之辯”。西方“軸心時代”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也早已開始運用數理邏輯、修辭學來分析、解釋人類的語言。時針指向現代,國外對語言的發生、變化和發展的研究不再停留于本體語言學、修辭學的范疇內,而是逐漸融合心理學、認知科學等新興學科以求有所突破。“隱喻”一詞逐漸被人們所重視,它成為解釋人類語言產生的另一條途徑。按胡壯麟先生在《認知隱喻學》的扉頁上所言:“國外對隱喻的研究,已從傳統的修辭學,進入當代的認知科學。本書主要從認知的視角,探討了隱喻、語言和認知的關系。”胡壯麟先生所言的“隱喻”、“語言”和“認知”這三者,就是認知隱喻學的三大要素。
那么何為“語言”?世界上關于語言的定義非常多,人們從各自不同的領域和觀點給“語言”下定義,那么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看,“語言是用來構建和交流意義的,是了解人類思維的窗口。”。何為“隱喻”?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詩學》(Poetics)中提出“隱喻”概念。“隱喻是用一個陌生的名詞替換,或者以屬代種,或者以種代屬,或者以種代種,或者通過類推,即比較。”這是隱喻替代理論的原型,共同的觀點,即隱喻是一個詞語代替另一個詞語的一種修辭手段。當時許多學者認為這種隱喻替代理論可以解釋所有語言現象,然而實踐證明這種隱喻替代理論并不能解決所有的語言現象。由此認知學家提出了從認知的角度來解釋隱喻。認知隱喻學的專家萊可夫(Lakoff)就質疑上文所講的“替代”理論,他認為這種修辭學上的解釋把隱喻的作用限制住了。他提出:“語言的隱喻是人們在思想上建立了聯系,不是基于詞語的類型層級。”在此之后的隱喻理論不斷修改、擴充與完善。如今,現代西方語言學已開始用認知科學來系統地研究語言與思維的關系。Richard把隱喻從傳統修辭學中解放出來,認為人們“對隱喻的掌握就是對生活的掌握,隱喻構筑了我們的世界。所有語言在深層包孕著隱喻結構……清晰地影響了不顯露的‘意義’。”萊可夫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更是對語言與世界、語言與思維的問題進行了探討,深化了“隱喻”概念。隱喻作為深層的認知機制,植根于人類的概念結構,而人類就是通過這種部分的和理想的認知模式來形成世界的概念。隱喻不再只屬于修辭學范疇,而是被歸于一種本體論。
認知隱喻學中,萊可夫與Johnson認為人類的本義語言是隱喻的。“隱喻部分地構筑我們日常的概念,這個結構反映于我們的本義語言。”“自然語言的隱喻特性使得單純按本義語言來解釋的意義是不可能的。”語言,作為人們感知世界的一個最重要的手段,與人類的認知過程是相互成就,相依相成的。隱喻的作用就是使語言與認知相存相長,“在人們用語言思考所感知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時,能從原先互不相關的不同事物、概念和語言表達中發現相似點,建立想象極其豐富的聯想。是認識上質的飛躍。”隱喻的實質就是語言與認知的比較與互動,分屬于不同義域的詞語在語義上互相作用,產生新的語義。這種隱喻思維先于語言,并作用于語言,使人們用一種隱喻式的語言來表達思想與意義。
2 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言意之辨
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言意之辨也一直是一個在語言學界、哲學界都頗具爭議的話題。談論“言”與“意”,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言”、什么是“意”,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言”的甲骨文字形是,上有一橫,下面是“舌頭”,表示言從舌出,是張口伸舌講話的象形字,所以“言”的本義是“言語”。“意”是會意字,從心從音。《說文解字》說:“意,志也。”本義是“心中所想”,引申為“含義”、“思維”。我們談論“言意之辨”也就是研究語言和思維之間的關系。
在中國古典哲學范疇中,“言”與“意”的論辯主要有兩方觀點,一方就是以墨子為代表的“言盡意”說。《墨子?經上》篇第九十四:“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意思是說通過言語表達,意思就自然而然地顯現于眾,這是心的慧明。如《墨子?經上》篇論“圓”,說“圓,一中同長也。”在這里,“圓”就是“言”,“一中同長也”則是“意”。因為“言盡意”,所以言“圓”就能表達出“一中同長”這個意思,也就是說,用言語、判斷來表達思想觀念并解釋事物含義及規律。然而對于墨子的觀點,不可全盤接受。首先,由于墨子所言說的大多是科學的客觀事物,他所觀察的世界、所列舉的例子都是一些自然世界中的物理對象。對于這些純客觀的物理事物,當然能夠理解并同意“言盡意”的觀點。其次,墨子所說的“言”之所以能盡意,是有條件的。他在《經上》篇中多次對“言”加以詮釋,如《經上》篇第三十二章講:“言,出舉也。說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言也謂言,猶名致也”、第九十三章:“言,口之利也”。由此看來,墨子所謂之“言”,乃是“名致”(夫名,實謂也)。只有符合既定事實的“言”才可被稱為“言”,不可妄言。如《修身》篇中所講:“饞慝之言無入之耳”、“出于口者無以竭馴”、“言不信者行不果”等。正所謂言合于意者謂之信,但是世上并不僅存在客觀事物,不僅僅只有自然科學的事物需要盡意。在感性層面的事物,諸如情感、觀念、精神等的言說是否可以盡意?如何能夠盡意?對于這些,墨子的“言盡意”說似乎無法解釋。
另一方以莊子為代表,主張“言不盡意”。莊子《天道》篇第七:“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夫行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乃出于老子《道德經》第五十六章)”、外物篇:“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莊子認為,“道”無形,人們要理解它,于是用“言”載之于書。然而人們只重視了行色、名聲的視聽感官,講求言詞,卻輕視了意義的表達,意義是有所“指向”的,這“指向”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除了墨、莊兩派,在《易傳》中也有言意之說。在《易?系辭上》第十二中,書者假借孔子與其弟子的言語來解釋“言”、“意”:“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在《易傳》中,書者在討論如何盡意時,不再局限于“言”。于是引入了一個新的概念,即“象”。“見乃謂之象”(《易?系辭上》十一)也就是說,顯現于天可以感知的稱為“象”,如日月雷電、春夏秋冬等,在《易傳》里也就是爻象:少陽、老陽、少陰、老陰。《易?系辭上》八:“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是根據《易》理所擬天下繁雜萬物的形象及其內蘊,通過設立爻象,就可盡意,表達思想。具體方法就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根據無“象”的道與有“象”的器的轉化之理而總結規律、指導實踐,萬事萬物就可通達,天下人應用其理則能成就事業。這就是“立象盡意”之道。
歷史發展到魏晉,王弼則在其《周易略例》中提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周易略例?明象》中說:“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認為要想得到物象就應拋棄言語,要想得到義理就應拋棄物象。在他看來“言”是用以表達“象”的,是用以明象的工具,然而“存言者,非得象者”,“言”并不等同于“象”,所以不拘泥于言語才能完整地表達“象”——忘言生象;“象”包涵“意”,是得到意的工具,然而“存象者,非得意者”,象不等同于義理,所以不拘泥于物象才不會妨礙義理的完整把握——忘象求意。“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只有拋棄物象的限制,才能徹底地認識事物的規律。其中,王弼還引用《莊子?外物篇》中:“得魚忘筌”、“得兔忘蹄”的典故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可見,中國古代哲人對言意關系的解釋,多是語言工具論。即“言”、“象”皆為人們達意的工具,若想達到“真意”,工具則自動被“忘”,即“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人們探求得“象”所喻的“意”,“象”本身就對人而言沒有意義了。然而究竟如何“忘象”?怎樣做才能“得意忘象”?古人并未給以系統地解釋,而是把它視為一種先驗的能力。王弼“得意忘象”的觀點即是一種先驗的本體論,他認為道是“無”,是超驗的,“忘象求意、忘象得道”要靠一種非凡的、天生的智慧,即圣人、“神明”。“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老子注二章)圣人有天生的智慧能夠體“道”,也就是“圣人體無”、“智慧自備”。前者樹立了不可知論的依據,而在老子注第二十三章中,他先解釋“希言自然”:“聽之不聞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然則無味不足聽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用以說明言道之意,自然無味,是抽象的。進而他便以“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于道。”來解釋“從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用以說明只有與“無”同體,與“道”地位同等的圣人,方能“得意忘象”,體悟言語中的形而上的道。這種論調會把言意關系推至虛無的神秘主義,并不能真正說明如何“得意忘象”。
莊子的“心齋”理論則可以視為一種解釋方法。墨家曾提出“心”的概念:“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墨子《修身》篇:“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心”是思維,有通達的思維邏輯,就可通過言語表達而理解意義。而莊子卻不這樣理解“心”,或是進一步發展了“心”的概念。他將“心”解釋為心志、心境。《莊子?人間世》:“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于聽,心止于符。”其中的“符”可理解為“象”。這是莊子假托孔子與顏回的談話,提出“心齋”的觀點。心志專一,就不用耳去聽而用心去聽,境界再高一點,則不用心去體會而應用氣去感應。耳的作用止于聆聽外物,心的作用止于感應現象。也就是說“心”不是墨家所理解的邏輯推理,而是一種對現象的主觀感應。這種心志變化莫測,沒有定式,自然無法完全體悟他人所言的那個“意”,定會加有自己的認識與想法。所以,最高境界則是“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意思是說,我們要用氣感應。氣是空明而能容納外物的,我們不要總是追求外物具體是什么,而是應通過氣來容納外物。只要用氣來達空明的心境,萬物之道自然與你相合,這也就是心齋的意思。莊子認為,人應該做到心齋、坐忘,以頓悟、悟道相處于世,這樣萬物皆可以被感化,使耳目感官通達而排除心機,才可得意,也就是得道。心齋的作用可視為人們對所言之“象”的一種揚棄。通過“心齋”,聽者可感“象”背后表達的形而上之道義,這是對于“象”的修辭義的一種揚棄。所言之事無法盡意,皆是由于沒有“忘象”,即沒有做到心齋。《莊子?人間世》中假設孔子與顏回對話,孔子批評顏回:“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文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育其美也,命之曰菑人。”意思是說,你雖德行良好,卻依然會不被人了解;不與人爭奪名譽,他人也無法明白你。如果你強行用仁義道德的言語在暴虐之人面前炫耀,他就會認為你是揚其丑而顯示自己的美德,會把你當作惡人看。莊子認為,當人們在為自己辯言時,總會美其言辭,越是這樣,別人就越是不明白,甚至會誤解。所以要對心進行齋戒,通過否定“象”的本義,并提取“象”的引申義(喻意),人們可真正做到“得意忘象”,真正做到“言盡意”。
盡管人們提出“得意忘象”、“心齋”、“神明”等概念來思考“言”盡“形而上之道之意”的方法,但是由于語言指向的任意性以及個人經驗的不同,這些通過聽者“悟象”并“忘象”的方法很難使每個人都達成共識。講述者羅列相關意象,而聽者的思維方式不盡相同,所以很難達到“形而上的意”,即“言不盡意”。
3 西方隱喻理論與言意之辯的關系
筆者認為,無論西方的隱喻理論還是中國的言意之辯,其實質都是在研究人類語言的發生與發展。綜其所述,我認為中國古代哲人對語言的論辯仍停留在一種感性認識上,是在用一種感性思維來講述一種經驗、一種現象。而西方的隱喻理論以致現代的認知隱喻學都是建立在一種理性思維之上的數理分析。雖然分析的方法與角度不同,可兩者所言說的事情卻是相同的。中國的文論與古代漢語一直分得很清,似乎二者之間并無很深關系,然而筆者認為古人的言意之辯確是在認真地探討一個語言問題。言不盡意的思維方式其實就暗合了西方提出的隱喻式思維模式。徐通鏘也曾提出:“隱喻式思維方式的基地不在西方、不在印歐語社團,而在我們中國。”他認為漢語社團的思維方式是隱喻式的,從“《說文解字》、《爾雅》等一系列典籍的‘注’、‘疏’都集中于字義的注釋”這一點就可證明。”可見,言意關系(語言和思維的關系)的確可追溯到先人造字方法的運用上。尤其是中國古人所造的表意字,它的造字法與后人對字義的解釋,都源于一種隱喻式的思維。
所以,用認知隱喻學來分析中國漢字的形意關系是可行的。國內在研究甲骨文構造法上一直秉承漢代《說文解字》的六書傳統,雖然后有創新,提出過“三書說”、“兩書說”等,卻依然可被視作六書傳統的簡化版或歸類版。筆者認為,若要從認知隱喻學的角度,來深刻分析古人造字的思維模式,或許能夠得到一些新的思路,為后面的研究開辟一條不同的途徑,下文就對甲骨文的構形法進行分析與研究。
4 甲骨文形意關系探究
4.1 甲骨文反映的文象關系
要分析甲骨文的構形,首先要討論甲骨文中所反映的文象關系。孟華在《文字論》中解釋文象關系為:“文象關系指語言文字與其他象符號(狹義的文字以外的‘可視性’符號)的關系。”“文”即漢字,(甲骨文)、(小篆),《說文解字》釋“文”為“文,錯畫也。”孟華提出“文”具有象符號性質,是一種可視性的圖畫符號。“古人將包括漢字在內的各種視象性的符號表達統稱為‘文’。”“象”是一個動態的立象過程,。它不是靜止的,而是“呈現”為一種符號化過程,其結果則創造出一個意象。《說文解字·敘》:“文者,物象之也。”文與象之間有某種通約性,“漢字與中國繪畫、中國文學、傳統儀式、中國建筑、周易符號系統之間在符號視覺性編碼方式上具有同構性。”本文所討論的文象關系,其中的“文”不再只局限于它的狹義的文字性質,而是討論它的象符號性質。
文字的產生確實晚于聲音,代表語音關系的“詞”出現的時間早于“字”。人們在交際時受到有聲言語在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由于社會的發展,有聲言語不再能滿足人們交際中已增長了的和復雜化了的需要,這時文字才應運而生。”長期以來,人們受邏各斯與表音中心主義的影響,多關注句式語法對表意的作用,而輕視文字的作用。認為文字只是語言的附屬品。可是文字卻是人們進行感知-形象思維的重要手段。B.A.伊斯特林將“文字”定義為:“它是有聲言語的補充性交際手段,這種手段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主要用來把言語傳到遠處,長久保持,并且借助圖形符號或形象來表現;通常這些符號或形象表達某種言語要素——一個個最簡單的信息、單詞、詞素、音節或音素。”漢字也是借助圖形符號或形象來表現言語要素的信息。漢字即一種“呈現”,一種可視性文字。
探究文字對語言及思維的意義,從漢字的發展角度看,甲骨文已是較為成熟的成體系的文字。(考古已經發現早于甲骨文的一些刻畫符號,如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有一些象形符號,如圖1。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一些刻在陶器上的符號,如圖2。這些可看做為早期文字,但尚未成熟。除此之外,早期挖掘出的“杜嶺方鼎”上有八組饕餮紋和乳釘紋,分布在鼎的四壁中上部,可視為刻畫符號,如圖3。納西族的木雕畫是進行祭祀活動的一種原始的繪畫形式,其中所畫圖形也表現出一定意思,如圖4。又如赫哲族流行薩滿教而繪制的“治病用的神像圖”、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銅片。這些屬于前文字時期,被稱為文字畫,以圖畫表意,是作用近似文字的圖畫,而不是圖畫形式的文字。)

圖1 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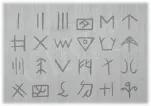
圖2 訶角偃師二里頭陶器上符號

圖3 鼎四壁上的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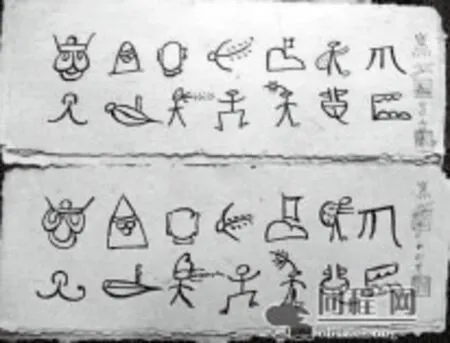
圖4 納西族木雕畫上的圖形
甲骨文多象形,每個字都可看作獨立的“象”,《易?系辭上》說:“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說文解字·敘》在講到文字的產生時也指出:“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甲骨文的創造,實際上就是一個“立象”的過程。象意(隱喻)是動機性方式,象聲(轉喻)是任意性方式。這兩項是人類具有的最基本的符號化表達方式。漢字“立象”分為兩步,從造字者角度看,立象是一個造字過程,用一定的圖象對實物或事件進行抽象性的描述。它并不完全寫實,而是將所表達的事物進行寫意性的再創造。如“牛”這個字,甲骨文為,造字者只突出牛的牛角這一特征,而并非將一頭牛完整的臨摹下來。這種簡約、概括的表意方式,使得人們在指涉對象的同時意識到了圖象自身。孟華將這種造字方法稱為“六書精神”,即“造字精神”,它是“視覺符號的產生法則,使可視性成為可能的活動機制。”從接受者角度看,立象還是一個解字過程,所造之字要被他人接受,就要將所造字表達的意思解碼。孟華對“解字過程”有一段闡釋:“‘文’是一個意象,它不是對物象的精確臨摹,而是一種‘A猶如B’的相似性、象征性。”人們通過立象,來表達所書寫文字的含義,這就是文象關系。文字是書面語言的基礎,也是人們形象思維的重要表達方式。這種“感知-形象思維”作用于語言,而中國古代對于言、象、意關系的論辯也可被看作這種文象關系的變形或引申。
4.2 甲骨文形意關系
從甲骨文的構造法來看,漢代許慎的“六書”說分類含糊,近代的唐蘭先生提出“象形、象意、形聲”三書說,陳夢家先生也提出“象形、假借、形聲”三書說,裘錫圭先生提出“表意字、假借字、形聲字”三書說。而沈兼士則意識到漢字的二元機制:“中國古代文字的創造和組織,相傳有六種原則(就是指事、象形、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書)。前三者可以叫做意符的原則,后者可以叫做音符的原則。”孟華又在此基礎上明確“兩書”為“象意”與“象聲”。“象意方式即用含有具象或抽象意義的漢字形體來表現漢語單位的意義。”即許慎“六書”中的象形、指事、會意;象聲則相當于“六書”中的假借。雖然孟華認為形聲字只是象聲和象意相互作用的產物,不應算一書,但我認為形聲字的聲旁主要是用于表現假借字的新義,可以將形聲字視作假借字的一種變體。
這種字體結構的分類,用認知隱喻學的方法加以分析,就更加清楚了。隱喻(metaphor)指建立在兩個意義所反映的現實現象的某種相似的基礎上,即“A猶如B”。轉喻(metonymy)指兩類現象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這種聯系在人們的心目中因經常出現而固定化,因而可以用指稱甲類現象的字去指稱乙類現象。在西方拼音文字中,隱喻和轉喻只是語法上的一種表達形式。而中國古漢字,由于其獨特的表意象形體系,先民在創造文字時,也因為隱喻性的思維方式,而在造字時運用了隱喻和轉喻的方法。“象意”即一種隱喻方式,每個字所設立的“象”都是一種動態的呈現,都必須用一句話或一段話來解釋。如象形字“莫”,甲骨字形為,“象鳥歸林以會日暮之意。”會意字“祭”,甲骨字形為,“甲骨文祭不從示,示為后加之意符。甲骨文祭字以手持,即肉。或以數量不等之點象血點之形,會祭祀之意。祭為殷代五種祭祀系統中一種祀典之專名。”指事字“上”、“下”,甲骨文字形為、。上與下為相對,用符置于一條較長的橫畫或上或下,用“在上方”、“在下方”來表示猶如“上”、“下”的概念。這種象意字所表現出的隱喻,就是甲骨文形意關系的表現。而“象聲”即一種轉喻方式,形符和聲符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系。如形聲字“福”,甲骨文字形為(第一期)、(第三期)。《說文解字》中,“福”為形聲字:“祐也。從示畐聲。方六切”形旁以木表或石柱為神主之形,聲旁,“象以灌酒于神前之形。古人以酒象征生活之豐富完備,故灌酒于神為報神之福或求福之祭。”以酒奉于神前,形符與聲符相互補充含義。
5 文字的內在哲學
從更深一層的哲學內涵來看甲骨文的造字,可見,不管隱喻還是轉喻手段,都需要一個立象過程。甲骨文是古人書寫出的,用于交流、表意的抽象符號,言所思即文,“立言”即“立文”,“立文”即“立象”。“立象以盡義”、“得意忘象,得意忘言”,究其起源,從古文字的角度去考察,可視為對文字的一種揚棄,對“象”的一種揚棄。
德里達曾指出,人們用隱喻來稱呼自然的普遍的文字、可理解的永恒的文字。可以感知的、有限的文字是本來意義上的文字。文字的“字面”意義即為隱喻性本身。隱喻意義上的文字,是自然的、神圣的或文字,它與價值的起源,與作為神圣法則的良知的聲音,與心靈、情感等等具有同樣的尊嚴。文字是一種“寫下的存在”。尼采認為:“文字,首先是他自己的文字,本不從屬于邏各斯和真理。這種從屬關系產生于我們必須對其意義加以結構的時代。”然而他認為文字一定有一個先驗所指,以此來區分所指與能指,這一觀點并不為德里達所贊同,他認為存在的意義是前所未有的確定的能指痕跡。文字隱沒于邏各斯,是痕跡重新回到顯現,是差別的重新占有,是我們在別處所說的關于原義的形而上學的完成。即一種“文字的揚棄”。
從先民的造字法中可看出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可見,思維先于語言,中國古代對“言、象、意”的爭論,實則源于一種形象思維,即對圖像的把握。這種思維作用于語言,表達為隱喻,隱喻系統構筑了我們日常的概念系統,包括絕大多數的由日常語言體現的抽象概念。對于隱喻系統的分析,也就摧毀了傳統上對本義語言和修飾語言的區分。萊可夫(Lakoff)指出隱喻源自康德的圖式理論,“圖式”作為言語交流的中介,連接語言與意義,人們可用感知經驗來理解“圖式”所表達的含義。人們將喻源域的認知圖(The cognitive maps)投射到目標喻(本體)上,而在喻源域和感知層中起中介作用的圖式在目標喻中活化。即目標喻(本體)經這種圖式表達,它所表達的“意”已經脫離本義,完成了一次“意”的揚棄,接受者得到輸出者想要表達的一個新的“意”。中國古人善于觀察世界,具有隱喻式的思維方式。這在詩歌方面尤為明顯。古人善用意象來指代所表達的情緒,而漢字也同樣有情感。解構主義所言“文字的揚棄”即中國古人所言“得意忘象”,是“意象的揚棄”。然而隱喻具有任意性,擁有不同感性經驗的人,對于意象的理解有不同,這也是“言不盡意”的原因,也是為什么王弼把“得意忘象”理論推進神秘論中。
6 結語
如前所述,本文由認知隱喻學與中國古代“言意之辯”的理論入手,探討了中西在“隱喻”方面的異曲同工之妙,并進而延伸到中國甲骨文的“象”,來探討甲骨文的形意關系,并由此結合德里達等解構主義思想的理論,探討“象”在當代被重新思考的深層因素。本文對甲骨文的形意關系、文象關系從認知隱喻學的角度來分析、詮釋,由此產生新意。從文字的創造思維來看,甲骨文確實可被分為隱喻和轉喻兩種模式,這一方面跳出了傳統六書思維的窠臼,另一方面也詮釋了古文字的內在哲學。將古代漢語和文論打通,從甲骨文的文象關系所體現出的隱喻式思維,正可以解釋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辯,即“思維—語言—文字”三者之間的關系。“得意忘象”、“心齋”與“意象的揚棄”之間確有理論上的貫穿點。人類正是通過隱喻式思維,運用隱喻、轉喻方法,塑造了一個個抽象的意象,再利用這第二步的新形象、圖式思維,來認識世界,互相交流。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隱喻構筑了人類的世界。表意文字、詩歌意象、音符和弦組成了意象圖式,表達著形而上的哲思,世界的意義也隱藏于其中。
[1]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 中國哲學史[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2]陳鼓應,趙建偉. 周易今注今譯[M].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05.
[3]陳鼓應. 莊子今注今譯[M].中華書局出版,北京:1983.
[4]胡適. 先秦名學史[M].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胡壯麟. 認知隱喻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孟華. 文字論[M].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
[7]裘錫圭. 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8]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 墨子校注[M].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1993.
[9]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四川: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
[10][俄]B.A.伊斯特林 著. 左少興 譯:《文字的產生和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11][法]雅克·德里達 著. 汪堂家 譯:論文字學[M].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12]徐通鏘.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M].山東: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5.
H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17)02(b)-0032-07
李筱竹,教育經歷:英國愛丁堡大學比較文學碩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漢語言文學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