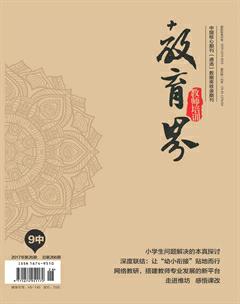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陸嘉明
(續前)
69
出入亂世,劍指天下。是非功過,任由歷史評說。
成也好,敗也好;舍也好,得也好,淡泊致遠而無愧平生之志,從容達觀而不失英雄本色。
隆中預言天下三分。力助劉備匡漢順天應物而據其一,建立西蜀,扶其登基稱帝,終遂出山建功立業之愿。
建蜀伊始百廢待興,身為相父輔佐后主劉禪勵精圖治國力大增,“兩川人民,忻樂太平”,終不負先帝托孤遺愿。
時值南蠻犯境邊臣作亂之際,毅然親自率軍遠征,七擒七縱蠻王孟獲,剛柔并舉攻心為上,終而平定叛亂,祭水凱旋,消除了外患內亂而國泰民安矣。
戎馬倥傯二十年,始終在“隆中對”的藍圖上行走,始終在“三分天下”的夢想中角逐,立下赫赫戰功,創出煌煌偉業。
諸葛亮者,功成名就之英雄也。
所成者,時也,勢也,機遇也;亦志也,智也,知遇也。
然而,成也于斯,敗也于斯。成者于斯,在于得;敗者于斯,在于失。
諸葛亮平定南蠻后,于建業五年(227)即上表后主率軍北伐中原,直至建業十二年(234),先后六出祁山與曹魏交戰,惜乎在數年的雙方勝敗交錯的膠著形勢下,終而六戰六敗,不僅無功而返,竟又命喪征途,從此一生心血皆付之東流矣。
難道諸葛亮真個計窮智竭了嗎?
非也,乃失天時失大勢失機遇也。
其實,諸葛丞相出征前,自也心中有數,對時勢了如指掌。《出師表》一開頭就說:“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是啊,自彝陵慘敗尚未復原;傾力征蠻損耗實力;況又地處僻遠國力貧弱;且曾與東吳結怨,鞏固盟約還有待時日;而曹魏稱雄北方力量最強,雖兵戈未起卻始終虎視眈眈于東、西大地……所謂“危急存亡”并非虛言啊。
既然人富我貧,人強我弱,人無安危之虞,我有存亡之憂,貿然出擊北征伐魏,時未到,勢又未得,機遇更未見端倪,那么,丞相何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呢?
情也。用情太專,太深,太重,在日月的流轉中固化為一種解不開的心結,一種風雨無憾的執念了。
天地無涯,人寰難測。即如大智大勇者諸葛亮,一旦被情捆綁,也難脫天地人寰的變幻和劫數。
何情之有?歷來非常知遇之情,人世難能可貴的感恩之情也。
那也有錯?當然沒有錯。不但沒有錯,而且知恩圖報向來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崇高品德和操守,一種文化傳統和精神標桿。問題在,“知恩”是心,“圖報”在行。心不可變,報當合時順勢,得其機遇而以涌泉出之,報則有功有利,有理有節,郁郁乎如高樹入云,潺潺乎如活水長流。反之,則往往不合時宜逆勢而上,弄不好即如一葉小舟遭遇滔天風浪,難免檣折桅斷甚至于遭遇滅頂之災。
這種淺顯的道理,常人也懂,何況智者?
不錯,諸葛亮是智者,更是君子,深摯儒家文化,言必信,行必果。一諾千金,報效以誠,天地為之感泣。先主曾有遺詔托孤,又留遺志匡扶復漢一統天下,諸葛丞相一一應諾,并在蜀帝病榻前信誓旦旦:“臣等盡施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是的,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銘刻寸心永世不忘,十七年超越尊卑的患難與共的泣血之情,念念于茲,日月可鑒。因之,謹遵先帝遺志出師伐魏,實出乎此種“情”也。這在《出師表》中表達得淋漓盡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后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托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由此看來,奉受先帝臨崩托付,夙夜憂嘆不已。憂也者,巴蜀僻處西南一隅,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嘆也者,先帝遺志一統天下,迄今依然前程渺茫。自憂自嘆自多情,半生滄桑半生擔當。
歲月不饒人,心里真個有點急不可待了。原來這出師伐魏攘兇除奸北定中原興復漢室,實為應先帝遺志而報知遇之恩,又為恪守盡忠而報托孤之責。一一皆出乎一個“情”字啊。
這個“情”字,落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間。便誕出一個“義”字;落在紛紛擾擾的人群中,則可博得一個“和”字;落在溫溫潤潤的人的心里,尚能漫出一個“真”字;落在跌跌宕宕的文學畛域中,那當仁不讓可得“真、善、美”三個字矣。
《出師表》有別于歷朝歷代的表章奏疏之文,堂而皇之地躋身于古典美文之列,首在情真意切,寸心畢現。既俱為“父”者的苦口婆心聲聲叮嚀,又聞為臣者的忠心諫言錚錚作響,慈父心腸忠臣肺腑,讀來感人至深。
二在大氣渾然,理脈可尋。作為相父雙重身份的諄諄告誡,無兒女情長的溫軟柔態,有治國安邦的風云氣象;非為謹小慎微的沉郁婉轉,卻有淋漓痛快的迫烈陳情;也不是憂患無已的芊綿詠嘆,卻露出征揮戈的縱橫豪宕……意在規勸后主立大志,親賢人,遠佞臣,納雅言,謹自謀,行善道,旨在“深追先帝遺詔”。為君者是,為臣者也是。可見表章敘實情與寄虛靈互為生發,理脈循循可尋,至道郁郁而起,自有理性的力度。
三是文辭樸質,不求自工。作為上奏的表章,重在務實、說理、建言,是非臧否皆依縝密之思邏輯之據情采之敷簡約之言循循出之,情理脈動,辭達而盡。《出師表》所奏事之大、理之深、情之真、辭之簡出類拔萃于歷代奏章,雖說出語平撲無意藻飾,然以特有的文學價值,呈現出異乎尋常的美學印記。
說到這里,愚之用筆則要繞個拐角來個大轉折了。依然是那個“情”字,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半生因之成就大業,半生因之失敗告終,悲乎抱憾飲恨魂歸五丈原;壯哉六出祁山屢敗屢戰盡顯智者風范英雄氣概!
真的,他沒有倒在失敗的腳下,始終有一腔無聲血揮灑在中原大地上,有智慧之光閃爍在精神高地上。
亂云飛渡仍從容。是的,他輸了,卻贏在俠風義膽上,贏在堅韌不拔的骨氣上,贏在逸興壯思的遒爍氣勢上……
不是嗎?那些個耳熟能詳的段子,諸如空城之計、減兵添灶之計、裝神弄鬼之計、木牛流馬之計、木像惑敵之計、預設錦囊之計……雖一一皆為敗退之策,卻使同為大智大勇如司馬懿之流聞風喪膽,顧盼驚慌進退兩難。戰事敗績,精氣神卻依然如故,不減當年!
他還是累倒在那個“情”字上的啊。
為報知遇之恩,為擔托孤之責,盡管伐魏時機未到,祁山之外也非有利時區,如前所說,明知不可為仍決然為之也。
《出師表》,是超越陰陽相隔的對先帝遺詔的一個回應,一種傾情的告慰;也是對無能后主的一個深情告誡,一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情懷。孤軍伐魏,逐鹿中原,無論勝敗,都是心的告白,情的傾訴。一段情,既已用一生的心血和智慧來報答了,又何惜用自己的安危乃至生命來償還呢?
血性男子當如是。
偉偉大丈夫當如是。
有話說,不以成敗論英雄。成也英雄,敗也英雄。諸葛先生孔明者英雄情懷如是也。
杜甫曾作詩發豪慨: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是啊,一掬英雄淚,綿延成歷史的長河,長流不息感啟后人;一腔英雄氣,凝結為歲月的滄桑,悉皆由時間來詮釋生詮釋死。
愚唯感到,人生難得如此,而時慚一己之渺小。
70
天數茫茫,世事紛擾。亂世無統無治也無序,興衰存亡,既在天,也在人。天人交集處,世間諸事和歷史過客,冥冥中果真自有定數?
魏蜀吳三國鼎立,稱王稱帝各自為政,依然紛爭不斷懷遠天下。但經血腥交鋒殘酷并吞,蜀先滅于魏,繼而魏又亡于晉,鼎立三足,二足先斷,唯剩東吳一方孑然而存,雖然艱難竭蹶獨足難支,卻延以時日,立足最為長久。這不能不說到孫權建吳立國的偉偉功業了。
說起來,論雄才大略,吳主不及魏主曹操,論寬和至仁,也不及蜀主劉備,然其剛柔得兼以及陰陽交合的縱橫之道,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也。盡管在羅氏筆下,吳主戲份不多,但每每挺身于風起云涌驚濤拍岸處,颯颯英氣逼人,戎馬倥傯激起驚天一鳴;而每每于柳拂殘月水起柔波時,則融融暖情怡人,君臣相顧化為春風一縷。
《周易》有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位誕生于江南富春山水間的亂世英雄,其人格和性格也許約略合乎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時或觀乎“天文”和“人文”,恰有山之定力,有水之至剛至柔的秉性,劍氣凌云和靈動若水的雙重性格,果然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不僅穩守父兄開辟的這片廣袤的江東大地,而且自19歲從兄長孫策手中接過治吳印綬,直至登基稱帝凡51年,而過古稀之年壽終正寢矣。
真不可小覷這位顯赫一世的亂世英雄,活,比曹、劉活得瀟灑,活得沉穩,活得左右逢源;死,也死得坦然,死得尊嚴,死在江山維穩功績昭著之時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