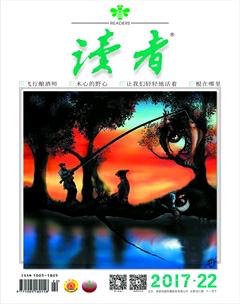讓我們輕輕地活著
譚山山
“2020年,在太空艙白得刺眼的房間中醒來。旋亮燈,連上Wi-Fi,在訂餐App上買一份免沖代餐加榛果巧克力調味包,戴上VR眼鏡,選擇IMAX模式看個4K、3D、120幀的最新電影。褲袋里的手機振動,摘下眼鏡拉開艙門,一瓶包裝簡單的代餐遞到你面前——營養均衡、食用方便,你甚至可以在艙內躺著喝完,不用擔心弄臟床單。”
在《還要多久,吃和住將從人類欲望中徹底消失》中,自稱“關心科技前沿的IT狗”高小山這樣描述“最小化生活”的未來。
事實上,高小山此前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禁食實驗”——每天以代餐粉這種“未來食物”度日。除了身體上的變化,體重從70公斤降到63公斤,另外,他對食物的感受性空前增強,甚至能分辨不同咖啡豆味道的差別。更明顯的變化體現在社交方面:退出了同事們的點餐群,推掉所有飯局,害怕見到家人和朋友(因為很難跟別人解釋吃代餐粉是什么感受),變得更宅。
體驗過戒斷食欲之后,高小山將他的人類欲望田野調查延伸到膠囊旅館上。在他看來,代餐粉和膠囊旅館這兩個具有未來感的概念,似乎能合成一種有趣的極簡生活方式。
“或許在未來,有些人并非被迫,而是自愿走進冬眠倉,自愿食用代替食物的合成粉末。總之,我希望將自己的生活內容壓縮到最小。”
關于“最小化生活”,你想到了什么?對,這是一種“斷舍離”,一種新型的“不持有的生活”,核心就是拋棄物欲、減少生活成本。就像法國哲學家吉勒·利波維茨基所定義的那樣,“卸除那些壓在我們存在之上的多余重量”,也就是讓自己變輕。
而且,不只是個體變輕了,整個世界也正在變輕。
新型的生活方式——游牧式生存
“至少在這個星球的‘發達部分,一些緊密相關并將對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的變化已然發生,抑或正在發生,這些變化為個體追求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環境,同時也帶來了一些人類從未遇到的挑戰。”
在闡述現代性正從“固體”階段向“流動”階段過渡時,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如此斷言。這是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已經煙消云散”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幾乎一切都變動不居的時代。
如果說,“固體”的現代性意味著嚴守戒律、道德主義、約定俗成,是“重”的,那么,“流動”的現代性則意味著輕盈、多變、不確定,是“輕”的。
承繼齊格蒙特·鮑曼所提出的“流動”現代性觀點,吉勒·利波維茨基引入了“輕”的概念。
他把當下這個時代命名為“超現代時代”,認為“輕”作為一種價值、一種理想和一種迫切的需要,不再局限于個人對待生活和他者的態度,而儼然成為全球經濟、文化的運作模式,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表現之一。
無論是齊格蒙特·鮑曼還是吉勒·利波維茨基,都提到了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游牧式生存。
正如齊格蒙特·鮑曼在《流動的生活》一書中所說,這些現代社會的游牧民,都精通并實踐“流動的生活”的藝術,認同迷失。他們喜歡創造,喜歡游戲,喜歡流動;他們“把新奇的東西看成好消息,把不確定性看成價值,把不穩定性看成必要的事”(法國社會學者雅克·阿達利語)。
在《流動的生活》一書中,齊格蒙特·鮑曼引用了《觀察家》雜志上一篇署名為“赤腳醫生”的文章,認為它描述了這些現代游牧民的生活姿態:“像水一樣流動……你迅速向前移動,絕不要抵制潮流,絕不要長時間停下來讓自己變得遲鈍,或者抱著河岸或巖石——你生活里遇到的財富、地位或者人——不動,甚至對你自己的意見或者世界觀,也不要試圖抱著不放,你需要做的,只是與你人生歷程中出現的一切事物進行一次蜻蜓點水卻又靈光閃現的接觸,然后優雅地放開手,任它飄然而去……”
“輕捷和優雅,隨自由一道到來——流動的自由、選擇的自由、棄舊貌的自由、換新顏的自由。”齊格蒙特·鮑曼這樣寫道。
對“飛”的向往
如此說來,“飄一代”是“輕生活”的引領者。
“飄一代”對物質的態度是“輕”的——只租房不買房,只打的不買車;他們對金錢的態度也是“輕”的——懶得存錢,理由是,不用養家,不用供樓,不想防身,不想養老;他們對待哲學(涵蓋一切嚴肅的東西)的態度更是“輕”的——對哲學敬而遠之,哲學顯然是沉重的東西,一切沉重的東西都是“飄一代”所不喜歡的。
“飄一代”對愛情的態度是“輕愛情”——愛過很多次,但從不為誰要死要活;他們的婚姻(如果有的話)是“輕婚姻”——悄悄結婚,絕不舉行盛大的婚禮,肯去婚姻登記處,已是他們對長輩最大的妥協了;他們的人際關系是“輕社交”——不對別人噓寒問暖,也不喜歡被人噓寒問暖,生病時愿意一個人,傷心時也愿意一個人,因為空間比溫情更重要。
而在怎樣擺脫鋪天蓋地的物質主義負擔上,日本人顯然更有心得。在社會學者三浦展看來,2011年發生的“3·11”東日本大地震是顛覆日本人物質觀的一個重要節點:已經被摧毀的物質,即便恢復原狀又有什么意義?下一場大地震、大海嘯照樣會來臨。在自然的強力下,物質已經不足以讓人感到幸福。因此,三浦展提出了“第四消費”概念,其核心轉變是從物到人、從錢到人。
對于日本年輕人沉迷的“小確幸”,上一輩的反應是恨鐵不成鋼: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寫有《低欲望社會》一書,他認為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愿意背負風險,不買房、不結婚、不生小孩,喪失了物欲和成功欲,是“胸無大志”的一代;作家林真理子寫有《野心的建議》,以自己從沒錢、沒身材、沒顏值的小胖妹逆襲為暢銷書作家的親身經歷,給年輕人打雞血——“只想維持現狀,是一種沒有出口的不幸”。
媒體給這些自愿變“輕”的年輕人賦予了種種名稱:飛特族——工作不穩定的打零工者或合同工;單身寄生蟲——和父母合住的單身者(或者是日劇《約會~戀愛究竟是什么呢》中的所謂“高等游民”);食草男——對女性不感興趣的男子……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這樣描述他們:“他們不認可父輩的消費主義,覺得那無異于揮霍浪費。有些人住在‘團體家屋里,和室友共享一室(日本新興現象),吃3美元(約合人民幣20元)的牛肉飯。要說他們肯在哪方面花錢,那就是旅行。在一個通貨緊縮的社會里,你買的所有東西都可能貶值,但經歷不會。”
我們不需要別人的認可,只需要自己認可自己——這是日本年輕一代的普遍心態,也是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的心態。從“飄一代”到“輕一代”,有一個特性貫穿始終,那就是對“飛”的向往——只有擺脫物質的負累,才能實現身體和精神之輕。
就像盧梭在《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里所說:“身外空無一物,只有自身的存在。只要這種狀態持續下去,人就能如上帝一般自給自足。”
輕,并不意味著生活質量的降低
所以,像高小山那樣一本正經地討論人類的欲望,并從最基本的吃和住這兩方面入手研究,是有價值的。
比如房子。是否人人都得有一套房子?在“飄一代”看來這是不需要討論的,但現在的多數年輕人則不然,是不敢,是無奈,或者也有不甘心。
日本建筑師黑川紀章于20世紀70年代設計的東京中銀膠囊大樓,是現代建筑史上首座真正以膠囊般的建筑模塊構成的建筑。黑川紀章與運輸集裝箱生產廠家合作,在工廠預制建筑部件,并在現場組建。所有的家具和設備都單元化,集納在約7平方米的一個個獨立單位里——也就是一個個“盒子”。
按照黑川紀章的最初構想,每25年“盒子”(或曰太空艙、膠囊)就應該替換一次。但事實上,自1972年建成以來,這幢大樓從來沒有替換過“盒子”。
日裔攝影師Noritaka Minami趕在大樓被清拆或重建之前,拍下了一組照片,讓我們得以一窺“盒子”里的細節:有些“盒子”還保留著預裝的柜體(還有嵌在柜子里的電視機);有些“盒子”則用沙發代替床,于是有了工作臺的空間,甚至還擺得下一把舒服的靠背椅。
這種單元格式、將住宿最小化的方式,如今正通過膠囊旅館或共享睡眠艙的形式逐漸擴展。“總有這么一批人,不需要寬敞的寓所、真皮沙發和全景飄窗,懶得再思考床單和被罩買什么花色,墻上該掛個壁毯還是加個櫥柜。只要你沒有幽閉恐懼癥,一間干凈、衛生、水電網齊全的‘膠囊,就可以滿足你最簡單的住宿需求。”高小山寫道。
當你舍棄了對于物質的執念之后,你將獲得的可能是更多的自由。比如,用代餐食物滿足基本營養,而把剩下的時間和胃口留給真正的美食;比如,住進“膠囊”之后,你會改掉買買買的習慣,因為放不下;還有一個好處是,你可以說走就走了。
“最小化,并不意味著生活質量的降低,而是在摒棄物欲之后,擁抱更加純粹的自我。”高小山相信,樂于選擇極簡生活的人將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