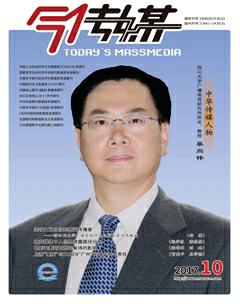文化精神在電影聲音中的書寫
岳伊娜?
摘 要:第五代電影帶著理想和激情走上影壇,探索文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電影聲音在創作觀念上的突破和追求,在對文化精神的建構過程中,留下了諸多寶貴的非物質文化財富。聲音作為電影重要表達手段不再只是輔助。在追求建構的過程中并不代表處處反傳統,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更折射出作品對傳統之下,具有高辨識度和自主意識的特色文化精神的深切關注。
關鍵詞:第五代電影;文化精神;聲音創作
中圖分類號:J9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7)10-0095-03
在文化學中,對于文化精神(Ethos)的定義有種種不同表述,最早是在1906年美國學者W.G.薩姆納在《民風》提出:“文化精神的定義是一個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那些特質的綜合。[1]”人類學家克羅伯認為:“文化精神是用客觀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主觀價值系統”[2]。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進一步闡釋:一種文化,就像一個人,或多或少有一種思想與行為的一致模式。胡繼華老師在解讀中國哲學家宗白華的思想時總結到:“文化精神就是支配著特定共同體建構生命形象的基本價值,在歷史中通過各種有意味的形式表現出來。[3]”本文探討的“第五代電影”以《一個和八個》為開端到《霸王別姬》為止的十年探索。1983年《一個和八個》劇組中從采風、改劇本到創作構思,進行了一場重大變革,“第五代創作者們以導演、攝影、美工、錄音主創部門集體下生活,集體改劇本的方法取代編導二人負責制”[4]。注重電影聲音觀念的表達,是第五代電影創作的重要手段,聲音不再只是呈現劇作和畫面的輔助,而是帶有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電影元素。與此同時,類似的人生歷程、藝術熏陶、群體特性促成了與“第五代作曲家”的合作。解讀第五代電影中的文化精神,就是解讀這個群體的創作行為,及在作品中顯示的該群體創作的獨特多種個性,第五代電影人于創作過程中思考并沉淀的歷史精神、生命精神和人文精神,滲透在聲音創作基理中的待我們進行探聽。
一、歷史精神的建構
(一)傳統文化的再現
《黃土地》中的音樂大多取材于陜西民歌和信天游,片頭一根管子奏鳴的《攬工調》原創初衷是對封建地主的血淚控訴,為影片奠定了蒼涼悲愴質樸的基調。《秋菊打官司》的碗碗腔由李世杰極具感染力的細膩演繹,加以板胡的穿透力,趙季平老師將形成于唐中期——明末清初的活化石挖掘到電影音樂中,使其寶貴價值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展示。《鼓書藝人》中“大鼓書”是在南宋時期遍及北方的漢族民間藝術,在歷史文化傳承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獵場札撒》中女人們在部落生活區的吟唱、牧羊人的牧歌、祝酒歌等所有歌曲都用蒙語進行原生態演繹,代代口頭相傳的遺產,可進行直接藝術審閱和文化分析。《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幕的切換時采用戲曲中 “急急風”鑼鼓打擊方式,多次出現的京劇西皮流水曲牌的女聲哼唱,到“楞里格楞”的循環圈中織體逐漸加厚,刻畫封建深宅的女人們掙脫不開宿命的壓抑。《霸王別姬》西洋弦樂與具有較高的辨識度的京胡、簫、打擊樂等民族器樂融合,調性的對置表現歷史厚重的滄桑。戲曲元素中旋律較多借鑒西皮、二黃、四平調和夜深沉曲牌,片中以尊重戲曲藝術原貌的態度借鑒昆曲和京劇片段。
(二)紅色記憶與文革
《霸王別姬》中解放軍進城時鑼鼓喧天歡歌笑語,戲院禮堂中部隊鏗鏘有力地齊唱軍歌;街道上《解放區的天》營造的朝氣蓬勃環境下,群眾的熱情被調動的空前高漲。《一個和八個》的主題曲《太行山上》為影片拉開悲壯的架式,樂曲渲染著不屈不撓的民族抗爭精神,也是是考驗主題的象征。影片結尾再一次響起,也是代表正義、民族利益的正面力量,給人留下的是一種強大力量的精神鼓舞和民族的強大凝聚力。大閱兵中《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反復在片中作為背景音樂出現,表現雄壯氣勢的同時,構建畫內畫外廣闊的空間中統一有序的狀態。《冰河死亡線》村民在家中收聽的廣博里播放著《我的中國心》;《秋菊打官司》中縣城郵局門口的街市環境中,背景音樂播放著流行歌曲《萬歲毛主席》;紅色記憶不僅在戰爭歷史題材,時至今日經久不衰。《銀蛇謀殺案》連環殺手家中的放映機對《紅燈記》不同電影的碎片式播映,臺詞、動效、語氣詞等一系列切換,象征記憶的瑣碎與主人公精神的分裂。《霸王別姬中》文革時期畫外音廣播里的聲音提示無產階級大革命來;菊仙自殺時破敗的院子里,屋內傳來段小樓發瘋的鬼號般的叫聲,廣播里播放著紅燈記樣板戲,家里的座鐘聲音失真,敲響喪鐘。《女兒樓》文革時期醫院內充斥著大字報和標語,病人用收音機收聽戲曲被勒令關掉,學習室內一位宣傳員念誦時環境的相對安靜,表現個性被壓制下的統一,收音機里的《紅燈記》展示了時代文化和審美趨勢。
(三)中西融合的嘗試
《少爺的磨難》將中國京劇打擊樂與西洋交響樂配合,“造成了一種極富喜劇特色的“國際”音樂語言”[5]。大鑼的響擊、掐音等技法,與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樂句重音重合,英雄贊曲的沉重感與鑼鼓的節奏伸縮,突出反差之下的荒誕效果;第五代作曲家基于傳統文化對西方現代音樂接納,文化整合召喚主體意識的覺醒;《滴血黃昏》的歌舞廳使用了拉丁與弗拉明戈版本的《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搖滾青年》多處英文歌曲和迪斯科音樂,使影片的敘事充滿了節奏感和韻律感;《銀環謀殺案》中披頭士的《Let It Be》作為殺手喜歡的音樂在片中反復出現,代表殺手的反文化心理;《黑炮》《錯位》《輪回》《滴血黃昏》等影片中,西洋樂器與電子音樂多處使用,甚至借鑒具體音樂的創作手法與噪音、各類音響、人聲相結合,音樂音響化和音響音樂化的段落比比皆是;《晚鐘》中多用十二音、無調性序列等音樂手法,影片中“第一聲鐘聲是采用西洋教堂里的素材”[6],與后面反復出現的中國民族宗教素材的鐘聲,形成強烈對比”。即使在中國民俗味十足的《酒神曲》的創作中,開頭兩句“使用了歌劇中宣敘調的寫法”。宣敘調由意大利音樂家在17世紀的佛羅倫薩歌劇中首創,趙季平老師的大膽嘗試為電影音樂創作開發了更多可能性。endprint
二、生命精神的建構
(一)自然生態的基調
《黃土地》中的黃河水聲在片中貫徹始終;《遠離戰爭的年代》多次借由水聲在回憶與現實中游走穿梭;《菊豆》中封閉庭院中的染坊水聲持續在背景中;在中國哲學中水代表了靈活、變化、轉型和適應,這是對中國文化的最佳描述。《詩經》中的“水”象征繁衍生息,《管子·水地》說:“人,水也。……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它孕育著生命的原初,體現自然和人的本性,在中華文明中水與黃土也是生命的象征。“大音若希,大象無形”把土地、民俗文化與人物二者統一起來,對聲音創作的民族特性、心理及命運的深刻反思和同情;《孩子王》中夸張的畫外帶混響的砍伐聲,與樹根轟然斷裂倒下留下巨大回聲和鳥叫聲,引發對于自然生態的關注。牧童喝牛聲、悠然的笛聲、與教室內的授課聲形成對比,一邊是關于對于偉大成果的說教,一邊是自然天成充滿創作藝術感天籟之音,規則與自然天性的分裂對立;《獵場札撒》利用人聲、音樂、音響對于草原環境的深描,建立視聽場景對于聲音的吸引和寫實寫意上的交叉,使畫內空間在層次、立體、延展性增加廣度與深度,影片所反映的草原狀貌就給觀眾展現選形象的同時還留有更多想象的空間。某種“空間特征”的效果可以為聽覺場景提供框架” [7]。
(二)烏托邦的理想空間
《霸王別姬》師傅戲班院子的環境中,頭頂的鴿哨聲在封閉與循環中縈繞,畫外的糖葫蘆、豌豆糕、磨剪子的叫賣聲,表現成長過程中對圍城之外的美好憧憬;《大閱兵》中孫淳房間內的畫外音形式播放的收音機節目:阿拉伯故事《天方夜譚》和《C大調幻想曲》,借用媒介中的文學和藝術來撫慰他經歷痛苦的精神;留聲機中的《御碑亭》保留的是梅珊當紅時的無限風光,重放是追憶亦是對夫妻圓滿感情的向往與諷刺;《獵場札撒》中祖宗原型與英雄原型重疊,在圖爾布山谷草原封閉或準封閉的文化社會,維持機制運轉的理想因素一應俱全。祖先規矩的宣布、獵場中的動物們的聲音、天上的鳥兒、水中的地鵏、地上的牛羊馬群、部落內的生產生活等,人們在這個空間中呵護生命、相互協調抑或實現理想。《盜馬賊》影片中禿鷲在歇息抑或飛翔,僧人們在搖動法鈴和嘎巴拉鼓,女聲高音哼唱與銅欽莊重的銅管樂應和,女聲高音的從上向下像是來自天空嘆息,貫穿著法鈴的聲音音響音樂化,西藏的神秘與神圣感呈現眼前,表現宗教神圣不可侵犯的威嚴。《盜馬賊》深入藏族日常世俗生活,“借助少數民族的“理想國”以及“理想國”的回歸或者破滅,來反射漢族歷史的文化背景”[8]。
(三)生命的審視與欲望
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言:“音樂藝術還有第二要素構成它的特殊性和異乎尋常的力量。除了數學性質,聲音還同呼喊相似”[9]。《紅高粱中》清脆的騾子腳步聲、隱約的鈴聲和如波濤般沙沙的高粱葉聲,渲染了細膩的愉悅心境和廣袤寧靜的和諧。姜文不經修飾沙啞野性的音色,原始且具有濃烈的鄉土氣息,敢愛敢恨的坦蕩的神氣和對人性意識的吶喊。自美國作曲家亨利·考埃爾Henry Cowell在1912 年最先在鋼琴上使用音塊技術,“野合”一場戲使用中國樂器吹奏的音塊寫法,30支嗩吶同時演奏吹出八度內平行進行的音塊,模擬人聲對于生命吶喊形成生命符號。4支高中低音笙做底,在兩個八度內演奏自然音塊加上大鼓的轟鳴,裝飾意味濃厚地渲染場景和人物情緒。《邊走邊唱》中縹緲的音樹聲好似來自天上、地上黃河川流不息,古琴錚錚一代琴師“驚天地、動鬼神”的高歌絕唱。天、地、人被包容在圣殿般的環境中,充滿了啟蒙與反思精神的民族寓言。聲音作為歷史存檔,在神圣儀式的建構過程中將人類的生命與身份變化進行續脈。《錯位》中趙書信感到“自我”即無法協調的恐懼,于是進行了生命的復制,聲音設計上從語言、腳步聲、音效等方面形成了差異可識別,有意義的生命被懸置,對另一個異化人格進行反思和審視。
三、人文精神的建構
(一)個體表達與反思
第五代電影講究意境的營造,對話過于繁雜就會破壞觀眾動用形象思維的潛在空間,畫外音以第一人稱“我”的形式大多是自我意識的呈現。《一個和八個》中許科長幾次內心獨白的猶豫,面對死亡突出人物的矛盾、良知的呼喚、意志的考驗。《大閱兵》不同個體的內心獨白,有效地構建了作為“表述行為主體”的人,壯觀的閱兵式訓練的背后個人與集體統一過程中的矛盾掙扎《女兒樓》中茫然的喬小雨內心獨自顯現出為革命“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敘事模式和文化精神,也把悲情的開放性疑問留給觀眾思考。《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多段內心獨白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心態轉變,也是批判對游戲人生的頑主文化。“當電影出現某些特定圖像時,聲音分隔的效果顯示它更少地使用聲音,我們稱為‘athorybes(從希臘語中借用而來,意為‘無聲的)”[10]。故靜默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沉寂,常用在比較強烈的聲音前后以造成休止符式停頓的思考對比。《一個和八個》土匪頭子大禿子大喊著痛快被炮彈炸的聲音打斷,煙霧以慢鏡頭向畫面右邊消散,爆炸后的音響余音逐漸消失,默哀的形式是語言的中斷和環境聲的消失,空曠的原野延展厚重幽遠的沉思。《滴血黃昏》也兩次用到靜默手法,表達了極度悲傷之下的失聲。
(二)民俗事項與儀式
婚喪嫁娶,儀禮規范、節日慶典中無不展現著文化的景象,《黃土地》中片頭悲劇性婚禮吹打著從遠處山坡蜿蜒而過,聲音距離感的控制有意展示一種間離效果,由對個人命運的關切上升到對一種廣闊歷史和文化的反思。《紅高粱中》的《顛轎歌》第一次出現在片頭出嫁場景,轎夫們在荒野中狂歡齊唱,嗩吶、笙和鼓等盡情地演奏著喜慶的氣息,與九兒的抽泣聲音形成強烈對比。熱愛生命的人渴望參加儀式,然而他們的權利卻常常被排斥在外。聲音亦在與死亡相關的祭奠儀式中彰顯儀式感,《菊豆》中出殯的一場戲,菊豆和天青聲嘶力竭地擋棺,喧囂嗩吶鑼鼓吹打樂器,漫天紙錢的揚撒,壓迫在生者身上封建禮教仍在折磨身心,幽怨的塤聲一如對宿命的嘆息,儀式是權力對于等級的維護、凈化方式,剝奪精神乃至生命的方式。《獵場札撒》片頭中用蒙語宣布作為道德律令和做人標準的“札撒”規則時,除了少許的環境和馬匹動效人們都安靜不語,恪守對祖先和規矩的尊重。《盜馬賊》除了表現少數民族生活風俗,是我國第一部以如此大的比重來表現宗教的影片,影片中佛教大型儀式“曬佛”,銅欽和甲鈴作為藏佛傳教樂器中的重要樂器渲染著西藏宗教文化的氛圍。箭臺祭祀儀式由統嘎(海螺)發起號令,男人們騎著馬聚集歡呼聲此起彼伏,呼喚著保護神祈福蜂擁插箭叩拜,乘風而颶的隆達象雪花般聲音應和著風聲飄滿山崗。endprint
(三)勞動生產與藝術
《紅高粱》的《酒神曲》取材于民間的勞動號子,表現對勞動和神明的崇拜,虔誠,曲調激昂旋律同音反復,充滿對生活生命的贊美熱愛,自然近似原生態的人聲一領眾和透著酣暢淋漓的力量。“一領眾和”是勞動號子的主要演唱形式,隨著人類的進化語言的發展,勞動的呼聲逐漸與含義明確的語言相結合,從詩歌的雛形逐漸從簡單的旋律、吆喝,發展為情感豐富的內容,曲調完整的歌唱形式。宋高承《事物紀原·杵歌》載:“今人舉重出力者,一人倡則為號頭,眾皆和之日打號。[11]”《妹妹你大膽地向前走》的曲調融入了趙季平老師在榆林采風時,一首老百姓打夯的北方民歌,歌詞中充滿的各類語氣詞如:呀、兒、啊、哇等。“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感情的激蕩而發出有如‘啊‘哦‘唉或‘嗚呼‘噫‘嘻一類的聲音,那便是音樂的萌芽……這樣界乎音樂與語言之間的一聲‘啊……便是歌的起源。[12]”《邊走邊唱》勞動人民面對黃河浩蕩滾滾滔滔,面無懼色,師傅帶著船工們過河引吭高歌,激蕩出人們內心的回聲。遠處男人們的歡呼,小二的瘋笑,小女孩扔火把進黃河的歡呼。男聲合唱、管弦樂隊與男人們的勞動號子聲、吆喝聲交融在一起,表現了西北黃河的雄壯和勞動人民的豪邁
四、結 語
從電影聲音角度來對文化精神進行建構,外在形式是各種各樣的聲音符號組成的可聽辨的對象,內在形式是支配著符號組織方式的創作方式個性。聲音作為可以跳出畫框范圍的元素,是比畫面更為抽象的集合,解讀第五代電影中的文化精神,就是解讀這個群體的創作行為,及在作品中顯示的該群體創作的獨特多種個性。第五代電影所開創的視聽前景,承載著他們個人成長過程及社會歷史的文化精神印記,聲音作為存檔的文化遺產,永無休止地在記錄和折射著文化精神。
參考文獻:
[1] (美)W.G.Summer.Folkzways,Boston,1906.
[2] (美)A.L.Kroeber,Anthopology,1948.
[3] 樂黛云主編.胡繼華著.宗白華 文化幽懷與審美象征[M].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4] 倪震.第五代電影前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 王云階,朱天緯執筆.新中國電影音樂創作綜述[J].當代電影,
1993(5):53.
[6] 筆者于2017年9月,針對《晚鐘》對王樂文老師進行創作采訪.
[7] (美)Altman, Rick : The Material Heterogeneity of Recorded Sound. In Rick Altman (Ed.): Sound Theory, Sou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pp.24.
[8] 厲震林.藝術人格:第四、五代電影導演的批評札記[J].戲劇藝術,1995(4):62-71.
[9] 丹納,藝術哲學[M].甘肅: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5):39.
[10] (法)希翁著,黃英俠譯.視聽:幻覺的構建[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
[11] 虞云國主編,宋代文化史大辭典(上)[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6.
[12] 柳倩月.文學創作論[M].廣東: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2013.
[責任編輯:傳馨]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