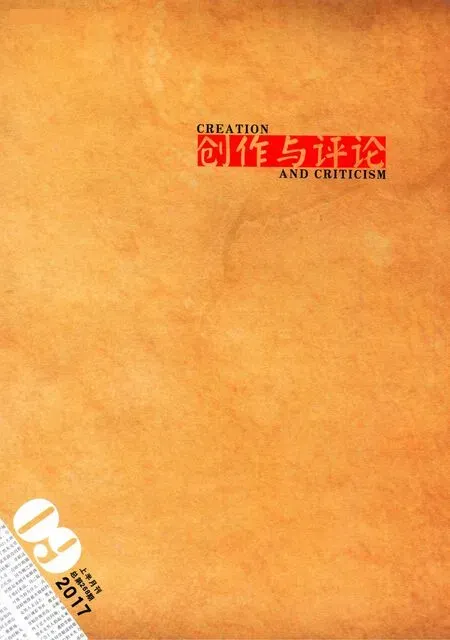假如大水漫過紅杉林(短篇小說)
○林漱硯
假如大水漫過紅杉林(短篇小說)
○林漱硯
一
初冬來臨,寒氣里仿佛帶著夜晚的陰影,一點點滲透到我的生活。我向單位告了假,獨自坐在窗前曬太陽。朝北的房間,陽光極為稀疏淡薄,耳畔似有落木蕭蕭的聲音。于是,臨時起意,想去追尋一片紅杉林。
三天前,我在醫院做了個活檢,醫生用鉗子從我身體某部位取下三塊組織,浸泡在福爾馬林液中,送進病理實驗室。五天后取結果,工作人員從口罩后面吐出一句話來。已經過了三天時間,我想象著,那三片蒼白失血的組織一定已經經過處理,被石蠟包埋、切片、制片、常規染色、中性樹膠封片,正等待醫生在高倍放大鏡下觀察并做出診斷了。人體是由數百萬億個細胞組成的,該停止生長的細胞卻無限增殖,就會出大事。還有兩天時間,這三片組織便能代表我龐大繁復的血肉系統,給我打上一個健康或不健康的標記。在等待中糾結,在糾結中等待,日子就這樣回旋往復。
同行者三人,一位是詩人,一位是攝影家,另一位是油畫家,都是在各自圈內聲名漸長的人。攝影家隨身攜帶著他那架大塊頭的單反;詩人隨口就對著某處旮旯角吟出一首詩來;油畫家的墨綠黑格裙子上還沾著白色的涂料,像從她自己的畫作中走出來的慵懶女人。只有我,什么也沒帶,出來時在發梢扎了一枚粗陋的百合發飾。
我跟油畫家是初相識。她問我,你呢,是做什么的?
我說,你看看我的打扮就知道了。
油畫家不解。
說是初冬,其實南方的冬天更像春天。南方往往是這樣,冬天里,有人穿貂皮大衣,有人穿襯衫。出來時有陽光,汽車跨過一座山后,霧霾突然涌了出來,窗玻璃上一片模糊。
攝影家很懊惱,說沒有光的日子,就相當于失去了眼睛,所以攝影家是絕不能在沒有太陽的日子出門的,否則,他就變成了一個俗人。比如今天,他就只是一個陪朋友出去走走的俗人。
油畫家說,就當我耗盡了油畫顏料,畫了一幅水墨畫吧。油畫家每次裝箱打包寄畫、收畫時都很惆悵,行李零零散散裝滿幾只集裝箱,絕不是一個45公斤體重的女人能夠搞定的。每當這個時候,她就恨不能舉起斗筆畫一幅國畫來得省力。
詩人觀察了許久,終于斷定說,這不是霾,是山上的霧氣,外表糊里糊涂,骨子里是清爽的。我們也寧愿相信這是水滴的純凈集合,便迎著這不知道是霧還是霾的東西前進。
汽車一直在山路上繞行,誰也不清楚這片紅杉林具體在什么位置。攝影家憑借超過常人的對光的敏感度,為我們指引方向。奇怪的是,當我們認為離想象中的凈土越來越近時,目的地卻總是在遠方。
詩人很開心,他說最好永遠找不到目的地,這樣,他就可以帶著油畫家去私奔,離開那位處處給他穿小鞋的上司遠遠的。然后,他們什么也不用做,只需她為他畫裸體像,他為她作燙耳的情詩。說著,他嚷著車里太熱,脫去外套,露出了緊繃著厚胸膛的棉質內衣。
我們在山里轉了一天多時間,吃光了攜帶的零食,累了靠在自己的座位上睡覺,經歷了陽光、霧霾、小雨、陰云。直到第二天午后,在百無聊賴中,詩人舉起一個火紅的蜜桔,把它比喻成是一朵盛開的向日葵。我們順著他高高舉起的手的方向望去,就看到了這片紅杉林。
幾百棵紅杉樹站在水庫中,延展到遙遠的灰色云層邊。周圍都是水,無邊無際,水很混濁,跟岸相連的地方漂滿了生活垃圾,空氣中泛著酸腐嗆鼻的氣息。不知道這樣的一片水何以被稱為水庫?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丑的水庫,這樣的水庫讓人感覺恐懼甚至窒息。
攝影家調好三角架的高度。這樣的水庫,他拍不到什么好風景,只能和油畫家拍一張合影。在無人操控的鏡頭前,他無聲地向油畫家靠過去。我注意到他們腳前的泥土地上,胡亂地扔著幾個用過的尿不濕。不知道在這樣風吹著杉林的水邊,父母給孩子換尿不濕時,濕風拂過孩子柔嫩的屁股,會是什么感覺。
詩人,正對著紅杉林里的一座椅子墳抒情。周圍是成片的濁水和成排的紅杉樹,卻只有這樣一座坐北朝南的墳墓被積水染成淺褐色。不知道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還是對生的眷戀,此刻它露出水面,在一片紅杉林的疏影中獨自靜默著。
詩人吟了一首詩,我聽到最后一句是:我們用一天/懷念漫長的一生/明年清明/我是不是該劃著小船來祭拜你?
詩人又對著一棵虬曲的大樹嘆發詩興:大水漫過你的發梢/我編兩團樹枝/贈你為耳墜。我抬起頭,果然看到最高的樹枝上,一左一右掛著兩團亂草枯根。詩人說,水庫的水位最高時可到這個位置,如果現在來一場洪水,我們都會變成退潮后的亂草枯根。
那么說,所有的紅杉都會被沒于水下?
那是當然,水杉,必須具備被水淹而巋然不動的氣質。水來時,浩浩滔滔;水去后,紅影點點。這才叫紅水杉。
我深深地同情起水中那座墳墓的主人來——大水壓頂時,會是怎樣的孤單與無助。或許,有那么多的杉樹與他一起眠在水下,也不至于孤單吧?
靠岸邊的一棵大水杉上,掛著一把折疊好的紅雨傘,彎柄緊緊地鉤在粗枝上。詩人讓我站在這個角度,為我吟一首詩。我怕他吟出西爾維婭·普拉斯式的詩篇來,心頭一緊,快快地轉過身去。
又來了一批人,有男有女。女的披著紅色、黃色、綠色的長絲巾,一來就對著紅杉林擺出各種姿勢。一個男人替她們拎著包、抱著脫下來的外套;另一個男人跑前跑后,“嚓嚓”地摁著相機。
你們來得晚了幾天,我之前帶朋友過來時,杉樹紅得可好看了。一位向導模樣的女人說著,翻出手機相冊,讓我看一張張艷俗得像明信片一樣的照片。
大約是為了彌補朋友們的遺憾,她突然對著水庫遠處的一葉竹排喊起來:喂,你把竹排劃過來,我們要坐你的竹排到水庫里去拍照!
竹排上的人只抬了一下頭,就繼續低下頭去。
竹排浮在浩淼的水庫里,上面的人看樣子是個女人,身著紅色衣服,并不穿蓑衣戴斗笠。
喂,劃過來!我們給你錢!那個埋在一堆衣服里的男人扯著脖子,粗聲叫起來。
竹排靜靜地泊在水面上。這一群聒噪的人只得無趣地走開了。其實,我并不認為到水庫里去拍照有什么好的,沒有陽光的日子,紅杉倒映在水里,像是水底下涌動著的陳年暗血。
攝影家、油畫家和詩人對水中央的一座孤嶼產生了興趣,周圍都是鐵銹般的紅色,只有這座小島,具有突兀的綠意。他們要沿著水庫岸邊,一直走到島上去。
攝影家說,我要在那里拍到一張前所未有的好照片。
詩人說,我想在島上邂逅一條美人魚。
詩人早些年非常喜歡釣魚,天天往人少、水清的水庫跑。但是后來,詩人得了非常嚴重的頸椎病,從脖子到后背,似有無數根魚刺扎著他。他相信這是懲罰——每天把活生生的魚釣上來,看著它們透明的嘴巴鉤在鋒利的魚鉤上,拼命掙扎。他把它們捧在手里、從魚鉤上摘下來時,感受到它們微弱的體溫,它們搏動的求生欲望。他原本可以放了它們,卻終究將它們收入魚簍里。自從變形的頸椎骨挾制著他轉頭、低頭、抬頭時,越發覺得自己受了神秘的詛咒。因此,他再也不釣魚,也不吃魚了。
油畫家說,我想找到一座無人島,以自己的名字給它命名。
我沒有什么想法,但也跟著他們一起走了,因為我不想獨自留在這水里的墳墓前。雖然,遠處的竹排上還坐著一個人。
要繞水庫走大半圈,才可以抵達綠島。
遍地都是裝農藥用的棕色塑料瓶,它們里面的液體早已滲入到腳下的土壤里,而瓶體卻經久不腐。這種塑料瓶子,在周邊山頭隨地可見。某年端午節,我帶孩子去楊梅園摘楊梅,三歲的女兒踮起腳,摘下低枝上的一個楊梅直接塞進嘴里。我低頭看時,小姑娘穿著蕾絲襪子的小腳像一對蓓蕾,正踩在這種塑料瓶上。我奪下她即將送入口中的楊梅,女兒無辜地大哭起來。
岸邊成排地臥著爛成半個的大魚頭,雪白的頭骨排列整齊,魚眼干枯深陷。這種場景,我有似曾相識之感。
我很早就開始關注油畫家的作品,上半年,她在本地開過一個小型畫展,叫“照亮魚眼的微光”。全場三十幅油畫,畫的全是魚,大頭小尾的,有頭無尾的,肚皮朝上的,長著八條腿的,色彩絢爛、奇形古怪,但是無一例外地翻著死魚白眼,像被真空機抽光了空氣。只有一條瘦瘠的魚,背部扎滿二十厘米長的箭矢,一只魚眼里打了一絲幽暗的亮光,可惜另一只眼睛也已經瞎了。整個展廳散發著一池死水的氣息。
那天,油畫家有事外出不在現場,詩人替她看著畫展。只有寥寥幾個人來看展出,他們看一會兒,討論一會兒,又搖搖頭說,油畫家是靠畫人體畫起家的,那些畫好,眼前這些死相猙獰的魚,叫人真心看不懂。我讓詩人介紹一下這些畫到底是什么意思,詩人說,油畫家接了個電話就匆匆出去了,只留下一句詩一樣費解的話:你拋出詞語的長線,也休想從我的畫里釣起魚來。
詩人看著眼前的景象,大約也想起了那場畫展,不由得變了臉色。他沉默了許久,嘆息道,我不釣魚/魚依然因我們而死/早知它們死相如此難看/還不如在我手心掙扎。
二
前往小島的路,我走了不到三分之二。當他們手腳并用,攀過橫在水面的一棵傾倒的樹干時,我突然發現自己的手機不見了。思索再三,手機應該是落在我們看水杉的地方了。
我一個人返回到原來的地方,出乎意料,那只土黃色外殼的手機竟然還躺在黃沙地上。手機里有好幾個未接電話,其中一個是紫欣的。
紫欣是一名醫生。醫生如果生病,那是清醒著的痛,肯定比一般人更疼一些吧。
一雙看不見的大手,往人世間撒了一把種子,很多惡毒的東西發芽了。憑借僅有的醫學知識,我知道癌癥不是瘟疫,因為它不具傳染性。《啟示錄》中說,在末日,地上要滿了瘟疫。我寧愿被人嘲笑無知,也要把癌癥歸類到瘟疫的行列中。因為有那么多的人,像被傳染一樣,染上了至今幾乎無法可治、無藥可醫的癌癥。
醫學專家們都在尋找癌癥的根源,其實我們普通人也知道,無非是環境污染、食品不安全、人體抵抗力下降等等。所不同的是,醫生們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意欲找到攻克癌癥的良藥。而普通人,用超出自己能力范圍的金錢、精力、時間和體力,去消受這些所謂的良藥,像某種可憐又偉大的小動物。
醫生,在當下不知道算是個好還是不好的職業,醫患關系日益復雜,醫生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子承父業。但是作為一名患者,即便只是得了感冒,也認為自己是難受得要死的人。
現在的紫欣只是一名病人,重病人。剛得知自己生病時,紫欣坐在醫生對面,焦躁不安地問,自己不抽煙、不喝酒、崇尚素食,每天在體育館走路四千米,吃水果花的錢比吃飯還多,為什么還會得肺癌?
醫生說,得不得肺癌,跟這些都沒有關系。
要是這個病人之前是抽煙、喝酒、從不鍛煉、飲食無節制的呢?醫生肯定會說,得癌癥跟你上述不良生活習慣有關。聽者心里鐵定悔不當初。
有專業人士統計說,現在的疾病譜發生了巨大變化。三十年前,得肺癌的基本都是男性煙民;但如今,反而是不抽煙的中年女性得肺癌的概率更高些。紫欣說,那就是命了。
十多年前,紫欣的父親也死于肺癌,她的病跟父親的病如出一轍。基因真的是個很強大的東西,紫欣非常幸福地活到了四十歲,卻還是逃不出它的掌控。但是她沒有埋怨父親,肉身的一半是由來自父親的因子塑造的,好與不好,在一剎那間就已經決定,不能因為生病就對歸入墳墓多年的父親發出暴戾之氣。
把突遭橫禍歸結于命運,這實屬無奈,但紫欣原本并不是個認命的女人。她立刻飛到了香港,在一家醫院接受靶向治療。一個療程六次治療,要做兩個療程,費用接近七位數人民幣。費用上暫時還負擔得起,前幾十年辛苦打拼攢下的錢,原本以為可以用來養老的,沒想到變成了救命錢。
紫欣生病至今剛好一年。
過西方情人節的時候,老公給紫欣買了一束玫瑰花。那時候的她因為天天掉頭發,干脆理了光頭,臉上皮膚卻還光潔,化著淡妝,精神狀態還不錯,顯得光頭也挺有個性。她個子不高的老公捧著玫瑰,單膝下跪,拍下了她生病以后的第一張照片。那天,是她第三次治療結束的日子,醫生舉著CT片子驚喜道,你看,治療效果非常理想,肺部陰影消退得差不多了,只要堅持做完兩個療程,你就可以像以前一樣該干嘛干嘛了。蛇咬蟲噬般的痛苦,在這句承諾面前又算什么?紫欣隱忍地點頭,老公也欣喜若狂。
七夕時節,老公給紫欣買了一朵紅玫瑰。那天,他陪紫欣做完治療有點遲了,匆匆跑出去,過了很久才回來,右手捏著一朵花瓣有點卷邊的玫瑰。這時候的紫欣已經戴上了一頂原色假發。她哥哥架不住八十歲老母親的再三央求,打開視頻,讓她們母女隔著玻璃屏幕相見。紫欣努力地對著母親微笑,母親瞇縫著老花眼看了又看,這才點點頭說,在外頭進修要保重啊,一個女人家,學那么多干嗎啊?
陽歷年底,紫欣的狀況急速衰弱下去。兩個療程結束了,肺部的陰影的確消散了,但是身體其他部位快速地出現了散兵游勇。在電話里,她的聲音不再那么明朗,偶爾會不由自主地帶著哽咽。掛電話前,她的聲音緩緩地沉下去,帶著逶迤的尾音,讓人疑心她會忘記掛斷電話。醫生跟他們商量下一步治療方案的時候,她老公都會垂手站在一旁說,聽醫生的,我沒有意見。紫欣已經懶得戴假發,皮膚也灰暗無光,簡單地攏了一塊真絲方巾,遮住了她光禿的頭皮。
紫欣在醫院附近租了一個小房間,一個月4000元,帶一間小廚房,為了能夠每天做一點熱飯吃。人到生病的時候,連再平常不過的睡眠、飲食都成了奢侈品。她治療時住在醫院,治療結束就回出租房休養。
我去看過她一次。經過維多利亞港,夜景映襯著水面,不知道是暈飛機,還是迷離于這光怪陸離的燈光,我感覺自己頭眩得很。我用病房門口的消毒液搓了手,才敢走近她。紫欣的手,從手掌一直到指尖都是冰涼的。我握著她的手,像握著一片酥涼的薄冰,呵一口氣就會融化似的。紫欣不但要做各種各樣的治療,還要吃各種各樣的藥,升白細胞的、升紅細胞的、增強免疫力的等等,甚至吃未經認證的抗癌藥。我問,你自己都是個醫生,怎么會吃這種藥呢,誰知道里面裝著什么。她搖搖頭,艱難地吐出幾個字,為了活著。
中間那張床鋪的上海女人在過四十六歲生日,丈夫、女兒、準女婿都來了。丈夫仔細地為她梳理頭發,女兒插蠟燭,認真地數著,一、二、三……她對母親說,過了生日大一歲,我插七支蠟燭了哦!大家唱起生日快樂歌,丈夫扶她起來,她努力呶起嘴,家人在旁邊悄悄地一起幫著吹蠟燭。燭光滅了,大家一齊給了她熱烈的掌聲。我夾雜在被悲傷摧殘的人群中,也不自覺地鼓起掌來。
在場的每個人都分到了一塊蛋糕,除了三個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在共同的疾病面前,病友都成了親友。紫欣在我耳邊悄悄說,就是她,一直住重癥監護室,前幾天想用刀割自己的動脈,但是連這個力氣也沒有了,可憐。我端著紙托盤的手在瑟瑟發抖。生日儀式還沒有完畢,這個女人又被七手八腳送進了重癥監護室。原來,醫生護士都在病房外隨時待命。
以前,經常聽一些怨婦說,自己是為了孩子活著,為了父母活著。只有到了這個地步,才能明白到了某些時候,人真的不是為了本體而活著。
紫欣穿戴好,和我一起在病房前的走廊里散步。紫欣說,等她也到了那個時候,絕不要給她組織搶救,她無法想象,身上插滿各種各樣的管子,被掛在維持生命的機器上。那時候,活著的是機器而不是她本人。還有,她寫好了遺囑,等她一死,讓老公馬上去娶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回來。只有年輕漂亮、身體好的女人才可以更好地照顧他的下半生,她這一輩子,欠他的太多了。她說著,眼睛里盈盈地亮起來。
似乎有一股冷風穿透了我的身體。
三
有一塊石頭一直懸在我頭頂。至于那塊石頭的形狀是怎樣的,我卻不得而知。這是一塊看不見的石頭,它的陰影投在我心間,沉沉地壓著。此番出行看到紅杉林中的一座孤墳,一種不祥的預感才突然攫住了我。不錯,懸在我頭頂的石頭就是那樣的形狀。
病理科醫生的電話還沒來,她跟我相熟,說一有結果就告訴我。紫欣的電話又恰巧在這個時候打來,每次接到她的電話,我總是不由得心里發緊。眼下更是如此,我需要醞釀一些什么話出來,才有勇氣回撥電話。
紫欣的情緒明顯好于往常。她前段時間又接受了一些新的治療方法。
利用液氮的超低溫性質,來使局部腫瘤壞死脫落,體溫在瞬間降到零下四十度,然后身體因為應激反應,又緩緩發燒至四十二度,冰火交融,渾身疼痛難忍。還有一種什么基因療法,這是一項頗受爭議的技術,在一些醫院已經被叫停,另一些醫院卻還在偷偷開展。反正只要醫生認為能救命的,她都愿意一試,萬一能夠抓住那百分之幾的希望呢?
紫欣馬上發了對比圖片給我看,化驗報告單上,一些腫瘤標志物指標的確在直線下降。紫欣很想大笑出來,卻馬上壓抑了回去,她害怕一笑出聲,好運氣就會變成喉嚨里沖出去的那道白煙。那位院長撫掌大笑,表示要將紫欣作為成功的案例,或許可以拿這個數據,去國外申請醫療集團上市。我不是醫學生,都知道那些指標下降說明不了什么,紫欣卻高興得忘乎所以,令我又想起了畫展上的那幅畫,一條瘦瘠的魚,背上插滿了箭矢,一只眼睛已瞎,另一只眼睛里透出一絲幽暗的亮光。它被破壞,被損害,奢望帶著一身的傷痛逃離,卻終究被禁錮在原地不動。
紫欣問我,知不知道干達山里一個叫紅杉林的地方?聽說那里就是人人羨慕的世外桃源,被叫做長壽之鄉,很多生重病的人都會去那里療養。因為紅杉多,空氣質量明顯優于其他地方,尤其適合于肺癌病人。
此時,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片紅杉林。我可以現在就收藏一個定位,下次指引紫欣順利到達這里。但是,我不知道該不該對她說說地上扔著的紙尿褲、水邊瞪著死魚眼睛的半個魚頭,還有那些根部腐朽的樹。
紫欣下了決心,表示不懼路途遙遠、山路崎嶇,一定要來一趟。雖然她身體羸弱,但是可以讓家人開車載著她,慢慢開、慢慢走,總有一天會抵達那一片長壽之鄉。——她說,我們一起選的那張照片,或許可以緩幾天再用了!
紫欣在接受這些新療法之前,跟我在微信上聊過天,發了三張證件照給我看,問哪一張最好?我說,第一張,笑容太大;第三張,神色太嚴肅;第二張剛剛好。她說,她也這樣認為,只有第二張用來貼在訃告上最合適。我很懊悔自己又中了她的圈套,她也許是為了向我討個吉言,我卻無意間順了她內心的畏懼。
面對這樣的病人、這樣的心愿,我很凌亂,贊成或反對的話,一句也說不出口。云朵下垂,天空斜滿了雨絲,撲到眼睛里,像撒了一把細針。
你上來吧,避一下雨。那片原本遠遠漂著的竹排劃到了眼前,一位穿大紅色毛衣的年輕女子向我招手。
我擺擺手,我不會游泳,素來害怕浩淼的水和飄搖的船。
竹排前頭蹲著兩只體型碩大的水鳥,通體是優雅的淺灰色,并非常見的鸕鶿或鵜鶘或白鷺,這些水鳥我都認得。紅衣女子說,她養的水鳥不吃魚。或許,現在大家都不再依靠大自然的內部循環系統來維持生態平衡,水鳥捕不到魚,也不再需要捕魚。水里的魚也在悄然改變自己,它們自行原地爛掉,我們注定沒有鮮活的魚吃。
或者,你可以用那把傘,是我掛在樹上給游客用的,山里的氣象變化特別快而且令人措手不及。
記得小時候,我的小伙伴想撈起漂在河面的一枚塑料梳子,失腳跌進了河里。母親緊緊地攥住我的手說,水里一切的東西都是不潔的,那很可能是某種東西搖身一變而成的,我們將手伸向它的時候,它就伸出一只看不見的手,把我們拖下水去。對水的恐懼,可能在那時候就種下了。何況眼下,孤墳就詭異地蹲在那棵紅杉樹下。
她見我遲遲不敢伸手,微笑起來,將竹排靠在岸邊。岸,在這里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水漲的時候,所有的土地都是沼澤地;水退到哪里,哪里才可勉強被稱為“岸”。竹排上撐著一把釣魚人用的大傘,紅衣女子坐在傘下,像一只紅色的大水鳥。我蹲在岸邊,我們就這樣聊上了天。
我問她,你怎么一個人在這里,不怕嗎?
紅衣女子說自己已經在這里呆了幾個月,活得還挺好,遠遠超過了醫生給的生命期限。至于那座椅子墳,她已經與它成了熟人,毫無懼怕的理由。她沒有其他事情要做,她帶著時間,時間馱著她,就在水上漂著。說完,她問我,你知道干達山里一個叫紅杉林的地方嗎?
這話跟剛剛紫欣問我的一模一樣,我嚇了一跳,警覺道,你是誰?
我只是住在紅杉林里的一個人。
這里,也不見得好呢,感覺污染很嚴重。
除了幾個本地村民,都是重病人住在這里,不污染也不可能呀!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想來,對他們來說,不來一趟,心里永遠放不下。你想過沒,假如現在大水漫過紅杉林,會怎樣?
我惶恐起來,真的會突然發大水嗎,水庫里也有潮漲潮落嗎?那這個椅子墳該怎么辦?
那就再死一次唄。你認為臨死前肉體會疼痛嗎?
這……肯定會吧。
我認為,到最后的一剎那,應該是很舒服的,全身毛孔都舒張開來,那是超越死亡的解脫吧。
一片紅杉林。一座孤墳。一對水鳥。一位紅衣女子。我亦是孤身一人。我居然在這樣的情景下,跟一個陌生的女人聊起了“死亡”。
年輕一代,大約都曾經經歷過許多不忌邪、不信邪的日子吧。小城剛開始推行火葬的時候,同辦公室的年輕小伙說,他可以第一個去試試爐溫高不高。現在,我們每逢談論起死亡,都會用隱晦的詞語來代替。在這個可以大手大腳過日子的年代,我們反而要謹小慎微地活著。到處似乎都有邪惡的種子在發芽,進入腹中的,從心里出來的,沒有一樣是令人放心的。
就在來紅杉林的前一天,我正坐在辦公室里,努力地宣傳重癥病房的一名主任醫師。前段時間,他的科室送過來一個四歲的小女孩,不幸患上高危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高燒至四十二度,消化道大出血,經過主任醫師的治療,女孩度過了危險期,也算是個奇跡了。主任醫師的電話恰在此時打過來,叱責我說,這個孩子你抱回家養著吧!
這個女孩住院的當天,我正坐在辦公室里寫稿,根本不知道重癥病房的病床上多了一條才四歲的小生命。她滿臉悲凄的父親慕名找到我,迫切陳詞道,他跟妻子失業在家,救治孩子需要一大筆錢,他們拿不出來,又實在不忍心看著女兒夭折,問我能不能給他們搞個眾籌?家里很窮,孩子出生后就一直住破房子,連生日蛋糕都沒吃過,怎么會得白血病,她還有機會吃一口蛋糕嗎?說著,他一雙眼角各繞起一條光帶,眼睛望向我,眼神卻瞟著地上。
我之前也做過類似事情,他一定了解了我的信息,所以才用了“慕名”一詞。
女孩瘦弱如一尾擱淺的魚,被包裹在一堆儀器中,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珠掙扎著望向我。我用筆發聲,替這位年輕的父親聲淚俱下,懇請大家伸援手。第一個療程結束時,好心人捐的善款也用完了,她本該回家休養一段時間,再來繼續第二療程的治療,但她父親卻把她扔在了醫院,向主任醫師丟下一句話:是你們把我的孩子治壞的,我要起訴你們!
不知是否因為被喂了太多的藥物,女孩的臉蛋圓而蓬松,看起來有股癡傻的福氣,眼珠子也變得粗糙黯淡,我無法再將她與擱淺的魚聯系起來。
領導特地找我談話,嚴令我今后只管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行了。我當然知道自己的“本職工作”是什么。那么今后,若是再有無辜兒童像條瀕死的魚,雙眼盯著我,在我面前翕動嘴唇時,我該漠然地走開,還是該掬一捧水,澆在他的身上?
當晚,我與一幫朋友在酒吧,他們喝白酒,我喝檸檬水。都是一樣的白色,這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甚分明。就像我喜歡文藝,卻混跡醫療圈,常常分不清哪是圈內,哪是圈外。在這個很文藝范兒的酒吧里,有位戴草帽的歌手唱起了《雁南飛》,聲嘶音渾,悲愴蒼茫,撞擊著酒吧粗糙的墻壁、昏黃的馬燈。
旁邊的朋友告訴我,他是內蒙古人,在我們這座南方小城的小酒吧里駐唱一年多了。我一邊“哦哦”地應著,一邊往前走去。被取下三塊組織的部位還在隱隱作痛,牽扯著胸口也疼起來。我不算是個愛流淚的女人,平日里走路風風火火,說話呼呼咋咋,跟柔弱的外形相去甚遠。那晚,我心已被揉碎,對著一根開裂的粗大柱子流下了淚。我想把淚水灌進柱子的裂縫里,卻讓它不爭氣地流在了臉上。
四
攝影家、油畫家和詩人回來了,同時對蹲在竹排上的水鳥發出一聲長唳般的尖叫。攝影家馬上打開鏡頭蓋,油畫家和詩人舉起了手機。水鳥倏然展翅撲向水面,他們誰也沒有捕捉到水鳥的影子。紅衣女子微笑了一下,用竹篙撐了一下竹排,竹排又慢慢地往水庫中央蕩去。
詩人問我,似乎你們剛才聊過天,這個女人在竹排上釣魚?
可能吧。
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孤身在這里釣魚的。
釣魚人一定要有什么特征嗎?
她眼里缺乏熱情,真正釣魚的人,你看對方的瞳孔,是像魚鱗一樣閃閃發光的。我釣魚的時候就是這樣,剛學會釣魚的時候,我釣上了一條大魚,但它在掙扎時,把我魚竿的前兩節弄斷了。眼見著魚竿要隨水漂走,我什么也不管不顧,扔下手里的另外幾節,連外套都來不及脫,就跳進了水里。結果,當我撈到這兩節魚竿從水里鉆出來時,才發覺渾身冷得打戰,連眼鏡什么時候被水沖走的都不知道。那時已經是十一月了。
詩人的外套是一件藍白相間的海魂衫。他連連惋惜,說本來應該坐著紅衣女子的竹排,潛到水下,看一看椅子墳的墓碑上,先人的名字可還在。
我問他們,你們在島上看到了什么?
攝影家說,幾座傾圮的舊房子,一地倒伏的枯草,好好的一座島頹廢成這個樣子,我的鏡頭該去哪里尋找落腳點?
攝影家平素喜歡拍攝色調黯淡的舊建筑,殘舊的門樓,墻角的瓦當,街邊的柱礎石、門枕石,他每次看到都像初見一般歡喜不已。有一回,我們另外幾個朋友住在某處深山的仿古民宿,山里的夜雨格外充沛,雨水打在瓦當上,女人們都煩不勝煩一夜無眠。攝影家卻說,像聽了一夜的鋼琴奏鳴曲,可以兩天不睡覺。攝影家認為,有些建筑再頹廢,仍有直擊人心的溫情,通過鏡頭可以讓它重生;而有些建筑一旦頹廢了,就只能繼續地頹廢下去,直到消亡。
攝影家拍了一組死魚頭的照片回來。一圈圈雪白的帶著肌理的頭骨,蒙著一層霧翳的眼睛,灰白色的腐肉,用了黑白色調,似乎在告訴我們,生命只不過是用這些元素組合而成的。他之前拍過一幀照片,公園的人工湖里,一群錦鯉爭相拱著頭,像一大塊紅布要沖出薄灰色的水面。攝影家說,人工湖里人工養殖的魚,是最蠢的,為了一點吃食就恨不能飛起來,攝影家說。死魚頭無法自主命運,與攝影家鏡頭下的舊建筑頗有些相似之處,只能隨時光流逝而流逝。
有必要指出的是,攝影家的手機屏幕上,是油畫家畫的一幅女性裸體。油畫家平常畫的最多的便是女性人體畫,都具有水蜜桃一般光鮮的身體,性與欲卻是淡淡的,幾乎無跡可尋的。但這一幅畫例外。畫中的女人仰躺在床上,長發松垂,遮去了大部分的臉蛋,雙臂緊緊擁著一尾大魚,雙腳踝綰在一起。雖然大魚遮住了女人的胸部和臀部,但整個人體仍有一股甜醉感呼之欲出。那魚的魚鱗異常鮮亮,眼睛炯炯有神,噘著透明的魚唇。那次,攝影家去上海大劇院聽過一場音樂會后,帶著渾身暢流不息的細胞,走進了油畫家的人體畫展。他看過所有的展品后,唯獨對這幅畫念念難忘。攝影家想不通,油畫家怎么可以一會兒將魚畫得這么丑,一會兒又畫得那么美。閑逛了幾天,在回程的動車上,攝影家居然又碰到了油畫家。他裝模作樣地拿出一本新買的莫奈油畫作品集,遞給油畫家,請教了她幾個關于莫奈的問題。其實攝影家根本不懂畫畫,之前也不認識油畫家。
詩人說,我看見島的周圍豎滿長長短短的炊煙,而這島荒蕪人煙,就想落淚。人類發明了農藥,發明了化肥,發明了激素,讓我們可以在酒店里大吃大喝,但是最終我們也要像莊稼一樣,被生化機器一茬一茬地收割掉。土地是詩歌的起源地,我們卻親手斷送了身上裊裊滲出的詩意。
油畫家說,我無法用自己的名字為島命名,因為那里有個船埠頭,我猜,有船在島上停靠,那么它一定已經有名字了。
油畫家說要把剛才拍的照片發到朋友圈里,就是那張把頭靠在攝影家肩頭的照片,證明自己曾經來過。攝影家阻止了她,理由是:那張照片把油畫家拍得老氣了。油畫家仔細看了照片,發覺自己真的變老了很多,難看了很多,驚呼道,我終于明白了,為什么筆下的女人腹部越來越松弛,眼神卻越來越嫵媚。我是不是該結婚了?
攝影家和詩人異口同聲地說,你還年輕著呢!
我又想起了油畫家筆下的魚,趁機問她,那個畫展是什么意思?
油畫家曾經做過一個噩夢。她被拋棄在一個奇異的國度里,一堆的美人魚圍著她,臉蛋全是她熟識的人,閨蜜、同事、鄰居、下半身是長尾巴,紛紛擾擾糾結在一起像麻花一般。她們將帶著魚鱗的大尾巴直接伸進油畫家口中,腥臭味攪得油畫家快要窒息了。為了活下去,油畫家只能奮起反抗,飛快地咬那些尾巴,跟吃雞柳一樣咬得嘎嘣脆。可這些人魚的尾巴長不完,滅了還有。油畫家把各種色彩不一的畫筆當飛鏢,插進她們身體上的軟肋處,卻總也擊退不了。她們受傷的部位飛快自愈,根本不是油畫家熟悉的那些閨蜜同事鄰居,分明就是一群妖魔。在即將被這種窒息感湮沒時,油畫家不知怎的竟然意識到這只是個夢,硬逼著自己醒來,然后打開燈,畫起了魚。一天一幅,畫了一個月,油畫家才真正從這場噩夢中醒來。
油畫家說完這個夢,喟然長嘆一聲說,今天去了這個島上,恐怕又要掉進夢魘里了,不知何時能醒來、醒來后又要畫些什么。她頭暈得不行,估計是暈車了,便提出要自己開車。攝影家跟她換了位置,仍舊與她相鄰而坐。
攝影家和詩人爭著從易經或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油畫家的夢境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們還談論到,為什么人會越老越難看?那個掉進女兒堆里的男子何以會說,女孩兒老了,更變得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呢?活魚的眼睛,其實是很漂亮純凈的。
我說,大部分的人都是越老越固執,相由心生嘛,外貌也就相應地變得難看了。
油畫家不疾不徐地打著方向盤,問我,你還沒告訴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只是一個寫故事的人。
油畫家說晚上要請我們吃飯。我說,想吃一條從水庫里撈上來的大魚,做剁椒魚頭或者豆腐燉魚頭,都挺好。
攝影家說,我們到黃昏,才可以吃上一條清晨釣來的魚。
油畫家沒有回答,一直、一直地朝著水庫開過去。真不知道是那天的霧霾實在太大了,還是她因為暈車而腦袋迷糊了。遠處,一列動車呼嘯著,穿過山洞,仿佛一根線快速穿過針孔。時光在漸漸縮小。我們都沉默了。
詩人說,假如大水漫過紅杉林,我們也會像那些魚頭一樣,整齊地排列在岸邊。
林漱硯,本名林曉秋,1979年生。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芙蓉》《青年文學》《江南》《西湖》等刊物。有小說曾被《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轉載。
責任編輯 馮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