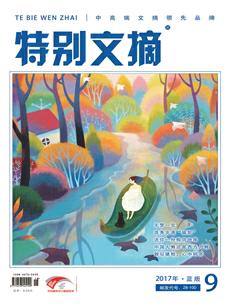“小確幸”與“小確喪”
陳魯民
“小確幸”,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發(fā)明的一個詞,意思是指“微小而確定的幸福”。譬如自己上街購物,與朋友小聚,冬日賞雪,午后品茗,完成工作的休息等,都是微小而確定的幸福。 “小確幸”一詞,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后,曾很受歡迎,風靡一時,成了許多年輕人追捧的對象。因為,它追求的是一種現(xiàn)世的安穩(wěn),營造知足常樂的氛圍,勸告人們要珍惜眼前的幸福,很合乎喝慣了“歲月靜好”雞湯的國人胃口。
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風云突變,乾坤顛倒,“小確幸”忽然不吃香了,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小確喪”。這兩個詞雖只是一字之差,但意思風格卻天壤之別,一正一反,一陽一陰,一樂一悲。“小確喪”們最愛說的話是“我想我差不多是條廢咸魚了”“每天都頹廢到憂傷”;最愛唱的歌是《感覺身體被掏空》;最愛擺的姿勢是“葛優(yōu)癱”;最標配的形象就是電影《本命年》里梁天那段自白:“活著怎么就那么沒勁,上班沒勁,不上班也沒勁;吃飯沒勁,不吃飯也沒勁;搞對象沒勁,不搞對象也沒勁。怎么就那么沒勁!”概而言之,這是一種不想工作、漫無目的、情緒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地活下去的頹廢心態(tài)。
不久前,上海一個繁華的商業(yè)中心悄然開出一家名叫“喪茶”的奶茶店。黑色店面陰冷沉郁,服務員無精打采。貼在墻上的飲品單,更是讓人心頭發(fā)涼:“你的人生就是個烏龍瑪奇朵”“加班不止加薪無望綠茶”“加油,你是最胖的紅茶拿鐵”,還有“沒希望酸奶”“負能量奶茶”……居然生意紅火,一些年輕人排起百米長隊,甚至花錢雇人排隊,只為買到一杯“喪茶”。這也是“小確喪”文化的一個典型標本。
為什么會從“小確幸”走紅變成“小確喪”當?shù)溃棵襟w和專家們有很多解讀,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這是對鋪天蓋地雞湯文化的一種逆反心理,是以自嘲與反諷來排解壓力的方式,是青年人好奇求變的一種思維反映;二是認為這是對前途無望的一種抱怨,是對生活無奈的一種哀嘆,是無所作為消極人生觀的反映。不管是哪種情況,“小確喪”的基本格調(diào)都是灰色的,頹廢的,哀傷的,負能量的。如果屬于第一種情況,倒還問題不大,假以時日,靜觀其變,青年人自己就會調(diào)整出來,重新振作精神,走上正軌;如果屬于第二種情況,青年人對“喪文化”信以為真,受“小確喪”意識蠱惑影響,不僅會變成心理問題,發(fā)生信仰危機,扭曲自己的人生之路,而且再互相影響,發(fā)酵放大,形成輿論氛圍,極有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當然,“小確喪”的異軍突起,還主要是一二線城市少數(shù)青年人之所為,既不能大驚小怪,當成什么可怕怪物,洪水猛獸,也不能掉以輕心,放任自流。還是要引起重視,加強輿論引導,思想教育,營造積極向上的社會氛圍,最主要的是要深化改革,革除積弊,給青年人提供更多公平競爭、施展才華的機會,讓他們用創(chuàng)業(yè)的激情、奮斗的汗水,來沖刷頹廢、灰暗、惰性的泥垢,品嘗生活的“小確幸”和成功的“大確幸”,那些無病呻吟暮氣沉沉的“小確喪”,自然也就沒了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