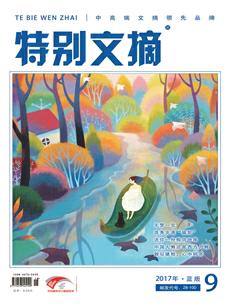裹足婦女逃命難
呼延云
纏足的“始作俑者”,現在大多數人認為是南唐后主李煜,不過,也有人認為,這口黑鍋應該由南齊廢帝蕭寶卷來背,因為《南史·齊東昏侯紀》有記:“(蕭寶卷)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李后主也好,蕭寶卷也罷,都屬昏君中的昏君,照理說沒有什么值得后世效仿之處,偏偏他們“發明”出纏足這么個摧殘人的玩意兒,居然能貽害千年,也實在是不可思議。
面對纏足陋習,政府并非“不作為”。有清一代,統治階層曾經多次下達禁令。順治初年,孝莊皇太后明令:不許纏足女子進宮,否則斬首;康熙三年朝廷下旨:“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家長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于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力度這么大,責罰這么狠,依然禁不住。
清代學者丁柔克在筆記《柳弧》一書中曾經記載,當時纏足陋習,盛行于北方,而南方部分地區則較少:“甘肅某縣,每年四月二十四日婦女做小腳會。屆時婦女淡妝濃抹坐于門首,皆蹺一腳于膝,以供游人賞鑒。或評其雙弓窄窄,或稱其兩瓣尖尖。最小者則洋洋自得,而其門如市。故其縣無大腳,間有稍大者,其時唯閉門飲泣,合家垂頭喪氣,真陋習也。江南天長、六合等縣,則婦女盡皆大腳。”
和平時期的洋洋自得和垂頭喪氣,到了戰亂就難免調換了位置。清末學者況周頤在筆記《眉廬叢話》中寫道: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南北各省兵禍頻仍、戰火連天,當時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逃難者中的女性“多大足婦人,而裹足者卒鮮”。裹腳的婦女因為跑不動,大多只能在家中坐以待斃,偶爾有豁出去跟家人一起出逃的,往往又成為累贅,遇到危急關頭,為了不丟下她一個,剩下的親屬都要放慢逃亡速度,“又或子為母累,夫為妻累,父母為兒女累,兄弟為姊妹累,駢首就戮,相及于難者指不勝屈……夫自古至今,婦女死于兵者,莫可殫述,而皆未有知其死之多累于裹足者。”
按理說,裹腳還是不裹腳,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應該能讓人有所醒悟了吧?然而并不,直到光緒二十七年,慈禧太后還得專門頒下懿旨:“漢人婦女率多纏足,行之已久,有傷造物之和,嗣后縉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但是這一陋習的徹底消亡,還是到新中國成立以后,隨著暴風驟雨般的種種除舊布新,才成為歷史。魯迅先生有云,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要付出流血的代價,以感慨在中國實施改革之難,而一部纏足史足以證明,改革之難有時未必是統治階層刻意阻撓造成的,假如桌子腿被鐵釘牢牢固定在地上,那想搬動,才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