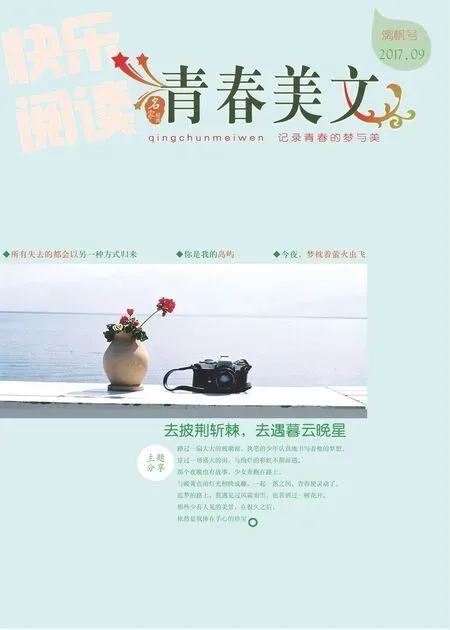短發青蔥的年華
■ 簡 潔
短發青蔥的年華
■ 簡 潔

我把留了10年的長發剪短了,從長卷發剪成long bob,再從long bob剪成短發,越剪越短,越剪越上癮。自覺并沒有多大的事,但剪了兩三個月后,還是被認識的人看見后驚呼:“你怎么把頭發剪這么短了?”我才發現不管什么時候,剪短發仍然是一件有儀式感的事。
我最初把短發和儀式感聯系在一起,還是年少時看郁秀寫的《花季·雨季》,里面提到林青霞失戀之后去剪短發,后來,這便成為失戀的一種儀式——斬斷情絲的新開始。那時,我連林青霞的電影都沒看過幾部,就莫名覺得這種治療傷心的方法帥氣極了。
后來我才知道,削發明志其實并不是新鮮事,大抵都是想以全新的面貌示人,以表重新開始的決心。因為這種懵懂的誤解,六年級時,我剪過一次男式短發,直接原因是我爸給我剪頭發時一刀剪斜了,間接原因是當時期中考試沒考好,總覺得要做點什么來明一下志。兩種情緒交疊起來,我便豪情萬丈地跑去理發店,一坐下來,就沖剪發的阿姨喊了一聲:“三七開。”
后來那個場景,在我的腦海里無數次重放。我高估了家門口的理發阿姨連村口Tony都不如的手藝,也高估了我臉型的適配度,直接后果就是,第二天,我不得不在一點都不冷的天氣里,戴了一頂手邊唯一能找到的毛線帽子去上學。我幾乎立刻能從大家的反應里,得出“剪掉的長發等于失去的顏值”的結論,只需要一剪刀男孩們就能從以往的討好轉變為嘲笑。剪發對失戀有沒有治愈效果,我不知道,對收心學習的效果卻是極佳的。照鏡子和照相變成了我最討厭的事,每天煩躁地確認完頭發的長度之后,我就迅速扎進作業里,一直到小學畢業。頭發在我上初一的時候恢復了可以扎起來的長度,但每次考試之前,我都會去剪一次頭發——在安全的長度以內。
至此,剪頭發成了我的一個小小的儀式,梁詠琪的《短發》,我是當勵志歌曲來聽的,歌里唱我“已剪短我的發,剪斷了牽掛。”于是雜事不念,一往無前。對于我來說,好像已經剪斷了這一行為最后一絲旖旎的氣息。
上大學后,我不再有這個習慣。頭發拉直、弄卷都隨理發師去折騰,唯有比畫剪的長短時,心頭會陡然一凜,心生戒備,反復交代“不要剪太短”。于是,一頭長卷發留過了我20歲之后大多數的年月。
今年剪發時,我卻躍躍欲試。此時,我已找到稱心的發型師,在剪之前拿了幾十張明星照和他研究、對比,各種手段齊上,就算此時我再叫一聲三七開,也不會有少時那一剪刀下去的悲劇了。這大概是一種精心準備的淡定與懵懂無知的意氣之間的區別吧。但也許正要有那一口意氣,剪短發才算得上是個儀式。
最近在看日劇《我不是結不了婚,只是不想》,初戀組男主櫻井失戀后,和籃球隊的人在小飯館里大唱失戀情歌,多年以后大家還記得這件丟臉的事,可唯獨女主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一刻我突然想,如果男女主角當中有一個失戀之后去剪短發或剃了頭,大概就能知道彼此的心意,不會錯過了吧。
也許當時我有點會錯意了,剪短了在帥氣之外,其實有一點倔強地強撐,向所有人或者是向某一個人傳遞了自己不愿承認的信息:你看,因為你,我過得不太好。這是最后敢于讓自己狼狽的一點勇氣。
當然,生活不會是這樣巧合的電視劇,但無論如何都不是一件壞事,最后無可挽回地確認了,才有向前走的決心,這大概就是儀式的意義,不管目的何為。
(摘自《愛格·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