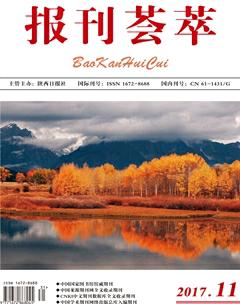曹禺劇作《家》與巴金同名小說異同解讀
摘 要:曹禺和巴金這兩位作家都創作過名為《家》的小說,本文主要針對同名卻有著不一樣的文體的小說進行剖析,將兩者進行對比解讀,從而發現兩人創作的《家》在主旨內容、情節構造、審美核心和藝術特質的異同。本文從作者和作品內容出發,深入解讀作品,從而解讀兩者異同。
關鍵詞:切入點;原著藝術;改編藝術;異同
一、切入點之大“家”和小“家”
在巴金先生筆下,我們了解到這里的“家”是一個大家族,而且是一個封建性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是以專制與腐朽的大家長“高老太爺”為核心的,小說共70多個人物,有愚昧墮落的五老爺克定、貪婪奸詐的四老爺克安等人作為與“高老太爺”統一戰線的封建統治階級,又有站在反封建與專制一方的丫頭鳴鳳,勇于用自己的性命作斗爭;以及溫柔老實、被封建禮教迫害而默默忍受一切悲痛折磨的梅表姐,還有柔和厚道的瑞玨等等。代表先進知識分子,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向往自由與追求解放的覺慧、覺民等先進青年也是及其重要的人物。作者將這些人物穿插進一個較大的藝術結構中,由人物之間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情感糾紛、離合悲歡等內容來表達人物內心的世界,透過分析種種性格的不同,來揭示人物的命運異同。從“家”的描述中,我們在裝飾和擺設上得知,等級制度觀念的根深蒂固,繁瑣的禮數與宏大的景況,我們在《紅樓夢》中可以看到相類似的場面,巴金受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影響,將結構處理中“家即社會”這一部分進行發揮,由“家”來映襯社會,顯示時代特征,在高家的公館中,主人與奴仆間、新一代人和老一代人間、夫權統治之下與婦女追求自由的爭斗此起彼伏,權力的金字塔結構十分突出。而在曹禺改編的劇本“家”之中,我們知道曹禺先生只是選取了其中的典型人物,在他的小“家”之中,其典型人物主要是:覺新、瑞玨和梅,他們三個是中心人物,劇本中以環境來襯托其中的詩意美,青春的反抗這一主題得到彰顯,也有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的意識的申訴。
二、原著藝術
巴金先生的《家》一直是他情感的深刻寫照,他的寫作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他由自己對生活的觀察寫出了自己的感受,在《家》中所表現出來的所有情緒,都是他在自己所處的封建的家庭環境下的情緒發泄,他由高老太爺這個封建大家長為入手點,帶領大家認識舊社會的黑暗與腐朽,他是這個大家庭中所有的主宰,他可以輕易通過馮樂山葬送奴仆鳴鳳的生命,在他手里,任何人都可以輕易被他支配,封建社會的歷史在他手里得以彰顯。以他為主要人物,還有更多在他的理念之下,又能培育出來的一代又一代新的封建統治者,與此同時,又不乏反抗他的人。巴金先生的《家》在審美上的藝術性來講,屬于青春性的文學創作,對青年形象的解讀,讓我們能引起深刻的反思,在當時的背景之下,我們知道,封建的愚昧與腐朽,加上當權統治者的暴虐,我們根本沒辦法反抗,但是還有人去斗爭,活出自己鮮活的生命,在強有力的筆墨濃染下,巴金先生寫出了自己的情緒,同時我們也深刻感知到情感的基調是傾吐式的。曹禺先生作為巴金先生的好友,在保留巴金先生原有情緒不變的基礎上,加上了自己在生活中的深刻體悟,抒發了情感的審美,同時也對都這有引導作用,從藝術化的角度而言,文學的陌生化,更多幫助我們理解文本,剖析這一情感,提高審美趣味。
三、改編藝術
曹禺先生將巴金先生的小說改編為劇本,是否遵循了巴金先生的創作理念,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話題。有時,我們嘗試新的事物,往往也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曹禺先生勇于改變,將大家喜歡的小說改編成劇本,在他看來,自己感受最深的場面和景況會引起他的共鳴,無論是主旨內容方面,還是情節構造方面更都是曹禺先生融合自己的生活感悟,來進行改編的,因為他的理念就是:原封不動地生搬硬套原著的語言文字是改編不出完美的作品來的,沒有自己的體會,是改編不好的。曹禺先生的《家》中,重心相對有所轉移,不僅從覺慧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知,而且劇本更多地側重于對覺新、瑞玨、梅表姐三人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的呈現。曹禺先生的著作可以說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與閱歷來進行改編,在開頭與人物形象、情節構造上,我們都可以得知其劇本構思中,人物情感的跌宕起伏占據了較大分量。覺慧這一形象在劇本中出現時,沒有朋友出場,這對于別的情況而言,說明作者對有些日常生活狀況也有不清楚的地方。至于覺新、瑞玨和梅表姐這三個人物,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錯綜復雜的關系是一個焦點性問題,覺新這一形象,在改編者筆下,更多賦予了關懷和同情,瑞玨的性格中則更多的是正直與柔和,在與高家人的接觸中,她能與高家姐妹們和睦相處,而梅小姐則天生高冷,很難與高家的姐妹們融洽相處,曹禺先生在改編劇本的過程中,由劇本的情節構造和結構塑造人物來入手,覺慧與鳴鳳兩個人的美好愛情,在劇本里,改編者充滿熱情地去修飾與描繪,鳴鳳死后,覺慧才真正發覺這封建社會的邪惡與墮落。語言的變動還是較為明顯的,劇本而言,都是戲劇化的語言,第一人稱的形式為多,對話與心理描寫更多的是在劇本中體現。而在巴金先生的小說《家》中,第三人稱的敘述較為豐富,言簡意賅,并且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能夠靈活自由地反映客觀內容,展示人物廣闊的活動范圍,相較于改編版,新的形式更多地增添給了人們理解作品、感悟經典的途徑,更多的我們知道曹禺先生是在融合自己的理解上形成的對小說《家》的整體解讀和改編。
參考文獻:
[1]徐敏.對《家》的解讀——巴金《家》與曹禺《家》之比較[J].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2015(11).
[2]唐衍歡.教學大戲——話劇《家》的舞臺分析[J].戲劇之家.2016(20):48.
[3]李澤文.悲劇婢女形象對比—以《家》中的鳴鳳和《雷雨》中四鳳為例[J].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7(1):32-33.
作者簡介:
顧新苗(1976.6—),女,籍貫山東文登,研究生,單位:湖南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教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