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解放日報社經歷的審干與搶救運動
我喜歡讀毛澤東主席的書。前年偶然購買到一部八卷本的 《毛澤東文選》,非常高興,因為其中有許多以前沒有出版與發表過的文稿和談話稿。認真地讀下去,想不到其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延安審干與肅反。例如,《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的“整風、審干、鋤奸問題”部分中有這樣的話:
“審干中搞錯了許多人,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難過,我們也很難過。”“對搞錯的同志,應該向他們賠不是,首先我在這個大會上向他們賠不是。在哪個地方搞錯了,就在哪個地方賠不是。為什么搞錯了呢?應該是少而精,因為特務本來是少少的,方法應該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們搞的卻是多而粗,錯誤就是在這個地方。”“所以關于特務,以前的估計是‘瞎子摸魚,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現在知道了只是極少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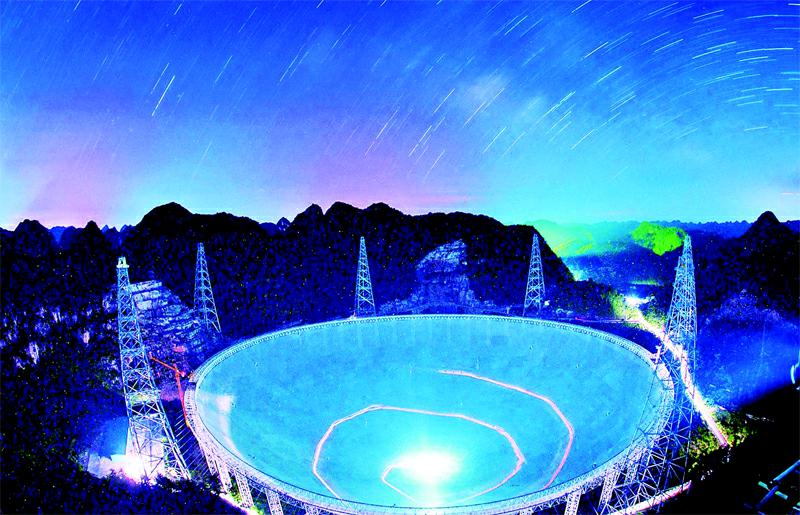
(一)
讀到這里,我想起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還講過審干與肅反問題。在哪篇文里呢?我在 《時局問題及其他》 一文的“審查干部問題”里找到了,他是這樣說的:
“上次我在這里講過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沒有聽到,我再講一下,”“前年和去年我們進行了審查干部的工作,在這個工作中,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犯了許多錯誤。”“拿件數來說就很多,黨校就犯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我是黨校的校長。整個延安也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也是我。”毛澤東承認犯了錯誤,并且承擔責任,特別是還要賠禮道歉,這很了不起。毛澤東接著又說,“在審查干部中搞錯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務、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黨派分子,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們對這些人要和氣,和他們團結,他們自動講出的也好,被逼出來的也好,只要講出來,我們就歡迎,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毛澤東講了工作成績,他不因為有錯誤,而否定成績,特別又強調要全面與正確認識審干與肅反,強調團結。在這里,毛澤東又說了殺人問題,他說:“口頭講一個不殺,如果殺了兩個,那豈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確我們是一個也沒有殺。”讀毛澤東這段話,我相信延安時期審干與肅反沒有殺人,近年有人說殺過幾個人,這是誤會。大家知道作家王實味被錯殺了,那是解放戰爭時期康生批準殺的,當時毛澤東不知道,事后提出過批評。
毛澤東“上次”在中央黨校講過一次審干與肅反問題,文集里找不到,不知是因為文集是按“精選原則”編的沒有選入,還是“上次”講話根本沒有整理記錄稿。那時毛澤東的講話有許多都沒有整理或發表。
讀毛澤東上述關于審干與肅反的講話,我感到又受一次深刻的教育。首先,是他講得實事求是,“是就是”,“非就非”,講成績,也講錯誤。其次,是承擔責任,不往執行人身上推,也不強調犯錯誤的客觀原因。
還有,是他找出犯錯誤的根源是“瞎子摸魚”,這是很有分量的說法,瞎子入水本是危險事,你還摸什么魚呢?最重要的,是毛澤東總結了經驗,他說:“在審干中間,提出一個不殺,大都不抓,九條方針 (按:即“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干與廣大群眾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干部,教育群眾”) 并不是一開始就發明出來的,而是經過幾個月情況的反映,逐漸積累才搞出來的。廢止肉刑,不輕信口供,特別是再加上九條方針、一個不殺、大都不抓,亂就出不來了。”
關于 《在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一個不殺大都不抓》 的指示,是1943年12月27日毛澤東、康生致華中局等電報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有的文件匯編中把康生的署名刪掉了。
(二)
現在讀毛澤東關于審干與肅反的論著,歷歷往事,浮現腦際。我是在延安解放日報社參加整風的,我被審查過,也被“搶救”過。
1942—1944年在 《解放日報》 任過兩年總編輯的陸定一 (1942年8月下旬至1944年大約也是8月下旬),在1981年 《解放日報》 創刊40周年座談會上“談 《解放日報》 改版”(發表在當年的《新聞研究》 上) 時,說:“還有一個問題值得講一講,就是‘搶救運動。‘搶救運動在報社也搞了,后來停下來。很多機關把青年打得很慘,《解放日報》 損失較輕一些。”
整頓“三風”的報告,毛澤東1942年2月1日與2月8日分別向“七大”代表、高級干部與業務干部1000人或800人作報告,由康生分別于2月21日和3月7日向2200多干部與3000多干部作傳達。4月3日中宣部發出 《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和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以后,18日又由康生向中央直屬與軍委直屬機關在八路軍大禮堂舉行整風學習動員大會,向2000余人作布置。
陳清泉所著 《陸定一傳》 中說:“《解放日報》學習西北公學,召開群眾大會,由博古報告形勢,號召有問題的人上臺坦白。臺下分小組‘促,搞得很熱鬧,沒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個人上臺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務。”
(三)
事實是這樣的,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出的整風指示,是公開發報刊上的,是思想革命,是清除黨內封建思想、資產階級思想與小資產思想。1943年4月3日中央發出的繼續整風的指示,沒有公開發表,一般黨員都看不到,是組織革命,清除混進黨內的特務內奸分子。
1943年7月15日,因為有敵情,康生在中央直屬機關大會上作了 《搶救失足者》 的報告,這個報告很長,現只摘錄少許主要的部分。
同志們!
今天的大會,是緊急時期的會議,是軍事動員時期的會議。因為我們這個會議是正當著國民黨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的三個集團軍的主力,以暫二十五師、六十一師、二十八師、五十三師、新三十七師、第八師、一百六十五師、新騎二師、新二十七師、一百六十七師、七十八師、新二十四師、新二十六師、二百九十一師,及七個保安團、一個炮兵旅、一個重炮營作為第一線的兵力,將我們邊區南線緊緊包圍,待令出擊之時來開會的。是正當著日寇第五縱隊的國特機關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而國民黨中央社向全國全世界廣播之時來開會的;是正當著國民黨為了取消共產黨,取消邊區,不惜將第一軍、第九十軍等河防部隊調離河防,背向日本,面向邊區,內戰危險有一觸即發之勢,我們的會議正是在這樣一個時局中間來開的。如果一個普通的政黨,普通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是會嚇倒,如果一個意志薄弱的人,看到國民黨撤退河防,發動內戰,會發生悲觀失望的。但我們卻還是照常開會,更加積極地工作、學習,整頓三風,發展生產,審查干部。因為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是八路軍,我們是邊區人民,我們堅信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無論國民黨想如何挑動內戰,我們的黨和軍隊都是有力量打破和粉碎他們這種禍國殃民的陰謀的。endprint
現在邊區的軍隊、邊區的人民都動員起來了。因此,我們延安各機關學校更要加緊起來審查干部,鞏固組織,清除內奸,這是我們目前急不可緩的任務。我們不要忘掉一九四二年五月時局緊張之時,于炳然特務已準備好人,準備好槍,企圖配合國民黨進攻邊區的軍隊來破壞我們,雖然于炳然這個陰謀被我們破獲了,但是這個教訓我們是不應忘記的。
在三個月以前,我們在此地曾告訴過大家,日寇和國民黨訓練了大批偵探奸細來破壞我們,國民黨特務分子、破壞分子他們不去破壞敵人,而是與敵探一起來破壞共產黨、八路軍、陜甘寧邊區和華中、華北各個抗日根據地。他們不是去拯救被日寇毒害的中國青年,而是將許多有為的中國青年,拉到特務的罪惡泥坑中去為日寇的第五縱隊服務。因此從四月十日起,我黨中央又一次的以寬大政策號召這些青年們起來改過自新,脫離特務陷阱。三個月來,經過所有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人的努力,促使許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黨的號召,起來控訴日寇與國民黨殺害青年的罪惡,到今天為止,已經有四百五十人向黨坦白悔過了。不管他們其中尚有許多人未徹底覺悟,但我們應該歡迎他們這種進步,因為他們已經給了我們一個可能,使我們可能引導他們跳出罪惡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國民黨與共產黨兩種不同的政策,擺在所有失足者的面前,何去?何從?這是很明顯的。因此四百五十個人向黨自新改過,正是這兩種政策對照的結果,黨的寬大政策勝利的結果。但是不是所有失足的人,都明白了這個道理呢?不,還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沒有向黨坦白,他們除了一部分少數甘心為敵人作第五縱隊的人們外,其中大多數是在他們的腦子中尚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他們過去想不通,我們尚有時間等待,但是現在是軍事時期,我們應該趕快地促使他們覺悟,今天開會的重要意義就在這里。
最后康生說:我們的寬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是有鎮壓政策的另一方面的。因此,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分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為了堅決鎮壓特務,我們又有鋼鐵意志。如果他們絕對堅決,不愿改悔,甘為敵人第五縱隊,那我們必須以嚴厲辦法堅決鎮壓之。
我們希望未坦白的人,對于國民黨的問題,對于共產黨的問題,對于寬大政策與鎮壓政策的問題,都要仔細地想一想。在這里我們送給他們一副對聯,“懸崖勒馬,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康生當時的職務是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總學委副主任。總學委主任是毛澤東,康生可以說是黨的第二把手,康生作報告由總學委委員彭英主持,會上還有中直機關的幾名“特務”上臺作坦白報告,再次宣布讓各機關回去依照做。
(四)
這時,報社沒有人坦白交代自己是特務分子,怎么學著做呢?報社被社會部抓去四個特嫌,他們是李銳、黃操良、繆海棱與S,S在社會部坦白自己是特務,S的妻子、在某文工團擔任支部書記的L也在社會部坦白了。于是,把S要回來,作坦白報告,這是清涼山第一次坦白大會,這次坦白大會上,沒有別的人坦白,坦白大會是晚上在清涼山中央出版局處邊的小坪壩上開的,陳清泉說的“《解放日報》 學習西北公學,召開群眾大會……有六七個人在臺上坦白交代……”,是第二次群眾大會。第一次大會說沒有搶救出特務,康生發脾氣,說:“你們清涼山是特務集中的地方,為什么搶救不出來特務?”于是編委會(也即是整風學習領導委員會)研究,讓陳坦秘書長去西北公學學,回來搶救出三四個特務,就開第二次群眾大會,就有了陳清泉說的:“由博古報告形勢,號召有問題的人上臺坦白,臺下分小組‘促,搞得很熱鬧,沒有想到居然也有六七個人上臺交代自己是特務。”博古報告,就是按康生講的話講的。上臺坦白有四人,新華社一女二男共三人,新華社副社長陳光寒積極,搶救的特務多。解放日報有一個女的,中央出版局秘書長許之禎穩當,沒搶救出一個,不是陳清泉說的“六七個”,這些都是事前準備好的,不存在“沒有想到”的情況,這次群眾大會,在博古報告形勢以后,是陸定一講話 (這一點,《傳》 中沒有寫)。號召“有問題的人上臺坦白”。陸定一講話簡單有力,氣魄也大,他說坦白交代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有問題不坦白交代是不行的,這是“關系你們一代青年的大事”。當時我心里想:一代青年是特務分子、壞分子與有問題的,這抗日戰爭與中國革命事業可怎么搞?
這兩次群眾大會,是由博古領導的駐在清涼山的解放日報社、新華社、中央出版局等單位的搶救動員大會,這幾個單位健在的人還很多,許多人記憶得很清楚。
在群眾大會上“坦白交代”的女士,都說特務“強奸”了她的靈魂,也“強奸”了她的肉體,還有人說了具體的經過,以致后來被作為笑料。“搶救運動”時,各機關封閉,外出采購與調查材料的人出入憑證、夫婦親友不準來往。各種晚會與舞會通通停辦,報社一般窯洞鴉雀無聲,積極分子的窯內鶯歌燕語與肉味棗香,生活不正常,以致氣得副總編輯余光生在編輯部會議上大聲批評:×××女士,一天也離不開男人,這樣亂搞是不允許的。余光生在清涼山全報社或報社編輯部,搶救大會上都沒有講過話。
至于陸定一說的報社“搶救運動損失較輕一些”,則是個人的看法、說法,我只說些事實。有一天,在文津俱樂部碰見李銳,我說,溫濟澤在 《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的自述》 (以下簡稱 《自述》)里說 《解放日報》 編輯部被搶救的人有百分之七十左右,你說報社搶救過多少人呢?他說,你說呢?我說總有二分之一,編輯人員搶救得多,行政人員搶救得少。他說,1943年春天我就被社會部抓走了,后來的情況我不清楚,社會部抓我,博古不同意。他向康生提過意見,沒有用。
某傳記中說:“報社被逮捕12人。”我打聽不到第五個人是誰。這四個被捕的有一人的家“破”了,有一個坦白的人的家破了。有一個被批的人要結婚,經過九曲十八彎,經博古幫助才結成。某傳記中說,“報社總務科長是河南人,思想不通,竟刎頸自殺”,“終于死了”。報社總務處只二十來人,我在報社五年多,還在行政處宿舍住過,至今打聽不到行政處總務科或別的科有河南人。我記得總務科長是葵孝父,安徽省人,“文革”后自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崗位離休,如真的有人自殺,損失又有人亡一項了,被搶救搞壞身體的很有一些。某傳記中說的那個被搶救以后坦白的“姓鄧的青年”,1946年與國民黨和談時請假去重慶,在那里某報社工作,不要黨籍也不回來了,這位“姓鄧的青年”是鄧友新。我記得還有記者田海燕與資料員林堅夫婦,嚇得逃跑到重慶,向董必武報告:我不是特務,延安 《解放日報》 要整我,我不干,偷跑出來了,我要求在重慶地下黨領導下干革命。新中國成立后,田海燕與林堅才在武漢市重新入黨。endprint
報社出報,新華社要發稿,不能像一般機關學校整天搞運動,只是半天搞運動,開會少,談話多,魯迅藝術學院的張魯和徐之不約而同地被逼無奈交代我是他們復興社的領導人。L找我談話,他的警衛員拿出盒子槍,手扣扳機,L站起身問我是不是特務,我說不是,我說我能找到證明人。L向我走一步,警衛員持槍前進一步,把我逼到窯角,L說你再不坦白,我送你去社會部。我沒辦法,寫個條子裝在口袋里,準備送我去社會部以前交給博古,說我不是特務,請他救命。我認為博古實事求是。
在副刊部,最早向大家說L沖動的是溫濟澤,他說:老艾 (思奇) 在整風學委會上說黎辛的問題是不是應當兩點論,因為有人說他有問題,也有人說他沒有問題。L聽了立刻拍桌子,說:“你老艾是什么人,包庇特務分子,也要審查你,我撤銷你學委會委員的職務。”學委會主任博古沒有說話,副刊部仍由艾思奇領導運動。溫濟澤還說:副刊部協助老艾審干的林默涵與他也受到批評;特別是在L與余光生參加的支部大會上,還揭發他與溫崇信的關系。他在 《自述》 中,只說在余光生主持的支部大會 (黎按:只是少數積極分子參加的所謂支部大會) 上,有一個“坦白”自己是“特務”的人,大著嗓門說:“我要揭發溫濟澤,他有個叔叔叫溫崇信,是西安附近寶雞地區的國民黨專員兼少將保安司令……把他的侄子派到延安來搞破壞……”“我一聽就火冒三丈……我厲聲地反駁說,‘我1938年初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到中央組織部談清楚了我在白區工作的經歷和社會關系”。當場,老艾為溫濟澤說了好話,“支部會就草草結束了”。溫崇信不僅是寶雞專區的專員,還是個不大不小的CC分子,北平市解放時,他任國民黨北平市政府的秘書長,北京雖然是和平解放的,他也畏罪逃往臺灣去了。溫崇信的獨生女溫聯琛在揚州中學讀書,受江上青老師的影響,堅決要去延安參加革命。曾經從家里逃跑,溫崇信不能不給她買飛機票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報考抗大,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她把溫崇信的情況與社會關系都說清楚了,辦事處伍云甫處長介紹溫聯琛認識將與她同乘一輛軍車去延安的陳學昭博士,陳學昭說伍處長“要我一路照顧她”。可是,“搶救運動”時,卻全校批斗她,還不征求她的意見,給她作了特務分子的結論 (1946年,她調中央黨校工作時,中組部為她改正了結論)。假如揭發溫濟澤的人,知道溫濟澤從蘇州反省院出來,是溫崇信保釋的,出獄后到延安以前又是住在溫崇信家里的,那次支部大會是不是可能不會“草草結束”呢?這是溫聯琛告訴我的,她還健在。
某傳記中還說:“解放日報就分別召開了大型和小型平反大會。”這與事實不符。中央與毛澤東都說過在什么場合搞錯的在什么場合平反,這不可能做到,比如在中直搶救會搞錯的,怎么召開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報告的大會平反呢?解放日報沒有開過平反會。
《自述》 中特別說: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這個決定對敵情作了過分的估計,開頭就說,“特務之多原不足怪”。接著說國民黨有個“龐大的特務系統”,日本法西斯“利用中國人做特務,其數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務是一個世界性群眾性的問題”。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 《搶救失足者》 的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的“搶救運動”。溫濟澤說的繼續整風的決定是4月3日發出的,但是他只說了“整風不但是糾正干部錯誤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溫濟澤引用的那些話,出自1943年8月15日中央發出的 《中共中央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康生作 《搶救失足者》 的報告是7月15日,在中央發出審干決定之前一個月。
解放日報社審查干部從1943年春天開始,艾思奇在副刊部提出:“我們審查干部怎么開始?第一個審查誰?”陳企霞首先說:“我的歷史復雜,先審查我。”陳企霞被國民黨逮捕兩次,英勇機智,沒有問題。他自己交代抗日戰爭初期與托洛茨基派翁濤去浙江組織過抗日游擊隊未成,延安沒有適當的人證明他與翁濤的關系,只好作為一個問題保留起來,以后再議。
審查下一個人時,老艾說,陳企霞的問題費了很多時間,下一個我們審查個歷史簡單的人。誰報名?陳學昭與我同時報名,老艾說先審查陳學昭,再審查我。審查陳學昭,很快結束了,結論是歷史清楚。
審查我,前兩天沒事,第三天溫濟澤提出疑問:黎辛在河南省參加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是什么組織?這時康生揪出來的大特務張克勤 (聽說新中國成立后改正了) 誣蔑甘肅、河南、四川等有的共產黨是假黨,是特務組織。黨的外圍組織民先當然也是假的了。溫濟澤在 《自述》 里,說張克勤造謠說,四川、河南等省的黨組織并不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而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它們“打著紅旗反紅旗”,就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吸收青年入黨,其實是把青年騙去當特務。
我媽媽從河南省農村寄來100元法幣,我按規矩去邊區銀行找王坦 (黨員) 兌換為邊幣使用。溫濟澤在會上提出這特務經費是誰寄來的?并兩次向王坦調查,新中國成立后王坦仍在銀行工作,常把此事當作笑料談。我不承認是特務,批斗到“搶救運動”結束,又侮我為“運動的絆腳石”,比特務還壞,因為我阻擋副刊部搶救別的特務。
副刊部沒有揪出一個特務,是報社最不爭氣的單位,怎么辦?搶救結束了,副刊部繼續搞“搶救”,總編與副總編來,從別的編輯組調來積極分子加強火力,拍桌子打凳子,兇過搶救,斗爭的對象是舒群與白朗。舒群1936年在青島被國民黨逮捕過,按規定應當審查,這是歷史問題,不是特務性質。舒群倔強,不承認是叛徒,罵他是“文痞”,他也拍臺高喊:“我抗議!”幫助艾思奇審查過干部的林默涵在批斗我時看過全部材料,認為沒有問題,不發言了,批斗舒群沒有材料,他也不發言了,副刊部的積極分子,只剩下溫濟澤一人了,下午開會,溫濟澤與外部門的積極分子發言,晚間被派去監視舒群,住在舒群的窯洞里。白朗沒有什么問題,她的丈夫羅烽是文抗的負責人,在偽滿洲國被日本侵略軍逮捕過,保釋出獄后,同白朗一起逃回上海,審問白朗:“羅烽不投敵,怎么能出獄?”“哈爾濱淪陷后,什么機關開介紹信,讓你們到關內來?”開始,白朗作些解釋,會上提出“羅烽已經坦白了,你還不交代?”她就再不開腔了,一直到日本投降調她去東北工作,白朗在報社幾乎成了啞巴。這樣,副刊部仍然沒有審查與搶救出一個特務。
在副刊部總結審干工作時,老艾說:“我沒有懷疑過副刊部誰是特務分子,對陳企霞與黎辛的歷史問題提的意見也是對的,但這并不能說我完全對,我就沒有錯誤了,我的錯誤是沒有在審干方針上,與報社學委會對立起來。”老艾是實事求是的,說話有分寸。老艾只說他沒有在審干方針上與報社學委會對立起來,《自述》 卻三次說他與老艾不贊成與反對“康生的那套做法”。康生當時是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的,又沒直接過問過副刊部的事,怎么說對“康生的那套做法”呢?
1944年1月,黨中央發出 《關于對坦白分子進行甄別工作的指示》,5月又發出 《關于在反奸斗爭中糾正過左及逼供信的指示》 以后,陸定一與學委會諸領導同志的態度也變了。我認為,報社的工作做得好,凡被搶救過的人無論本人坦白與否,都要根據他自己的交代,有關他的檢舉與揭發,以及批斗時提出的問題,經過內查外調進行甄別,逐個作出結論,征求本人意見,本人簽署同意或保留意見后,適時與迅速在本單位宣布,并賠禮道歉。
經過甄別,報社與清涼山沒有一個特務分子,S不是特務,被抓去社會部的李銳、黃操良與繆海棱也放回來了,不是特務,皆大歡喜。組織與個人相互了解與團結增強了。我問博古怎么清涼山一個特務都沒有?他說如果每個機關都有特務,那還得了?
1944年初,陸定一在“搶救”我的窯洞向我賠禮,態度誠懇,說他的思想方法主觀片面,態度急躁,請我原諒,我的歷史清白的結論是報社最早作出的。陸定一、余光生與博古都在編輯部作過檢討,向被整錯的同志賠禮。博古的態度是從容的,因為他對審干與肅反的態度比較冷靜。整風初期他與文藝欄同仁聊天,回答提問時曾經說過以前蘇區的肅反錯誤,他是有認識的,他下達過阻擋的文件,他沒有下令殺過一個人,他沒有利用保衛機關處理過黨內問題;談到他以前負責中央的工作,開口第一句都是“我犯過路線錯誤”,而后才說別的,博古很謙虛。
(選自《親歷延安歲月》/黎辛 著/陜西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版)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