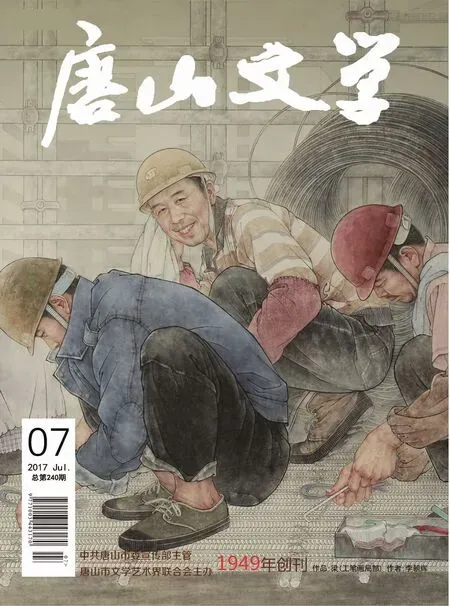實踐理性與儒家哲學
◎張穎超
實踐理性與儒家哲學
◎張穎超
一、法治概念
說到法治概念,會想到亞里士多德,他曾說過“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究竟何謂良法呢?李步云教授在論述什么是良法時,認為廣義的良法是指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或推進作用的法,從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真”是指法的內容的合規律性;“善”是指法的價值的合目的性;“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學性。其中“真”所涉及到的合規律性指的是什么規律呢?
若將知識分為科學知識、技術知識和實踐知識,其中,科學知識是指將各種知識通過細化分類(如數學、物理、化學等)研究,形成逐漸完整的知識體系。它是關于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學問,它以不變的事物為研究對象,具有永恒、必然、普遍的屬性,它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技術知識是指制造一種產品的系統知識,所采用的一種工藝或提供的一項服務,不論這種知識是否反映在一項發明、一項外形設計、一項實用新型或者一種植物新品種上;實踐知識是以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為基礎,自身向善的包含目的性和價值的知識。顯然,法學并非我們所說的技術知識,那么,它是科學知識嗎?科學研究的對象是不變的規律,而法學所研究的對象不可能是不變的,法學是以整個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學科,社會現象具有發雜性和多變性,按照這種說法來看,法學應該屬于實踐知識。所以,我認為法律的合乎規律性中的規律應該就是說法律所調整的對象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在處理復雜性與多樣性的過程中我們就肯定會遇到事情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這時就需要應用實踐理性去解決。要想實現法治社會,就必然運用實踐理性。
二、實踐理性與儒家哲學
實踐理性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康德的倫理學用語,指純粹理性的實踐能力,即給人的行為規定先天道德準則的先驗理性。實踐理性與理論理性并不是兩個不同的理性,而是同一純粹理性的不同方向,前者與意志有關,后者與知識有關。實踐理性所規定的道德律,對人是一道至上的命令,只有依據這種絕對命令的行為才是道德的行為。康德把實踐理性看得高于理論理性,目的在于限制知識,為信仰開辟地盤。實踐理性是人用觀念把握世界的最高領域,它以道德為最高標準,其本身具有合規律性,合目的性及審美屬性即情感的合理性。當無法用具體規則解決社會中的實際問題時,我們不妨依靠實踐理性。那么,中國是否也存在相類似的思想呢?
儒學講究經權變通,在方法論上,“經”是根本原則,“權”即權變,是對原則的靈活運用。經權變通強調靈活而又不失原則,這種辯證思維就是實踐理性的體現;除此之外,程朱理學將儒家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并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程朱理學認為,由于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這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實踐理性;再如,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與康德的實踐理性更是貼近。所謂“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系,也就是指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系。“知行合一”主要包括兩層含義即“行中有知、以知為行,知決定行”。
由此看來,中國的儒家哲學與康德的實踐理性非但不沖突更是存在相通之處,他們都堅持辯證思維,都強調道德標準,并且都追求實質理性以達到心中的善。這就為我們認識、了解實踐理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這也是對中國儒家哲學的進一步發展與弘揚。
三、實踐理性與實踐智慧
實踐理性要求我們堅持辯證思維,以道德、善作為行為標尺,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呢?如何才能把特殊與普遍這種微妙的關系處理得恰到好處?這就需要我們具備實踐智慧!實踐智慧是以實踐理性為基礎,堅持實踐辯證法的基本理念和思維方式,主張在普通與特殊,抽象與具體之間尋求良好的結合點。同時,實踐智慧也是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重中之重。
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那么,接下來的任務則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社會。要想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就應該將法學研究范式由立法中心主義轉向司法中心主義。當然,這兩種思維方式并非對立的關系,我們只是將注意點從強調立法到強調司法,畢竟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律的靈魂在于司法,而司法中心主義思維模式的根基在于實踐理性。實踐理性本源在于實踐活動當中,實踐必須是對人有益的、合目的性、合理性的活動。法律是一種實踐理性而非科學理性,所以不可從科學的角度去理解法學,法本身也包含著對善的追求,掌握了實踐理性中的善就知道在具體情境中怎么辦,其根據就是實踐理性的善。我國自古以來持實質合理的態度,故我國文化土壤難以接受惡法亦法的觀點。我們通過法官對法律解釋來展現法律本身,現在也應在司法運用過程中由法官充分論證,這符合我國的本土文化又符合實踐理性。
法律是普遍的,而根據法律來確定的案件是個別的,要把個別現象歸結為普遍現象,就需要判決,而判決就需要法官,而要想擁有一個完美的判決則需要法官堅持實踐理性,運用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問題,也就是說,法官判決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處理特殊與普遍之間辯證關系的過程,要想正確處理特殊與普遍的關系,需要法官具備實踐智慧。因為只有具備實踐智慧的法官才能經權變通,達到實質理性。因此,實踐智慧要求法官具備如下因素:
首要因素是法官的德性。亞里士多德說過,公眾視法官為“活生生的正義”即人格化的法律程序。不管怎么樣,在社會中,法官肩負著代表正義的職責,按照一般法律的觀點或對大多數民眾來說,他就是法律。故,一個法官的德性對其審理案件具有重要指引作用。
其次,法官的法律專業素養,除了具備良好的德性,法官還需具有扎實的法律功底,不僅要掌握具體學科,還要熟知法律體系,以便更好地解決部門法之間的沖突問題;不僅要具有實踐經驗更要明白其理論淵源,以便使法律文書合情合理,具有說服力。審判本身就是一門復雜的藝術,不僅要求法官掌握法律知識,還要具有嫻熟地運用法律、分析和判斷是非、評價和分析證據能力以及組織駕馭整個庭審活動的技巧等。
最后,要求法官能像王陽明那樣,做到知行合一。因為,法治是一種行動,既然是行動就離不開實踐,而實踐又離不開人,有什么樣的人群就有什么樣的法律。所以,法治社會的構建必然強調法官的實踐智慧!
四、結語
如今,我國正處于法治社會的構建時期,法治社會的構建必然要求實踐理性、實踐智慧!倡導實踐理性、實踐智慧不僅對法治社會具有現實意義,而且對于弘揚與發展儒家傳統文化具有積極作用。所以,我們要通過倡導實踐理性、培養法官的實踐智慧來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050061
張穎超(1990-),女,漢族,河北遵化人,河北經貿大學法學碩士,研究方向:法哲學。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