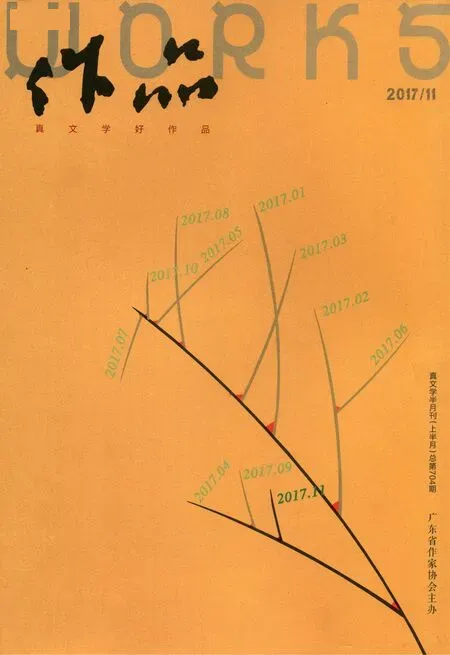勢不可擋
文 /弋 舟
勢不可擋
文 /弋 舟
弋 舟小說家。曾獲郁達夫小說獎(第三、四屆)、中華文學基金會茅盾文學新人獎,魯彥周文學獎,敦煌文藝獎(第七、八屆),黃河文學獎(第二、三、四、五屆),《小說選刊》年度大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第十六、十七屆),《作家》金短篇小說獎,《青年文學》 《十月》 《當代》 《西部》 《飛天》等刊物獎及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小說家提名。著有長篇小說《我們的踟躕》等五部,小說集《劉曉東》 《丙申故事集》等多部,隨筆集《猶在缸中》等兩部,長篇非虛構作品《我在這世上太孤獨》。
大戰爆發的前夜,龐博跟我說晚上他又要去小車間工作。
他沒說那個“又”字。“又”是我的心理反應。我因為這個“又”字而矛盾。我有點兒為他感到驕傲,畢竟,他是我的丈夫,在我們這個集體里,晚上“去小車間工作”是一項不折不扣的榮譽;當然,我也有點兒為自己感到難過。盡管已經是2027年,但我跟大多數女人一樣,依然愚蠢地被捆綁在史前人類的本能之中。沒錯,我在新的時代里,依舊殘存著舊時代的嫉妒心。重要的還在于,對于這種矛盾的心理,我自己也難以判斷好還是不好。
“寶貝,總會好起來的,”他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緒,對我說,“我想,要不了很久,你就會完全適應嶄新的一切了。身為一名女性,主任當然最了解你們女人需要克服多少心理的定勢與成見。我想,給我這樣的機會,沒準正是她想要幫助你早日獲得自由。嗯,她可能更看重的是你。”
“去吧,”我說,“我挺好,也為你感到高興。”
他套上牛仔外套走后,我在晚霞絢爛的天光中游蕩于廢棄的廠區。
這兒曾經是一家大型化工廠,如今密布的管道和高聳的廠房都已破敗。管道與管道之間的連接有的已經斷裂,好像被一雙大手掰成了兩截;完好無損的廠房所剩無幾,差不多所有窗戶的玻璃都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擊碎了——沒誰擊打它們,它們會突然“砰”的一聲自爆。你要知道,這一切并沒有經過人工的破壞,完全是源于大自然的偉力。不如說,是沒有人工的參與,一切才凋敝得如此迅疾和匪夷所思。
廢墟在黃昏中被鍍上了一層金屬銹跡般的紅光。那些鋼筋水泥之中長出的稆生植物都有了一種青銅的光澤。
這兒就是我們的圣地。半年前我們這群人聚集在了這塊荒蕪的廠區里。
勢不可擋,不到十年的工夫,大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類已經被取代。新技術滲透到了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工種。身邊的人紛紛降格為“無用者”。我們這群人還算好,可能屬于最后幾批被淘汰的群體了。當年專家們做過預估,數據顯示,我們這個群體排在被淘汰那個行列的倒數第三位,看來還是靠譜的。
我們是一群作家和藝術家。就在兩年前,我還在廣州的畫室里畫著油畫。如今從最南面的海岸線到最北面的邊陲,時速2000公里的飛行列車只用一個小時就能抵達。人類突破了地球曲率的障礙,突破了聲音空氣傳播的速度,扔掉藝術的約束還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因為將一截直徑50毫米的螺紋鋼徒手磨成了直徑5毫米的螺絲刀,杜英姿成功地把我們這群曾經的作家和藝術家吸引到她的身邊。我們沒什么可以奉獻給她的,這讓我們對她的順服顯得更加純粹。“無用者”首先喪失掉的就是感知物資匱乏的權利,我們無權再享有依賴工作才能換取必需品的生活。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沉淀為無用的數據,不過是加添宇宙的信息垃圾。于是,奉獻財富那種古老的辦法沒有了用場。對于杜英姿,我們能做的,只有追隨她的精神。
作為最后那幾批被淘汰的人,我們可能算不上是人類最沒用的一群。所以,在對杜英姿的追隨中,某種尚未顯明但卻彼此似乎已經默默達成的信念將我們聯合在了一起。
似乎是,我們依然殘存著某種可以被稱之為“反抗精神”的理想。
這事兒放在十年前,我們一定會遭到恥笑,甚至會被看成遭到邪教組織洗腦的白癡。你瞧,我們這群曾經自視頗高的家伙,居然把一個在街邊擺了半輩子攤兒的女鞋匠視為了可以去虔敬膜拜的圣母。
但現在是新的時代。
這個中年女人重新燃起了我們生命的活力。我們一度幾乎喪失了鮮活的生命感,差一點兒就要掉進“無用者”那無憂無慮的、凝滯的深淵。無憂無慮,曾經是所有人的盼望,但當這樣的現實真正降臨時,如果你不是一個天性墮落的人,你就會發現,原來這樣的生活有多么令人窒息。“憂慮”忽然變成了特權,變成了奢侈品,變成了你之為你的確證,繼而,就像昔日爭取無憂無慮一般,不甘失敗的人將去為自己爭取憂慮。
爭取憂慮的道路異常崎嶇。我們既要丟棄舊我,又要讓舊我一點點復蘇。因為,我們畢竟還活在時間的鏈條里。時光賦予我們的積習讓我們在理解嶄新現實的時候困難重重,我們必須拋棄固有的一切,我們的世界觀,我們經年養成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慣性,都需要我們與之決裂;同時,為了抵抗這嶄新的現實,我們又似乎只有一條道路可走——頑固地抓住我們的積習,給一種看似徒勞的努力找出神圣的目的,借此,一點一點回到曾經的自我感受中去。是的,這很難說得清楚,如果需要比喻,我想,如今的我們,仿佛是處在母親產道中的“玩意兒”。我用了“玩意兒”這個詞,是因為我實在難以對我們的現狀做出準確的指認——你既不是一個胚胎,也難以完全地被稱為新生兒,你只是一個正擠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柔韌而潮濕的產道中的“玩意兒”。
縮回去還是鉆出來,這是一場斗爭。
在這場斗爭中,我們幸運地遇到了一雙為我們指引方向的手。杜英姿那雙具有啟示意義的手如此粗糙,經年磨鐵,使得它們宛如鐵本身,掌心的硬繭猶如生銹的鎧甲,十指布滿瘢痕,就是十根確鑿無疑的螺紋鋼。這是新的時代圣母的雙手,和既往懷抱基督的那雙柔嫩的圣手截然相反。它翻轉著我們的想象力,安撫著我們茫然的靈魂,推動著我們殘存的勇氣。
龐博每次晚上去小車間工作,我的心都要被這雙手蹂躪一遍。我能夠感到它粗糲的觸摸。不,這不是一個比喻,這完全是我真實的生理反應。我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失落,同時,隨著失落感而來的,竟然是那種性欲般的生理沖動。這當然是嫉妒心使然。可是這種負面的感受,如今卻又顯得稀缺。有什么東西在熬煉著我的肺腑心腸。
肉欲已經很久不再能夠困擾絕大多數人,只有少數特權者還享有著這項古老的試探。如今性愛機器人唾手可得,并且幾乎算得上是免費供應,據說有些街道的居委會還會上門分發。而失去了滿足肉欲的門檻,男女間的嫉妒心就無可避免地被稀釋掉了,變得罕見。以舊眼光看待,杜英姿是超越性吸引力的,或者干脆可以說,她毫無性的吸引力,甚至在那方面還具有排斥力。但在這新的時刻,她有力地顛覆了一切。
“晚上去小車間工作”,成了男人們渴望的事情。如果他們有伴侶,也應當為此而感到驕傲,因為,這幾乎算得上是一種恩賜和嘉獎了——選中者得到了和杜英姿秘密交流的機會。當然,她會手把手地和他們共同磨螺紋鋼——是真的手把手,她將那雙粗糲的圣手捂在男人的手上,和他們一起用力,一二三四,前前后后,一二三四,前前后后。
最早發現杜英姿神跡的,是一個叫羅旭的攝影家。他是我和龐博共同的朋友。七年前,羅旭在街邊換鞋掌時,看到了今天的圣母。那會兒,杜英姿的修鞋攤冷落地擺在一邊,沒有生意,但她卻沒閑著。有如神啟,羅旭的目光落在了那雙正在磨著螺紋鋼的手上。即便以一個舊時代攝影家的眼光來看,那雙手和那根螺紋鋼所共同構成的美學價值,它們運動的軌跡,都極具象征性的意味——它們獨立于一切邏輯之外,甚至可以脫離物理世界的拘囿,自身便構成一個抽象而崇高的概念。光著一只腳的羅旭按下了相機的快門。
其后,時代的輪子驟然加速,人類熟悉的一切落葉般地紛紛從時間之樹上跌落。據說,新技術帶動的相關產業規模已經超過了10萬億元。飯館沒了,商場沒了,電影院沒了,藝術館沒了,最后,連大會堂都沒了。但杜英姿的修鞋攤還在。那可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個修鞋攤,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孤零零地擺在早已不復往日景觀的街邊兒,水落石出,像是一塊在水中露了頭的紀念碑。當然不會再有人來光顧,沒人還會修理自己腳上穿破的鞋子,人類完全掙脫了破鞋子的枷鎖。杜英姿巋然不動,坐在自己的修鞋攤后,坐在湍急的時光里,面無表情地磨著她的螺紋鋼。
十年如一日,她就這么磨了下來。時代的洪水讓這個行為彰顯而出,就像滔滔的大水涌過,也不得不在一座孤立的豐碑前小小地迂回,它貌似一個無足輕重的阻礙,但的確給寬闊浩蕩的水域制造了不容忽視的波瀾。龐然之力因它而局部地改道。其意義,已經被我們這群人反復地討論過了。
最先,羅旭跟蹤拍攝了那雙磨鋼之手,他將照片傳給朋友們看。力量被傳遞和擴散。大家原本還囿于陳舊的審美,只當這些照片就是那種約定俗成的“作品”。但漸漸地,所有人都被大水漫過了頭頂,“作品”便開始凸顯它神圣的本質。隨著我們越來越窒息,照片中的那根螺紋鋼卻越來越纖細和鋒利,它就是一個反向的力量,充滿了救贖的指向。當它終于在某天成為一把螺絲刀的時候,我們都聽到了從天而降的召喚。
在我們這群受過所謂良好藝術訓練者的心目中,磨螺紋鋼的女鞋匠杜英姿,即便不能被視為再次降臨人間的耶穌,也堪稱現世磨著鏡片的斯賓諾莎。猶如一堆塵埃般的鐵屑,我們被一塊磁鐵所吸引。在喪失了曾經作為藝術家、作家的優越感之后,大家陸續集合在杜英姿身邊。
羅旭說服杜英姿離開了街頭。他差不多扮演了施洗約翰的角色,就像是救世主的開路先鋒。很容易,大家便找到了這塊廢棄的廠區。如今,離開城市的核心區域,大地上遍布著這樣的遺跡。而所謂城市的核心區域,是一棟上千米的摩天大樓。少數“有用者”盤踞在里面,一邊目睹機器讀取星辰一般海量的數據,日夜不息地自我迭代進化,一邊享用著人類寶貴的欲望、恐懼、歡喜和煩惱。
鑒于“勞動”已是一種被壟斷了的特權,我們這些“無用者”一致同意,將我們安身的這塊家園稱為“車間”。做出這個命名時,我們將其和“公社”進行了深入的比較,最后的結論是:“車間”聽起來更具有“勞動”傳統的含金量,而相對于“公社”的大,“車間”在本意上的“小”,也切合我們意圖抵抗時代洪流的心情。你瞧,我們從來就是一群不可救藥的小眾分子,十年前是這樣,十年后,我們依然還妄圖這樣。于是,那個屬于我們的核心區域,天經地義,被我們叫作了“小車間”。它原本的確就是一個小車間,如今,我們主要的勞動都在那里面進行。與之匹配的是,我們將杜英姿尊稱為“車間主任”。我們認為,在這個人類遭到全面碾壓的時代,這比將一位心靈的導師喚為“圣母”或者“教主”,更加具有創世的力量。
來這兒之前,龐博和我在廣州生活了差不多十年。這是斷崖式的十年。我們相互眼睜睜地看著對方信心崩塌,看著曾經驕傲的戀人一天天變得猥瑣。十年前,智能機器人就寫出了小說,還獲得了日本的直木獎,那時,身為一個小說家的龐博已經嗅到了危險的氣味兒。但他心存僥幸,用變態的傲慢來支撐自我的確認。可重錘一記接一記地砸下來。先是發表作品的紙媒消失了,繼而龐大的評價體系垮臺了,最后,人們完全不再需要“小說”,仿佛剛剛跑出了叢林,壓根不知道還有文藝這樣的玩意兒。我經歷了跟他差不多的打擊,如今,隨便一臺機器,就能將畢加索和達·芬奇結合得完美無缺,如果你需要,還能隨便再給你來點兒凡·高、拉斐爾,它們在“聽說讀寫”這些核心感知力上全面超越了人類。難度被抹平了,于是價值也蕩然無存。價值彌散,人們于是對之也不再抱有興趣。
我們是第一批到此定居的成員,后來陸陸續續又來了不少同行,其中不乏曾經在各自的領域里卓有成就的家伙。目前,“車間”的規模大概有將近兩百人。社會上如今出現了大量的群居部落,那可是真正的群居,他們生活在廢棄的體育館或者音樂廳里,在巨大的屋檐下共同吃喝拉撒;但我們妄圖捍衛自己的小眾氣質,即使聚集在一起,依然保持著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
這塊廢墟足夠大,曾經容納過上萬人。大家分散開,各自給各自找了窩。我和龐博選擇了一臺巨大的車床,它在一棟大廠房里和另外幾臺機器并列著,天然就像一張闊大的架子床。我們在這臺車床下面構建了自己棲息的領地,在它上面的那一層堆放生活用品。
這樣看來,如果在空中俯瞰我們聚居的“車間”,肯定更像是一個超大的蜂巢,成員們各自獨立,又被緊密而有序地組合在一起。事實上,也經常會有政府的飛機飛來,在空中對我們進行航拍。世界被更加有序地管理著。
我是一只縮在隔板里的蜜蜂——龐博晚上去小車間工作的時候,躺在車床下面的我,呼吸著帶有鐵銹味道的空氣,就是這樣想象著的。我想象著,有脆弱的翅膀在我肩膀上艱難萌生,有黏液糊在我的身體上,我的四肢稍微碰撞,就有可能折斷落下終身的殘疾。在這樣的時刻,如此具有溫度的焦慮彌足珍貴。你要知道,如今,人們入睡前更多地只會將自己想象成浩瀚矩陣中一個微末而冰冷的數據。
龐博黎明時鉆回了車床下面。他在我身邊小心翼翼地躺下,手臂輕輕地搭在我的腰上,從身后抱住我,將呼出的熱氣沖著我的脖頸。晨曦無聲地侵入了我們的領地,只照亮了我躺著的那一半。我還沒有完全醒過來,從亮處轉身,用一只蜜蜂的心情抱住了暗處的他。
起初,在半夢半醒中,我們一動不動地就這樣抱在一起,像是被自己生產的蜜汁黏連住了。后來,我漸漸蘇醒。“蜂后”這個概念在一瞬間突然躍進了我的意識,同時,就像被驚動了的蜂群,與之相關的那些欲念也蜂擁而起:生殖器官發育完全的雌蜂,由受精卵發育而成,壟斷交配權,能分泌蜂王物質維持蜂群的次序。
我依然沒有動,但呼吸變得粗重、急促。
龐博也沒有動,但我能夠感到他抱著我的胳膊加重了力道。
我們開始默默用力,閉著眼睛,一言不發地抱緊對方。
“給我。”終于,我忍不住向他索要。
“怎么了,怎么回事?”他卻用質疑拒絕著我。
我們很久沒有在一起了,究竟有多久,我竟說不清楚。此刻,久違了的欲望令我既欣慰又難過,就像他的拒絕一樣,也是令我既難過又欣慰。欣慰不用去多說了,難過卻也是無從說得清楚。
十年前,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就推出了先進的男用性愛機器人,“洛克希”,身高170公分,體重27公斤,膚色和發色可以定制;她不會打掃衛生,不會做飯,但在那方面她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她還能傾聽你,感受到你的觸碰,她也會入睡,并且,她還復制了人類的十幾種人格特質:奔放,狂野,害羞,冷淡,天真,善良,友好……但和今天的這類設備相比,“洛克希”就像一只剛剛走出非洲的母猩猩。女用設備也早已經齊頭并進了。肉體欲望的解決途徑早已不成其為一個問題。
如果理解了這樣的背景,你就會理解我在這個清晨欲望升起又被拒絕之后的欣慰與難過。我渴望某種復蘇,它降臨了,讓我變得濕潤多汁,但我又不愿復蘇了的渴望被簡單滿足。我被懸置在了一種兩難的境地,像一只琥珀里被囚禁的蟲子。我只有咬著嘴唇,濕漉漉地眼涌淚水。
“瞧瞧你,瞧瞧你,居然還哭了。”龐博嘆息著,一邊替我擦眼淚,一邊說,“你瞧,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晚上去小車間工作了,你明白,如今只有工作才是唯一的救贖,那是我們終極的道路,你都說過,每一次工作,就好比是一次信仰的儀式。”
這話我可能說過,但我此刻不愿想象那個“信仰的儀式”。我把頭埋在他的胸前,等眼淚完全被吞下后,起身從車床下鉆了出來。
我走到了室外。晨風薄涼,草木在廢墟中隨風輕搖,世界衰敗,但像每一個清晨那樣依然宛如一個奇跡。
我在外面的水龍頭前洗漱干凈,回去穿上牛仔外套,拿起我的那根螺紋鋼,走向一公里外的小車間。
路上不斷遇到上工的同伴。曾經的作家、藝術家們用眼神默默地打著招呼,頂多輕輕互道一聲“早安”。我們都穿著相同的牛仔外套。如今政府統一給“無用者”配發服裝,款式極其豐富,任由你滿足自己著裝的想象力。當你走入人群中,你會覺得自己身在一個繽紛的時裝發布會。在這樣的風尚面前,我們這個群體選擇了最樸素的牛仔外套。它不僅僅是我們統一的工裝,穿上它,還會令我們具有一種整齊劃一的修道士的氣質,同時也令我們獲得了一致的認同感,覺得我們就是一個命運的共同體。
小車間孤零零地矗立在廠區的一隅。它可能是做某種高危化學實驗用的,當初就沒有和這座大型化工廠的主體建筑融為一體,形同孤懸海外的一塊飛地。這恰恰成了我們挑中它的緣由。
如今通向它的道路完全是靠我們的腳在雜草中踩出來的。數條蜿蜒的小徑最終在它那里匯聚,令它像是道路的終點和真理的歸宿。也許通往它的道路是平緩的,但每次走向它,我都有種爬坡的攀登感。我想我的這種錯覺,其他人可能也有,因為大家行走在通往它的小徑上時,身體都是微微前傾著的。于是,日復一日,走向它的我們將它走成了一塊心目中的高地。
在這個清晨,當我們快要走到小車間時,大家都看到了我們的“車間主任”。
杜英姿背對著我們,面朝小車間洞開的大門,短短的灰發在風中紛飛。遠遠望去,一個臃腫的身形鑲嵌在黑洞洞的門框里。在我眼中,這個畫面有著一幅中世紀宗教畫的效果。不,她沒有那種畫風里圣徒們超拔的氣質,但那臃腫的中年女人的背影,卻更符合我在這個新的時代里對于救贖者的想象。
她像一頭緩行的豬,時代風馳電掣的飛行列車從她身邊呼嘯而過。這樣比喻,我絕沒有一丁點兒詆毀她的意思,相反,這頭緩行的豬,在我內心代表著這個時代最高的沉著。
當我們走到她身后時,大家不約而同停下了腳步,和她保持著大約十米的距離。這個距離大約就是凡俗與神圣之間的距離,既不是那么遙不可及,也不是那么觸手可得。有人開始給我們分發早餐。每人一杯熱牛奶,一塊羊角面包。大家默默地吃吃喝喝,像是儀式的某個進程。
她兀自面朝著小車間敞開的大門,似乎是在善解人意地等待著我們先填飽肚子。小車間的這兩扇門值得說說。原本,它當然是那種銹跡斑斑的鐵皮門。我們到來后,將鐵皮門拆掉扔了,代之以兩扇極富東方色彩的那種會令密集恐懼癥者不適的布滿門釘的大紅木門。至于為什么這么干,誰也沒給出過答案,好像這么干壓根就不需要有個說明。我想,這是源于我們對自己文明頑固的自信。
有人收走了我們手里的空紙杯。杜英姿又站了片刻,才慢吞吞地轉過了身子。正在抹嘴的人將手停在了嘴上。我不想描述她的容貌,因為既有的那些陳詞濫調一旦用來形容她,就會充滿了褻瀆和詆毀。所以,我只能簡單地說,她長著一個中年女鞋匠應當長著的臉。望著這張臉,我的心里常常暗自喟嘆:唉,我為何還要嫉妒?!但是,上帝啊,又讓我如何才能不愈發地嫉妒?!
她也望著我們,眼神像往常一樣空洞。偶爾,她的眼睛會拼命睜大一下,形同下意識的痙攣。人來得越來越多了,大家穿著同樣的牛仔外套,每人手里都扭著一根30厘米長的螺紋鋼。這場面,就像是一場革命前夕短暫的寂靜——暴民們正在等待他們的領袖發出起事的號令,暴風驟雨正在最后的關頭醞釀。
跟往常一樣,我們依然期待著她能對我們說點兒什么。但依然跟往常一樣,她什么都不跟我們說。實際上,我們之中可能沒幾個人聽到過她說話,反正我是沒有過。她是一個沉默的先知,只行動,不說話。據說被她特許在晚上進入小車間工作的男人們,才有可能聆聽到她的只言片語。但傳出來的那些“只言片語”更像是一些氣聲,例如“哼”和“哈”這樣的象聲詞。這愈發令她接近了一個圣母所應有的神秘。
她不說話,像是只身和我們將近兩百人對峙,像是一頭困獸陷在圍獵的中心。她的氣場一點都不遜于我們。她只需要站在那兒,就能散布磅礴的蠻力。時間在晨風中凝固了,或者被按下了暫停鍵。鴉雀無聲,唯一的動靜是有人整理牛仔外套下擺發出的那種聲音。
終于,她揚起了雙手,動作就像一個遲緩的老婦在做著第十八套廣播體操。舉起,放下,舉起,放下,如是三次。那雙粗糙的圣手有力地掀動了凝固的時間。于是時間得以重啟,繼續流轉。我們發出了克制的歡呼,隨著她起伏的雙手,“噢”“噢”地低聲叫著,同樣如是三聲。難道,這還不能算作一個鼓動人心的儀式嗎?我們猶如剛剛完成了一次洗禮,額頭儼然還掛著圣潔的水珠。
然后,她就垂下雙臂,慢吞吞地挪開了身子。她就那樣突如其來地慢吞吞地走開了。她一挪動,你才會發現她比你原來認為的還要臃腫、遲鈍,還要不知所以和不知如何是好。她在行動中釋放出來的信息好像是:她自己覺得來這兒給一群瘋子當圣母是一個荒謬的錯誤。
我們目送著她離開,消失在我們的視野里。她走得真是慢啊,在這個峻急的時代里。
小車間容不下將近兩百人一同進去工作。如今幾乎每天都有新人不斷地加入,隨著團體可以想見的膨脹趨勢,規則也制定出來了:每次能夠進入小車間工作的,限定為五十人,其余的人在室外圍坐著干活兒;分批次輪換,所有的人都能夠有規律地進入到小車間里去。這種規則的確立,不但形成了有效的秩序,還使得我們的小車間完全具備了一座圣所的公平性。
它的確是一座能夠用以朝拜的圣所。當我們在清晨的時候走進去,晨曦從天窗涌瀉而下,宛如一道天幕垂掛在眼前,而這道天幕的聚光所在,恰恰是那把锃亮的螺絲刀——它居于小車間的正中央,擺在一張綠漆斑駁的鐵皮工作臺上,唯一的裝飾就是襯托著它的那塊白色的毛巾。沒錯,它就是杜英姿畢十年之功將一截螺紋鋼磨就的那件圣物。
我們團團圍坐在這把螺絲刀的周圍,開始了一天的勞作。
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磨螺紋鋼。大家領到的螺紋鋼規格統一,直徑50毫米,長度30厘米,完全符合我們供奉著的那件圣物的原初形制。我們就在地上那么磨著,一二三四,前前后后,一二三四,前前后后。水泥地面不可避免地被磨出了縱橫的溝壑。天長日久,除了供奉圣物的那張鐵皮工作臺的下面,小車間的地面逐日下沉,漸漸地,被我們人工磨出了落差,像是給這個空間升起了一塊長方形的躍層。沒有誰指出這個現象,但大家心照不宣,不約而同地不去觸碰那塊長方形的神臺基座,同心協力地通過降低地面來抬高我們心目中那塊神圣的祭壇。磨了半年,水泥地面下沉了大約有3厘米,但我們中大多數人手里的螺紋鋼,還是一根標準的螺紋鋼。
我們就這樣磨呀磨。我們通過磨呀磨抵抗著自己“無用者”的命運。你可以說這是滑稽,但確鑿無疑,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莊嚴。
由于并沒有一個現實性的訴求,我們這種非現實性的勞作其實是很輕松的。沒誰想要給自己制定一個時間表,手里的螺紋鋼究竟何時會被磨成螺絲刀,我們壓根并不關心。我們只是盤腿而坐,機械地磨來磨去。這個時候,我們終于放空了自己,開始冥想,神游天外。當然,也不排除打盹乃至酣睡。
每過一個小時,會有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大家可以站起來活動活動腿腳,也可以走出小車間,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和外面的同伴聊幾句。來這兒之前,大家都是舊時代“壇壇圈圈”里的人,相互之間熟人不少。說是“聊幾句”,其實不過只是個說法兒而已。如今我們沒什么可聊的,在龐然的現實之下,人在逐漸喪失著說話的動力。
為此,羅旭開始組織大家一起唱歌。他擔心我們過快地喪失語言能力。他真不愧是一個先知的開路先鋒。在很大程度上,“車間”的形成完全是因了他的努力。我可以肯定他是受到了某個啟示,才會像施洗約翰那樣走向曠野,預言神的到來。是他最早用鏡頭捕捉到了磨鐵的圣手,是他將杜英姿引來了這里,當大家越來越沉默的時候,他負責用語言來闡明制度和紀律。天經地義,羅旭是我們車間的“副主任”,他是主任的助手和代言人。
對于他如今所扮演的角色,我心里有著蒙昧的感受。他是我和龐博共同的朋友,還是龐博介紹我們認識的。但我跟他上過床。其實也不是在床上,是在我家的廚房。他把我放在櫥柜的臺子上,讓我的兩條胳膊撐在身后,掀起了我的裙子。那已經是許多年前了,當時龐博爛醉如泥,因為他剛剛聽到機器人寫出的小說獲得了直木獎。
羅旭瘦弱,單薄,長發披肩,但如今他宛若受到了神秘力量的加持,有了金剛不壞之身,明晃晃地煥發出驚人的能量。
他在我們休息時組織我們唱鮑勃·迪倫的《時代正在改變》:
嗨!到處流浪的人們
聚在一起吧
要承認你周圍的水位正在上漲
接受它。不久
你就會徹骨地濕透
對你來說如果你的時代值得拯救
你最好開始游泳,要么就如石頭般沉沒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嗨!作家們,評論家們
用你們的筆做預言
睜大你們的眼
這種機會千載難逢
不要說得太快
因為車輪還在旋轉
很難說誰會成名
因為現在的輸家將是未來的贏家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
不是嗎,這很應景?
小車間的外圍經過半年螺紋鋼的打磨,現在已經初具一個小廣場的規模。我們在小廣場,在秋風里,在午后,唱著應景的歌。
午飯基本上還是政府提供的。如今政府負責“無用者”一切的生活所需。但我們已經嘗試著自力更生。有一組人專門去種蔬菜了,番茄和黃瓜,萵筍和土豆,還養了一些雞。但收成尚無法滿足我們全部的所需,目前只具有象征性的意義。中午十二點半的時候,會有一架無人機準時降落,艙門打開,伸出的傳送帶為我們輸送來盒飯。我們排著隊,按人頭挨個認領一個飯盒。
飯后的午休時間只有半個小時,這足夠了,因為我們實在沒怎么累著,不少人實際上是半睡半醒了一早上。
在這半個小時,由羅旭的妻子帶領大家唱歌。她本來就是教聲樂的,之前在一所音樂學院當教授。她的嗓音婉轉,猶如百靈鳥——由于使用語言的頻率在大幅度減少,現在我的詞匯量越來越貧乏膚淺了。當我想要描述什么時,開始漸漸地習慣使用陳詞濫調。是的,她挺美的,“像一朵花兒”,當她領唱的時候,我的心情有些“波浪般的漣漪”。
我已經難以準確地體察自己復雜的內心,于是,內心反過來,也漸漸變得越來越不復雜。“太陽是溫暖的”,“花兒是芬芳的”,“男人是山”,“女人是水”,世界在我眼里越來越被簡化,抽象成了一些不知所云的比喻句。但是對于這對夫妻,我還是想要努力想得清晰一些。沒錯,我跟羅旭沒什么情感上的瓜葛,我們不過是在多年前有過一次櫥柜上的性事。但如今我們集合在“車間”里,他確乎有著顯而易見的地位,于是,對于他,對于他身邊的妻子,我的心情還真的是有些“波浪般的漣漪”。有什么古老的本能在我身體里作祟。
他美麗的妻子在午休時引導我們合唱:
嗨!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們
請留心電話
不要站在門口
不要擁堵在走廊
因為受傷的他會停滯
外面正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戰斗
很快,你的窗戶抖動,墻壁咯吱作響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嗨!各地的父母親們
不要說你們不懂
你們的兒女已超出你們的控制
你們的老路正在迅速老化
如果你們無力,請避開這條新路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
黃昏,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去后我并沒有看到龐博。
往常這個時候他應當在車床下睡覺。每次他在晚上去小車間工作后,翌日都會大睡一整天。他不在,我也并沒太放在心上。冷漠是“無用者”集體的特征。
已經有人送來了雙份的晚餐,兩塊牛排,兩小碟被保鮮膜包著的水果。同樣是政府供應的,集中投放在指定的位置,“車間”有專人挨家挨戶地派送。車床下還多了床羽絨被,想必也是政府新配發的。天氣已經轉涼了,無論有著怎樣彎曲的夢境,“無用者”也需要一個暖和的被窩。
我并不是很餓,先去外面的水龍頭清洗自己。如今所有的水龍頭流出的都是熱水。當然你也可以調整出水的溫度,從零攝氏度到一百攝氏度。它還可以直接飲用。所以我一邊洗著臉一邊用手掌捧著水喝。今天的水好像有些發澀,含在嘴里有種舌苔被氧化著的滋味。
我們的鄰居是位男雕塑家,大概五十多歲,一個人住在隔壁偌大的廠房里。他也在清洗自己,將一根淋浴蓬頭接在龍頭上,赤裸裸地露天沐浴。他的身材真好,像亨利·摩爾雕塑作品中的人物那樣富有不一般的表現力,他的左耳掛著一枚亮閃閃的、夸張的大耳環,在夕陽下熠熠生輝。他一邊沖洗著自己,一邊用南方口音向我打著招呼:“嗨!”
我看出來了,他試圖想要表現出挑逗我的意思,但我知道他毫無此念。他的那玩意兒低垂著,毫無動靜。他不過是想要給我釋放出禮貌性的善意。如今,對異性表達出性的趣味都是一種致敬了。
“嗨!”我也回敬他,盡量顯得風騷一些。
回去拿了蓬頭,我也赤身沐浴起來。已經是初秋了,黃昏的秋風還是有些涼的。很快我就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乳頭也凍得硬邦邦的。
雕塑家吹起了口哨。還是那首《時代正在改變》,我也哼唱了起來。
后來我裹了一塊浴巾,抱著肩膀坐在暮色四合的曠野中,眺望著天邊最后一片暮靄變暗。我感到了冷,可這正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夠做到,我還想要來點兒孤獨的感覺。遠處城市的核心區域傳來若隱若現的警報聲。
天完全黑了,龐博還沒回來。我回去躺進車床下面,用新的羽絨被裹住自己,只能睜著眼睛發呆。
大約凌晨時分,我被羅旭從夢中喊醒。
他搖晃著我的肩膀,對我說:“醒醒,龐博呢?”
我迷迷糊糊地坐起來,兩條胳膊撐在身后,那感覺就像是他又要掀起我的裙子。
他當然沒那么做,只是一迭聲地問我:“龐博哪兒去了?龐博呢?”
我告訴他我并不知道龐博的去向,下工回來我就沒見到過他。我開始努力回憶自己最后一眼看到的龐博。似乎是,他背對著我躺在車床下面,躺在陰暗面,像一個準備要維修機器的修理工。同時,我對他的愛也被依稀地想起。這說明,我依然還在愛著,哪怕這愛的情感已經螢火般微弱。徹底滅絕了的愛依然是難以令人想象的。
“跑了,他們跑了,”羅旭怔怔地自言自語,“主任也不見了。”
像是要給他的結論加一個注腳,我的眼睛看到了那件牛仔外套。它扔在不遠處的地上,好像還被人踐踏過一樣。這是龐博的外套,我們的工裝,穿上后會令我們有一種整齊劃一的修道士的氣質。可那個修道士現在脫下它跑掉了。
我套上自己的外套,爬起來跟著羅旭走了。外面還站著幾個人,平時“車間”的成員們好像都是平等的,但在這個深夜,人類組織結構根深蒂固的本質暴露了出來。此刻站在夜色里的這幾個人,顯然突出了他們的核心身份。也不知道是誰授意的,總之他們好像有著不證自明的權重。而我現在好像也加入到了這個核心里面。我是唯一的女性,這似乎令我有些高興,沖淡了我的傷心。
羅旭帶著我們穿過深夜的廢墟,再一次搜查了杜英姿的住所。
那是一間不大的配電室,里面仍遺留著過去的配電柜,一排排的按鈕讓人感覺很有發號施令的派頭。我們一無所獲,不過是搜出了幾包衛生巾、幾件闊綽的性感內衣,還有一堆一望可知是派什么用場的小儀器。
聞訊而來的成員被羅旭指揮著在廠區里四處尋找。同樣一無所獲。我在黎明的時候向大家宣布,我們的主任,我們的先知,她走了,走向了“終極的道路”——我想起來了,這個詞是龐博在上一個黎明時對我講的。那時候,我還身在一個有關蜂巢和母蜂的欲念里難以自拔。
有人在哭,是的,有人在哭。這可真難得,真了不起。
我們在晨曦中集體走向了小車間,就像是一個被揀選出的民族在走出埃及。今天清晨的天空格外具有穹頂的感覺。此刻如果發生任何奇跡我都不會覺得驚訝,哪怕一瞬間行走著的我們都變成了一根根行走著的螺紋鋼,哪怕天空倒垂,大地壁立。空氣中有一股電腦主機被電流燒毀時的嗆味兒。
推開沉重的大紅木門,我們幾位核心成員進到了小車間里。這同樣沒有經過誰的授權,但好像大家都這樣接受了某個事實。新的領導集體形成了。今天我們來得早了一些,晨曦依然從天窗涌瀉而下,依然宛如一道天幕垂掛在眼前,只是亮度比往日顯得昏暗。天幕的聚光所在,那把螺絲刀發著暗沉的灰光。
我們幾個核心圍繞著鐵皮工作臺站定,像是一群圍在解剖臺邊兒的醫生,像是有著一個巨大的傷口正等待著我們縫合或者繼續切割;我們也像是幾個擁有權柄的祭司,正準備將什么犧牲抬上祭壇,在動手前各自盤算這得花多大的力氣。
我們誰都不主動開口,但是彼此心知肚明。那個共識我們其實已經達成——喏,沒錯,信仰坍塌了,理想破滅了。我們不過是拉了一個街邊兒的中年女鞋匠來做自己假想的偶像,其實,一目了然,她的腦子有問題,空洞的眼神,遲緩的動作,都暴露了她的精神狀況。誰知道她曾遭受了什么,于是在十年前磨起了不明就里的螺紋鋼。但我們卻賦予了她的行為深刻的宗教性的意蘊。就在這座圣所,在這張綠漆斑駁的鐵皮工作臺下面,那塊兒唯一沒有經過我們螺紋鋼打磨的平滑地面上,她和晚上被自己宣召而來的男人行著淫亂之事。而我們卻終日勞作,手工將這塊兒穢地升高為了圣壇。還有什么能比這更令人羞恥和心碎呢?
我們啞口無言,但各自羞恥和心碎的心情卻接近一種享受的狀態。我們沉浸在污穢凄苦之中難以自拔。自從被降格為“無用者”,我們與這種強烈的心情已經暌違太久。是的,有什么寶貴的東西正在我們胸中復蘇。我覺得我有義務講點兒什么,畢竟,是我的丈夫參與到了這個背棄的事件當中,我有無可爭議的發言權。
我正準備開口,羅旭卻先說話了。
“可以報警。”他說。
當然可以報警,這是對那兩個背信棄義者最直接的懲戒。當你只要支付一百塊錢就能買到人腦計算速度的電腦產品時,政府就預見到了人類社會將要面臨的巨大風險。許多管控的法律條文早早被制定了出來。譬如,為了免于人類社會組織結構的迅速崩盤,法律嚴懲挑戰婚姻關系的行為,婚內通奸者會被立刻處死。現在,這兩個私奔的家伙踏上的就是一條律法的不歸之路。他們逃不掉的,外面的世界如今全是虹膜識別系統,天羅地網已不僅僅是個形容詞,任何一個逃犯都插翅難逃。
但是,我們不能這么去干。
“不。”我堅定地說。我還想多說幾句,但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兒。我只能含淚說:“不!”
盡管一想到龐博和杜英姿在我腳下的這塊水泥地面上翻滾我就感到惡心,但我仍然堅定地這么說了。這個決定我做得毫不勉強,就像是另外有一顆心在替我做著思考和決斷。我強烈地感到:圣靈運行在小車間里,真正的生門開啟了。
之前的一切都只是序幕。上帝讓那兩個人合演了一出戲,演給天使和世人看,在你以為是結局的時候,真正的大幕徐徐拉開。正是因此,我們才能從蒙羞中覺醒,重新尋找拯救自己的方案。難道不是嗎?此刻,難道我們沒有因為感到羞恥、心碎而一陣陣惡心嗎?這多美妙!我甚至都要為龐博感到驕傲了,他是那個被上帝選中的受難者,他以自己小說家的智慧和肉體,為我們做出了崇高的犧牲。
如果此刻我們蒙受著深重的羞恥,那么,將近兩百個成員有誰比我蒙受得更加深重?如果此刻我重拾了信心,那么,有誰還有什么理由不隨著我歡呼贊美?
“主任!”
良久的沉默之后,羅旭一把抓起了我的右手,高高地舉起來,宣告著新先知的就位。
“主任!主任!主任!”
如是三聲,他低沉地吼著,一邊將我的右手舉起、放下,如是三次。
核心們跟著他低沉地怒吼,像一群經歷了空難卻突然發現自己毫發無損的人,不禁要嗷嗷叫著來慶幸自己居然還活著。
他牽著我的手率眾走出小車間。很奇妙,我的心情卻像是一個被牽引著的新娘,就像當年被他拽進廚房時一樣。迎著將近兩百雙眼睛的注視,我的步子有些別扭。我想盡量走得端莊一點兒,就像是從地平線走來的那樣。我理解了過去人類的新娘為什么會穿著拖地的裙子,因為那可以遮擋她們裙子下面哆嗦的腿。圣所外的成員們等候已久。他們穿著統一的牛仔外套,手握著30厘米長的螺紋鋼,在這個清晨迎接新世界的到來。
羅旭再次重復了剛剛的動作。
“主任!主任!主任!”
眾聲合唱,我被加冕。
——就在這個時刻,大戰終于勢不可擋地爆發了。
天空中升起了三顆蘑菇狀的云朵。它們在空中緩慢地膨脹擴散,像是要漲破蒼穹。
政府早就對民眾進行過國防教育——當空中浮現出這樣的天象時,就表明大戰已經爆發。
回望歷史,兩次技術革命先后引發了人類的兩次大戰,這一次的技術革命引爆再一次的大戰,早就在人類的理性中被預定了。所以,一切平靜得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窗戶沒有抖動,墻壁沒有咯吱作響,天空中的蘑菇云不過像是慶典時的煙花。沒有人會感到恐懼,因為想象大戰展開的形式和所能達到的烈度,已經完全超出了我們這些“無用者”的智力水平。
我們所能理解的,只有我們有限的那些經驗,諸如消失的榮耀、破碎的完整,就像此刻我們只能將空中的預警理解為新先知確立時的天啟異象。
朝陽刺破蘑菇云映上了我的臉龐。我覺得自己從未如此的火熱,牛仔外套下面的身體在微微發燙,并且還在不斷地升溫,讓我變成了一臺有待沸騰的小鍋爐。環視一周,我發布了“主任”的第一道圣諭。
“你,”我看著身邊的羅旭,面無表情地說,“今晚來小車間工作。”
“車間副主任”羅旭如今留著長發。他若有所思地含著一縷頭發,眼神狂熱而迷亂。
說完,我在人群中尋找著他的妻子。那種人類鉆出叢林之時就與生俱在的調皮勁兒,那種混合著良善與邪惡的人類的原始本能,猶如已經爆發了的大戰一般,勢不可擋地在我胸中喚醒。
我看不到他的妻子,但聽到她百靈鳥一樣清亮而恢弘的領唱:
線路已畫好,咒語已實施
現在緩慢的,在未來將是快速的
現在的“當代”,將是未來的過去
制度很快過時
現在領先的,在未來將是落在最后的
因為時代正在改變
我在流淚。心想,如果戰火沒有在一天之內毀滅一切,我就去城里找間美容院,用蠟脫掉一身的汗毛。自從“無用”以來,我的體毛都生長得可恥的旺盛。
(責編:王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