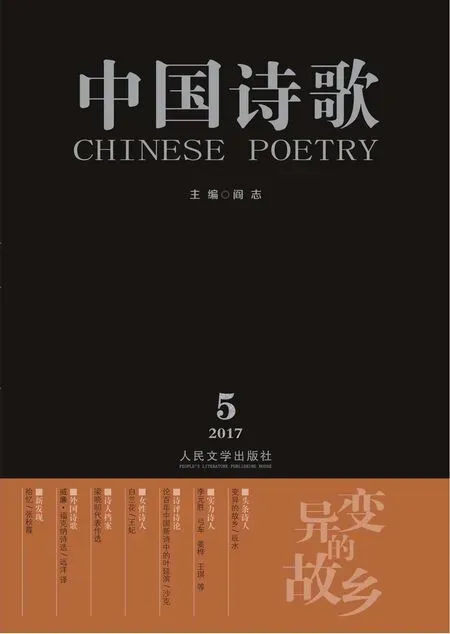盎然的詩性感受與存在的詩性意義
——梁曉明詩論
□苗霞
盎然的詩性感受與存在的詩性意義
——梁曉明詩論
□苗霞
梁曉明自1984年開始寫詩,至今在三十多個年頭里創(chuàng)作出了數(shù)百首詩篇。在這數(shù)百首詩篇中,詩人努力地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甚至追求“應(yīng)該有一種聲音,在不是聲音的地方/他挺身顯現(xiàn)”(《聲音》)。在我看來,他的聲音訴求可以歸為兩類:一是叮當脆耳的風鈴聲;一是雄渾尖利的海嘯聲。前者以《節(jié)日》、《以后》、《風鈴》、《林中讀書的少女》等為詩意柔婉的代表;后者以《開篇》組詩、《告別地球》組詩、《剝》、《玻璃》、《我將第一人進城》等為剛烈嚴峻的代表。對于前者,論者多有提及,但筆者認為恰是后者奠定了梁曉明在第三代詩人群中的地位和價值。這些詩歌,因其獨異的詩歌觀念、超拔的詩歌想象力、極強的主觀表現(xiàn)力、措辭方式的個人性,更重要的是詩對思挺進的幽深等方面,構(gòu)成了當代詩壇的另一面景觀、別一種高度。筆者接下來的闡釋主要是針對后者而展開的。
初讀梁曉明的詩歌,第一印象來自于其語詞或狂暴或溫柔的感受性。他的詩句總能巧妙地把情感、思想、精神上的感悟化為身體上的感應(yīng),仿佛摸到、觸到、聽到、嗅到、看到那抽象無形的一切。這樣一來,其詩句具有可感觸性,讀者能感觸到其思之輪廓、色彩、聲音、重量、硬度等。譬如“孤獨這塊圍巾/我圍在脖子上”(《半夜西湖邊去看天上第一場大雪》,“那曲子像是剛從眼睛里流下來/濕淋淋的都是淚”(《二泉映月》),“陽光在她的皮膚里走動”(《辦公的時候》),“時間紛紛從頭發(fā)上飛走”(《但音樂從骨頭里響起》)等等。這一點,是詩人一貫的詩歌信念和追求。早在1986年創(chuàng)作初期,詩人在其詩篇《詩歌》中就寫道:“詩歌沿著我兩條眉毛向后腦發(fā)展/詩歌擁抱我每一根頭發(fā)/在每一塊頭皮上它撒下谷種/詩歌在我的鼻孔里醒來/醒來就迅速張起篷帆/順流而下”。對梁曉明來說,對詩的認識來自于身體的綜合反應(yīng)。直到2012年的《向詩說話》他還堅持著:“它是裸體、是踩著你的身體一路走來的/你的欣喜、醉后的悲傷/是無法后悔的你暗自的恥辱。”可以說詩歌是從詩人的身體上生發(fā)出來的,帶有他的體溫。
身體化是梁曉明一個隱喻的詩性思維模式,詩人以此來感知的世間一切物象、事象乃至抽象都是血肉豐滿、感性立體的。這樣一來就不難理解,散撒在梁曉明詩歌中的天空與大地、植物與星辰,如“大雪”、“海水”、“燕子”甚至于連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學(xué)的概念如“時間”、“聲音”等,也被詩人冠以“你”、“他”的人格化稱謂。即使是抽象哲思也以溫度、濕度、色彩、形狀、線條、質(zhì)地、聲音或寂靜的形式,進入其聽覺、視覺、觸覺、味覺、嗅覺的意義譜系。身體化思維會造成其語言的細膩感覺化,語言的感覺化也就是詩歌的“詩意”化。詩意是什么?“詩意并非什么縹緲之物,它就置身于純樸的感性和清新如初的感覺經(jīng)驗中,置身于如雨后的晨曦一樣的目光中,一首詩之所以說它沒有詩意就是說它的可體驗的感覺經(jīng)驗的匱乏。”而梁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給了我們豐盈充沛的詩意化。
第二印象是其超拔的想象力,在其每一個詞語之頂巔及每一行詩句之深谷中涌動著一股獨特的想象之光。讀梁詩,如同重臨想象的沒有邊界的千座高原。有的想象狂放峻急,可以上九天“認識月亮的版圖”,下深海“挽著帶魚唱歌”。聽聽吧:“是誰,在一小包火柴中將我等待?/我燃燒,將時間里的琴弦/齊聲撥響/在一把大火中,我的白馬出走”(《真理》,“刮過太陽的鼻子、搭過村莊的肩膀/最后我來到天空的瓦片上……駕駛過飛機、潛入到海底/曾經(jīng)挽著帶魚唱歌……認識月亮的版圖、訪問過大雨的廚房/用小號把冬天全身吹亮”(《用小號把冬天全身吹亮》),“所有紀念碑都頂著我的鞋底,風暴擠入我內(nèi)心……/我潔白的骨頭向喊叫逼近”(《刀子》)。有的想象溫婉柔麗,浸涌著一種古典詩詞的流韻神采。聽:“和欄桿一起微笑”(《用小號把冬天全身吹亮》),“亭子里楹聯(lián)與黑暗交談/遠處的狗叫把時間當陌生人/介紹給我”(《半夜西湖邊去看天上第一場大雪》),“一枝荷花幾乎是一大把夢想的頭發(fā)”、“飄帶忽然回收的下巴”(《歌唱——獻給折磨我、溫柔我、瘋狂我、遐想我的YKM》),“她笑起來像石頭上濺開來的水花”(《22歲時有一個冬天》)。有的想象奇崛吊詭,不惜以蕪雜乃至歧義的方式使詩具有多重闡釋的可能。如“在眼睫的堤壩上/向大海的更高處眺望”(《說你們》),“我太沉重/一開口你就將步入森林/鋼刀將使你重新出血/那片原始的沼澤、那片蒸騰的光/將使你步入危險的峰頂”(《病》),“讀到我的臉在一個最小的標點符號上/一個逗號/沿著江南的雨絲從天上/掛到地下——”(《一點人生》)。至此,你不能不佩服詩人想象力的開放闊展和縱橫捭闔。想象力這匹放縱無羈的野馬隨意地穿梭于詩景的各個層面,傳遞出一種從文本內(nèi)部擴張來的自由自在感。
無論其想象是狂放峻急、溫婉柔麗,還是奇崛吊詭,有一點是相同的,構(gòu)成其想象王國的材料都是日常物象、語象和事象,但詩人在想象的高飛遠舉之中去掉了這些現(xiàn)實材料的習(xí)慣的、傳統(tǒng)的意義,用它們建造了另一個詩意葳蕤的世界。至此,想象成了詩人真正的創(chuàng)造抒情的想象。這種意象度集中而銳利的想象方式帶來了其詩歌語言的特殊肌質(zhì)、紋理,具有不能為散文語言所轉(zhuǎn)述和消解的本體性。我想,所謂的詩意還包括此吧——現(xiàn)實與想象間的遙遠距離,及其所導(dǎo)致的一種會飛翔的語言。
對梁曉明詩歌語詞的感受性和其想象之光的論述只是一種外圍式的逡巡,遠沒有進入其詩歌的內(nèi)質(zhì)。那么梁詩的內(nèi)質(zhì)又是什么呢?我認為它是一個堅固的核,核的中心是巨大的存在感。對梁曉明來說,詩歌遠非是一剎那的感興,瞬間的哀樂,詩更是存在之思,是對生命的澄澈,寫詩就是精神的突進。出于這樣的信念,深入、進入成為了詩人內(nèi)在的努力向度。在《進入》中詩人唱道:“我經(jīng)歷過風,我深入過最早的語言”。進入詩,進入語言,也即進入時間、生命、歲月、存在的深處。詩歌寫作是語言和存在同時打開的過程。所以,詩人又唱道:“在棉花地里我深入過季節(jié)”(《進入》)。“我能否深入泥土?深入花?”“我曾經(jīng)深入過最早的稻谷?”(《深入》)“曾經(jīng)深入人間”、“曾經(jīng)深入畫眉和危巖”、“深入過權(quán)力”(《偈》)。這一切的深入和進入無疑是對生命、歲月、存在的多向度、多方面的掘進和勘探。而這種進入深入又是那樣的犀利堅銳,原因是“在風的永恒吹拂下/我變成了一把刀子”(《刀子》)。尼采說過:真詩人是用刀子對他們時代的美德的胸膛進行解剖的。對梁曉明來說,這種解剖不僅如此,還是對于自我心靈史和精神史的無情解剖:“哪怕我被顛簸出車廂,在亂石撞頭的血液中/我依然堅持在血液中剝、強忍著疼痛朝向往中剝……”(《剝》)這使我們領(lǐng)略到了“解剖”的痛楚與入木三分的犀利。難怪詩人會立下這樣的誓言:“我將說遍你們的屈辱、光榮、尷尬、丑陋/我用大海的語言,鋼鐵的心”(《說你們》)。
在進入的同時,詩人也退居收縮,從世俗的存在中退居到個人化的心靈空間。“我也將退居,在嬌小的窗前/在自己擦亮的天空之下”(《進城》),“我越狹小越空曠,越孤獨越是騰出了容納世界的寬大曠野”(《我和詩歌的關(guān)系》)。進入,是對“在”的不倦追思;退居,是對“詩”的永恒堅守。退居下來的我甘愿做一棵樹的等待,“我是樹,等待便是一切/我是樹,或者我就叫等待”。等待的日子就是做蛹的日子,自己研究自己的臉的日子,是另一側(cè)面的進入。所以說,進入和退居互為條件又互相打開,是個“二而一”的問題,二者構(gòu)成了梁曉明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精神路向和致思趨向。
沿著上述的致思趨向,梁曉明詩中的思之在主要有:對死亡的沉思,對時間的沉思,對黑暗的沉思。三者渾融在一起構(gòu)成了梁曉明詩歌形象中一種深沉的存在音色。這種深層體驗總是關(guān)乎人本體屬性的命運、死亡和愛憎,就是要使人去直面人生之真,去解人生之謎,使人的生命達到一種澄澈透明性。
費爾巴哈說過:世間最殘酷最摧殘人的真理就是死亡。有人還說過:“死亡與詩歌是錢幣的兩面的藝術(shù)。”是的,死亡是詩歌最持久的贊頌和最偉大的沉思,對死亡的思索是詩人的共同主題。作為一個存在感極強的詩人,梁曉明自不會不去思索死亡。在他那里死亡首先是身體的冷卻,聲音的消失,視野的消失,知覺的消失,被滔天的洪水淹沒,被無限的黑夜覆蓋。“最后的鐘聲終于翻開了我的瓦片/我身體的各個房間都開始冰冷”(《尾聲》),“感覺上我的皮膚、肝、腎、腸、肺、膽,/結(jié)冰的日子”(《水》)。死之國度是一種黑暗的想象性空間,密實和沉重仿佛使黑暗物質(zhì)化了,它遮蔽了人物的視線,讓人覺得整個世界在垂直地向地獄沉去,“在世界的盡頭鳥從來不飛/在世界的盡頭我沒有消息”(《石碑上的姓名》)。但是詩人不會在這一慣常的認知面前止步,在《挪威詩人耶可布森》中他繼續(xù)深化這一死亡的命意,在死亡中尋求高于死亡的東西。“他說死/不是死/死/是一縷煙/在空中/漸漸散開/的/透明過程”。這也許是死,但更是變化,死亡寄寓于無限的化身之中,這個過程“已經(jīng)沒有邊緣,可到處都是邊緣/已經(jīng)沒有了生長,可到處都是生長”(《石碑上的姓名》)。梁曉明的死亡觀的實質(zhì)在于他懷疑在死亡和生命之間是否真的存在對立,或者說它們兩者之間是否真有明確的界限。所以,“死去的人在風中飄蕩/正如我們在時間中行走”(《最初》),彰顯的是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生死觀,即死亡就在生活本身之中。顯然,梁曉明的生死之辯既有傳統(tǒng)文化中盤古垂死化生和梁祝化蝶的神話影子,又有現(xiàn)代哲學(xué)中存在主義的思考。
弗雷澤曾說過,人是先有死亡意識從而才有時間意識的生物。對死亡的感知理所當然地就會帶來對時間的省察。梁曉明還是一位有強烈時間感的詩人,他在詩中多次感知時間、諦聽時間,或?qū)r間拉長、變軟、無限延伸,或瘋狂地撲向時間,攫取時間,在瞬間中感受著永恒。他所注重的不僅是時間的尺度,還有時間的色彩和形態(tài)。“時間紛紛從頭發(fā)上飛走”(《但音樂從骨頭里響起》),摹寫出時間如驚鳥一掠而逝的情狀;“我喜歡風鈴/我喜歡敲打?qū)庫o的風鈴/坐在孤寂的家里,停下來和歲月相依相伴的風鈴”(《風鈴》),表示與時間緩慢流逝的親近。有時詩人還會聽到時間之箭穿過空氣時在耳邊留下的寒冷而恐怖的聲音,“我的時間不多,我做得更少/我看著墳?zāi)乖絹碓郊钡叵蛭艺惺帧薄r間的感悟使詩人遠眺人的生命整體,為生死之間成長和衰老的急遽短暫而抒情。人,作為生命的個體,盡管有往上飛翔的生命愿望,“眼睛在太陽上生長出旗幟”,但無可阻擋的是“歲月樓梯一樣往下去的日子”,死亡的降臨是必然的宿命。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歷史的片斷,“所以你我的臉只是一塊蠟,生命是一場風/在夏天的活躍中我們最活躍/在冬天的冰冷中我們又最冰冷”(《問》)。但是,在時間翻飛的手掌下,詩人試圖“將時間里的琴弦/齊聲撥響”,“從時間中將真理確定”,把寫作放在季節(jié)的門外,追求高于生命的永恒價值。這不由讓人想起紀德的“花開在時間之外”,在生命中尋求高于生命的東西。這樣一來,“在我的死亡中你永遠不死/因為我逝去你再度擴寬了永恒”(《允許》)。思想者會死亡,思想?yún)s永遠不會止息,思想的疆域會因為思想者的探索而不斷被拓寬延展。
梁曉明的寫作還從已知的境界向黑暗行進,沉入到黑暗的無限之中。他在《無論我愿不愿意》中寫道:
無論我愿不愿意,天還是黑了下來,
它從門外黑進窗臺,又從屋頂黑到了桌面,
它很快黑到了我的手指
我如果不開燈
我心里就會裝滿黑暗
我的心里已經(jīng)黑暗,它揮著歡快的小手
擠在眼睛邊,它要走遍我的全身
它要在血液里扎根和發(fā)芽
我要起身開燈,但我卻紋絲不動
我看到黑暗降臨大地
我不能幸免
遙遠的星星自己發(fā)光
像一粒粒
自在的螢火蟲
它越過時間,獨自前行
直到與黑暗相敬如賓
該詩抒寫的是夜的黑暗如何像潮水一樣從“我”的眼睛里一直涌向“我”的心間。人性的幽暗意識、內(nèi)心的黑暗像夜晚一樣,時時刻刻都會降臨,無論我愿不愿意,它都會以強有力的方式侵襲過來。波德萊爾在《湯豪澤》中說道:“任何發(fā)育得很好的頭腦自身都帶著天堂和地獄這兩種無限并在這兩種無限之一的任何形象中突然認出了自己那另一半”。瓦雷里曾說過,每個人身上都隱藏著黑暗的東西。這種黑暗就是我們各人自身所帶來的無限。對之,光明必須正視接受,“遙遠的星星自己發(fā)光/像一粒粒/自在的螢火蟲/它越過時間,獨自前行/直到與黑暗相敬如賓”。詩人看到了光明與黑暗兩種勢力并轡而行。不僅如此,詩人還有暗中發(fā)現(xiàn)亮的能力,希望從黑夜中萃取出“黃金”,提煉出“精神的黃金”(《黃金》)。
梁曉明的上述詩思,從來都沒有絕對化,生與死、光明與黑暗、時間與永恒不是截然的二元對立,而是對立與對應(yīng),互否與互補,如雙腳般相互制約又相互提攜。“最高的啟示/恰恰來自最低暗的觸動”(《故宮》),“而最高的責問/也恰恰是世界上最低的責問”(《深入》),“在最上品的歌聲中/我恰恰看見下品/最鋒利的刀刃口我恰恰看見了遲鈍”(《慚愧》)。過強的思辨性使梁曉明成為一位哲思型詩人。他曾說過這樣的一席話:“情感,這是一柄兩面開刃的利刀,幼稚與不成熟的詩人很容易受傷害。為什么我國的許多詩人和許多詩,都把情感當成了生命的歸宿?詩歌的惟一家鄉(xiāng)和泉涌?這恰恰是一種障礙、一塊擋路的巨石。在此,多少人將詩歌轉(zhuǎn)向了發(fā)泄(正面的和反面的)?又有多少人青春的才華一盡,便再也寫不出像樣的作品?這也是我國的詩人為什么詩齡短,給人造成只有青年時代才是詩的年齡的錯誤的傳統(tǒng)認識。”正是意識到把感情當作詩歌表達的惟一內(nèi)容的弊端,所以詩人才在詩中追求主智的大腦。
更重要的是,梁曉明的詩思不是空洞空泛的形而上玄思,而是對可觸摸的此在生命與歷史的感悟。詩人通過將死亡、時間、黑暗等融化在自己的血肉中,在死亡、時間、黑暗中悄然蓄入一己內(nèi)在的體驗,從而使它們成為對自己生存經(jīng)驗的更高程度的綜合。詩歌,對詩人來說,是對存在的認識和對于真理的表達。如果沒有這些形而上的理性思考,詩人不可能使詩歌一下子抵達人生本質(zhì)。誠然,思想的縱深是沉重的、艱澀的、辯證的,但詩人借助于超拔的想象力把靈魂之思一定程度上轉(zhuǎn)化為身體上的感應(yīng),不僅達到了思想的飛翔,還使思想具有可觸摸性。梁曉明的思辨在感性中游走的運思方式無疑會把我們的審美視線牽引到二十世紀左右象征主義的詩藝觀去。愛爾蘭詩人葉芝稱寫詩為“身體在思想”,所謂“身體在思想”,便是身體的所有部分都要調(diào)動起來,像腦一樣去感覺生活。他并且接著說“詩叫我們觸、嘗,并且視、聽世界,它避免抽象的東西,避免一切僅僅屬于頭腦的思索,凡不是從整個希望、記憶和感覺的噴泉噴射出來的,都要避免”。對之,瓦雷里稱為“抽象的肉感”,艾略特稱為“思想的知覺化”,即將思想還原為知覺,“像你聞到玫瑰香味那樣去感知思想”。這一切在梁曉明那里就轉(zhuǎn)換為這樣的詩句:“詩歌沿著我兩條眉毛向后腦發(fā)展/詩歌擁抱我每一根頭發(fā)/在每一塊頭皮上它撒下谷種/詩歌在我的鼻孔里醒來/醒來就迅速張起篷帆/順流而下”(《詩歌》)。梁曉明把詩思的震顫、回聲延續(xù)到感覺(觸覺、視覺、聽覺、嗅覺等)的邊界,反過來,這種感覺的敏銳是和思想的深刻和對事物的理解的深度分不開的。詩對思的形而上的哲理探尋又都是被富有啟示性的、詩意盎然的話語緩緩瀉出的。所以,對梁曉明來說,詩歌遂成為思想與詩歌語言、想象、感受性的統(tǒng)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