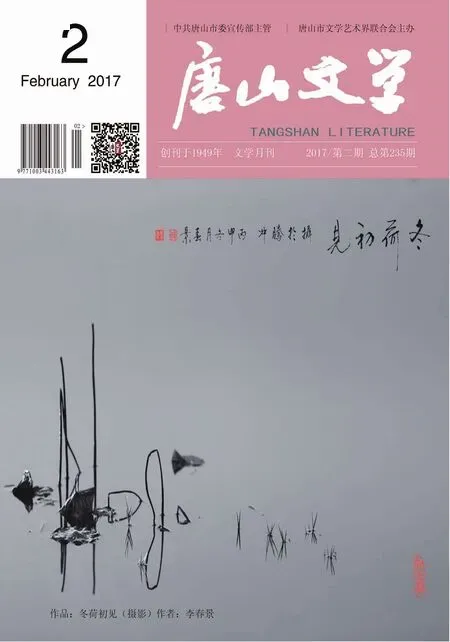從教學實錄出發論錢夢龍課程觀及教材觀
李紅麗 孫 勇
從教學實錄出發論錢夢龍課程觀及教材觀
李紅麗 孫 勇
錢夢龍老師在八十年代提出 :三主四式:教學理念,在他的教學理念中表現出他獨有的課程觀與教材觀。本文試從他的《愚公移山》和《少年中國說》教學實錄,探討他對語文這門學科的課程觀與教材觀。他認為語文這門課程一定要抓住其本質特征,對下一代進行民族語教育。對待教材既不要死扣文本,也不要隨意歪曲,使其工具性和人文性達到統一。
錢夢龍是我國著名的語文特級教師,對語文教育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三主四式”語文教育思想。雖然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是錢夢龍的“三主四式”語文教育思想對現在的語文教育仍有很大價值。“三主四式語文導讀法”是指以發展學生的智能為前提,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為主要目標,讓學生通過三到六年有計劃的訓練,達到“不待老師教而學生自能讀書”的目標。其中的“三主”語文導讀思想可以概括為“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以訓練為主線”。主要揭示了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問題,以及如何教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的問題。在這個理論上錢夢龍老師提出了課堂上的“四式”教學法,“四式”是指四種基本課式:自讀式,教讀式,復讀式,練習式。這種教育模式把教師的接力棒交到學生手中,使學生在教師的引導下圓滿完成教學任務,實現教學目標。
在《愚公移山》這篇課文的教學中,錢老師帶領大家先辯體析題。大家利用工具書初步了解了寓言這種文學體裁的特點,老師進一步就本文提出問題:這個故事寄寓著什么深刻的道理?我們應該受到什么教育?大家帶著問題進入自讀,借助于詞典和課本的注解,逐字逐句讀懂課文。這正是錢夢龍老師提出的自讀。自讀不是學生隨心所欲、各取所需的“自由閱讀”,而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的有目的的訓練過程。這種方法貫穿于課堂始終,很好地體現了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理念。在對自讀時的問題討論中老師也盡量讓學生自己解決。如有學生問“曲”字的意思時,老師先讓學生回答,大家都不會時就查字典解決,老師指導大家選擇正確的釋義。而在這其中錢老師是緊扣文本的教學。學生在自讀后一般都是認讀,就課文中的字詞進行學習。這體現了語文的工具性:字詞的辨認和理解。錢老師在他的教育觀中提出:語文這門課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他認為“語文課如果抽去了工具性,抽去了識字、寫字、閱讀、寫作、思維、口語交際等基本技能的訓練,就不再是語文課而變成了別的什么課,可見工具性是語文課程區別于其他課程的本質屬性;而語文課如果抽去了人文性,雖然還是語文課,但卻失去了精、氣、神,變成了僵死的語文課,可見人文性是語文課程的必要屬性。”同時錢夢龍老師是反對文言文串講這種教法的。當時教文言文多是“字字落實,句句清楚”,老師一字一句“嚼爛了喂”,以應付考試,把課文肢解得七零八落。文章不再是飽含思想感情的篇章,而變成了碎片化的按照一定規律串聯起來的實詞和虛詞。錢夢龍老師提倡“文言文首先是‘文’,就應該把它作為飽含思想感情的‘文章’來教,詞句的解釋應該在理解文章意蘊的前提下進行”。在《愚公移山》這堂課上,錢老師就是通過對人物和人物情感的把握去學習字詞,很好體現了語文這門課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這堂課教學環節分為四步:
第一,初步理清人和事。經過學生一起學習,明確人物:愚公、其妻、其子孫、遺男、智叟。在熟悉人物特征中,使學生掌握了“且”;“叟”;“齔”;“遺男”;“孀妻”等詞的含義。在這其中錢老師采用了“曲問”。這是錢老師所提倡的巧問的一種表現形式。簡單來說就是“問在此而意在彼”,讓學生的思維拐個彎才能找到答案。如本課中,要了解學生對“愚公年且九十”的“且”是否理解,錢老師沒有直接問,而是問“老愚公多大年紀了?”令學生思考一下悟“且”的含義。其余的詞也都采用了此法,意在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并使學生開動大腦。這對教師也是很大的考驗。提的問題要環環相扣,還要具有啟發性。由人物引出本文寫的事-移山。錢老師問這事做起來難嗎?然后讓大家從文章中找出句子來說明。體現了老師的主導,同時也表明了錢老師對待文本的態度:改變傳統語文教學中“文本中心”、“仰視作者”的態度;又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一切以讀者為中心隨心所欲地解讀文本,而完全無視文本的存在。在課堂上錢老師在對學生提問引導時,常常讓學生回到文本中找答案。學生回答問題時根據書本上的內容回答,這樣解決問題才能有說服力,也更深刻地理解課文。如學生問“本在冀州之南”的“本”的意思時,另一學生回答“因為太行、王屋二山后來搬走了,不在這個地方。”錢老師表揚了回答問題的同學,肯定了他思前顧后地讀文章。通過學習使學生從文本中了解參加移山的有五個人,而山“高萬仞”“方七百里”,通過分析明了任務艱巨。后面錢老師小結了一下:移山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能顯示出人們不同的精神面貌。指導學生體會文章的人文精神。
第二,分析人物對待移山的不同態度。明確:智叟“笑”,譏笑;其妻“疑”,獻疑;其子孫“許”,紛紛贊同;遺男“跳”,高興。在分析智叟態度時讓學生從文中找出“汝之不惠甚矣”,不但講出了它的語法意義-倒裝句,而且指出運用倒裝強調愚公不聰明到了極點。知識與情感的培養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還有在講到智叟和愚公妻稱呼愚公時的不同,一個是“汝”一個是“君”,運用對比來表現出不同的情感態度。在比較智叟和愚公妻對待愚公移山這件事的態度時,錢老師“現在請你們再在文章中找出兩個字來,把兩人的態度分別用一個字說明一下”。學生答道:其妻是“疑”,智叟是“笑”。錢老師又引導學生理解這兩個詞背后有什么樣的感情。這樣一分析學生就能體會出差別了。在學生讀懂的基礎上,把隱含在文字背后的意義給學生指點一下,使學生悟出隱藏在文字背后的意義。這就是老師在指導學生學習與文本對話。教師的“導”主要是控制對話的方向,營造對話的氛圍,使學生保持參與的熱情,使對話始終圍繞當前的話題。錢老師把學生當作具有發展潛能的人,而不是教師見解的復述者和被動的知識接收器。引導學生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發現問題。這樣會使學生更好地理解文本,體會出人物態度的不同。不同的態度顯示出不同的精神境界。
第三,分析愚公笨不笨,智叟聰不聰明。先討論其他人對待移山的態度,自然引到移山事件的主人公,水到渠成,學生易于接受。而且這個問題具有一定的思辨性,需要老師引導。愚公笨不笨,錢老師不是讓學生隨意發揮,而是指導學生根據文章找答案。先找出愚公移山的動機“懲北山之塞,出入之迂也”;再找移山的好處“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得出愚公是明白自己要做事情的目標的。又用當代大家對待一名公共汽車售票員的不同態度,使學生明白一件事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結論。從而引起學生思考、探索的欲望,也體現了錢老師對課堂較好地把控。后又引入文本中,讓學生得出結論—愚公大智若愚,而一對比就得出智叟—小聰明。學生尋求答案的過程,正是對文本理解逐步深入的過程。學生學習是個特殊的認識過程,但在其中學生是認知的主體,他們的認識要通過自己實踐和感知得來才印象深刻。灌輸得來的認識,即使老師講解的面面俱到,印象也不會深刻。在指導學生學會閱讀的過程中字詞句逐一落實,學生也自然而然受到課文中所蘊含的思想情感的熏陶。
第四,辨析移山靠愚公還是神仙。經過討論得出愚公精神感動了天帝,顯示了愚公挖山的精神感人至深。在得出愚公大智若愚之后,學生自然得出“神仙搬山是因為愚公感動了上帝”,“操蛇之神他已經怕愚公了”的認識。從一開始任務艱巨,在有人懷疑有人譏笑的情況下依然堅持,最后感動天帝,層層深入,很好體現了愚公的精神,也顯示了錢老師較高的處理教材的能力。錢老師提出“會讀”才能“善教”。老師要教會學生讀文章,首先老師自己要會讀文章。老師若是確實讀好了文章,“得之于心而不是僅僅求之于書”,那到處理教材和選擇教學方法時就能得心應手。錢老師的“會讀”與“善教”都是建立在充分體現學生主體性的前提下的。破除教師講解課文傳統的“授-受”方式,把語文教學的著眼點轉移到鼓勵學生自己讀課文,強調學生認知的主體性,“喚醒”學生讀書、思考、求知的欲望。“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小心翼翼地保護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導讀”的過程若沒有學生的主動參與是失敗的。然后老師一步步指導學生理解文本,滿足學生的認知需要和審美需要。
“事后張春林對我說,當時定下這篇課文,他是有些擔心的,怕我‘創新’得太離譜,比如誘導學生去批判愚公‘缺乏科學頭腦’,稱贊智叟是‘智力型人才’,或提出‘移山不如搬家’之類的見解,因為當時正有一些同志在報刊上鼓吹這類時髦的`新'思想。聽課以后他放了心。因為我不僅沒有否定愚公精神,沒有削弱這篇傳統課文固有的教育功能,而且把‘文’和‘道’交融得那樣自然熨貼。他認為,傳統課文被教出了新意。”但現在也有人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情況下,錢老師的課可以說是非常完美,既突破了文言文教學“串講”的傳統,又關注了語文教學的人文性和實踐性。但是,與當前普遍要求關注學生主體性,注重探究學習來講,對學生獨立思考,批判爭論、自主建構能力培養方面還顯得不夠。”我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這堂課是面對初二學生,他們獨立解讀文本的能力是不足的,還需要老師的指導,而且要有批判、有創新首先要對這件事有全面深刻的理解。還沒走穩就要跑是容易摔跤且跑不遠的。沒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下的批判與創新是經不起推敲且誤人子弟的。任何一篇文章都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創作的。你偏要拿現在的情形去解讀不同歷史條件下的文本,去批判去創新是不尊重客觀事實的。而初二的學生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自我意識逐漸加強,但看問題還不全面,一方面容易迷信權威;另一方面又易反叛權威。這時需要對他們加以正確、積極、清晰地引導。錢老師在課堂上采用師生平等地問答互動;課文經過大家的認真思考,共同探討;以思維訓練帶動語言學習,以語言學習促進思維訓練的教學方法,又把人物精神加入其中,有利于引導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錢老師的教育理念很明確:培養學生自學能力。而錢老師的教法就是要學生先學會閱讀文本,學會與文本對話。培養良好的語文素養,為學生的終生學習打下基礎。
學習完課文后錢老師讓大家一起做了一個作業。這個作業是篇文言文短文,請學生給其加標點。短文由課文中的文言詞語和句式連綴而成,這樣的斷句練習,因為詞語、句式大多已在課文中遇到過,舊詞句,新環境,內容與課文相關,這樣既能擴大學生的知識面,加深對課文的理解,同時又有助于知識的遷移。這也是錢老師“以訓練為主線”的教學理念的體現。在提倡素質教育的今天再談“訓練”好像有些不合時宜。有人將“訓練為主線”與“工具說”綁在一起,批判訓練為主線。我覺得有些矯枉過正。訓練只是一種方法,本身沒有什么對錯,只是看你如何使用它。語文是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而語文課程的“工具性”主要表現在語文能力的培養上。學生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訓練的結果。新課標中提到語文素養這個基本概念,但目前也沒有權威性的界定。錢老師認為語文素養包含了如下這些素養:“1.必要的語文知識;2.較強的語文能力(閱讀、寫作、口語交際等能力);3.對祖國語言的深厚感情和正確態度;4.較高的文學審美趣味和能力;5.較寬的文化視野。”而其中語文能力是決定因素。初中的語文教學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學生的讀、寫、聽、說能力,而這種能力是需要在訓練中摸爬滾打得來。而語文課程的人文性是在掌握其工具性的過程中通過讀寫聽說等的具體學習潛移默化習得的。錢老師在學習完課文后緊接著的訓練也有復習的作用。德國心理學家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對遺忘現象做了系統的研究,把實驗數據繪制成一條曲線,稱為艾賓浩斯遺忘曲線。曲線表明了遺忘發展的一條規律:遺忘的進程不是均衡的,不是固定的一天丟掉幾個,轉天又丟幾個,而是在記憶的最初階段遺忘的速度很快,后來就逐漸減慢了,相當長的時間后,幾乎就不再遺忘了,這就是遺忘的發展規律,即“先快后慢”的原則。所以錢老師對學生進行這樣的訓練一舉兩得。錢老師提倡綜合的、立體的、生動活潑的訓練,通過這樣的訓練實現語文“兩性”完美的統一。學生要學會讀書,學會與文本對話,就必須在教師地指導下進行閱讀訓練。在這樣的訓練中學會讀書,積累知識,培養能力,使思想情感和審美情趣得到熏陶。最后錢老師在大家做完練習后,借用訓練短文中的一句話“若我十億中國人,人人皆為愚公,則山何苦而不平,國何苦而不富?”又進一步引導大家認識愚公精神,前后呼應。
錢老師認為設置語文這門課程是為了對下一代進行民族語教育。而漢語言文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與其它的拼音文字有著明顯差別。漢語遣詞造句主要依靠語感和對詞語的語境意義地把握,不像英語或法語有那樣多的形態變化顯示句子的關系。所以我們的語文教學就要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而閱讀教學就是一種重要的方法。教材中選出的文章都是我們民族語中優秀的篇章,通過對它們的閱讀,可以讓學生很好地學習漢語。但要避免兩種情形:一是死扣文本,進行字詞句肢解式教學;二是架空文本,憑空進行人文精神教育。語文教學要緊扣文本,但一定要把文章的精神熏陶體現出來。在教《少年中國說》這篇課文時,文章結尾處有一段贊頌少年中國的韻文“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這段每句都用了比喻,讀起來令人情感激昂。錢老師問學生讀到比喻句時要做什么?沒想到學生一致表示要先找出本體和喻體。優美的文字組成令人感情澎湃的文章,沒想到被教成一堆堆本體和喻體,完全失去了文章的美,不得不令人遺憾。而錢老師引導大家展開想象,展開想象前老師解釋了“河”、“鷹隼”、“初胎”等詞語,然后大家閱讀想象,后來請班里文章寫得最漂亮的一位同學把她想象中的畫面描繪出來。描繪的很好,錢老師尤其提到她描繪“一輪紅日剛從東方升起”,很好扣住原文“紅日初升”,讀書很細心,顯示了錢老師對文本的尊重。但后面有同學對“初胎”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是含苞初放;有的認為是含苞欲放。錢老師并不要求標準答案,讓同學們根據自己的想象去發揮。這一方面體現了對學生主體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語文這門學科人文性的注重。《少年中國說》這篇課文文字流暢,作者情感強烈,很有感染力,錢老師采用了背讀法教學。他指導學生在體會作者對國家前途滿懷信心的感情下,理解文意找出作者的寫作思路背讀課文,在背讀的過程中又加深了對文章的理解。到第二節課結束時,學生幾乎已能背誦全文。
錢老師在他的教學理念下,緊扣文本教學,重視語文課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提出語文教學是對本民族語的教育,要尊重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讓學生多接觸文本和語言,在聽說讀寫中熟練運用自己的民族語,吸收精神養料,表達情感,與人交流。隨著時代的進步與發展,不斷會有新的理念的提出,但優秀的思想是經得起歲月洗禮的。錢老師對語文教育事業的貢獻時至今日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李紅麗(1974-),女,河南沈丘人,碩士研究生,陜西理工大學學科教學(語文)專業,研究方向為語文教育。
孫勇(1972-),男,安徽廬江人,現就職于陜西理工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