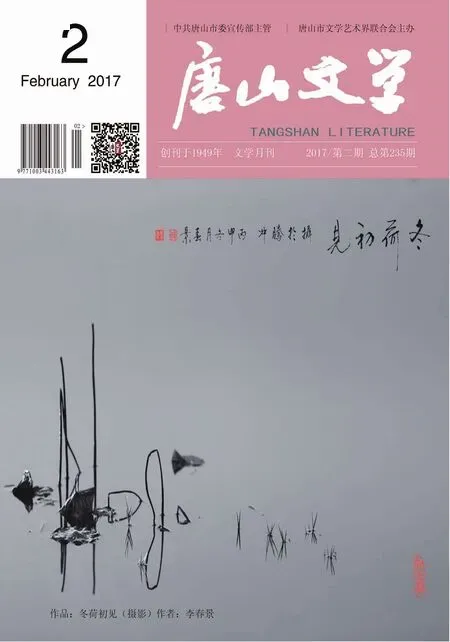網絡玄幻小說主題人物研究
張培
網絡玄幻小說主題人物研究
張培
網絡玄幻小說移植和借鑒了大量歷史故事和傳說,所以才妙趣橫生,富有魅力。因此研究網絡玄幻小說人物是較為恰當的角度。論文以師父形象和至尊形象為例探討了網絡玄幻小說主題人物背后的社會文化成因。
一、“師父”形象:當代人性深層的窺探和解讀
“師父”作為千百年來文化傳承和技法流傳的施教者,在民間傳統和文學作品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宣揚和贊同,得到了社會大眾的廣泛認可和贊許,也消弭了讀者潛意識里對權威的抵觸和排除,成為了代表非凡能力和善良寬容的人物標識。而且在寫作過程中,用“師父”替代父母這一角色既擺脫了難以言表卻又不可或缺的父母親情的束縛和羈絆,又可以寫出類似親情卻勝似親情和亦師亦友的“師徒情”,也使得讀者由對傳統親情體會的麻木狀態轉變為對這種新鮮靈活的師徒情誼的欣賞和贊美。
另外,網絡玄幻小說的大部分受眾為學生、打工族、白領等年輕讀者群體,雖然他們都認同父母在自我成長過程中發揮的無可替代的教育作用,但內心深處卻對父母這一角色存在某種心理隔閡,不能完全徹底地對父母吐露心聲,尤其是那些正處于叛逆時期的青少年,更是對父母存在極大的情感排斥和行為反叛。但是他們內心深處又總是期望能有一位完全了解自己內心世界,能給予自己支持和鼓勵,在關鍵時刻給予自己必要幫助且無怨無悔的“知心長者”。而且,師徒情誼是從古至今中國歷史中不斷傳承備受推崇的親情佳話,是亦師亦父和亦徒亦子等親密關系的完美寫照,更是深入中國文化傳唱不休的文學美談。
二、“至尊”形象:終極意義的哲學化探尋和對庸常生活悲劇性的解構和顛覆
由于借助于靈寶、靈獸和所修煉的神功,網絡玄幻小說主人公往往無所不能,甚至能創造新的宇宙(如秦羽)。這種強大而浪漫的主體形象具有強烈的現實反諷意義。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中,人曾經所具有的美好形象遭到徹底的解構和顛覆,或者說,原來附著在人身上的意識形態的美麗外衣被剝掉了。首先,從認識論上,人的傳統的現代主義的哲學地位遭到后現代主義哲學的挑戰。人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歷史的能動“創造者”,而是卑微渺小的福柯意義上的“沙灘上的足跡”,很容易被各種力量抹去。其次,在現實層面上,人的主體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殘和打擊,這也正是產生后現代主義哲學轉向的深刻原因。就業難、買房難,甚至結婚難,都成為當代青年人必須面對的生存難題,這種生存壓力是前所未有的。因而,當代人會感到悲劇是日常性的,正如舍勒說的:“確切地說,悲劇性系宇宙本身的一種基本要素。感到痛苦是永恒的:“痛苦成了真理的本質,而幸福生活卻成了空虛的事實。因而,當代人所面臨的主體性的悲劇是實實在在的,既是全球性的悲劇性事件,也是本土性的問題。因而,網絡玄幻小說中高大完美的主體形象,具有重要的現實反諷意義。
三、消費主義思潮下文化與權力的沖突與桎梏
受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所啟發的文化研究認為,文化既不是一個“真正的”敵對階級的文化(或任何其他從屬的文化),也不是由文化工業所施加的文化,而是一個兩者之間的“折衷均勢”(compromise equilibrium)也就是說,文化是一個沖突力量的混合體,這些力量包括來自“下面”的和“上面”的力量,“商業”的和“真實”的力量,被標示為“抵抗”的和“團結”的力量,“結構”和“主體”也都參與其中。
第一,自由開放性。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創始人之一約翰.P·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網絡/賽博空間獨立宣言》中說到:“我們正在創造一個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可加入,不存在因種族、經濟實力、武力或出生地點生產的特權或偏見。我們正在創造一個世界,在那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達他們的信仰而不用害怕被強迫保持沉默或順從,不論這種信仰是多么的奇特。”正如他所說,網絡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平臺,每個人不論年齡、性別、貧富、地位高低、距離遠近,都能夠超越差異和局限,以平等的身份進入網絡空間暢快交流,而這種平等在現實世界中是很難實現的。
第二,交互性。
研究玄幻小說主題學中文化與權利的關系實際上也是大眾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反叛與重構。主流文化,也叫主導文化,是一種表達國家正統意識形態的支配性文化,它以“主旋律”為文化表達形態,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一種體現,是處于政治場引力作用下的一種重要的文化力量。國家意識形態提倡什么,鼓勵什么,主流文化就要依據這些問題去表意,以整合社會各個階層,保障良好的社會秩序,滿足社會對文化的需求。(布爾迪厄的社會學理論)主要包括:大眾文化的狂歡精神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巴赫金《狂歡主義》),玄幻小說借主流文化的“殼”來表現社會和人生。大眾文化對主流文化凝聚力的削弱:去權威、去中心、平面化。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110136
張培(1991-)男,漢族,山西太原人,文學碩士,遼寧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