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為誰而鳴?
何宇軒
1
2016年11月,一則音樂會報道赫然充斥各大古典音樂社交媒體版面——俄羅斯小提琴家維多利亞·穆洛娃在上海演奏會后于推文上劍指中國聽眾“沒素質”:
一半上海聽眾在我演奏巴赫的時候從未中止地拍畫質低劣的照片和視頻,而寧愿錯失聆聽音樂的重要性。
我就想知道,這些拍視頻的人之后會拿這些視頻做什么呢?難道他們就喜歡那種糟糕的聲音和模糊的圖像嗎?
消息一出,中國愛樂者和當時在場的聽眾紛紛表示“抗議”。他們反駁道:確有一些人在演出過程中使用手機拍攝,但人數連三分之一都不到,更別提“一半”了。且完全沒看見有人“從未中止”地拍攝,都是偷偷地拍兩下,然后收起手機(這種事兒雖在國中居多,但在國際音樂廳里也并不是完全沒有)。這樣刻意夸大事實“罵人”的做法,實在不是一個被人口口稱道的藝術大師該有的風范。
于是乎,一場關于是聽眾還是演奏家素質低下的爭論占據朋友圈、微博熱點頭條,甚至一些非音樂愛好者也紛紛刷屏轉帖。
2017年5月,我剛忙完大學畢業雜事,坐四小時短途飛機去蒙特利爾閑散一番。傍晚,聽了一場早先訂了票的長野健與布雷哈馳(Rafal Blechacz)在蒙特利爾交響樂團的音樂會。上半場“老肖第十五”樂章間隔,聞一坐席老人手機鈴聲大響莫扎特《土耳其進行曲》。鈴音實屬太大,全場觀眾皆驚。只見本來準備開始指揮的長野健驟然轉身,嘴角上揚,用法語面向老太道:“這可能是加演曲目,現在放還有點早。”
對比之下,這樣的玩笑既可愛又不失禮節,與穆洛娃事后諸葛又帶有恨意的做法有著天壤之別。結果是,聽眾哄然大笑,隨即慢慢安靜,默待第二樂章到來。
為何兩位音樂家對待聽眾“不符合規定”的行為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難道他們的音樂追求如此不同嗎?
這么一問,關于“素質”的問題在我腦袋里更加作怪了:“素質”到底是何物?演奏家僅僅是音樂的“代理者”嗎?聽眾是音樂“唯一”的聆聽者嗎?一場音樂會上,演奏家需求什么?聽眾又需求什么?或者再簡略點:
音樂究竟為誰“發聲”,又因誰而發生?

2
音樂當真只為自己演奏嗎?
大藝術家最常被人解釋的“氣派”——他們不在乎他人,他們只為自己創作。
他們只為自己演奏!
格倫·古爾德,而立年始逐漸作別音樂廳,隱匿自我,好像遺世而孤立的藝術王子。從單一緯度看,古爾德確可稱為“為自我演奏”的人。但古爾德稱自己喜愛沙龍氛圍,坐擁滿堂的音樂摯友才是他的音樂理想。而且,他做電視節目、錄制唱片來推廣音樂。——古爾德不愛接觸人,但希望有品位的人欣賞他(或者互相交流),亦希望通過電視和錄音為聽眾傳遞藝術信息。而這攝像機和錄音筒的“對面”不正是大眾么?這些大眾的數量動輒萬千,豈是一座音樂廳容納得下的?古爾德走出音樂廳,卻獲得了更多的聽眾。

如此說來,不想接觸人與單純為自己演奏很可能是兩件事情——古爾德不愿接觸人,但他為聽眾演奏。
再回憶少年懵懂時期的自己。傻乎乎,經常是一到深夜,照著根本看不懂的樂譜,想象著歌劇院舞臺的富麗堂皇,憑借記憶大聲哼唱威爾第的詠嘆調。當時心想:這音樂是給自己唱的啊!但仔細推敲根本不對——觀眾不在現實,卻“生活”在幻想里。那幻想中的舞臺和動人的嗓音,其實是為歌劇院里的觀眾而“存在”的。此刻端著樂譜一臉呆氣卻躊躇滿志的我,其實“表演”的是舞臺上那個為聽眾表演的美聲男高。
只給自己演奏或創作的思維模式也許根本不存在。許多巴洛克作曲家為教堂寫作,他們對應的聽眾是教會人員、信徒,甚至(心里想的)可能是上帝本人。古典主義音樂家為宮廷創作,并開始向大眾過渡。浪漫主義時代,世俗全面襲來,作曲家直接面向聽眾,或是沙龍,或是音樂廳。樂評人、批評家也粉墨登場,音樂家的身份逐漸走向現代。如此看來,音樂家其實一直是有“對應”的聽眾群體的,他們在寫作或演奏時分也定會以聆聽者角度考慮藝術的創作思維。而對于當代人來說,即使是自己“瞎玩”,沒事拉拉琴,唱唱歌,有時也是假設聽眾存在的,或者,根本就是假設自己是自己的聽眾。這個“眾”字很重要,因為在假設自己是聽者的同時也認為自己代表了一群人或一類人的欣賞感受。我們在自我陶醉的同時,也幻想著交流的快感與共鳴的樂趣。
關于藝術是否為欣賞者而存在,杜尚有種論調,但它可能代表一個極端。這位不羈的畫家創造了“實物藝術”(Readymade),目的是去掉藝術家亙古不變的權威,以此增加欣賞者的權利。在他看來,觀眾遠比藝術家大,他們才是藝術的決定者。當藝術品的制作不是由作者本人完成,而是拿來主義——直接購買現成的商品——的結果,藝術家就再也不是“老大”了,說了算的就完全是欣賞者了。《泉》(Fountain,1917)、《自行車輪》(Bicycle Wheel,1913)、《瓶架》(BottleRack,1914)等等,其實都是“為了觀眾”的藝術。
我想,杜尚的觀念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絕對的現代思緒。聊回音樂,在現代主義到來之前,音樂都是經歷某個群體的“等待”而到來的,藝術往往是“為了觀眾”的產物。西洋作曲家少有東方水墨文人那種有感而發、即景抒情的雅致情趣。魏瑪與科騰時代的巴赫為親王和貴族創作,到了萊比錫時代,每周的教堂禱告都在“等待著”巴赫一部新作的到來,更不用說亨德爾、海頓為宮廷忙碌而辛勤作曲的故事了。總結說,這些作品因一些人群的直接“需求”而產生,它們不僅沒有泯滅天賦,反而代表著在某種規格下更高級和更純粹的天才。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慨嘆“訂件時代出天才”并非無理取鬧。當藝術的“設定”處于統一規格,創作的主題和對象也由觀者預先定好,天賦可能更容易“顯現”。同樣是畫耶穌,大小、構圖也都“按要求”類似,你若畫得好,豈不一眼便知?誰若是天才,不想與眾不同都難。相較下,今天的藝術家實在處境艱難,他們可以“為所欲為”,卻為了個人風格和刻意的創想而鬧破腦筋。每個人創作的東西都不一樣,你不揪盡全力去“與眾不同”,怎可能展現天才?逐漸,人為的造作愈發演烈,自然的天賦也就無法分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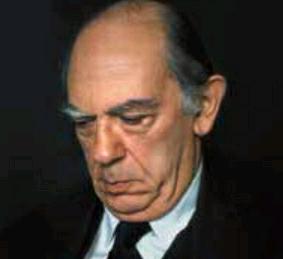
關于這種說法,你不得不說還是有它的道理的。若是諸位去過歐洲大小教堂、宮殿,或再有幸于這些場所聽過一兩場音樂會,當有如此感受——貴族音樂在宮廷聽,宗教音樂在教堂聽,還是對味。這也解釋了為何國中樂迷愛好浪漫主義音樂,緣吾土音樂廳眾多,大多浪漫主義音樂正是為音樂廳創作的。而教堂和宮殿的音樂則由于缺乏場所而潛在失去了演奏家、場所與聽眾三位一體的“對位價值”,故在我地不太吃香。雖然我們不必苛求聆聽場景,理論上所有的“聯系”都可以靠音樂引發的“高級幻想”而完成,但在音樂廳聽馬勒,在宮廷聽亨德爾,在教堂聽巴赫,總是那么撓人軟肋。
那靈感又是什么呢?靈感偶存于作曲家創作思維深處突覺遁入無人之境之時——將自己交給音樂,無所謂聽眾,無所謂自己,也無所謂時間和空間。這樣的體驗,不少演奏家也有,但它并不代表演奏的一切,這些偶然發生的“奇妙體驗”不是演奏的整體思維,僅是繆斯“突襲”的神秘旅行,演奏的整體還是要面向聽眾,曾經和現在的作曲家也還是要面對教會、宮廷、貴族、批評家和愛樂人的。當一個天才般的點子或體驗突然降臨,你也還是需要用那些“煩人的”條條框框將它們規整起來,從而完成一次完整的創作或演出。藝術的產生需要“形式”,每一個靈感都在期待某種形式去完善它,也正是這種形式促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可以具體化地為觀者或聽者欣賞和聆聽。保羅·克利(Paul Klee,1879-1940)說:
藝術既超越現實,也不是想象中的東西。藝術同現實進行著一場不可知的游戲。就像一個孩子在模仿我們,而我們則在模仿那個創造了并還在創造世界的上帝。
克利的話大致接近我闡述的意思,但更進一層。他嘗試討論藝術的產生與現實的對接關系。藝術有種本能式的靈氣,這靈氣是野性的、天真的,“就像一個孩子在模仿我們”。而現實則需要我們用學習和“模仿”來的結構去創造一個圍繞著這份靈感的“世界”。靈感本身是不能成為世界的,因為它是純粹個人的,而世界是需要相互交流而存在的,所以我們要學會如何架構它,也就是學會如何交流。話深理不深。克利還有一句名言:“偉大的藝術能夠在生活的幻覺和藝術技巧之間得到一種快樂的聯想。”“幻覺”代表的是內心極致的個人體驗,而“技巧”的建構則是為了與這個世界(的他人)溝通。兩者缺一不可,缺一者則不能被稱為藝術。
幾年前,我見過紀錄片中英姿華發的米爾斯坦。記者在演奏會結束后前去采訪,一問:“能談談你對今天演出的理解嗎?”米爾斯坦將手中的小提琴輕輕放在自己精心收拾“打扮”的旅行箱里,細致地將鎖頭關好后轉身曰:
我的音樂不需要談論,我的想法需要你去聆聽!
聆聽!聆聽需要聽者,演奏是為了聽眾,演奏的本質是一種交流,借作曲家的音樂和靈氣來連結“我(演奏家)”的理解與“你(聽者)”的認知。說透,米爾斯坦對藝術的理解與克利無異。
演奏家的作用跟文學書籍的翻譯家有些許相似之處。比如不同的翻譯家譯出的同本小說,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感覺。我曾分別讀過兩種版本的《罪與罰》與《復活》,讀完竟一時以為俄國出了兩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兩個托爾斯泰。音樂亦通此理,聽過米爾斯坦的“柴小協”和奧伊斯特拉赫的“柴小協”,居然頃刻仿若世上同時存在著兩個柴科夫斯基:一個凌厲哲思,一個自然溫暖。翻譯者是個半作家——一半創作,一半讀者。演奏家是半個音樂家——一半是演奏家,一半是聽眾,是鑒賞家。但有時,對于文學譯者來說,當作品全部翻譯完,自己重讀譯文之時,很可能全然走出創作層面,搖身變為單純讀者,即使改正糾錯也會跳出作者身份,以讀者的角度“找毛病”。可對于演奏家來說,這個任務就只能借助唱片和錄像了——演奏家每每聆聽自己的唱片時,總會發現毛病,無不妄自嘆息:“原來聽起來和我想象的不同啊!”這時的演奏家,是自己錄音的聆聽者,也是自己的聽眾。再一論,聽眾雖然是演奏家需要“對付”的永恒主題,但個人的性格也不該泯滅。那么,個性的位置應該擺在哪里呢?
復制時代,穿越而來的古人可能會嚇出心臟病。走進音像店,一下子就見到唱片封面上一百張霍洛維茨的臉,更別提內中曲目了,那是多少個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曼啊!在一種人格的一百個復制品面前,它們的個性還在嗎?或許,只有當你打開一張唱片,單獨聽,細細品味其中奧秘,方能體會演奏家隱于作品背后的個人心緒吧。
2015年去世的薩蒂鋼琴作品權威奇科里尼,生前平淡,死后來潮。不少樂評人這樣評價他的薩蒂:“他的好在于將自身的個性、情緒隱藏在結構和形式之后。”此話講得好,奇科里尼的偉大正是于此,他將自己奉獻給音樂本身的純凈——這也是偉大演奏的奧秘之一。
我并不是說一定要全然匿藏自身,個性是可以盡情展現的,但要像里赫特那樣,將自身的個性與“偉大的”作品結構結合一同、相得益彰。好的演奏一定是不喪失形式的。只保留自我情緒的演奏是災難,因為它們不僅違背了作品的“本意”,也隔絕了與聽眾交流的能力,成為自我迷醉的宣泄垃圾。
3
2016年末,我隨友去波士頓參加通俗管弦樂團(Boston Pops Orchestra)的圣誕音樂會,未曾料想遭遇一場空前“饕餮”。此“饕餮”非為比喻,卻當實在——我居二樓席位,本以為聽眾如云,結果頭往下望,一樓座位已清一色被換成圓桌,桌上羅列各類飲品小吃。此刻“純聽眾”只得退居二層,主要座次是食客與狂歡者的家園。音樂韻起,席間眾人更是鼓掌叫好、歡呼合唱。在音樂廳吃飯,與臺上如此互動,這樣的音樂會我是沒見過的。如今憶起,竟一時恍惚,音樂曲目居然“皆空”,腦子里盡是狂歡的熱鬧非凡。
我的意思不是厭煩(我不僅不厭煩這種狂歡,甚至享受其中),而是一種思索:這番熱鬧歡騰還是否是一場音樂會?臺上的演奏家自然不為自己演奏,為的是烘托年度圣誕的歡愉,這是與觀眾的一次最大程度的“交流”。但這種交流并非通過音樂,而是通過氛圍。更重要的是,此刻臺下在位的也不是聽眾,而盡是狂歡的眾人。我的目的本是音樂,此間經歷迷惑、吃驚、恍惚,片刻也化為節慶的呼聲與彩帶,融入美國人民的節慶熱鬧中去了。
再想想我們看電影的經歷,不亦是如此嗎。我們早就習慣背景音樂在影像流動的同時“自我行走”,根本沒人在乎音樂講什么,我們看的是電影,音樂的作用與波士頓的圣誕狂歡同理,是氛圍的烘托者。話粗理不粗,電影音樂就是來告訴你電影講的是什么,而不是,也不應該是反之的。在觀看電影的時候,雖然音樂就在耳邊,可我們根本不是聽眾,而是電影的觀眾。
更不用說我們成天掛著耳機的手機和mp3了,它們讓生活現實里充滿了千奇百怪的“背景音樂”。用著這些高級電子科技的產物,有時我們的確會單純享受音樂,但大多時刻我們無存欣賞,僅為了生活的瑣碎增加耳朵的輕松。
真正的音樂聽眾到底在哪兒?
張愛玲說,音樂是“圈套”,聽音樂是需要“中計”的。兒時聽唱片,好聽,有趣,因此愛上古典音樂。后來年少長成,有幸進入音樂廳聽,結果根本傻掉,連約翰·施特勞斯都比唱片和想象中的震懾百倍。自嘆,原來來到現場,音樂的“詭計”這才奏效。
而現在的我,儼然一名音樂愛好者,搖身成為音樂會座上客里的“老菜皮”——當浩瀚音樂入耳,已如止水般冷靜。當初始的心緒全然消散,心中默然生疑,兒時那種無知的聆聽和震撼的“傻掉”(如此這般美妙的經驗),在成為“老菜皮”以后的我心中還會出現嗎?
明代大儒王陽明一語中的:
破山中之賊,易。
破心中之賊,難。

在演奏家和音樂會的商業時代,試問,中音樂計的“家伙”還有幾位?“閉眼聆聽”的體驗還是否存在于世?我想,多數人是中了商業的計,中了信息的計才前去聽音的吧——你選擇一場音樂會本身不就是甘愿落入宣傳和名氣陷阱的結局嗎?見一張海報,看到上面的臉和名字,抑或聽聞一則媒體或網絡的宣傳新聞才會選擇購買門票。在進入音樂廳之前,我們本身就不是“閉眼”聽眾了。當這些充斥著信息的“賊”悄然闖入心中,你的聆聽也就不再純粹了。反而是那些被專業人士或愛好者口口稱鄙的“外行人”倒成了音樂的純粹聆聽者,他們蒙忽忽進來,根本不知演奏家是誰,也不知曲子的來歷云云。他們的聆聽只能源于音樂本身,美妙抑或糟糕的體會,完全是出自于此刻聲音的聆聽帶來的感受。“閉眼”在于無知,是因無知而帶來的純粹,沒有多余信息籠罩的藝術才叫純粹的藝術。比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小說《巴黎永無止境》(Never Any End to Paris)中這樣寫道:
理解可能成為一種判決,而不理解則可能是一扇敞開的門。
這就是在概括這層“不理解”和“無知”在藝術體驗中的重要性。然而,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1928-1987)用全新的藝術告誡人們,進入二十世紀,想逃掉商業是不可能的。商業的信息早已融入到藝術本身,成為藝術的一部分了。音樂演奏后暴風雨般熱烈的掌聲有多少是獻給巴赫、勃拉姆斯、貝多芬的?對許多聽眾來說,赫赫聞名的“三B”可能只是死后亡靈,他們是給演奏家的表演添油加彩的,所有的激動與熱情還是要統統獻給演奏家的。“演奏家”這三個字可真是要了親命,它既不代表音樂,也不代表演奏——它就是“演奏家”本身,是明星,是名氣。此刻的我們,竟一味為名氣二字在鼓掌啊!
名氣的“賊”一旦作祟,誰也逃不開,我們都中了信息和商業的詭計。這是一面:我們借音樂的聆聽來間接幫演奏明星助長聲譽(音樂會的上座率直接顯示著演奏家的知名度)。而另一面,更有甚者,直接走向極端,成為裝腔作勢的投機分子,“利用”音樂來證明自我人格的存在。《巴黎永無止境》還引用過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的話:
裝著去愛而不變成情人,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有些人就是喜歡“裝”。他們違背了自然規律,一輩子沒能變成音樂的“情人”,卻“裝”了一輩子“情人”。無論是聽眾還是演奏家,都不乏這樣的“人才”,他們往往享受于他人對自己高雅姿態和學識淵博的慨嘆中無法自拔。對于這些人,貢布里希的解釋冷酷且周到:
他們害怕一旦承認自己喜歡那種明顯惹人喜歡的作品,就會被認為是無知之輩。于是冒充行家,失去真正的藝術享受,卻把自己內心厭惡的東西說成偉大。

一番論調過來,不禁失落惆悵。自己聽樂多年,雖有幸未成為“裝”的那一圈子人,卻怎奈也距本來的純粹和無知越來越遠,愈加阻隔——人的、事的、社會的、時代的。想到這層,我猛然憶起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電影《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電影里那糾結不安的艾森巴赫,其實是托馬斯·曼以馬勒為原型的創造。而它的主題,正是描繪作曲家與“美”的層層阻隔:藝術家追求美感,卻被事實處處打斷,導致終無法親近而遁入掙扎。影片里展現的那種道德的阻力實際暗含著社會和人性對于藝術與純粹的羈絆。
遙談至此,我并非欲意加重不安,只是為了看清事實,才能找到改變的道路。在被信息包圍的時代,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尋索音樂的初衷。
上一部分談到演奏場所與音樂的關系,好像如此說來,在準確的場合聽相應的音樂是可以增強聆聽者對于音樂的體驗,也更接近“無知的純粹”的。沒錯,我想有過體驗的諸位也會認同,此法確有促進效果。但宗教音樂在教堂聽,宮廷音樂在殿堂聽,對于很多歐洲本土人來說,都根本是古歷之事,早是前世的記憶了,更別提我們這些“外地人”了。現今談及,豈不等于烏有?那么生于音樂廳時代的我們,到底該如何找回這種感覺呢?
關于此折,作曲家欣德米特曾有過“應對措施”。他創作一系列“實用音樂”,意欲讓音樂回歸到對應相應人群的“老路子”中去。說白了,是巴赫、海頓和亨德爾的原始模式——為特定的群體寫作特定的音樂。比如,根據現有時代,欣德米特專為學生寫一些作品,其主題和格式都是為了學生這一特定群體而寫的。以此類推,可以為工人寫,為廣播電臺寫,為藝術家寫,為特殊場合寫……
欣德米特的方式承接古典主義之前,確有理據,也有“實踐價值”,但它的“操作方法”僅限于新作品的創作。我想,對于喜歡聽“老作品”的我們來說,“操作方法”自然有所不同,但若看清、看透,做起來就不難。
那就是,找到自己。
那就是,在極度喧囂的年代,敢于脫去炫耀才學與資本的塵埃,敢于面對無知,享受無知。
摒棄他人旁觀,勇敢面對未曾包裹信息入侵和商業攻勢的赤裸裸“站”在你面前的藝術珍品,才能走進純粹和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