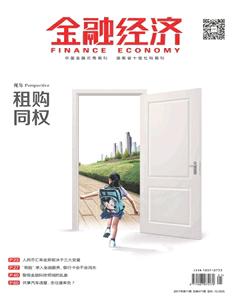選擇什么樣的產業政策至關重要
吳敬璉
去年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場引起了學界、產業界、政界廣泛關注的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這場討論影響很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采取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關系到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穩定的發展。
產業政策有不同類型,不可一概而論
一概否定產業政策或者一概肯定產業政策的人,其實都沒有注意到,我們現在討論的產業政策是有不同類型的。因此,有些人心目中想到的產業政策是指20世紀80年代主要從日本和韓國引進的那種產業政策,或者叫做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所采取的那種產業政策。其實,這只是產業政策的一種主要類型。
日本產業政策,是日本過去戰時統計經濟的遺產,也是五六十年代一批經濟學家的助推,當時的產業政策主要是兩種——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前者。核心內容就是“運用財政、金融、外貿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導的手段,有選擇地促進某種產業或者某些產業的生產、投資、研發、現代化和產業的改組,抑制其他產業的同類活動”。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叫做“有保有壓,選擇產業”。所以這種產業政策后來就被叫做“選擇性的產業政策”。
1973年,日本第一次石油危機時,石油價格猛漲,發生了長達四年時間的經濟衰退,從20世紀60年代10%以上的年均增長率下降到負增長,這個時候,許多日本經濟學家就對產業政策提出了懷疑。他們并不否定產業政策,而是根據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之下,也應該靠政府的干預來彌補、補充市場失靈,來提升市場的功能。后來,日本的產業政策就開始從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向提升市場功能的產業政策轉變。這些日本的經濟學家提醒要注意三個問題。
第一,是要正確地判斷市場在什么情況下出現了真的失靈,需要政府進行干預。這對我們很有啟發,從我們引進產業政策以來,存在把市場失靈泛化的傾向。有一些說法很明顯是誤讀的,比如把市場失靈說成是市場天然的缺陷,這就等于把市場失靈泛化了,使得政府合理的干預就變成了沒有界限的干預。
第二,是要針對不同的市場失靈應該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第三,是要認識到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的時候,還要注意,政府干預也是會失靈的,這就需要權衡。有時候,為了彌補市場失靈而采取市場干預措施,造成的損害比市場失靈造成的損害還要大。這就需要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使得收益最大、損失最小。
產業政策的發展與完善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從1987年我國正式引進產業政策以來,我們也經歷了一個探索實踐的過程。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擔任國家計委產業規劃司副司長的劉鶴,他長期做產業政策規劃和執行的工作,在1995年寫了一篇論文,非常明確地提出,應當用功能性的產業政策來逐步替代差別化的產業政策(劉鶴把選擇性產業政策叫做差別化產業政策)。他說變革的主要內容是:“逐步淡化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差別對待不同產業的色彩,以增強其產業的競爭力,反對壟斷、保持競爭和廣泛提供信息等原則來支持產業的健康發展,通過提供信息、建立市場秩序等方式,增強市場競爭功能的內容,將成為新的產業政策的主要特征。”這段話我覺得說得非常深刻,而且是切中時弊。可是要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個轉變不但跟人們原有的觀念相沖突,而且涉及到有關主體的利益。
比如1973年,日本的石油危機以后很多人的思想就開始轉變,而且他們反對日本選擇性產業政策,特別是學界的力量很強大,但改變仍然不容易。因為這些力量都是年輕一代的,受過現代經濟學教育的經濟學家幾乎都持有相同的意見,但是又跟老一代的經濟學家沒法達成一致,而老一代經濟學家都是日本經濟學界的“大佬”,很有地位。
我親身經歷的案例就是日本利用產業政策支持開發模擬式高清電視的失敗導致的最后失敗。當時各國都在開發高清電視,日本通產省和日本廣播公司NHK研究后選定了模擬式的技術路線。模擬式的方法確實有優勢,比如只要加強掃描密度,清晰度馬上就提高了,果然也首先取得了成功。但是模擬式電視機也有兩個缺點,首要的缺點是創送流程復雜,成本高——因為它傳播的時候不能用數字信號,是模擬式的波傳播進來,接收以后變成數字,處理完以后再轉化成模擬波。
這個時候,美國非常擔心,因為美國不是由哪個政府機構來選定技術路線的,而是各家自己搞自己的,于是在1990年出現了數字電視的苗頭,但是因為數據量大,也比較復雜。就這樣,日本太注重短期利益,所以大量的產業政策都去支持開發性研究,而不注意基礎性研究,而美國的基礎研究比日本強得多。通過基礎性研究,也就是說算法的研究,美國解決了信號的壓縮和解壓縮問題。當信號的壓縮和解壓縮問題解決以后,傳輸就不成問題了。所以,日本便吃了一個大敗仗,舉國之力投資搞的模擬式高清電視全部打了水漂。
前不久,清華產業政策和環境治理研究所請日本嘉賓來講,在90年代后,日本的政府對于強化競爭政策,消除政府選擇性干預的影響所做的工作。他們說日本的四任首相都致力于消除舊體制和產業政策的負面影響,來強化競爭政策,但是到現在并沒有完全成功,這個事情非常艱巨。實際上也是這樣,剛才講到劉鶴在1995年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種意見學界很多人都覺得非常對,說的很準,但是進展起來非常的困難。
選擇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改善產業結構、提高效率具體的表現,就是“三去一降一補”,“三去一降一補”有兩種辦法去實現,一種辦法是用行政的干預、有選擇地去扶植一些產業、抑制另外一些產業;另外一種辦法,就通過提升市場的作用、通過加強競爭來實現。我們的這項工作已經進行了兩年多,今后也是我們經濟工作的一個核心部分,但是選擇什么樣的產業政策去實現我們的目標,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情。
現在很有必要加快產業政策的轉型,怎么樣進行產業政策的轉型呢?
第一,要認真總結30年來執行產業政策的經驗和教訓。改進的方向已經非常明確,我們要沿著這個方向去做——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職責是什么呢?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在我們現實的條件下,實現轉化的要點就在于處理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之間的關系,一定要改變過去所提出過的政府經濟政策的中心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只是競爭政策的輔助。所以,我們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實現這個轉型的要點就在于,從以產業政策為中心轉向以競爭政策為基礎。
第二,進行產業政策轉型很重要的前提是,要按照黨中央決定的方向,充分吸取中外關于產業政策研究的成果。采取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怎么來執行產業政策?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有許多好的成果值得吸取。
比如,羅德里克有一本書《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政策處方》里講,現在不是要否定產業政策,也不是要制定更多的產業政策,而是要有更好的產業政策。他提出一個問題叫“信息的外部性”,即對企業來說,有一個市場失靈,就是因為他很難取得產業進一步向什么方向發展的信息,這個信息的取得是有外部性的,拿到正確的信息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要消除這個外部性,政府其實可以做很多工作。
第三,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政府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許多方面不應該用行政方法介入,而有些方法能夠提升市場的功能,能夠強化競爭,政府還有很多事情可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