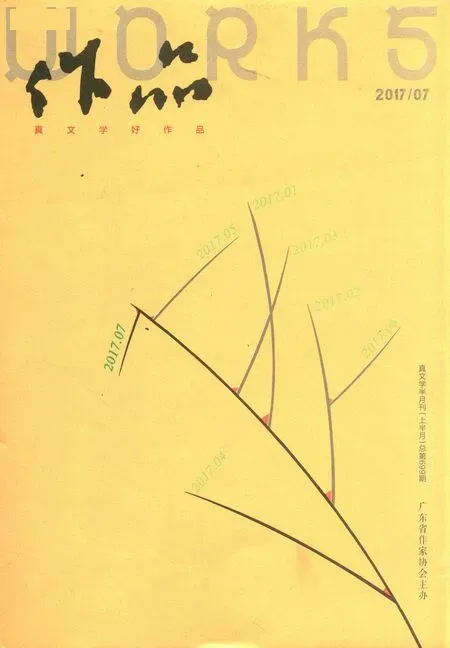憶父輩的詩友
文/王則楚
憶父輩的詩友
文/王則楚
王則楚1945年3月出生于浙江溫州,現為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特聘參事,廣東省政協文化文史委員會文史專員,廣東廣播電視臺特約評論員。
近日,在永昌堡(我們家宗祠)后人的群里有人發了一幅夏承燾先生書寫給施執存的字,內容是父親(王季思)論詩的一段話:山谷謂作詩如作雜劇 臨了須打諢 方是出場 其和子瞻戲效庭堅體詩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 公如大國楚 吞五湖三江 皆能詩 言結云 小兒不知客 或(可)許敦龐 誠堪(婿)阿巽 買紅纏酒缸 則打猛諢出矣 。勾起了我對父親與親人、友人詩詞來往的回憶和思考。在父親111歲誕辰和去世11年之際寫下來,做個備忘。
溫州是詩人謝靈運的故鄉,詩詞歌賦和南戲一樣,在溫州人的生活里是一個有機的組成,在文人墨客來往之中都有許多記載。我們家的祖上有許多的詩文和戲曲故事留下來。記得父親就講過,戲劇《荊衩記》里,丞相的原型就是我們王家的先祖。清朝平定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之后,清廷曾經下旨對溫州免賦救災,但府縣地方官仍匿旨不宣,照常征賦。曾祖父王德馨字仲蘭寫文章揭露知縣陳寶善違抗朝廷,匿旨擅征。被縣官派人捉拿。仲蘭公越獄逃亡北方,流亡了好幾年。歸來之后,他在積谷山下的東山書院當山長,面對詩人謝靈運的池上樓與春草池,他吟詩作畫,成為一時名宿。他的詩曾被民初大總統徐世昌編入《晚晴簃詩抄》,至今在溫州圖書館還留有詩集《雪蕉齋詩抄》。
家傳的詩文愛好自然也一直在王家這個書香門第里影響著每一個人。在父親那一輩里,父親的大姐夫陳仲陶是南社的成員,和柳亞子先生都是同期的南社活躍分子。他與溫州劉節的父親都有聚會的記錄。他的《劍廬詩鈔》有柳亞子的題詞:豪氣元龍百尺簍。甌江江上舊風流。一門更喜都人杰,六秀從來世少儔。章士釗也題長句一律,其中說他“吐納眾流成別士,推排細律作詞人”。他在重慶的時候,還收了民國第一俠女,為報父親被割首示眾之仇而親自開槍打死孫傳芳的施劍翹為徒,成為詩壇佳話。父親在《劍廬詩鈔》的“后記”里承認:我青少年時期寫的詩文經常得到他的指點,他后來寫的詩詞也往往抄給我看。這種家傳的詩風,也使父親得以交會了許多詩友。
前面提到的夏承燾就是與父親有深交的詩友。他們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少年時代,這些來往在父親的書里、夏承燾的日記里、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章里都有提到,但最集中、最有影響的還是1957年1月父親邀請夏承燾先生到廣州中山大學交流的那次活動。整個活動、以及和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的交流都有詳細的報道。我當時只是一個11歲的小學生,大人之間的學術交流我是不了解的,但家里準備飯宴請夏承燾先生的美味佳肴倒是記憶深刻。那天,媽媽是特別用心地安排父親和夏先生之間喝酒的菜,一般的涼菜當然有,但溫州的鰻魚片夾肉我記得就吃過這一次。那是頭天晚上就把鰻魚干泡軟了,熱后斜斜地切成薄片,和水煮熟的五花肉涼冷了切成薄片,梅花間竹的放在盤里,再上蒸籠蒸熟,放到溫熱才端上桌。那在廚房里的香味,就已經讓我忍不住偷吃了。那天是父親53歲的生日,飯前,爸爸請夏承燾先生書寫他自己撰寫的對聯:三五夜月朗風清與卿同夢,九萬里天空海闊容我雙飛。這是父親描寫他和母親愛情的一副對子,母親也特別喜歡。那紅底宣紙上是撒著碎金點的,鋪在家里的飯桌上,父親把書房里的筆硯拿過來,父親親自研墨。后來,我還去幫著研墨。夏先生寫到“卿”字之前,母親也過來觀看,對“卿”字,母親提出改為“子”字,夏先生遵囑寫下。字裱好之后就掛在家里的飯廳。我一直記得寫的是:三五夜月朗風清與子同夢,九萬里天空海闊容我雙飛。文革前在北大的政治學習的思想匯報里,我還說過這副對子,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父親想讓我們成為他們的孝子賢孫。此匯報還被高年級的同學看到,很羨慕地抄下這副對子。到底哪個才是真的?近日,則柯哥哥在回憶文章里也肯定了是“子”字。并且抄錄了夏先生的《天風閣學詞日記》,在夏先生的日記里寫明是:“午飲季思家,是其五十三歲生日。屬寫一聯曰:三五夜月朗風清,與子同夢;九萬里天空海闊,容我雙飛。其夫婦二三十年前故事。”一年之后,母親因病去世,一字之改,深深地把母親對子女的母愛、和希望父親能夠與子女同夢的愛情化在了這個對子上了。可惜,文革之后再也沒有找回這副對子。
我記憶里,在搬到東南區1號之后,書房布置好之后,父親給自己的書房命名為“翠葉庵”,請商承祚先生的父親、清末健在的探花商藻庭(衍鎏)先生為之書寫。我隨父親到過他們當時居住的東北區許崇清校長坡下的家,進門就能夠看到案桌上玻璃罩著的御賜寶劍。不久之后,就看到父親書房圓拱門上掛著這個豎寫的牌匾。
此外,父親的藏畫里一幅黃賓虹的翠葉庵讀曲圖,這是黃賓虹先生應父親的要求而畫的,并從杭州寄來羊城。父親收到之后,當即寫下《洞仙歌》詞一首作答,謂“黃賓虹先生自西湖巢居閣寫寄《翠葉庵讀曲圖》,賦此答謝”:
西樓倦臥,任榕陰移晝,夢想闌干壓金柳。
費經營,凌溪一桁軒窗,簾卷處萬壑千巖競秀。
巢居閣子里,一老婆娑,湖上陰晴幾翻覆!
頭白喜春來,腰鼓秧歌,想畫里長開笑口。
愿把酒為公祝長年,看劫后湖山,重鋪金繡。
為此,父親還專門請詹安泰先生書寫該詞來配在畫頭。詹安泰先生在書寫之后的說明里寫道:一九五零年一月 黃賓虹先生為季思兄寫翠葉庵讀書圖自杭州寄來羊城 季思賤此詞謝之而囑余別書一通以配圖 詞自佳妙 惜余書拙劣 不免佛頭著糞之誚耳。
在反右之前,毛澤東詩詞也已經發表,而且還有和柳亞子先生之間的唱和。內地知識分子在那段比較起來幾乎最好的日子里,享受到比較寬松的“早春天氣”,互相之間的詩詞唱和也是比較多的。中山大學里也一樣,例如1957年4月1日,廣州京劇團來中山大學演出,演出以后,演員與教授歡聚一堂。陳寅恪先生非常高興,寫了三首絕句,送“祝南、季思、每戡先生一笑”。陳寅恪的詩和三位教授的奉答之作,均刊登在其后的《中山大學周報》和《南方日報》。
我還記得小時候,跟著父親在1956年的十一假期,晚上和董每戡、詹安泰還有另一位教授,在中大北門叫了個小艇,從北門劃到黃埔島再劃回來。四位教授在艇上就著艇家的新鮮魚、蟹、蝦、蜆,吟詩作對,喝酒至父親大醉而歸。
反右時,董每戡先生由于在陶鑄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詹安泰先生由于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竟然被打成右派。詹安泰這位饒宗頤先生的老師、詩詞成就非常高的廣東學者,因而早逝于文革之中,實在令人惋惜。文革后,黃賓虹的畫和畫上詹安泰先生書寫的父親寫的詞裱在一起,直到父親去世,都一直掛在家里的客廳。后為大哥所收藏。父親的詞也編入了大哥整理的《王季思全集》里。自反右之后,我所見到的教授們之間的詩詞唱和就少了,一是父親北上北京大學講學和編輯《中國文學史》,二是1963年他回中山大學,而我卻北上北京大學讀書,彼此交集很少,也再難見到詩詞會友的場面了。
打倒四人幫,父親是詩興大發,寫有不少詩詞,來表達他對打倒四人幫的高興和對改革開發的支持。當時,許多人把“四人幫”看成橫行霸道的螃蟹,父親又是最喜歡吃螃蟹。即興寫下了《齊天樂》:
四兇落網,普國歡騰,持鰲把酒,共慶勝利。
潮回暫落吳江水,尖團一時俱起。澤畔橫戈,泥中擁劍,噴沫都成毒氣。
秋風漸厲,看汝輩橫行,為時能幾?竹簍禾繩,元兇行見駢頭死。
玻杯興來高舉,劈雙鰲一蓋,連呼快意!
海市煙消,蜃樓泡滅,玉宇澄清無際。
豪情萬里,正月到天心,潮生眼底。料得明朝,豐收歌“四喜”。
他特意把這首詞,抄寄給上海的三弟王國楨(我的三叔)。三叔還特意請人書寫了保留下來。
1978年1月,父親向商承祚先生出示文革之后尚存之齊白石所繪的《群蟹圖》,還請商先生為之書寫了他1919年所作的詠蟹詩,裝裱在畫頂。詩曰:
公子無腸不解愁,江湖豪氣孰能儔。橫行郭索空千里,直吐璣珠瀉九秋。入籪有時傾澤國,乞符何日屬監州。平生玉質真知己,換得尖螯妙句投。
至于那篇在政協會議上即興寫的諷刺向錢看的《水調歌頭》,調侃的寫到“我亦萬元戶,年年爬格子”,見報之后,不時被人提起。文革之后,教師節,父親也寫過詞,請商承祚先生書寫,發表在中大盟訊里。那些復印的底稿,在家里的廢紙堆里,我看到過。
父親晚年,更多的是與王越先生有詩詞歌賦的來往。1983年王越先生寄來他的詩集,父親回信:“論詩絕句對前代諸名家大家,不是一味拜倒,而是一分為二,分析批判。一年多來夏承燾論詞絕句,蘇仲翔論詩絕句,先后出版。他們都是一代專家之學,詩詞功力,兄或有所不及,胸襟見地,兄實過之,不悉以為然否?”
1993年12月26日父親寫了《鷓鴣天》:
新歲將臨,沉陰放晴,東廊曝日,喜而成吟。
萬里晴光透碧霄,寰球漸見息烽飆。朝陽軟似黃綿襖,淑景鮮如五彩綃。
人意好,歲收饒,同心為國看今朝。持盈防腐歸中道,珍重中華百煉刀。
父親囑我抄好寄士畧(王越先生的號)學長指正。
1994年1月29日,父親還親筆寫下:甲戍新春抒懷(又一首)
賀卡聯翩到枕邊,謝天放我老來閑。窗前花影無心顧,樓外鶯歌不費錢。
春意好,物華鮮,江山詞筆兩壇妍。愛他逐日追風客,擲杖成林又一年。
1994年3月29日,根據父親與我和董上德老師的談話整理出來的父親的文章《說“服老”》在《羊城晚報》上發表。里面寫到:“不服老”是空話,“老當益壯”是空想。一個人由少壯而衰老是自然規律,哪里有老當益壯的呢?廉頗老年并沒有為趙國再立戰功;馬援到了五溪蠻以后,看到那里氣候環境的險惡,羨慕起他弟弟在故鄉的悠然自得,并沒有真正的不服老。至于文學作品的句子,曹操寫《步出夏門行》這首詩時不過四十歲上下,并沒有到暮年;王勃寫《滕王閣序》時不過二十歲左右;往往帶有理想的色彩,并非自己親身經歷。
王越先生看到之后,專門寫了詩《讀“服老”篇》寄給父親:服老不服老,如何為懷抱?孔丘常發憤,不知頭白了。生入玉門關,班超見機早。圣哲與英雄,殊途同歸好!
看著父親簽名、大哥手寫的1994年給王越先生的信,里面寫道:我和兄青年時在南京同學,南來廣州后,又在中大、民盟共事多年,諸蒙照扶,兩家子弟也親如手足。則柯、則楚在中大附小多蒙操心照料,得以有成。
現在想起來,這樣的日子已經隨著這一輩詩人的離去,再也不會回來了。但愿我們這些不學文科的兒輩能夠慢慢體會他們的詩友情誼,記下來留下記憶。
(責編:楊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