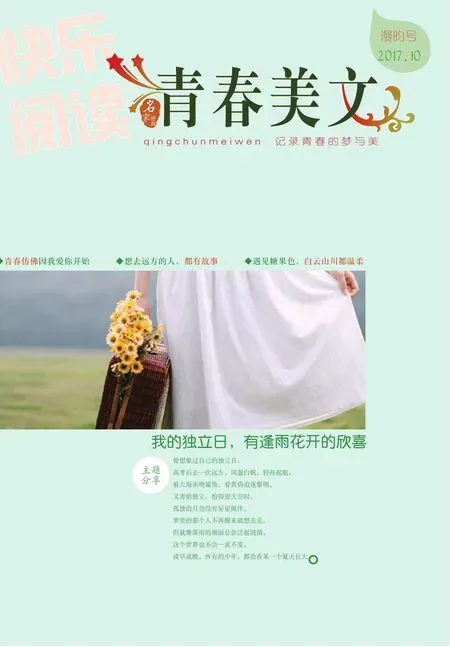島嶼之間
■陸俊文
島嶼之間
■陸俊文

從公寓走往圖書館的路上,我常能看到那些修女,她們平和、優雅的面容,總讓我想起在廈大的校園里漫步的南普陀寺里的和尚。剛來臺灣的時候,冬天還沒有過去,轉眼現在已經入夏。這所學校安靜得過分,我習慣了在廈大看每天來往如織的游人,對這里一到周末便人去樓空的校園并不太適應,所以除了躲進圖書館看書,便是到附近的鎮上沾沾人氣。
我對臺中市的印象長久地停留在綠園道。那天晚上,我和三個朋友去誠品書店,路上卻被街頭唱歌的藝人吸引住了。一個吹薩克斯,一個彈著電子琴演唱,兩個人看上去至少都有三四十歲的年紀了,可他們分明笑得那么開心。他們就站在公路邊緣的一棵大樹下,身后是飛奔而去的汽車,眼前被駐足聆聽的市民圍了好幾圈。我們坐在一條水泥砌成的長磚上,剛坐下去,他就開始唱王菲的那首《人間》。我驚訝于他溫柔、細膩的嗓音,雖不似王菲那般輕盈、空靈,卻把這首《人間》唱得如此真摯而滄桑、動情。那天晚上,稀疏的葉間落下零星的雨滴,風撲面而來,我們就這么長久地坐在那里,聽他們的唱和與吹奏。直到10點整,他們的時間到了,人群要散了,我們才挪動腳步離去。
回憶起來,我總覺得那兩個沉醉地吹著薩克斯和入情地撫琴而鳴的老男孩,同詩人那么相像,他們只站在那里,就有足以打動人心的力量。
對一座城市的喜愛常常就在這樣的不經意里。在廈大白城的沙灘上,我也曾遇到過一個在夜里的海風中吹著薩克斯的年輕人。有時候漲潮的海浪漫上來了,周圍已經寥落無人,他仍對著海獨奏,孤獨的背影和曲調讓我不得不想起電影《大路》里的小號。有些人總是那么執著地去追逐一樣東西,10年、20年,甚至一輩子,而我們大多數人,總是在跨出去一小步的時候,就哆哆嗦嗦地把腳從布滿荊棘的小道上收回來,踏在平穩的土地上。
時間是個太過迷人的東西,卻也是一副太懂得如何催人淚下的藥劑。
我想起在杭州的時候爬寶石山,在半山腰路遇一家叫“純真年代”的書吧。書吧隱蔽在叢林之中,我輕掀珠簾進去,為里面沉靜、安逸的閱讀氣氛所吸引,隨手把書架上的書翻開,封頁間留有作者饋贈的筆跡。事后得知書吧的主人竟是一對愛文學的夫妻,還都是廈大的校友,妻子讀外文系,丈夫讀中文系。我不禁驚呼,幾年前,林丹婭老師在散文中提到的那對在西子湖畔開書吧的神仙眷侶,她的那個朋友,不正是這間書吧的主人嗎?因為10年前的一場重病,在迷離邊緣的她毅然在西湖邊開了一家書吧,而她的丈夫也傾其所有為她開店。之后她病愈,辭掉了高校的工作,專心打理這家書吧,成了遠近文人名士流連的一方小天地。10年里,書吧從西湖邊遷到了寶石山上,每年都在虧損負債,可他們仍舊堅持著,開文學沙龍,辦書吧活動。
若不是真的踏進去,我還不肯相信這如小說情節的故事竟是真事。想著人生是個多么奇妙的東西,若非在緊要關頭,或許先前的遲疑不定斷然不會如此決絕,而經歷了多少年歲、多少事,依舊惦記著那份純真,又是多么難能可貴。都說有緣千里來相會,才會有那么多意料不到的偶遇吧。
我忽然發覺,城市和島嶼最打動我并留存于我記憶深處的,都不是這地方的面貌、形態,而是那些發生在我與那個地方之間的,一段段似是而非、真實得晃眼、直擊心靈的故事,它可以是漫長的十多年,也可以是一瞬間。這像極了漂浮在大海上逐浪而居的擺渡人,在島嶼之間,記憶游移著,我在此岸看到彼岸,念此情想起了彼景,它模糊地存在著,卻又如此清晰。這些如浮嶼一般生生不息、長在我腦海深處的記憶,是故事用有力的筆調,畫出那一個個城市最細的輪廓、最粗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