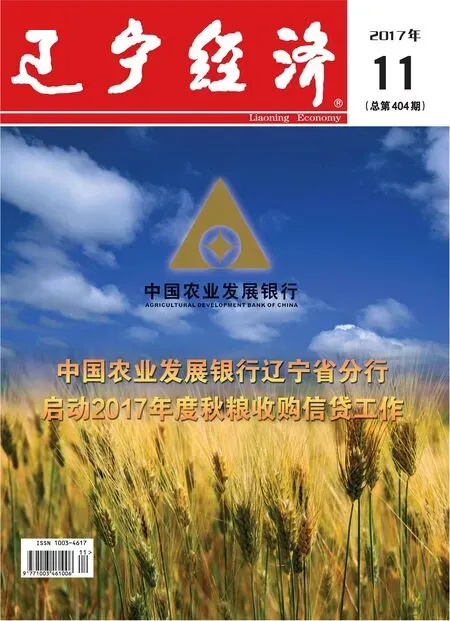淺談《孝經》中的“孝”
◎戴金洋
淺談《孝經》中的“孝”
◎戴金洋
孝,是中國古代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孝經》作為古代孝文化的專著,在中國倫理思想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僅影響深遠,而且當今也需要認真研究,在賦予時代內涵的基礎上繼續傳承,進一步發揚光大。
《孝經》 孝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代代相傳,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所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即使在圣人的德行中“孝”也是最重要的。《孝經》全文共十八章,以“孝”為中心,記載的是孔子向曾參講述孝道的言論。全文字數很少,但是卻明確體現出“孝”的作用以及由“孝”推衍出的“忠”的表現。
一、什么是“孝”
古代最完滿、最理想的孝行,把“孝”與君主之間聯系起來。“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意思就是說,所謂孝,最初是從侍奉父母開始,然后效力于國君,最終建功立業,功成名就。孔傳也說:“自生至于三十,則以事父母,接兄弟,和親戚,睦宗族,敬長老,信朋友為始”;“四十以往,所謂中也,仕服官政,行其典誼,奉法無貳,事君之道也”;“七十老致仕,懸其所仕之車,置諸廟,永使子孫鑒而則焉,立身之終”。強調從“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損傷”到“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只有做好這些,才算做到了完滿的“孝”。
二、“孝”的地位
“孝”在古代被奉為崇高的地位。一是“孝”符合天地的規律。“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如天道星辰永恒不變照耀世間,如大地山川華育萬物生生繁衍,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品行。二是“孝”為倫理道德的規范。“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的出發點。“孝”,即使是在圣人品德中也是最為重要的,即“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對于圣人來說,“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三是“孝”可以治國安邦。“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四是“孝”能作為法律規范。《五刑章》中提及“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其宗法等級關系和道德秩序。在這里,“孝”既被賦予了自然屬性,也被賦予了社會屬性,并被看作是國家統治,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
三、“孝”的不同內容
《孝經》盡管文字簡約,但內涵豐富,根據不同人的身份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一是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于其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用自身的孝道來感化百姓。二是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這樣才能使得自身“長守富”“長守貴”“富貴不離其身”。三是卿大夫之“孝”要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這里強調要達到“三者備”,即“先王之法服”“先王之法言”“先王之德行”。四是士階層的“孝”要求“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五是庶人之“孝”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做到身邊能夠做到的事,因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如果你說你做不到孝道,那根本不可能。與儒家其他文化一致,《孝經》里的孝文化也是博大精深,微言大義,兼顧到社會各個階層且都有具體規范。
四、“孝”的做法
物質上的做法為:“用三牲之養”。而重要的是精神上、行為上、態度上,最直接的做法有五種:一是“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起敬(孔傳:謂虔恭朝夕,盡其歡愛。要充分表達出對父母的恭敬)。二是養則致其樂(鄭注: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要充分表達出照顧父母的快樂)。三是病則致其憂(鄭注: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疾止復故。要充分表達出對父母健康的憂慮關切)。三是喪則致其哀(父母去世時,要充分表達出悲傷哀痛。如《喪親章》中所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四是祭則致其嚴(祭祀的時候要充分表達出敬仰肅穆)。
在這五者之中,筆者認為其中祭祀的重要性很突出。如《圣治章》“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用比較的手段強調“配天”,即祭祀祭天的重要性,并舉周公祭天之例,使得四海之內各諸侯恪盡職守。同時,祭祀也突出了孝經談孝的天人感應。《感應章》中提及“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說明了明王能明察天之道,明曉地之理,以奉事父母的孝順奉事天地,天地之神也就名察明王的孝心,充分顯現神靈,降下福祐。其中,還有“宗廟致敬,不忘親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說明祭祀感應天地,突顯出“孝”的天人境界。
《孝經》非常嚴謹,還談及了諫諍,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的回答為“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聽從父親的命令是應該的,不能算作“孝”,但“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面對父親不義的行為,應當及時勸諫。
五、“孝”的推廣
《廣要道章》中談及“禮者,敬而已矣”,由敬的方式出發,通過尊敬對象的不同延伸出孝、悌、忠、信、禮等。這點在《廣揚名章》中有更多的提及,“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這里將《孝經》中的重要觀點提了出來,使得《孝經》不只談孝,更注重于以孝勸忠,為治國安邦給出哲學觀點。
有關孝與忠,《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系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并把“孝”的社會作用推而廣之,認為“孝悌之至”就能夠“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中國古代在選拔官員時,也常常把“孝”作為極為重要的標準。如漢代舉孝廉成為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為官的制度,作為察舉制的主要科目之一,為官吏晉升的正途,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對漢代政治影響很大。古代朝廷也通過各種途徑訪察孝悌之人,或選為官吏,或大加表彰,以弘揚“孝”和“忠”,來規范社會風氣,維護國家統治。《論語·為政》中提及“孝慈則忠”,《論語·八佾》中提及“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兩篇都將“孝”與“忠”結合一起,“忠”正是由“孝”所轉化而來。《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將對父母的孝推廣到對君主的忠誠,也是將家庭和睦推及到國家安定。由此可見,君王將孝引用于治國安民之中將會使得全國上下同心,國家富強穩定,這對于當下新時代的中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孝,作為儒家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孝,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美德,《孝經》在規范和弘揚這一傳統美德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孝,盡管在今天被賦予了某些新的內涵,但其傳統是一以貫之的。孝,仍是中國當前社會大力提倡并需更好的繼承和弘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小到家庭的和睦,中到社會的和諧,大到國家的穩定,孝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們要重視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承,孝文化應該擺在重要位置。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院)
責任編輯:宋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