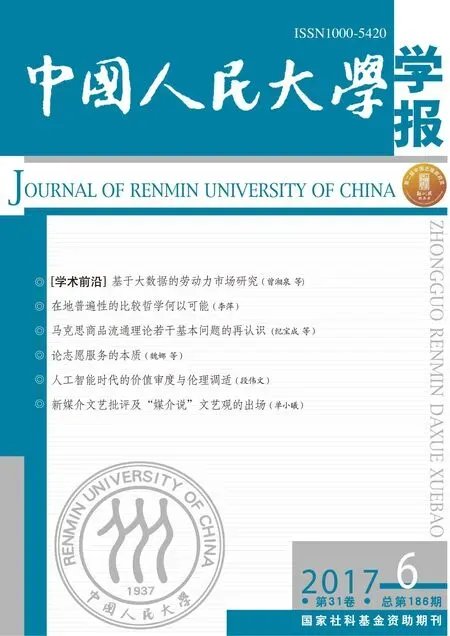政府、社區、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機制研究
——基于三個街道案例的比較分析
張楠迪揚
政府、社區、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機制研究
——基于三個街道案例的比較分析
張楠迪揚
政府、社區與非政府組織(NGO)合作成為近年來我國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的新模式。這種模式以社區為項目執行主體、以NGO為組織與能力培育平臺。NGO的參與有效連接了政府與社區的居民,保障了項目執行。通過比較同一NGO參與三個街道社區的治理,可以看到政府、社區、NGO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的角色轉變。政府從以往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轉變為資金支持者和規則制定者;居委會成為公共服務項目的設計者和社區居民的組織、協調者;社區居民被有效整合進社區治理項目,NGO致力于提供技術支持和能力提升。由于存在NGO財政來源單一、社區自組織及能力不足、合作項目的可持續性受政府領導更迭影響等問題,需要予以改進。
參與式治理;城市社區;政府;非政府組織
政府、社區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簡稱NGO)合作成為近年來我國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的新模式。這種模式以社區為項目執行主體、以NGO為組織與能力培育平臺。NGO的參與連接政府與社區的居民,有效保障了項目的執行。但這種多方合作的模式是否可以從結構上改變傳統政府“自上而下”以行政指令治理社區的模式?是否具有持續性?研究政府、社區、NGO合作模式下的社區參與式治理機制,分析三者在合作治理中的功能角色、互動模式等問題,對探討我國社區治理的新機制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本研究以三個城市社區街道為案例,比較政府、社區、NGO在合作中的功能角色、合作模式,并對項目的可持續性及原因做出分析。
一、文獻回顧及研究方法
既有研究對影響我國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成功與否的因素做出了有益探索,分析了政府、社區、NGO在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參與式社區治理強調賦權社區居民[1],將社區自治權力歸還給社區,拓寬公民有效參與政策制定的途徑。[2]參與式治理主張政府與居民建立良性互動合作關系,特別強調政府應增強同第三部門的協商與合作。[3]政府的政策支持、居委會的角色、社區自組織及精英的產生與能力、參與程序、非政府組織的推動等,都會影響參與式治理項目的開展。
第一,政府角色。政府的政策和態度是參與式治理能否實行的前提。地方政府具備引入參與式治理的政治能力、支持參與式治理的行政能力,以及有選擇地支持項目的財政能力。[4]政府主導的參與式治理取決于地方政府是否愿意向民眾開放公共政策過程。[5]政府官員的態度也成為參與式治理是否可能的政治要件之一;開放的政府態度和政策平臺等可以使人們從對抗迅速走向合作。[6]有研究者依據政府態度的開放程度以及社會參與的積極性強弱程度將參與式治理分為五類:政府強力控制型參與、政府干預控制型參與、政府自愿引導型參與、政府許可的社會自主型參與,以及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的規范型參與。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起,我國已有地方開始探索參與式治理模式,但地方參與式治理存在“政府向社會賦權不足,公民社會作為社區主體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行動能力有限”[7]等問題。但既有研究較少討論NGO介入參與式治理后,傳統的政府角色是否有所變更,政府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從社區事務抽身等問題。
第二,居委會角色。居委會在傳統社區治理中處于弱勢地位,面臨“行政化困境”和“邊緣化危機”[8]。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1989年12月26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對居委會定位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組織。”居委會或因承擔過多行政職能而導致功能錯位。[9]通過成立“社區工作站”和“社區服務中心”吸納居委會行政職能的地區,又使居委會的地位迅速下降,被邊緣化。[10]參與治理模式是否有助于居委會向居民自治組織回歸?特別是在他組織NGO的參與下,居委會的角色是否有所改變?既有研究關注較少。此外,社區居民是社區的重要組成成員。在NGO參與的條件下,社區居民扮演何種角色?自治能力是否得以提高?這也是既有研究關注較少而本文將著重討論的內容。
第三,社區自組織角色。社區組織在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11]社區自組織的參與是城市社區公民社會形成與發展的標志。[12]培育公民社會、發展社會組織是彌補市場失靈、政府失敗的“第三條道路”。[13]近年來,我國城市社區自組織發展迅速,但社區自組織類型比較單一。社區自組織的參與過程和程序關乎治理模式是否能夠順利進行。參與式治理不僅是理念,還是方法。開放論壇、參與式游戲等各類工具的發展有利于參與式治理理念的實現。[14]在他組織NGO的介入下,社區自組織是否得到了實質發展?角色有否轉變?既有研究關注較少。
第四,他組織的角色。有研究引入了對他組織的討論,比如有研究提出參與式治理遵循“多方需求—多方壓力—多方協作—體制創新—需求滿足”的模式。[15]該模式引入了“他組織”,主要指街道及社區居委會,并非NGO,因此未解釋NGO參與下三者的互動模式。也有研究對NGO的角色做了描述,指出非政府組織在參與式治理中發揮支持作用,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提供培訓推動社區組織化建設及治理能力培育。[16](P13)但這些研究并未解釋他組織NGO的參與是否會改變政府、居委會、居民在傳統社區治理中的角色?NGO可以在何種程度上改變,以及如何改變“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的治理模式?
本研究選取三個城市社區街道作為案例,進行比較分析。這三個案例來自不同的城市社區,有著不同的經濟、社會及人口結構背景。三個案例存在一些相同點:第一,皆由政府、街道、居委會、NGO及社區居民參與。第二,參與的NGO一致。S中心作為NGO參與了全部案例,且在各方互動中扮演相同角色,主要負責植入居民議事方式,以一致的程序組織居民討論公共事務。第三,資金支持充足。三個案例皆有來自政府較為充足的資金支持。
我們通過公開資料收集與深度訪談,獲取三個案例的主要資料。公開資料包括三個案例的基礎信息、統計信息,主要通過官方網站以及公開發行的統計資料獲得。深度訪談對象包括三個案例所涉及的政府機構、社區工作人員、社區居民,以及參與三個案例的NGO的工作人員。
二、政府、社區、NGO在城市社區參與式治理中的角色與合作機制
本研究選取的三個案例為浙江省寧波市W街道、遼寧省某市Z街道、北京市某區Q街道。這是中國第一批在街道層面上政府、社區和NGO合作開展的社區參與式治理的街道。三個案例皆由同一家NGO(S中心)介入。
(一)三個案例的基本情況
案例一:寧波市某區W街道。該區是全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社會組織發展程度較高。2003年,區政府出臺《社區民間社會組織管理辦法(試行)》,社會組織開始蓬勃發展。2014年初,該區入選民政部公布全國首批70個社會組織建設創新示范區。本研究關注的W街道是該區8個街道之一,是中國城市地區最早一批實現參與式社區治理的街道。區政府發布文件鼓勵社會組織發展后,S中心于2004年來到該區實施參與式治理項目。 W街道是所處區西部弱勢群體集聚的城鄉接合部街道。S中心之所以選取W街道,就是希望通過參與式社區建設更加關注社區邊緣和弱勢群體。
案例二:遼寧省某市Z街道。該市曾是我國計劃經濟典型地區,是重要的鋼鐵工業基地之一。隨著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企業轉制并軌,大量經濟和社會組織回歸屬地管理,社區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顯。2003年底起,Z街道利用轄區資源,通過企業冠名社區的方式推進社區公益項目的社會化,部分地解決了經費不足、場地缺乏等問題。但這種模式主要依靠街道領導與企業負責人的私人關系,且社區居民在項目決策的參與度與項目對居民需求定位準確度低。2005年起,S中心開始介入Z街道的參與式治理項目,期望改善此種局面。
案例三:北京市某區Q街道,位于北京市南部。2001年1月,國務院批準撤縣設區,自此該區加速了城市化進程,常住人口由當時的十幾萬人增加至2014年的154.5萬人。*北京市某區2014年末常住人口,該區統計局數據,2015年1月。與北京城區內街道不同,Q街道所在區為新興城區,下轄社區較多,且社區類型多樣,既有高檔別墅區、普通商品房,也有經濟適用房區、老舊小區企業職工大院以及流動人口聚集的平房社區,形成高檔小區、普通商業小區、老舊小區、新居民聚居社區的混雜結構,社會治理問題相對復雜。S中心自2005年起介入Q街道的治理分析案例。
三個案例的經濟、社會背景、人口結構、街道規模各不相同。寧波市W街道屬于沿海發達城市的城鄉接合部地區,遼寧省Z街道屬于轉型后的老工業城區,北京市Q街道是由郊縣地區發展起來的社會階層復雜的新興城區。三個案例的共同點是都存在社區治理需求,且傳統治理模式不能有效滿足治理需求。這為政府、社區與NGO的合作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政府的角色:項目準入與財政支持
本研究中的“政府”指區級政府及其派出機構街道辦事處。三個案例中,政府在合作中處于強勢地位。政府決定NGO是否能夠進入社區;政府直接組織和領導社區工作人員;政府行使項目審批權、對社區項目進行主體財政支持、過程監督和效果評估。區級政府為NGO介入社區治理提供政策環境。但并非全部案例都有區政府的直接介入,強勢的街道可直接決定NGO能否進入社區。
在寧波市W街道,區政府在NGO社區準入上起決定作用。在確定與S中心合作之后,區政府負責項目統籌協調與方向性指導,并對項目提供財政支持。街道負責審批項目,并與區政府一同對獲批項目提供資金支持。街道全程參與項目運行,由分管社區的副主任作為聯系人,參與社區項目的策劃、撥款、執行和成效評估。
在遼寧省Z街道,其社區治理工作在該市乃至全國范圍的影響力較大,街道在NGO社區準入上具有決定權。在確立合作關系之后,街道負責提供資金和資源支持、監督及協調項目的利益相關方。街道成立項目協調小組,成員包括街道辦事處主要領導、社區建設科科長、轄區企業領導、社區居委會干部、社區領袖。此外,還成立了社區項目管理辦公室,作為常設機構,負責深入社區、調查需求、監督以及評估項目運行和效果。Z街道在財政支持方面并非全部來自政府,某基金會也對該項目給予支持,但這并未改變政府對項目擁有審批權,因此來自基金會的資金并沒有在實質層面上改變幾方的合作模式。
在北京市Q街道,街道辦事處是NGO能否進入社區的決定者。在正式締結合作關系后,Q街道選出四個試點社區與S中心合作。街道與S中心合作對轄下23個社區居委會的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在項目挑選與實施階段,街道負責項目審批,對通過審批的項目予以財政支持。
(三)社區的角色:社區項目執行者
社區由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居民組成。社區居委會雖屬群眾性自治性組織,但傳統治理模式中,居委會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居委會工作中相當部分屬于政府的工作。為改變這種情況,各地區成立社區服務中心,以承接居委會的行政職能。三個案例中,北京市Q街道和遼寧省Z街道已成立社區服務中心。社區服務中心的成立有利于居委會回歸居民自治組織,但由于居委會部分行政性職能被社區服務中心吸納,反而出現了角色和職能困惑。
政府、社區、NGO的合作為居委會注入了回歸自治組織的新職能。操作層面上,街道辦事處與居民并非進行直接聯系,居委會在街道和居民之間起到了重要的溝通協調作用。三個案例中,社區居委會承擔需求調查、項目設計、組織和協調的職能。有的街道將需求調查權下放給社區行使。比如北京市Q街道,街道賦予社區居委會進行需求調查的權限。該區新居民較多,這是傳統以戶籍人口為服務對象的社區服務體系無法覆蓋的人群。某社區3 000多居民中,1 700多人為新居民。居委會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社區中無正式工作、以照看孩子為日常主要工作的婦女群體更需要社區提供各種服務。社區將其鎖定為新的目標群體,對其展開進一步的需求調查。
在需求調查的基礎上,社區主要負責設計項目,報送街道審批,以獲得資金支持。項目實施中,社區牽頭物色項目執行人,提供項目支持和協調,必要時參與調解居民矛盾。寧波市W街道在需求調查的基礎上,有社區策劃了家庭理發項目,確定了項目執行人,并確定執行人以志愿者的身份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務。
社區居民在傳統治理模式中屬于被管理角色。居民在部分社區事務上缺乏意見表達空間,對街道自上而下組織的活動缺乏熱情、自治能力不高,有些自發成立的社區組織因資金匱乏而無法持續。比如遼寧省Z街道,老工業區的居民多為經濟轉型時期的下崗職工,居民忙于個人生計,對社區事務關注度低,公民意識薄弱,公共議事能力較低。當這些居民被邀請參與討論時,他們往往偏離討論主題,抱怨、宣泄自己個人生活的種種不滿,甚至情緒激動,頻繁打斷別人的談話。在北京市Q街道,相當數量的居民認為“居民干嗎摻和居委會的事”;聽到外國社區治理經驗時,也有人認為“人家的經驗,中國辦不到”。
在S中心的介入下,社區居民被重新動員起來,參與社區項目需求調查、項目設計及執行。在寧波市W街道,社區為了調和居民對如何辦好老年飯桌的意見分歧,邀請了享受待遇的老人和不符合條件但確實有困難的人一起討論。受邀者聚在一起商議,達成共識,既完成了社區居委會的需求調查,也參與了方案的決策制定過程。
此外,社區居民中產生了“社區能人”、項目執行人以及自我服務型組織。在遼寧省Z街道,居民起初不關心居委會的工作及公共事務,通過多次參加培訓和座談,逐漸開始關心社區事務,并成立了社區公共事務小組和社區工作小分隊。在北京市Q街道,居民成立了項目實施小組,執行已批復的項目。
(四)NGO的角色:規則植入與能力建設
本研究所關注的 S中心是2002年成立于北京的非營利民間機構,主要致力于促進城市社區的參與式治理。按照世界銀行對NGO的分類標準,S中心介于運作型與倡導型之間,屬于規則植入與能力建設型NGO。與提供社區公共服務為主的運作型NGO不同,S中心致力于輸出居民議事規則、社區居民能力建設與社區自組織培育。同時S中心也非倡導型NGO,其與社區合作的項目皆由政府主導,并不宣揚特定的使命,也沒有表現出倡導型NGO的激進的特點。S中心的角色既弱勢又重要。“弱勢”體現在NGO的進入與對項目的主導程度上。三個案例中,S中心能否進入社區取決于政府是否提供進入機會。在項目的進行過程中,S中心在資金與項目選擇上沒有主導權。但S中心的參與具有重要性,主要體現在S中心的介入注入了新的理念,輸入了新的工作方式,改變了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是社區居民參與式治理模式形成的關鍵。
在社區進入方式上,NGO處于弱勢地位。三個案例中,S中心并非通過市場行為與政府締結合約式正式合作關系,而是首先通過私人關系或在非正式場合與政府建立聯系,在獲得政府信任與肯定之后,才有可能獲得進入社區的機會。政府的默許并不足以成為NGO進入社區的充足條件,政府主動與NGO締結合作關系才準許其進入社區。在三個案例中,S中心皆是在獲得當地政府的邀請后才與指定街道建立合作關系。
在寧波市W街道,S中心負責人被區領導邀請參與研討會并分享社區參與治理的經驗,建立了與區領導之間的信任。此后,區政府決定正式邀請S中心進入區內開展項目。在遼寧省Z街道,街道領導在一次社區治理經驗交流會上結識了S中心負責人,認可其社區治理的理念,于是邀請S中心介入。在北京市Q街道,S中心負責人開始被邀請參與指導街道社區治理工作,后來經過與街道領導討論商議,最終獲得項目合作機會。
在對項目的主導上,NGO同樣處于弱勢地位。三個案例中,區政府以及街道主導項目資金,街道具備項目審批權力,S中心既無權決定項目資金分配數額,也無權決定何種項目應該受資助。S中心主要提供技術支持,包括咨詢、管理培訓及參與式技術指導。但這種技術支持的重要意義在于其直接影響了參與式治理模式的形成。咨詢、培訓與參與式技術指導在理念與操作上根本改變了傳統“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的社區治理模式。咨詢內容既包括政府向S中心進行的咨詢,也包括S中心為正在進行的社區項目提供咨詢。
培訓是S中心進入與街道項目合作初期或與項目持續過程并行的主要工作。培訓的主要目的是幫助街道、社區工作人員、社區居民了解參與式治理的理念和思路。培訓內容既包括對基層官員、社區領袖開展的參與意識的培訓,也包括針對社區參與方法的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分析社區現狀、發現問題和尋找社區需求、撰寫項目申請書、項目實施計劃和執行人的選定等。S中心開展培訓的另一個目的是催生社區內有自治能力的社區自組織。在對社區工作者的培訓中,S中心強調尋找“社區能人”和社區“非正式領袖”,并邀請在社區中有影響力、有意愿為社區服務的居民參與培訓。比如在北京市Q街道,S中心開辦了“能人工作坊”,邀請社區中的積極分子參加。很多居民雖然是社區內的積極分子,并有一定影響力,但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參與熱情不高。但隨著培訓的展開,參與者的觀念開始發生變化。通過開辦“能人工作坊”,S中心成功發掘了一批項目執行人和核心團隊。
參與式技術指導指S中心傳授參與式技術,這是S中心介入社區治理的重要特色和貢獻。這是一種被稱為“世界咖啡屋”(World Café)*“世界咖啡屋”的概念由美國人朱尼特·布朗和伊薩斯·戴維提出。世界咖啡屋是指有意識地在會談場所營造類似咖啡館的輕松環境,并嚴格按照規定的程序進行討論,以宜人的環境和充分有效的討論而著名。的公共議事方式。植入這種議事方式是S中心介入社區參與式治理的重要使命之一。這種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區的議事方式。
雖然S中心在三個街道開展的項目不同,但在居民議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同的,均發揮提供討論平臺,并將“世界咖啡屋”討論方式植入居民議事過程。通過引導居民討論公共議題,按照規則充分進行利益表達,S中心在三個案例中皆有效地組織居民對有爭議的議題達成共識。
“世界咖啡屋”需要專業團隊進行組織,保障規則可以順利執行,以實現此種會談方式的議事效果。同人力有限的街道與社區工作人員相比,NGO的特性可滿足此要求。S中心將這種“世界咖啡屋”的議事方式植入城市社區居民的參與式治理過程,改變了原本散亂、無章法、制造矛盾的爭吵式討論方式。在采用這種方式之前,S中心利用專業團隊力量深度走訪社區,對社區特點、人口結構、社區領袖等進行調查。在此基礎上,根據擬實施項目的目標人群,擬定參加“世界咖啡屋”討論的可行性名單。為使這種源自西方的議事方式對中國城市社區居民有親和力,S中心將“世界咖啡屋”的提法本土化,改名為“社區茶館”。
(五)政府、社區與NGO的合作機制及特點
由于S中心的參與,三個案例中的幾方表現為同一的合作模式。這種模式改變了傳統“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式治理模式。如圖1所示,基層政府從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者變為資源掌控者;社區居委會由行政指令的執行者逐漸轉換為居民自治領域的領導者;居民由缺失狀態逐漸進入社區公共事務視野,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和執行;NGO從被排斥在社區治理之外,變為社區治理過程中的咨詢、培訓與參與式技術的提供者。

圖1 政府、社區、NGO合作的參與式治理模式
與傳統模式相比,這種模式使得社區治理向參與式治理的方向發展,但社區作為治理參與者的能力有待增強。在政府角色上,政府雖然從提供公共服務的事務性工作中抽身,但仍然直接掌握著社區公共服務。
第一,政府擁有NGO進入許可權。三個案例皆顯示,NGO只有獲得政府邀請才可能進入社區,作為政府和社區項目的咨詢者和技術支援者。而這種支援行動要滿足政府的意愿和需求。
第二,政府對社區居委會行使組織和領導權。這種三方合作模式雖然有助于淡化社區居委會的行政色彩,特別是存在社區服務中心的地區,居委會的行政職能被吸納,但這主要體現為職能淡化,居委會更關注社區服務,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府與居委會的行政領導的關系。居委會仍需完成街道布置的任務。
第三,政府通過掌握關鍵資源來主導社區項目。三個案例顯示,政府掌握項目審批權、資金劃撥權。雖然有的項目有來自基金會的支持,但社區項目的主要資金來源于政府。在寧波市W街道,社區項目資金全部來自區以及街道兩級財政。遼寧省Z街道少部分資金來自基金會,但主體項目資金來自政府。北京市Q街道的項目資金也來自街道層面。在三方合作中,凡需要資金支持的項目,都由社區居委會負責撰寫項目申請書,然后向街道提出申請,獲得批準的項目才可獲得資金支持。對于不需要資金支持的志愿項目,街道的意志主要體現在項目策劃期間,這也是為何強勢的街道不會把需求調查權下放給社區的原因。
作為NGO的S中心雖然可以把討論技術植入議事環節,但并無權啟動居民議事過程,也無權決定討論會的參與者。NGO通過培訓令政府意識到了需求調查的必要性,但NGO并不具備需求調查權,因此也就無權影響項目內容、使用目標人群。三個案例中,NGO的介入只是在技術層面發揮工具性作用。社區居委會并未完全回歸為居民自治組織,仍為政府與居民信息的上傳下達性組織。三個案例中,多方合作下的社區雖然更注重社區服務應滿足居民需求,但其更重要的任務是完成政府下達的行政指令。居委會之所以成為項目策劃者,組織協調居民執行項目,主要目的是完成街道布置的工作。
雖然政府主導社區居委會、社區項目與NGO進入,但社區居委會的職能在此過程中發生了轉變,NGO被允許參與社區治理,社區居民的需求得以被關注,社區居民被引入參與式治理過程,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提高。在NGO將“世界咖啡屋”討論方式應用于社區居民議事過程后,社區居民能夠運用理性、有序的討論方式表達需求、交換意見,在爭議問題上取得共識。但這仍是一種被動的參與模式。社區居民在收到街道或者居委會邀請之后才可能參與有關議題的討論,制度化、組織化的日常意見表達機制和討論平臺的匱乏,使得社區居民難以自主啟動討論議程。
三、多方合作下參與式治理可持續性的分析與政策建議
三個案例中,多方合作的參與式治理模式均以不可持續而告終。這并非因為項目效果不佳。多方合作模式在提升社區服務豐富程度以及居民滿意度上取得了成效。比如在寧波市W街道,S中心介入的第一年中,街道層面投入了2萬元資金,共開展了23項服務,受益人群1萬多人次。這些項目根據需求調查設計,目標人群明確,并采用“世界咖啡屋”方式解決爭端和沖突,項目實施過程中受益居民參與熱情較高,自我管理和議事能力也有所提高。
在三個案例中,項目未能持續的原因是一致的,主要體現為:
第一,政府成為參與式治理能否持續的關鍵變量。政府領導的更迭對項目的可持續性有決定性影響。三個案例中,合作模式皆因政府領導發生變動而未能持續。在寧波市W街道,政府領導發生變動,新主管領導因有其他發展規劃而終止了與S中心的合作。在遼寧省Z街道,S中心與該街道的合作由街道主管領導促成,合作的實施計劃由該領導與S中心共同制定;街道層面其他合作部門的負責人由該領導任命;合作過程中街道的想法皆由該領導提出。因此,該主管領導的調離直接導致Z街道與S中心的合作終止。繼任領導上任后雖然表示愿意繼續支持與S中心合作,但實際合作逐漸減少。北京市Q街道的項目也因相同原因而終止。
第二,社區自我管理型組織欠缺,項目缺乏可以持續的組織平臺。即便在項目進行過程中,政府與NGO的旨趣也已經發生偏差。政府更傾向于社區開展文體活動;S中心希望通過提高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鼓勵居民建立社區自組織。社區居民雖然獲得參與機會,但與政府還是“組織與被組織”的關系。社區居民只有在獲邀參與政府以及社區設計的項目時,才有參與治理的機會。治理模式的改變提高了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但并沒有從結構上改變政府與社區“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社區自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很難產生。因此,一旦NGO撤出,絕大部分社區項目難以為繼。
第三,資金來源單一。三個案例中的資金主體來源于政府資助。這使得需要資金支持的社區項目和社區組織雛形無法離開政府的扶持。政府支持則資金充裕,政府不支持則資金鏈斷裂,項目無法持續。在寧波市W街道,區政府予以支持的階段,區與街道兩級財政對社區項目給予資金支持。區級財政最初對W街道予以10萬元的年度經費,后來有的年度經費增加到15萬元。街道層面的財政投入也呈現增加趨勢,社區項目沒有資金壓力。但當區主管領導更換后,參與式治理模式失去了來自政府的支持,合作項目也因此告終。遼寧省Z街道雖有來自基金會和企業的支持,但這并沒有改變社區項目資金來源單一的結構。失去政府的支持等于失去外部資金支持。當Z街道支持合作模式的領導調離后,項目可持續的部分逐漸減少。
第四,居民議事能力不足。NGO的培訓令政府及社區意識到了參與式討論的重要性,將“世界咖啡屋”的議事方式植入討論過程可以幫助居民有序表達意見。但這一階段,社區居民處于被組織與熟悉規則的階段,尚未形成獨立自我組織的議事能力。討論主持人對居民議事能否有效、順利進行至關重要。合作期間,NGO擔當規則實施者的角色,負責主持討論,通過提出有明確導向且有建設性意義的問題引導討論全過程。主持人是否有能力控制局面,既通過保障實施規則令參與者充分表達意見,又可以引導討論向著產生建設性共識的方向發展。NGO較難通過短期項目培育居民議事主持人。居民議事主持人需要以社區內自生的社會組織為依托,在NGO的長期介入下挑選和培養,并在實際討論過程中逐漸提升能力。
綜上所述,通過對三個街道的比較分析,在政府、社區、NGO合作的治理模式中,NGO的介入并未改變傳統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社區治理模式。但通過NGO的參與,政府與社區的角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調整。政府從以往的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資金支持者和規則制定者;社區居委會由政府行政指令執行者轉變為公共服務項目的設計者和社區居民的組織、協調者;社區居民被有效整合進社區治理項目,參與需求表達和項目涉及與執行;NGO在治理過程中提供咨詢和技術支持以及能力提升。
在合作模式的可持續性上,政府、社區、NGO合作的參與式治理模式受基層政府領導更換的影響顯著,項目合作的持續性不佳。三個案例中,多方互動的合作模式皆因政府主管領導調離而未能持續。政府通過掌握社區服務項目審批權、財政來源,以及NGO的社區準入等方式,主導著社區服務項目。社區居委會、社區居民以及NGO處于弱勢地位。社區居委會依舊要完成政府交托的任務,任務形式從行政指令變為社區服務項目;社區缺少居民主動表達需求的平臺與機制,居民需求通過被動征集機制整合進社區服務項目。通過非正式渠道與政府建立合作關系的NGO的角色限于提供技術支援、規則植入與能力建設,NGO與基層政府建立的信任關系相對脆弱。
基于此,本研究對完善城市基層參與式合作治理機制提出如下改進措施:
第一,增強居委會對社區公共服務類項目的自主性。本研究顯示,在政府、社區、NGO合作的參與式治理模式下,居委會功能雖然有所改變,但自主性仍有待強化。為推進居委會回歸社區自治組織,可借鑒新加坡“政府主導,法定機構組織,民眾參與”的社區共建經驗,理順政府、社區與居民的關系。在社區公益項目上,區、街道可將自治范圍內社區項目的選擇、管理與設計權限下放給社區,由社區根據居民需求完成項目遴選、設計與過程管理和監督,這有助于調動居委會的工作積極性,令公共服務類項目更貼近社區。
第二,建立長效機制,培育社區居民對自治事務的議事能力,增強對社區自組織的培育。本研究顯示,社區自組織匱乏是參與式治理模式持續性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方面可借鑒美國經驗,通過社區會議培養社區居民的參與及議事能力。建議基層政府以居委會為組織平臺,對社區居民進行系統培訓,逐漸使社區居民形成管理自治事務的能力,能夠有效參與并設計社區自我服務項目,激發社區活力,促進和諧社區建設。
第三,適當拓展資金來源。本研究顯示,社區自組織資金來源單一是社區自組織與他組織合作可持續性較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議拓寬社區自組織資金來源渠道,加強對資金平臺與渠道的監管。此方面可借鑒美國NGO與政府、社區合作的資金供給模式。政府更多地負擔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通常越貼近基本公共服務,政府財政撥款所占比例越大。在拓寬社區自組織資金來源問題上,可參考美國經驗,政府有側重地向社區提供財政支持。在拓寬社區自組織資金來源的同時,應規范資金提供機制,加強必要監管。國務院主管部門可建立社區公共服務類慈善公募基金清單管理制度,規范社區公共服務資金來源渠道。慈善公募基金清單可成為全國范圍社區公共服務資金來源渠道。這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公共服務經費區域不均的情況,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均等程度。
第四,將他組織NGO進入、退出社區的方式制度化,提高政府、社區與NGO合作模式的穩定程度。本研究顯示,NGO通過非正式渠道進入社區是其參與式治理模式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建議在既有項目制的基礎上,基層政府可嘗試與他組織NGO建立中、長期合作機制,使在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上已取得一定成績的NGO得以獲得長期合作機會。在社區進入方式制度化的同時,明確退出方式,進一步規范政府、社區、NGO的合作模式。
[1][2] Archon Fung ,and Eric Olin Wright.DeepingDemocracy:InstitutionalInnovationsinEmpoweredParticipatoryGovernance.New York: Verso, 2003.
[3] Eran Vigoda.“From Responsiveness to Collaboration Governance: Citizen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 2002, 62(5).
[4] Wampler,B.“When Doe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eepen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Lessons from Brazil”.ComparativePolitics,2008,41(1).
[5] 張緊跟:《參與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體系創新的趨向》,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6)。
[6] 張緊跟:《從抗爭性沖突到參與式治理:廣州垃圾處理的新趨向》,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
[7][11] 陳剩勇、徐珣:《參與式治理:社會管理創新的一種可行性路徑——基于杭州社區管理與服務創新經驗的研究》,載《浙江社會科學》,2013(2)。
[8][10] 鄭杭生、黃家亮:《論我國社區治理的雙重困境與創新之維——基于北京市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實踐的分析》,載《東岳論叢》,2012(1)。
[9] 楊貴華:《轉換居民的社區參與方式,提升居民的自組織參與能力——城市社區自組織能力建設路徑研究》,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12][15] 王敬堯:《參與式治理:中國社區建設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3] 羅重譜:《“第三條道路”理論與參與式治理模式的構建策略》,載《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08(2)。
[14] 賈西津:《社區參與式治理的理念和原則》,載《中國民政》,2015(3)。
[16] 賈西津:《中國公民參與——案例與模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AComparativeCaseStudyonParticipatoryGovernanceunderGovernment-community-NGOCooperation
ZHANG Nan-di-y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Government-community-NGO cooperation has been the recent pattern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in China’s urban communities, with communities in charge of program implementation, NGO in charge of technique support and capacity building. 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n three urban street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instead of directly getting involved in community affairs, governments turned out to be rule-mak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ers; residents’ committee plays the role of program coordinators; and residents’ demands are included in public service programs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NGO. However,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communities and NGO is inherently weak since governments dominate their NGOs’ community entry and the cooperation relies much on informal ties and local cadres’ alteratio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urban communities;government;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張楠迪揚: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政企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100872)
(責任編輯林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