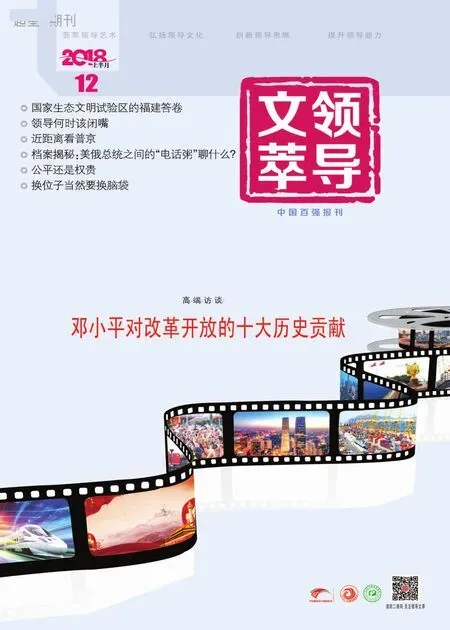從洞朗對峙看中印戰略競爭
朱翠萍
自2017年6月18日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界進入中國境內、企圖阻止中國在洞朗地區的道路施工、挑起中印邊境對峙,持續數月之久。盡管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中國外交部也以大量史料為依據,指出印方越境行為的非法性,警告并敦促印方無條件將越界邊防部隊撤回到邊界線印方一側。但不知道是“騎虎難下”還是“有意為之”,印度的撤退事拖延許久,該對峙已經成為中印自1962年邊界沖突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事件。
國內民意煽動+“地緣政治想象”
仔細觀察不難發現,此次印度非法越境而導致的洞朗對峙,存在內部驅動與外部因素兩方面的原因。
內部因素:第一,為總統大選“造勢”。對峙發生一個月之后的7月17日,印度即舉行總統大選。莫迪政府希望印度人民黨(BJP)候選人拉姆·納特·考文德勝出,從而夯實執政黨在議會的權力基礎。果然,印度選舉委員會7月20日宣布的總統選舉計票結果顯示,考文德以2930張選票成功當選印度總統,以絕對優勢擊敗反對黨提名的候選人。這一結果不僅可以鞏固執政黨在人民院(議會下院)的勢力,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目前在聯邦院(議會上院)實力不如反對黨國大黨的情勢。第二,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轉移國內矛盾。莫迪執政以來,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廢鈔、征地、稅改等。這些措施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激化并積累了不少矛盾。此次中國在洞朗地區修路,無形之中成為印度政府轉嫁國內矛盾的“契機”。莫迪有意借此機會,將國內不利的輿論氛圍轉變為積極的民意支持。一直以來,受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的影響,“中國因素”極易引發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三,減緩市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速度。目前中國的手機、家電和玩具等消費品正在加速占領印度市場,這讓莫迪政府擔心會造成更大的對華貿易逆差并沖擊到印度國內產業的發展。
外部因素:第一,中國在洞朗地區修建公路和基礎設施增加了印度的擔心,印度建立在“地緣政治想象”基礎上的“威脅感”加大了。印度擔心中國修建公路和基礎設施會使洞朗地區由原來的中國—不丹“爭議區”轉變為中國實際控制區。他們還認為該地區有可能成為一把“尖刀”,而它一旦插入被印度稱為“雞脖子”的西里古里走廊,就會成為中國“肢解”印度的“利器”,增加印度在陸地方向的戰略被動。第二,印軍越境行為也有對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通過巴控克什米爾地區表示不滿之意。近年來,不斷深化的中巴關系,讓印度認為“有理由”把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甚至是“假想敵”。特別是,建設力度不斷加大的中巴經濟走廊在印度看來簡直“如鯁在喉”。第三,與印度沒能如愿加入核供應集團而產生的“挫敗感”和“失落感”有關。2016年印度沒有如愿加入核供應集團,其將失敗的主要原因歸咎于中國。第四,為印度聯合美日進行軍演尋找“借口”。印度慣用“中國威脅”來為其國防建設和聯合軍演尋找理由,此次在邊境滋事也是在為聯合美日在孟加拉灣進行首次“航母軍演”尋找借口,回應“中國潛艇進入印度洋”。
不斷加劇的中印戰略競爭
此次中印邊境對峙事件引發了兩國外交和媒體之間激烈的“語言對峙”,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該事件背后不斷加劇的中印戰略競爭關系。多年來,中國在對印關系中,并未將印度當作對手,對印政策始終展現的是一種積極合作的姿態,但印度卻不那么“領情”。在印度的對華認知中,首先,它認為中國是印度追趕的目標,中印之間現實的實力差距對印度構成了威脅,中國被定位為印度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對手”。其次,印度還認為中國經營與南亞國家的關系和進入“印度的后院”印度洋,將會改變這一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并挑戰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霸主地位,削弱印度在印度洋的影響力。另外,印度還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逐漸形成對其的包圍態勢,中國被印度定位為戰略競爭中的“假想敵”。因此,可以說,印度這次的越境行為是其基于對中國周邊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錯誤理解”,是對中國在洞朗地區修建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誤讀”,以及基于地緣政治想象對整個戰略形勢的“誤判”,但它反映了中印戰略競爭的加劇。
從長遠看,印度之于中國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都不大可能指望印度助力中國,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重視印度。印度是南亞最具實力的國家,是除美國之外對印度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也是中國周邊經濟快速發展的最大鄰國。因此,中國需要重視印度,需要加深對印度的認識,更需要搞清楚印度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印度的對華外交戰略與政策走向是什么。
中印加起來有25億人口的消費市場,如果兩國能很好地進行合作,不僅雙方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整個世界也對兩國合作之于全球經濟的貢獻寄予厚望。另外,良好的經濟合作還可以成為維系雙邊政治關系的壓艙石,然而,理想和現實之間總有距離。
中印關系的復雜性超過預期
近年來,由于印度對華“觀念對峙”而使兩國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合作困境”。印度的權力階層和知識精英習慣于根據“地緣政治想象”所構建的“地理事實”來展開戰略應對,而正是這種“地緣政治想象”成為認知錯位、甚至導致安全困境與地區沖突的主要來源,這也是中印之間無論政治關系還是經濟關系都存在誤解和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對于印度來說,中國是一個追趕對象,同時也是最大的競爭對手。這不僅受獨立之初的開國總理尼赫魯關于印度必須在亞洲和世界事務方面發揮大國作用的觀念影響,也頗受深厚的“門羅主義”情結的影響。印度不僅將南亞次大陸的鄰國視為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意欲將安全范圍通過“東向行動”政策擴展到太平洋及其更廣泛的地區。幾乎印度所有的南亞鄰國,在面對印度的壓力之下,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以創造一種有利于自身的均衡。而這正是印度最為擔心的,不丹也不例外。中國被印度視為影響其經營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的一個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因此,印度對華即便是經濟合作,也會建立在對戰略環境的評估基礎之上,難以離開地緣政治因素進行考量。印度戰略界和知識界的精英對于“中國威脅”的認知,也是伴隨著各種事件的變化而此消彼長。比如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表現出過度的“疑慮”,特別是對中巴經濟走廊非常不滿甚至抗議,即便對已經上升到一軌層面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建設,也持有明顯的戒心。
筆者認為,中國需要將中印關系置于亞太甚至全球背景下考量,至少需要從區域層面而非雙邊層面考量,從中國的南亞政策和印度洋戰略視角考量。可以預見,印度根深蒂固的地緣政治想象和對中國的錯誤認知,將進一步助推中印地緣戰略競爭,使得中印關系充滿挑戰,中印關系的復雜性超過預期。
(摘自《世界知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