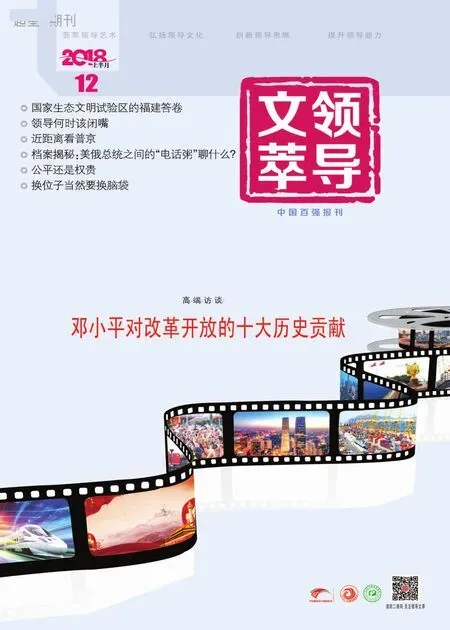后武則天時代的政治分野
孟憲實
中宗對于武則天的態度無法如五王那般堅決,母子之間雖然有政治上的立場差別,但是中宗無法回避的是孝道拷問
神龍復辟之后,作為唐朝應該如何對待武周?就此而言,似乎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對于處于政治最高位置的唐中宗,如何對待武周的另一個層面,則是如何對待母親問題,于是在濃厚的孝道時代氛圍中,中宗的抉擇便遭遇巨大困難。
嚴善思引發的武則天是否合葬乾陵的問題,其實僅僅是當時圍繞武則天展開斗爭的一個部分而已。
在嚴善思的報告中,把乾陵的修建完成當作不祥的開始,“修筑乾陵之后,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總萬幾二十余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所謂國難,正是指武則天的統治,可以概括為“武則天稱帝事件”。從時間的起始與結束來說,武則天稱帝事件,正是開始于高宗的駕崩,而結束的時間正是神龍政變。這個時期,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太后時期和女皇時期。對于唐朝而言,武周篡唐當然是唐朝的大災難,稱作國難并不過分。
嚴善思始終沒有明說,但實質內容人人都會明白,即給唐朝帶來如此災難的武則天,是否還有資格與唐高宗合葬?他的具體建議是“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看看乾陵形勢,以梁山為陵,既然不入乾陵,便是在梁山之外建立陵園,那相當于驅逐了武則天。唐高宗生前確實與武則天為夫婦,但在高宗駕崩之后,武則天背叛了唐高宗,甚至廢唐立周,自稱皇帝。誰都知道,武則天的帝位,是神龍政變之后被迫取締的,說武則天是唐朝的大敵并不夸張。然而,當武則天去世之后,這樣的一位高宗皇后,如何還能夠與高宗合葬呢?嚴善思反對武則天再入乾陵,從乾陵的情形看,那就是不入乾陵,不合葬,他稱之為“從葬”而已。顯然,這便是對武則天有罪的具體懲罰。
嚴善思的主張含有這些內容,但文字上卻不如此表述。把武則天當作唐高宗的罪人來對待,自然有可通之理。但是,此事過于復雜,是否把武則天看作是唐高宗的罪人,最關鍵的人物是唐中宗。中宗是唐高宗與武則天共同的兒子,在武則天的葬禮問題上,中宗是喪主,而且他還是皇帝,所以他的認知與態度的重要性是任何人都無法比擬的。歷史上,凡是涉及相關問題的,通常都是皇后被剝奪了名號,于是相應待遇自然被取消。而武則天的皇后名號,不僅是她自己的遺囑內容,也是中宗朝廷所承認的。這對于事情的最后結局而言,顯然是最根本的原因。
其實,此時的唐朝,對于武則天的評價完全沒有進行,整個中宗甚至睿宗時代,對于武則天的評價都無法進行。大概正是這種政治局面,決定了嚴善思的文字風格,思想內容很明顯,但不得不閃爍其詞。
那么,嚴善思的主張,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或者說,在當時的朝廷中,這種觀點是否反映了一定的政治分野及其斗爭呢?讓我們先看看嚴善思的經歷,大體估計其人的政治動向。《通鑒》有如此記載: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樸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共構陷善思,坐流歡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善思名譔,以字行。
由此看來,在武則天時代,嚴善思就屬于“公直敢言”者,是對于酷吏政治敢于斗爭,并為此付出過代價的人。然而,這些資料不能證明嚴善思就是反對武周的斗士,不能證明他的反對合葬主張是他一貫反對武周的新表現。
不過,神龍政變以后,新復辟的唐廷確實閃爍著詭異的光芒。武周雖然不復存在,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武周的影響力依然巨大。一方面,武三思作為武周勢力的代表,依然活躍,尤其與皇帝、皇后的關系依然密切,還在不失時機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人們對于武周的感情,并不是想當然地立刻劃清界限。神龍政變主導者希望的一呼百應局面,事實上并沒有出現。這是因為如今的皇帝,并沒有跟武周一刀兩斷的思想與行為,甚至不否定自己與武周的血肉聯系。此外,武則天提前進行的防范性安排,如今切實地發揮了作用。
總之,到武則天逝世的時候,中宗朝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武周政治勢力的代表不僅沒有受到清算,反而占據了更有利的位置。其中,觀察歷史記載,對于中宗的這種作為,史書通常表達的是不滿和無奈。尤其是,大書特書武三思與韋皇后奸情嚴重,而中宗對此卻百般維護,把唐中宗的弱智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其實,中宗對于武則天的態度無法如五王那般堅決,母子之間雖然有政治上的立場差別,但是中宗無法回避的是孝道拷問。神龍政變,在某種意義上說,對于中宗而言是多此一舉,因為武則天安排中宗為接班人的意圖天下共知。于是,愧對于母親的心理在中宗這里是多有表現的。中宗的這種思想,自然強烈地決定了這個時期的政治面貌。
然而,武周問題依然存在。武周對于唐朝的顛覆史,是大家共同經歷的,唐朝復辟成功,對于武周的歷史清算遲早要進行。趙雨樂認為“陵議之爭,是武韋黨人與張柬之附黨的初次交鋒,由此促使三思等人外放五王的政治部署。”其實,反對武周最具代表性的勢力即“五王”,在武則天去世時,就已離開了政治中心,認為嚴善思屬于張柬之附屬黨羽是難以證明的。嚴善思這位政治立場并不分明的官員,他提出的問題是真切的,是中宗朝廷需要面對的。即,武則天與唐朝的關系,應該給予恰當的評價,作為取代唐朝的武周皇帝,是否有資格再回復原來的皇后身份,重新進入李唐的太廟,顯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最終,中宗朝廷采取的策略是回避根本問題,堅持繼續維護武則天。中宗朝的政治,于是無法擺脫其過渡性質。不僅如此,睿宗也無法超越。這致使史學家不得不十分強調武周的強大影響力。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