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背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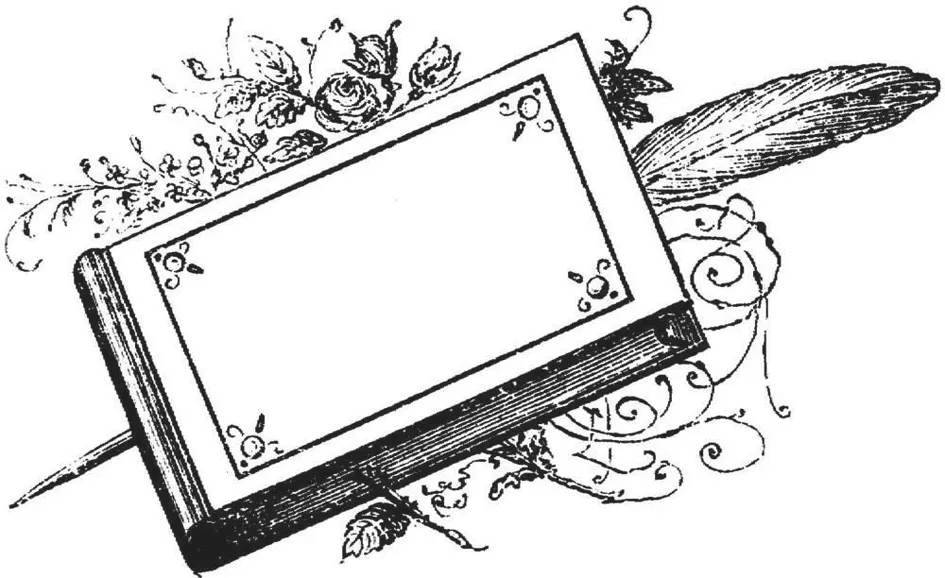
小學畢業那年,我是我們學校分數最高的學生。縣城里最好的私立中學給我開出一個誘人的條件——只要我肯去讀書,學校將會免除我在校的一切費用。和村子里那所簡陋落后的中學相比較,我自然選擇去縣城讀書。
九月份,灰蒙蒙的天空飄著若有若無的小雨,父親扛著一個巨大的編織袋,送我去學校報到。
我們坐在連接縣城與鄉村的破舊的班車上,窗外是一望無際的綠色小麥海洋。這片綠色飛速地后退,很快就被車子甩在后面。來不及道別,我就離開了這片綠色的麥田,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鄉村。
鄉間的土路很顛簸,那個被父親放在腳下的的編織袋不時隨著車子的顛簸來回地移動,父親的一只手緊緊地攥著編織袋的一角——編織袋里有母親為我做的棉被,還有她特意為我買的新衣服。
到了學校我才發現,原來好多學生都是父母開著私家車送來的。各式各樣的小轎車早已占滿了學校的操場,我的眼睛感到一陣暈眩。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么多的小轎車聚集在一起。
父親陪著我來回地忙活——先是去校辦公室報到,然后去宿舍,進了宿舍才發現還得去教室找班主任拿宿舍鑰匙和床鋪號,于是只能折返再跑一次。
匆忙穿過操場的間隙,我從一輛輛擦得锃亮的小轎車上看到我和父親渺小的影子,父親肩膀上巨大的編織袋將他壓得腰都彎了。
順利進入宿舍后,大汗淋漓的父親脫下洗得發白的外套幫我鋪床。我看見他的藍色背心上有一個破洞,露出一塊黝黑的皮膚。這時,宿舍進來一對夫妻,領著一個男孩。戴金邊眼鏡的女人一進來就捂著鼻子,抱怨宿舍里有一股霉味兒。西裝革履的男人幫兒子鋪床時對女人說:“現在就把羽絨被拿來是不是有點早啊,這才九月份。”女人說:“這羽絨被是我特地買的超薄的,還透氣,就是現在蓋的,入冬后再給兒子帶一條厚的來。再說,你以為是咱家啊?這里的暖氣到了冬天開不開還不一定呢!”那個小男孩也在抱怨六人間的宿舍太擠了,男人教訓他說:“你別挑肥揀瘦了,你知道家里花了多少錢人家學校才收下你嗎?”
我聽著一家三口的對話,默默把父親剛剛給我攤開的棉被卷了起來。我的手能感覺到,棉被里來自故鄉陽光的溫暖正在一點一點地消逝。
我又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城鄉差距”這個詞的具體含義,原來,人與人的不同,從一出生就開始了。
一切安排妥當之后,我們走出宿舍。天空中飄起了小雨。我們沒有帶雨傘,雨溫柔地落在我的臉上,仿佛是在撫慰我失落的心靈。
父親對我說:“我走啦,你在這兒要好好學習,缺什么就給家里打電話。”說完,就大步朝學校的后門走去。
我看著父親越來越遠的背影,突然意識到,從此以后我就是一個人了。周圍都是陌生的人,連小轎車都是冰涼陌生的——我又一次在一輛黑色的小轎車上看見自己瘦小的影子。我叫了一聲“爸”,我確信,我的音量足以讓父親聽見并回頭看我一眼,但是父親并沒有回頭,他遠去的背影漸漸模糊,消失在我的視野里。
最初的幾個夜晚,我總是會夢見父親的背影,我追著他的背影奔跑,卻怎么也追不上。
我是個內向的人,周圍又都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總是討論名牌衣服、籃球、明星,來自農村的我對這些一無所知。所以,我一直都是自卑的,永遠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好在,初中三年,我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后來我又去了市里最好的高中讀書,但我仍舊是自卑的,因為我來自農村——我帶著鄉音的蹩腳普通話經常被同學笑話。
這種自卑一直持續到高中畢業。大學期間,我終于不再自卑了——我可以用稿費買自己喜歡的衣服,我是宿舍里唯一一個不用向家里伸手要生活費的人。
大三那年暑假,我聯系好實習單位后,回農村老家住了幾天。離上班還有三天的時候,我對父親說,我要提前走了。
父親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我們并排等車,我發現我已經高過父親半個頭。
車來了,我剛要上車,父親突然喊了一聲我的乳名。我回頭,父親卻逃避似的轉身朝村子里走去。
那一刻,我突然憶起初一報到時父親離去的背影,我想父親此刻的心情和那時的我應該是相似的吧。面對離去,面對告別,我們只能留給最親的人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
坐在車上,我想起了龍應臺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楊召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