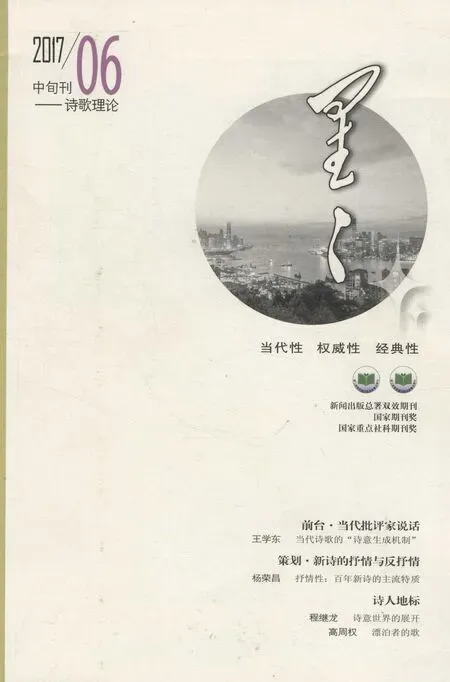新詩史書寫的新的可能性
——評張德明《百年新詩經典導讀》
陳 娟
新詩史書寫的新的可能性
——評張德明《百年新詩經典導讀》
陳 娟
事物的命名體現事物自身的建構方式,新詩從誕生之初就深陷于命名的糾紛,白話詩、自由詩、現代詩、中國新詩、現代漢詩等概念的提出,呈現出詩歌本體的自覺及研究者對詩學特定領域的關注。就一般意義上而言,新詩即采用現代漢語寫作的詩歌。從上世紀初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本白話詩集即胡適的《嘗試集》,到三四十年代層出不窮的詩人創作,到八、九十年代當代詩歌發展的新轉向,再到本世紀不斷個人化的詩歌創作,詩歌的發展呈現出多種態勢,“主題”、“意象”、“結構”、“口語化”、“日常經驗”、“敘事”、“反諷”等詞語成為評論詩歌繞不過去的關鍵詞。隨著新詩及其評論的不斷發展,新詩史寫作也在不斷進行,觀覽眾多的詩歌史,不得不承認新詩研究在史料挖掘、經典重評、詩歌史自身建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2015年由暨南大學出版的《百年新詩經典導讀》就是代表之一。
新詩史說到底是靠文本支撐的史作,觀覽眾多詩歌史,對于文本本身的關注遠遠小于對新詩運動、思潮、藝術形式、詩歌流派的關注,以致讀一本詩歌史記住的是“新月派”、“現代派”、“白洋淀詩群”、“朦朧詩派”等詩派的名字以及對這些詩派整體特征的描寫,但是具體到詩作本身,能說的甚少。再者,在詩派、運動、詩潮的關注下,詩人與詩人之間的區別性特征也被掩藏了,詩歌史淪為事件史,見“史”見“論”,不見“詩”與“人”。洪子誠曾經提到,廣義的詩歌史包括一切對新詩運動、思潮、藝術形式、詩歌流派和詩人創作的內在研究。新詩史的書寫應該把對新詩運動、思潮、藝術形式、詩歌流派和詩人創作的內在研究建立在豐富文本的基礎上。誠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言,《百年新詩經典導讀》的寫作立足于“以文本的形式來呈現中國新詩的歷史發展軌跡”,非常重視“深入文本內部進行細致考察”。[1]P4全書共十六章,直接以經典詩歌史上的重要詩派命名,特別地將港臺詩群、網絡詩歌與新世紀詩歌及易被忽視的中間代詩群分別單獨立為一章,讓人十分醒目地在看到一個連貫的詩歌發展過程的同時對港臺詩歌和當下詩歌有進一步的了解。新詩百年歷程出現不少詩作,《再別康橋》、《致橡樹》、《斷章》等早已是耳熟能詳的經典,作者浪里淘沙選擇49位詩人約54篇作品,采用細讀的方式對選取的詩歌作品的內在肌理進行挖掘,展現出超強的辨識能力和細讀分析能力。具體到章節設置,簡單的筆法對詩派和代表詩人進行介紹,落腳于對代表作品的導讀,或許作者本人也意識到一位重要詩人只選一首代表作有些局限,所以才以附錄的形式附上相關作品進行拓展。當然,全書最讓人欣喜的是附錄一的《新詩研讀方法舉隅》,常言道,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在現行的教育形式下,現當代詩歌的教育是相對薄弱的環節,不少大中小學生紛紛表示讀不懂詩、不知道如何讀詩,更有人一提到現代詩歌就直接搖頭否決:這能叫詩嗎?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讀詩讀得太少、閱讀的切入點沒有找好。《新詩研讀方法舉隅》無疑為如何讀詩提供了很好的范式,文章列舉了新詩研讀常見的六種方法(主題提取、意象穿綴、語詞細讀、結構剖析、中外比較、古今對照)并以典型的詩歌作為案例闡釋方法的具體運用,不愧是經典“導讀”。作者恰到好處地將西方現代文論的批評方法和中國新詩的獨特氣質融匯在一起,特別注重文本本身,使得整本書在見“史”見“論”的同時,見“詩”見“人”。
詩人參與詩史書寫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指詩人被詩史家編入詩史;二是指“詩人”創作新詩史。具體來講,“詩人被詩史家編入詩史”涉及到書寫新詩史時對詩人的取舍問題。“詩人創作新詩史”中的“詩人”是廣泛意義上的概念,包括曾經寫詩,現在專注于詩歌批評、理論建設的詩評家。而“詩人創作的詩史”或許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史,包括隨筆、日記等,它是另類的,稍帶著“野史”的味道,被洪子城熱情地稱頌為“細節詩歌史”,它以“活潑”、“輕松”或“開放”的筆調對嚴肅的詩歌史有力回擊,如詩人鐘鳴的《旁觀者》(海南出版社,1998年)、《沉淪的圣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豐富了可供“主流”新詩史采集的資料。從《呂進詩學研究》、《新世紀詩歌研究》、《網絡詩歌研究》等詩學著作中可以看出,《百年新詩經典導讀》的作者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者,同時在《星星》、《綠風》、《詩潮》等刊物上發表的大量詩作及詩集《行云流水為哪般》泄露了作者的詩人身份。正如詩人安琪所言“批評家向來以理論見長,職業訓練造就出的發達的邏輯思維如果再輔之以詩歌的形象思維,可謂相得益彰。寫詩的批評家進入文本往往更能一步到位已是批評界的共識,而詩人們對會寫好詩的批評家自然也有著天然的親近和信任。”學者的身份讓作者有嚴謹、專業的思考方式,詩人的身份則能讓作者更好地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出發理解詩歌。正因為二者兼有,《百年新詩經典導讀》才顯現出獨特的氣質。全書按詩派出現的時間先后順序安排章節,在分析詩人詩作時注重回到歷史場域及詩作本身,例如在評論《致橡樹》時首先就對詩作初發表時引起的論爭進行論述,隨后再對詩作的主題、意義進行分析。而在分析西川的詩作時,作者首先談到的是卡爾維諾提出的“何謂經典”、詩歌創作的背景,再進行文本細讀。理論和作品之間的闡釋是講究緣分的,沒有一個理論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作者針對不同的詩作不同的特點選取合適的理論切入點,顯示出作為學者本身獨到的理論素養和充分的辨識能力。當然,《百年新詩經典導讀》隨處充盈著作者作為詩人的真誠和熱情,寫到動心處作者也會直截了當、毫不避諱地大加贊美或者寫劃上一個“!”,如在評論《天狗》“正是因為這種現代性的高峰體驗才促成了閃爍著非凡藝術魅力的《天狗》這樣的詩歌的出現,并最終促成了標志著中國新詩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的詩集《女神》的誕生!”評論徐志摩《再別康橋》時坦言自己是把它當作愛情是來讀的。在對中間代詩人古禾《父親回到我們中間》進行評論時直接采用詩人安琪的文章。《百年新詩經典導讀》在尊重文本的同時,看到掩藏于文本底下某種正在或已經在流變的東西,使得詩歌文本處于互文的交叉點,不論橫向分析還是縱向引申,都有可供拓展的意義。
《百年新詩經典導讀》嚴格地說來并不是一本詩歌史,正如書名一樣,它更像是導讀,作者就像導游一樣帶我們游覽百年詩史中的經典作品。然而,它卻給了我們書寫詩歌史的啟示即讓慣有的詩論史、詩史史變成真正意義上的詩歌史、詩人史,讓我
們感受到的不是大事件大人物,而是豐富的細節。“今天,認為歷史是可總覽的整體的觀念正在被克服,沒有一個獨此一家的歷史總概括仍能讓我們滿意。我們得到的不是最終的,而只是在當前可能獲得的歷史整體之外殼,它可能再次被打破。”新詩史并不是一層不變,它在不斷的書寫過程中不斷修繕,從而展現出多重可能性,正因為這種不確定性,新詩史書寫才呈現出蓬勃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