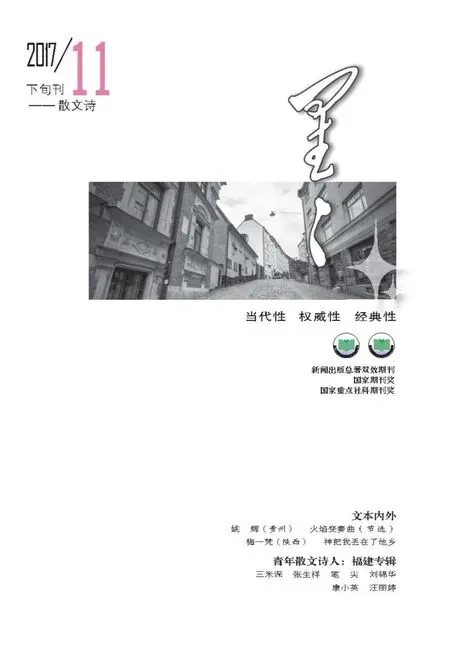遙遠的回鄉(xiāng)(組章)
讀數(shù)論
當我的生活越來越依賴數(shù)字,詩歌便越來越借助數(shù)字的排列和轉(zhuǎn)換。世界的中心已經(jīng)由數(shù)字構(gòu)成,所謂智能化,數(shù)字化,其實就是古漢語的象形會意和書寫功能逐漸喪失。站在金融中心的每一塊磚頭上,我都覺得是站在一個個數(shù)字上,我的腳趾和手指,都是因為數(shù)字而存在的,踩、摁、撥、按,都以數(shù)字為基本準則。這時候,詩歌退守血管,進而扼守心門,身體內(nèi)的數(shù)字像是藥物一樣源源不斷。我相信詩歌在變成科學(xué)之前最后一道防線就是被負數(shù)攻破的,每一個負數(shù),都長著一副無辜的猥瑣樣子。
數(shù)字,將親手送我到詩歌那里去。走在數(shù)字的地鐵軌道上,斷頭臺一個站一個站地越過,看起來鋼化玻璃里的每一個面孔都是向內(nèi)的,奔向更加智能化的人們,每一個都要做自己的反義詞,都要代替光芒去找到黑夜,而黑夜都是源自遙遠天體的空中災(zāi)難,一直在預(yù)言,從來就在發(fā)生。我們或許要經(jīng)過黑白鍵,發(fā)出簡單的樂聲,這更加加重藝術(shù)的恐懼。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數(shù)字替代。從遙遠的五線譜開始,到未來詩歌詞匯的匱乏。傾聽天籟和閱讀古典,都變成少數(shù)人的權(quán)利。這種權(quán)利,都可以用數(shù)字來遙控。詩人還在使用隱喻,因為大數(shù)字時代只有修辭手法有反抗的可能。
詩歌對數(shù)字的敏感基于辨析和規(guī)避的本能。我們需要知道二十四重人格是怎么被自我發(fā)現(xiàn)的,那將是人對數(shù)字反抗無效的自我分崩離析;我們需要知道十一種人生活出來是一個什么樣子,那將是人被數(shù)字結(jié)構(gòu)后的樣子,當然,庖丁只需要一把刀和一個點,將207這個有關(guān)骨頭的數(shù)字紛紛化解。之后,自成體系的數(shù)字虛擬世界,那些被無線電和磁場編織的網(wǎng)絡(luò),將詩歌帶入了靜音之中。于是詩歌就成了數(shù)字的靜音。看上去,這和死亡沒什么差別,也和微生物統(tǒng)治地球沒什么差別。
如果有人強迫你,讓你認識數(shù)字“一”,那是你父親,因為血統(tǒng)和愛;如果我喜歡在詩歌中插入數(shù)字,請原諒,那是因為我恐懼。因為,在當下和未來,數(shù)學(xué)不好的詩人都是可恥的。
詩歌的身體性想象力
想象力是詩歌之熱動力。想象力是詩歌之肇始和結(jié)束。想象力是詩歌之母。
中國學(xué)院傳統(tǒng)詩歌向來以揮霍想象力為樂,中國口語立場寫作也以在日常化敘述的背后激發(fā)讀者想象力為己任。如是詩人認為自己離開想象力而寫作,那是扯淡。就像詩人如果不承認詩歌本質(zhì)上的“抒情性”(不管是反抒情還是冷抒情,以及寓言詩和小說體,都會歸結(jié)到另一種形式的抒情上)也是扯淡一樣。
想象力基本上有三個階段:以最大限度發(fā)揮詩人想象力為目的;以最大限度激發(fā)讀者想象力為目的;以讓讀者來不及想象為目的。
第一種強調(diào)的是詩人才華,運用大量技術(shù)性的手段來實現(xiàn):比喻、擬情、通感、摹狀、象征、悖論、倒置、荒誕、寓言等。一般來說,會有支撐性意象以及意象帶來的想象空間,借以實現(xiàn)景象(物象)與心象之融合一體。
第二種強調(diào)的是詩歌張力,在平常的表述中開掘詩意的深度。這樣的詩,往往強調(diào)呈現(xiàn),強調(diào)直白,同時在平實的本后實現(xiàn)詩意的轉(zhuǎn)身,詩意的藏,詩意的跳脫延展。這種詩歌,看似藏起了詩人自身的想象力,實則能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力,讓人慢慢品味而不舍。
第三種強調(diào)的是詩歌爆發(fā)力。常說的捕捉靈感,瞬間、剎那、咯噔一下、怔住了,這類詞語可以來表述這種感覺。詩歌往往以表面的斷面、截面、極短時間和閉合空間,來展現(xiàn)出詩歌內(nèi)在的重擊、縱深、維度。
想象力往往有自然想象力、人性想象力和神性想象力。中國古典文化傳統(tǒng)中山水畫、意象詩,很多都是自然想象力的結(jié)晶。當然,像“念天地之悠悠獨,獨愴然而涕下”之類則是人性想象力的名篇。至于《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金剛經(jīng)》《道德經(jīng)》和與之相聯(lián)系的詩歌就具有了神性想象力的高度。于堅認為世界上的沖突本質(zhì)上是文化的沖突,文化的沖突其實是神與神的沖突。同理,詩歌的高度想象力的區(qū)別,實際上是神的想象力的區(qū)別。
其實,人性想象力的內(nèi)涵里,有一種非常具有根本性的想象力:身體性想象力。
詩人的身體性寫作往往以自我身體為立足點,在不斷自我審視中完成超級自戀和自虐。
神是人的最高人性
1
這些都是舊日里的舊人物,一個那卡,其實是多個那卡,她和她們。
2
四十不惑,方敬鬼神。把那卡說出來,其實就是把鬼神說出來。看自己,靈魂出竅,一半已枯。我就是那卡的舊日子,那卡是我的舊時光。時間把一切做舊,把我對村莊的想法,染上了更多悲劇的顏色。舊的,是輕的,也是重的。
3
因此這里的那卡,不是一個俗世里確切存在的人物,只是我想象里的一個綜合體。我賦予其形象,名字,血肉,情緒和命運。我的殘忍,在于將一個美麗的名字帶向了雪的溫度。
4
這一個系列,敘事多一些,描述多一些,貌似小說,實則是詩。我不管別人承認與否,那卡就是詩歌的,與小說無關(guān)。再說,把文體分得涇渭分明,實在是自擾。
5
那卡最初出爐的時候,是與代擺并行的。那卡是美麗和現(xiàn)代,代擺是鰥夫和執(zhí)拗。代擺能滿足我內(nèi)心對獨行俠和匪性的神往,對鄉(xiāng)村英雄主義的隱喻;那卡能滿足我內(nèi)心對溫暖和未來的追逐,那個神秘、柔軟和母性的象征世界令我著迷。
6
陽和陰,乾和坤,神靈與巫儺,就是代擺和那卡。
7
這是行將消失的文化的挽歌,當然,也是企圖挽留的一點掙扎。危機感和認同度,將那卡系列詩歌推向文化瀕危的形象化敘述中。可是我什么都不能做,也做不了。
8
神靈的出現(xiàn),是人的最高人性。因此我在余生會相信這一點。
9
僅僅滿足于小格局的人性,是詩歌的矯情。也可以說我矯情。這個世界里,相信神靈的人,太多了,因此藝術(shù)中充滿虛假,文學(xué)中滿是偽劣。我們需要把自己先洗干凈。
10
這個系列,讓我在寫作中有了久違的儀式感。
11
法師,是村莊里的請神人;銀匠,是村莊里的請神人;詩人絕不是村莊里的請神人。詩人是送神人,負責(zé)減少村莊的悲傷,特別是減少心靈的創(chuàng)傷。惟愿所有神靈來到我的村莊,可以什么都不干。
12
好吧,上香!讓詩歌里的那卡深受銀子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