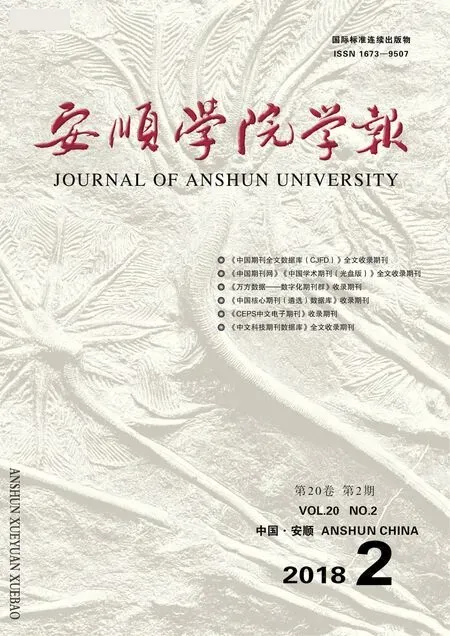略論大花苗核心音調外的“re”音
(安順學院藝術學院, 貴州 安順561000)
大花苗古歌是基于自然律的四聲羽調式,其四聲為la、sol、mi、do(其中sol是微升,do是微降),代表性的族性音調“啊嗚咿”即由此四聲構成[1]34-36。但在進一步的采集及走訪中,卻發現滇東北地區演唱的“飛歌”中帶有核心音調外的“re”音,而同樣的“飛歌”在黔西北及黔中即北盤江流域一帶仍是如前所述的四聲羽調式。那么,同屬大花苗族族群的音樂事象,其核心音調外如何還存在“另類”的“re”音呢?究其原因,主要系基督教音樂的影響,同時也是因應生境的巨變及歌曲創作需求的產物。
一、大花苗歌中“re”音存在情況的調查
2013年,在對紫云縣新弛村小學校長王玉華①進行大花苗族古歌的采訪過程中,他介紹了在新弛小學實施苗漢雙語教學的相關情況,教材來自昭通,苗語使用的是波拉德苗文即柏格里苗文。隨后參觀了當地大花苗在村中教堂做禮拜、唱圣歌的過程,新弛村教堂使用的樂器為手風琴,建筑為磚混結構,在大花苗村寨中仍屬“最豪華”的建筑。然后到王玉華家就餐,席間請其唱古歌,他說僅老輩人會唱,現在村中已無人會唱,但都會唱一些酒歌和山歌,也會吹蘆笙。在其酒歌演唱中,敬酒儀式、唱腔和旋律與其他大花苗村寨完全相同,但山歌演唱除旋律框架、調式等一樣外,卻“意外”地出現了“re”音。說它“意外”,是因為在其他大花苗村寨如普定縣仙馬村、鎮寧縣木廠村等的調研中均未發現相關演唱中有此音,并且,如按照仙馬或木廠等村寨中山歌的演唱,此“re”音應為微降“do”并在演唱中會適當下滑。
2015年,在鎮寧木廠田野調研時,村民們拿出幾張在云南昆明比賽的DVD光盤,其中有兩個人的演唱都是“飛歌”,其旋律框架仍是“啊嗚咿”。但來自貴州威寧縣的大花苗族歌手朱紅祺(音)的演唱是標準的四聲羽調式,旋律落音為“sol mi do”;而云南祿勸縣的大花苗族歌手龍慧芳(音)的演唱中即有“re”音,旋律落音為“sol mi re”②。與朱紅祺形成呼應的是,2011年“多彩貴州歌唱大賽”原生態組金獎獲得者韓靈花演唱的“飛歌”旋律中亦是無“re”音,且旋律走向與框架基本相同,區別主要是演唱內容與時長。
除田野調查外,在相關文獻資料中也發現了大花苗音樂中有“re”音的現象。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生陳蓓在其博士論文《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文化研究——以葛布教會為例》中即有表述。陳蓓在文中收錄了陶紹虎老先生演唱、楊世武譯譜的《救主耶穌》歌曲一首。此歌流傳于1905-1906年的石門坎苗區,1908年被收錄入傳教士編輯的苗文贊美詩集《福音歌》中[2]31-32。
從該譜例可以看出,旋律框架顯然是大花苗族的核心音調“啊嗚咿”,但第六小節和第十三小節均落音在“re”上。陳蓓在其文章中進一步指出,最早的苗族贊美詩比較普遍的是基督教的詞、苗族的曲,這種現象在筆者做的田野調查中得到廣泛的認同。
通過對田野調查和文獻資料的初步梳理,基本可以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大花苗族群的古歌演唱是完全基于其族群核心音調“啊嗚咿”而傳承的,其旋律框架純屬基于自然律的四聲(la、sol、mi、do)羽調式。大花苗信仰基督教者甚眾,絕大多數人已不會演唱古歌或僅會演唱片斷,目前尚未發現在古歌演唱中有“超越”其族群核心音調的現象。
第二,大花苗族群的“飛歌”(即山歌或情歌)演唱中,有是否帶“re”音的兩種演唱形式,且在大花苗族群普通民眾中,目前似尚未“知覺”其有何區別甚至其變化的重要性。
二、大花苗歌中“re”音產生與延續的原因
就目前所知,大花苗歌種中僅山歌類型中發現有的地區有“re”音,且甚至帶和不帶“re”音的演唱在同一區域中共同存在。大花苗先民通過口弦提取到的la、sol、mi、do四聲建立的羽調式的族群核心音調,卻在近代百余年間“多出來”一個“re”音,是何成因?何時引入?在此,擬就宗教音樂影響的推測和非宗教原因下“不介意”的態度來作些許探討。
1.基督教音樂影響
20世紀中葉以前,川、黔、滇交匯處聚居的大花苗生活條件非常惡劣,社會地位相當低下。“我們這支苗族啊,是從戰火中走過來的,但因敵人太強大,所以我們只得東跑西顛……。”在這個歷經磨難的民族中,際遇最悲慘的,又數流落在烏蒙山區俗稱為“大花苗”的那一支系。“據二十世紀初期苗族老人說,在土目‘諾’(大地主)的統治下,‘諾’自命為“五重天”以上的第一等人,……而處在最底層的或叫地底下的人,即‘苗子’。……苗族生育的子女,都屬土目‘諾’的私產,故需交納人租。苗族農民向土目地主交租時,逢夜晚,只能與牲畜同圈而眠,吃飯則用喂狗的器皿盛飯菜”[3]。
正是基于這種苦難,當能夠改變他們這種苦難的人出現時,那必然會是發自內心的接受,甚至是全方位的接受。這個改變他們苦難的人正是柏格里、黨居仁等傳教士。
19世紀末,英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年-1915年)在云南昭通、貴州威寧石門坎等地修建教堂、學校、醫院等,開始在這一帶的大花苗區傳教、行醫、教學,幫助苗族百姓打官司,幫助苗族創立文字及樂譜等。1905年,牧師們和柏格理用老苗文翻譯了《圣經》和贊美詩,從此,基督教及其音樂在苗區廣泛傳播,苗區90%甚至有些村寨全部信仰基督教,柏格理也被苗人尊稱為“拉蒙”(苗王)。柏格理說:“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學校”。當時很多村寨的教堂和學校就是同一幢建筑,平時做教室上課,禮拜天變成禮拜堂。
柏格理創立波拉德字母譜并用其翻譯贊美詩,他和教會學校畢業的牧師們將教唱贊美詩作為傳教的重要形式之一。教唱中一般以齊唱為主,水平較高的牧師還可以教合唱甚至混聲四部合唱。由于生存條件很艱苦,傳教士甚至為了更多的大花苗信眾都唱圣歌,他們想出了用古歌旋律填入圣經經文或故事的辦法[4]。如把圣經中“創世紀”“洪水滔天”“兄妹成婚”等故事移植到大花苗族的古歌旋律中。柏格里在其日記中寫到:
“……一引起苗族人精神抖擻地進行了祈禱。隨后,苗族婦女唱起了她們民族的創世紀古歌,一個女人打頭唱,其他人就跟上,她們用的是她們自己令人陶醉的曲調”[5]709。
從《救主耶穌》樂譜中兩處“re”音的使用與大花苗族群核心音調自然律四聲羽調式本身屬性對比可知,此“re”音本身即為“異類”,在其他眾多演唱中此音應為微降“do”并下滑。那么,是誰改的?為什么要這樣改?由于資料有限且基于某些敏感的原因,在此只能略作推測。
首先,改音的人是外籍傳教士的可能性最大。其一,1905年前后,外籍傳教士的聽覺習慣應是“十二平均律”,他們在自己的西方祖國神學院或相關學府求學時多是接觸風琴、鋼琴等“十二平均律”樂器,在他們聽來,大花苗基于“自然律”的演唱音是“不準的”,而且它的出現頻率很高,直接改成“re”音似乎更利于演唱,按當時外籍傳教士對音樂的學養,應尚無知息這個“聽覺誤差”是源于音樂的律制問題;其二,在西方傳統大小調調式音級中,“re”音在大調中為“上主音”,小調中為“下屬音”,功能明確。按西方傳統和聲理論及教堂對圣歌簡單、易學易唱的主流要求,“re”音在大調中通常配屬和弦,小調中則常規的配下屬和弦,簡單而穩定。
其次,信教與否及受圣歌影響半徑決定了是否唱“re”。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因各種原因而沒有信仰基督教的大花苗雖然極少,但目前能把山歌特別是古歌唱得好、唱得多的卻尚有些許老人,鎮寧的張紹成老人即是這樣。同時,圣歌影響半徑也起著很大作用。比較特殊的例子是普定等堆、仙馬堂一帶,由于教民承受不了教會嚴苛的要求(如不準唱自己民族的歌曲、不準吹蘆笙、不準穿民族服飾等),20世紀中早期就發生了等堆教民“抗教砸碑事件”,由此,他們似乎就此“遠離主的關懷”,而這一帶的苗族百姓演唱中就沒有“re”音。而紫云新弛王玉華等演唱中出現的“re”音,正是因他是隨父母自昭通一帶遷徙而來之故,且均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
2.非宗教原因下“不介意”的態度
首先是非宗教原因下“不介意”的態度。隨著國家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各項惠民措施的廣泛實施,手機、電視等現代通信工具在大花苗各大村小寨已不是什么稀有物品。當年青年男女勞動之余通過山歌向對方表情達意,現在外出打工或進修求學,手機都可以視頻通話;中青年多數不會唱古歌,老年人會唱的也“記不住、唱不動了”。古歌是很嚴肅、嚴謹的,不像山歌那樣可以即景即興發揮,現編歌詞對唱。因此,年青人唱山歌時,對于老祖宗留下的音樂遺產中是否多出一個“re”音,似乎已不重要,更似乎是一種“不介意”的態度。
其次是對現代音樂教學的認同。國家倡導條件適合的地方,幼兒園需辦到村里面,有條件的小學也像城市學校一樣,四年級都開英語課程了。“知識就是力量”“知識改變命運”已是共識,村民對現代教學的認同必然倒向對現代音樂教學的認同。那么,時下主流的音樂律制是以“十二平均律”為主的音樂,矛盾的現實中,苗族百姓中特別是年齡越小的苗族孩子必然趨同于“十二平均律”。唱的即便是“啊嗚咿”,但律制上已“自然糾正”為“十二平均律”下的“別樣”的“啊嗚咿”。在普定仙馬村小學采訪時,王貴光老師就感嘆“現在這些小學生,一唱我們家自己的歌就笑,說不好聽,都不愿唱。”事實上,這不僅是一種律制和另一種律制“沖突”,亦是對不同文化的否定與認同。
再次是現代審美趨向使得“re”音產生并延續。大花苗如其他民族一樣,對音樂的審美需求走向多樣化、時尚化,而對山歌、古歌的需求趨于減少,現實中原來對歌師的“高標準要求”已無跡可尋,唱好時下的流行歌曲成為青年們追求的時尚。不管是國內還是歐美的流行歌曲,從音樂創作角度而言“re”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不可或缺。由于現代音樂的審美趨向,而現代審美中“re”音又“無處不在”,繼而接受并延續它亦成為必然。
三、大花苗歌的“純性”傳承路徑
各民族的山歌可以說都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俗話說“山歌無本,全靠嘴狠”。相對固定而簡單的旋律便于歌詞的即興創編,而恰好是這個“固定而簡單”的旋律,極大地保證了各民族山歌在音調上的“純性”傳承[6]142-145。這里的“純性”,套用過來主要指山歌所體現的精神內涵與審美理法,是反璞歸真之后的藝術真實,也是歌者涵養與心態的流露。那么,大花苗山歌與古歌的“純性”傳承主要路徑是什么呢?在研究中發現,大花苗百姓主要通過三個路徑進行。
首先,大花苗百姓通過“阿江”(即口弦)提取出自己族群標志性的核心音調[7],這一歷史創舉,奠定了大花苗“獨一無二”的音樂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且我們知道,就音樂創作而言,越短小的民族音樂作品越容易發展成“宏篇巨著”。從《仙馬大花苗口弦曲》[8]的旋律可以看出,共三句旋律:第一句為核腔,第二句擴充mi-sol重復一次,第三句再擴充其重復兩次然后結束。此曲可以看成是大花苗音樂最原始的狀態,是“對隱藏在復合音中的諧音的發現,只是有人偶爾放大后聽到的第一感覺,后來把得到的不同諧音一個個連接起來就成了音樂”[9]109,其它所謂復雜的音樂均源于此。
其次,大花苗中的文化精英再以其族群的核心音調為基礎,創編了早期的古歌、蘆笙曲等,尤以古歌為最,將其文化、歷史、記憶代代相傳。提取出核心的音并組成核心音調,是高智商和高情商的有機結合,是審美需求與現實需要的完美體現,它們共同促使大花苗中的文化精英創編了代代相傳的、獨特的音樂文化。我們已難以知道大花苗先民是如何選擇并確立其核心音調,但可以作一點大膽的推測。
一方面是審美的獨特需求。按歌師張少成老人所唱,大花苗能征善戰。戰爭需要力量,表現這種力量的音樂則更需要張力,而從樂學角度講,極不協和的二度和七度音程最具張力,這在很多表現緊張、戰斗或戰爭場面的音樂中多有體現。大花苗核心音調調頭音la起始后選擇七度上跨到sol,且是十二平均律標準下的微升sol,即更加不協和。這是表現張力、表現戰爭的客觀需要,也許也正是大花苗先民們的審美需要。
另一方面是傳遞信號的現實需要。大花苗古歌中有大量反映苦難生活與征戰遷徙的內容,為了生存,先民們以唱歌的形式發出“信號”來確認是否安全。“……互相之間的來往,即使是自己內部的人,都要先用唱歌的形式問一下有沒有其他人,這樣能讓我們苗家的兵士區分出敵我以免上當”[10]174。
張紹成老人在講述苗家唱“啊嗚咿”時也講到,遠古時候的苗家男人外出打獵,婦女、老人和小孩在家。男人們歸來時遠遠的就要唱“啊嗚咿”,“對”上了才歸家,“對”不上或沒有“聲響”即視為家人已被害,男人們則須快速離開,到了安全地后才痛哭,并唱著凄涼的“啊嗚咿”以表對家人的思念。
那么,這個“信號”的傳遞如何實現準確性呢?當然最重要的是必須具有獨特性。大花苗作為最后大遷徙中“斷后”的作戰部隊,在戰亂中逃到了東北(注:僅據張紹成老人唱述,待考)并與當地居民雜居繁衍,大約在元、明兩朝交替之際從東北沿蒙古南面向西遷徙至甘肅、青海一帶。估計正是這一遷徙路線對“啊嗚咿”的選擇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簡單的說,蒙古音樂標志性旋律是以la作調頭起音,然后有兩個主要去向:la-mi上五度進行,如《嘎達梅林》;la-la上八度進行,如《敖包相會》。按中國音樂之五聲性原則,一般偏音不作為旋律骨架音使用,即向上的旋律不太可能用la-si或la-fa,余下只有la-do、la-re和la-sol,而中國傳統音樂中廣泛需求的“和諧性”中,la-do、la-re已大量使用,不具標識性和獨特性的“信號”功能。因此,大花苗選擇la-sol作為其“信號”傳遞的使者,具有鮮明的獨特性而成為可能。
再次,核心音調成為水平高下的評判標準。大花苗通過族群節日、賽歌會等,自然遴選出大家公認的優秀歌師特別是唱古歌的歌師。在大花苗居住區,優秀歌師的身份、地位相當高,他們通常也是優秀的祭師,是一個族群的靈魂和驕傲。
張紹成老人介紹說,以前大戶人家辦事都要請幾撥歌師對歌,一唱就是幾天幾夜,輸的一方須買頭牛殺來招待大家。由此可以看出,苗家人民對歌師的演唱水平是有嚴格評判標準,否則評判結果可能難以服眾。事實上,他們的評判標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即歌師的演唱必須是基于族群認同的核心音調,否則會認為“跑調”了;第二個方面是記得多、反應快,前者主要表現在古歌對唱上,后者主要為山歌對唱;第三個方面是演唱技巧,聲音要高亢洪亮,旋律要“會繞彎彎”(注:即裝飾音要多)。在木廠采訪時,村民潘志良就說,“韓靈花唱我們家的歌唱得好,不過彎彎少了些,要是我家二舅(張紹成)教她一下,就成了”。
結 語
大花苗在其長期的音樂實踐中,形成了世界獨特的,基于la、sol、mi、do四聲建立的羽調式的族群核心音調。千百年來,雖歷經征戰與遷徙,但在苦難的歲月里仍力趨其音樂文化的“純性”傳承。其基于自然律的“活化石”屬性曾經或正在經歷宗教音樂與現代文化的雙重擠壓而倍顯尷尬。核心音調外“re”音的出現并非偶然,如何保護大花苗核心音調的“純性”傳承既是當務之急,亦是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注釋:
①王玉華,男,大花苗族,從小隨父母自云南昭通一帶遷入貴州紫云新弛村,初中畢業后考入紫云師范學校,畢業后就教于新弛小學至今。
②2013年10月,由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區民族宗教僑務局協辦、團結街道辦事處主辦、棋臺社區居委會承辦的“唱響美麗苗山阿卯青年歌手賽”比賽實況錄像。
參考文獻:
[1][7][8]熊黏,王進.仙馬大花苗族族性音調初探[M].安順學院學報,2012(3):34-36.
[2][4]陳蓓.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會音樂文化研究——以葛布教會為例[D].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學位論文,2015.
[3]張坦.威寧大花苗遷徙磨難史.[EB/OL].[2013-11-28](2018-01-10).威寧自治縣政府網站.http://www.langmancaohai.com/article/article_2828.html
[5]東人達.在未知的中國[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6]劉曉紅.中國山水畫的純性與境界[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42-145.
[9]應有勤.一種不用計算的律制——渾然天成的自然律制[M].文化藝術研究,2009(6):109-123.
[10]王大陸.格米爺老尋找格資爺老的傳說[C].中國西部苗族口碑文化資料集成,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