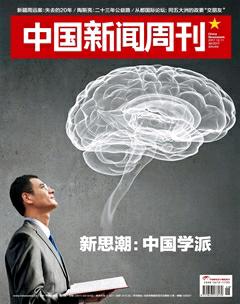吹響中國學派的總號角
蔡如鵬
“其實,我們想和年輕人說,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很酷的,從治理能力看,它是超前的;
而社會主義是很時尚的事業,恰恰是我們身邊涌動的時代潮流”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
12月2日,北京的夜晚已是寒氣襲人。不過,在清華大學一間教室里卻暖意融融,幾位學者正圍坐在一起,開著讀書研討會。他們中有幾位年輕學者,正是時下暢銷理論書《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的作者。
《大道之行》一書最初出版于2015年2月,時隔兩年,至今仍熱度不減。到今年6月,已先后印刷了37次,屢次刷新了理論圖書的加印紀錄。
《大道之行》能夠如此暢銷,是幾位作者之前始料未及的。事實上,這是一本嚴肅的理論書籍,探討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這類事關中國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書的作者之一、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鄢一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在一個功利與物欲的時代,每個人的心里都沉睡著一個理想主義青年。這個理想不僅是個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社會的理想。這本書之所以暢銷,或許正是書中的理想主義喚醒了大家心里面住的那個青年。
這群75后的年輕學者在喚醒廣大讀者社會理想的同時,也把一個全新的概念帶入了公眾的視野:中國學派。
新的學術思潮
一些學者認為,《大道之行》一書最大的特點,是帶著強烈的問題意識,以跨學科的學術視野,聚焦“中國問題”,不僅分析了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治理的優勢,而且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克服重重危機和挑戰。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在評價此書時說,它之所以讀起來讓人感覺千峰競秀,新意迭出,是因為該書中許多新的概念是基于中國實踐提出來的,超越了西方的話語。

香港中文大學政冶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王紹光。
就這一點而言,《大道之行》并不是孤例。目前,中國有一批學者正在摒棄西方主流的理論體系,以中國文化和中國實踐的視角,來詮釋對世界、對歷史、對全球當下重要議題的看法與見解。
比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對中國國情的系列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王紹光關于西方歷史中“抽簽理論”的著作,以及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汪暉所進行的歷史哲學問題研究等,都被認為是這類研究的代表。同時,他們也被統稱為中國學派。
什么是中國學派?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認為,就是受中國特殊性的啟發,在社科人文各學科里對已有知識做出具有突破性的貢獻,就是中國學派。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外國社會和在外國形成的現有社科人文知識體系,理解中國社會不同于外國社會的特殊性,是創立中國學派的兩大必要前提。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與許多人的想象相反,這些被稱為中國學派的學者絕大多數都不是本土派,幾乎都有在西方發達國家留學的經歷,而且很多人長期在國外學習、工作。比如胡鞍鋼,上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國外。
1991年到1992年,他在耶魯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他作為訪問學者到莫瑞州立大學訪學;1997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人員;2000年,到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做短期訪問學者;2001年到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做訪問研究;2003年到法國的一所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
潘維認為,正是這些國外研究和工作經歷,拓展了中國學派學者的視野,同時也更加堅定了他們要在國內做中國研究的信心。
而在鄢一龍看來,中國學派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由以西方理論為中心的知識建構方式,轉向以中國實踐為中心的知識建構方式。他說:“中國學派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解決中國問題的知識體系,并為人類發展提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事實上,除政治學、經濟學這些顯學之外,一些專業性很強的分支學科,近些年也陸續出現了構建中國學派的聲音,比如比較文學、翻譯學,甚至是財政學。
中央財經大學副校長李俊生曾撰文提出,建立財政學的中國學派。他說,西方的主流財政理論是建立在以市場失靈為起點,以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馬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理論為基礎的一種財政理論,這種財政理論的致命缺陷在于把政府置于市場的對立面,把政府財政視為彌補市場缺陷的手段,很難解釋和指導中國的財政實踐。
“例如在所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上,在當前國家推行的PPP、政府購買服務、政府采購等領域始終無法給出科學的解釋和符合我國實際的指導。”李俊生認為,中國亟待研究建立具有科學解釋力的,立足中國、服務世界的,中國氣派的財政科學理論體系。
中國學派在多個學科的興起,使它正成為一種新的學術思潮。鄢一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學派的構建不是某一學科流派的建構,而是一場涉及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范式變革,也是一場“大本大源”的思想革命。
最初,中國學派在各個學科的萌芽,大多都出于學者個人的學術自覺。如今,一些機構也開始參與其中,比如中信集團旗下的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以下簡稱中信基金會)。
中信基金會成立于2014年8月,成立之初就把“發展中國學派”作為其發展的宗旨之一。這些年,中信基金會通過組織研討會、支持學術研究、出版系列叢書等方式,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學派發生。
中信基金會理事長、原中信集團公司董事長孔丹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經過60多年的社會主義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迫切需要形成中國本土的理論創新和中國話語體系創新。
在他看來,中國學派應當來自中國深厚的歷史和文化,立足于中國本土的實踐基礎,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求和視野出發。他說:“中國學派并不是只研究中國的學派,要進行世界性研究,但是要以中國為立腳點,為出發點,為歸宿。”
對中國學派來說,更大的鼓舞來自于官方的認可和支持。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發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他在講話中說,“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也一定能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雖然,講話中沒有提中國學派,但我認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就是中國學派在官方語言中的另一種表達。”鄢一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因為兩者都強調基于中國實踐,形成一套理論體系。”
他相信,在這一過程中,事實將證明中國不但是世界的經濟巨人,而且是世界的精神巨人。
與中國崛起相伴
中國學派的興起,與中國這些年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崛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從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平均每年9.6%的高速增長,經濟規模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3%提高到14.9%。
很多國內外機構都預測,中國在2025年至2030年之間將邁進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以這么高的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的增長,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大奇跡。”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也發生著巨大的變革。“但對中國當前這樣豐富的實踐,西方理論體系卻沒有辦法進行解讀和詮釋。”《大道之行》的作者之一、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何建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本科畢業于清華大學機械系的何建宇,在大學期間被西方的社會科學所吸引,從研究生開始轉入文科學習。他至今仍記得第一次讀薩繆爾森《經濟學》時眼前一亮的感覺,“被他理論的解釋力所折服。”
但這份對西方理論的癡迷,并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到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后,何建宇越來越發現那些曾經令他折服的西方主流理論,無法解釋身邊發生的事情。“我的研究方向是比較政治學,這套理論體系基本上是以歐美國家的歷史經驗作為模板。”他說,“在解釋中國的時候,總是說不通,只能把中國作為一個例外。”
這種困惑同樣也出現在《大道之行》其他幾位作者的學術生涯中。鄢一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的集體崛起,這種情況出現了逆轉,以西方為中心的思想秩序開始受到挑戰,“中國學派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出現的。”
事實上,這已不是中國學者第一次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反思了。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一批被稱為“新左派”的中國知識分子,就嘗試著打破西方理論壟斷的局面,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當時,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就是有關“北京共識”的討論。
2004年,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指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消息傳到國內后,引發了學術界激烈的討論。但這場討論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影響范圍也僅局限于學術界。
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學者對西方主流理論的反思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標志性的事件就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在何建宇看來,與“北京共識”的討論相比,“中國模式”的討論更具有全球視野,深入程度也超過了前者。同時,也為中國學派的出現做了準備。
“不論是‘北京共識還是‘中國模式,討論都太過籠統。”鄢一龍認為,要對抗西方中心主義,需要中國學者基于中國實踐,在各個學科展開更深入的研究,重構一套新的理論體系。《大道之行》正是這個探索過程中的一個嘗試。
在他看來,《大道之行》一個成功之處是在嘗試重構話語權上取得了突破。他們在書的結尾處寫道,在這個移動互聯網的大時代,在這個屌絲塑造歷史的大時代,讓我們重申:全世界的勞動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的屌絲互聯起來!
“其實,我們想和年輕人說,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很酷的,從治理能力看,它是超前的;而社會主義是很時尚的事業,恰恰是我們身邊涌動的時代潮流。”鄢一龍說。
在爭議中前行
盡管中國學派取得了一些成功的嘗試,但在學術界它依然是個有爭議的名稱。比如就有反對者質疑,歷史上有美國學派嗎?有日本學派嗎?有必要單列一個中國學派嗎?
事實上,即便是在贊同中國學派的學者中,對如何理解中國學派也存在著差異。至今,對中國學派沒有一個統一的、明確的定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認為,中國學派是具有中國文化自信,從中華民族及國家立場出發,研究各類社會問題和進行思想探索的學術群體;是秉持實事求是,踐行中國道路,以建構中國話語,傳遞中國聲音為已任的學人共同體。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看來,中國學派不應當只限于中國人自己的研究。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不是因為中國人做的研究就叫做中國學派,這個定義應當更廣一些。納入中國學派的研究要更看重其學術貢獻,是否為現有的知識結構做出重要的貢獻。”
鄢一龍則認為,中國學派指伴隨著中國的復興,基于中國的實踐興起的一個學術派別。它的本質是擺脫學徒狀態、形成自我主張,從接軌研究轉向自主研究。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任何一個國家的學術要走向成熟并產生偉大成果,都必須樹立自主精神,形成自己的特色風格。不過,他同時也強調,建構中國學派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
在很多學者看來,這種對話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學系教授唐世平認為,要構建中國學派,必須達到相當的理論水準,能夠與西方理論進行對話。“讓西方學者能理解我們的理論,就像我們能理解他們的理論一樣。”他說,如果達不到這個水準,就不能稱之為中國學派。
唐世平這種對中國學派前景并不樂觀的看法在學術界不是個案。比如,國務院參事、經濟學家夏斌就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學派未必能形成。事實上,在當下的中國學術界,占主流的仍然是西學,絕大多數學者仍習慣于西方理論思維,對中國學派并不看好,也不理解。這也成為建構中國學派的一大障礙。
“你在大學里研究這些,不會給你的教學和科研有任何的加分。”何建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相反,很可能會被學術界所恥笑。”
事實上,《大道之行》在收獲暢銷的同時,幾位作者也受到了很多質疑。有人認為他們是“御用文字”,在粉飾太平。在這些質疑聲中,既有持自由主義思想的,也有來自對立陣營的。一些極左派攻擊他們一味取悅讀者,不符合經典的馬列主義。
比意識形態攻擊更讓踐行中國學派的學者苦惱的是,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與中國學派格格不入。鄢一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這套評價體系強調與西方接軌,更看重形式的規范性,比如要有經典的理論模型、要有量化指標等。但中國學派強調原創,并不依循西方的理論框架,形式上會相對粗糙,所以研究成果很難被接受,獲得認同。
除了來自現實的阻力之外,這些學者對中國學派的未來又存在著一些擔憂。何建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如果中國學派僅僅停留在討論層面上,沒有一大批腳踏實地、深入的研究成果來支撐,它很可能就只是一個階段性的概念,將很快成為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