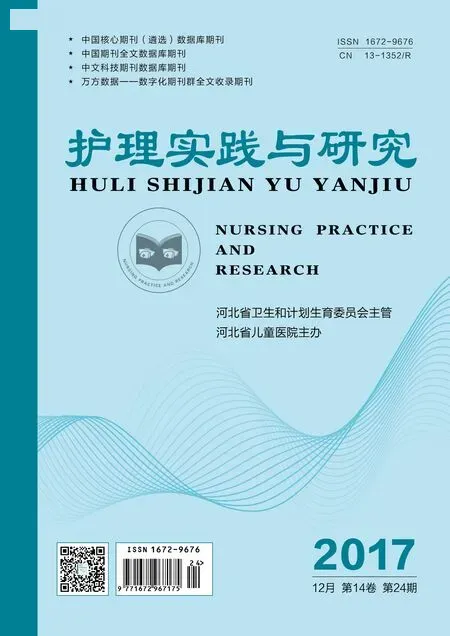精神疾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
賈 品 張 彬 王 寧 劉 煙 邢蓓蓓 葛 晶 王 巍
精神疾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
賈 品 張 彬 王 寧 劉 煙 邢蓓蓓 葛 晶 王 巍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學者就已預測到病恥感將成為精神衛生領域工作中的最大障礙[1],64.5%的精神疾病患者有病恥感體驗,55.9%的患者確實經歷過公眾的歧視[2]。全球70%精神疾病患者未接受專業治療,其原因除了患者缺乏對精神疾病識別及尋求治療途徑的相關知識外,擔心外界的歧視成為阻礙患者就醫的因素[3]。精神疾病病恥感不僅對患者的就醫意向及治療依從性造成影響,也給其工作、生活、家庭帶來重大危害[4-5]。病恥感作為一個涉及醫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范疇的復雜問題,已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
1 病恥感的概念模型
1963年社會學家Goffman將其定義為患者由于自身所患疾病而產生的一種內心的恥辱體驗,是一種患病后的心理應激反應[6],并廣泛應用于醫療領域,如精神疾病、艾滋病等。1984年Jones將“標記”概念引入病恥感的概念體系[7],認為具有令人感到羞恥、不快等特征的人會被加上“標記”,被“標記”者受到區別對待,病恥感隨之產生。隨著不同領域對病恥感的深入研究,其概念也趨于多樣化,的標簽理論對病恥感概念產生新的界定[8],Link認為,精神疾病病恥感是患者及相關人員對所患疾病產生的羞恥感以及公眾對精神疾病患者偏見和歧視的態度。2003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精神疾病患者由于其疾病特征或藥物副作用而與正常人的外在表現不同,公眾缺乏對其理解,多采用消極態度對待,病恥感也隨之產生。
病恥感是一個綜合概念,Corrigan等[9]將病恥感分為公眾病恥感、自我病恥感、標簽回避3種,之后運用認知行為結構,構建出精神疾病病恥感模型展示了3種病恥感“暗示-認知-行為”的動態發展過程模型(表1),公眾病恥感即公眾對患者的負性態度及行為,對患者有刻板的印象,這種負性認知指導行動,而表現為解雇患者、強迫患者接受治療。自我病恥感是患者感知到這種歧視,并將其內化,形成自己應該受到歧視的錯誤認知,發展到行動上為做事沒有信心。標簽回避針對的是僅有精神疾病癥狀,但還不足以診斷為精神疾病的人群,他們同樣將公眾的歧視內化,與自我病恥感不同,其不會將其強加于自己,并盡量避免被“標記”的情況,行動中表現為拒絕治療。 病恥感的概念模型[10],進一步解釋了不同病恥感種類之間的相互關系,認為公眾病恥感是相互關系中的核心部分(圖1)。

表1 “暗示-認知-行為”的動態發展過程模型

圖1 不同病恥感種類之間的相互關系
2 相關因素研究方法
2.1 量性研究
2.1.1 一般情況調查 在量性研究中涉及對調查對象一般情況進行調查,包括人口學資料和臨床資料,多為自設問卷,具體內容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發病年齡、病程、入院次數、家族史等[11-12]。
2.1.2 病恥感相關量表 對病恥感程度調查中可運用內在恥感量表(ISMI)、貶低-歧視感知量表(PDD)和精神疾病患者病恥感評估量表。ISMI包括疏離、歧視、刻板、社會退縮、抵抗5個因子,共29個條目,用于測量患者對病恥感主觀內心感受[12]。PDD用于測量患者對外界貶低、歧視態度的感知狀況[13]。精神疾病病恥感評估量表是2009年由學者曾慶枝等人編制而成,涉及社交、能力、治療3個因子,分數越高,感受歧視水平越重[14]。
2.1.3 其他方面的測量 盡管對患者一般情況及病恥感水平進行測量,但是患者的社會支持水平、生活滿意度的測量也是十分必要的,對病恥感相關因素研究起到補充和完善的效果。對患者社會支持測量的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從主觀支持、客觀支持、社會支持利用度3個維度進行測量。世界衛生組織生活質量評定量表簡表(WHOQOL-BREF)對患者生活質量進行測量,其優點在于該量表適用于任何人群,涵蓋了生理、心理、社會關系和環境4個領域,內容較全面[15]。
2.2 質性研究 目前針對病恥感相關因素研究方法上整體以量性研究為主,質性為輔的格局,以患者為訪談對象進行的病恥感相關因素研究尚不充足,大多集中于對患者家屬進行訪談,研究內容側重于病恥感產生因素、體驗及應對方式[15-16],其原因可能為患者認知功能損害,造成不同程度述情障礙[17],導致訪談無法順利實施。
3 病恥感相關因素
3.1 受教育程度 精神疾病患者受教育程度影響著患者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與病恥感程度密切相關,影響著患者對病恥感的應對方式。Razali等[18]對600個馬來西亞家庭調查顯示,社會人口學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對病恥感的影響要遠超過性別與年齡的影響。國內研究結果顯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病恥感體驗越弱,這可能是由于具有高文化程度患者的精神衛生知識知曉率高,早期接受治療干預及其對疾病的應對方式積極有關[19]。Corrigan 等[20]采用網絡手段對1307人進行隨機調查,結果顯示,高學歷者比低學歷者病恥感體驗少。王鶴秋等[21]的研究也表明,雖然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患者對外界對自我的看法和態度能夠容忍,對病情還是有較強的掩飾性,更易產生孤獨感、對別人態度敏感、人生機會喪失感等負性心理,但多采用積極的應對方式;低學歷患者歧視感體驗更加強烈,較多采用回避、不正面面對等應對方式。
3.2 職業因素 工作的穩定性影響著精神疾病患者自我病恥感[19]。有研究指出[22],穩定的工作對患者來說不僅意味著穩定的經濟收入,而且也體現著患者的自我價值。但吳志國等[23]研究結果顯示,就業狀況對患者自我病恥感總水平影響不明顯。就職業的種類而言,對公眾病恥感產生著影響。相關研究顯示,精神科醫務人員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視要明顯低于患者的家屬及朋友[24]。這可能與精神科專業醫務人員對精神疾病的正確認識,并與患者積極接觸有關。然而,職業種類及性質對自我病恥感造成影響的相關研究尚不充分,未有相關結論。
3.3 人格特征 人格特征是自我概念中價值和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個人經歷的影響。病恥感體驗與人格特征存在相關[25]。如表現為內向、孤僻、不友好、不近人情的人格特征病恥感體驗明顯;表現為情緒不穩定、無法自控的人格特征其病恥感體驗更加強烈[25]。人格特征中傷害躲避與自主能力2個維度與病恥感關系密切,傷害躲避敏感性越高其病恥感越強烈,自主能力的提升能夠降低病恥感體驗[26-28]。人格特征中的神經質相比自尊水平等對病恥感更具預測價值。
3.4 社會支持 Chronister等[29]的研究證實,社會支持能夠對公眾病恥感與內化病恥感造成影響,低水平的社會支持導致患者恢復程度不佳,生活滿意度差等后果。Verhaeghe等[30]指出社會支持主要通過影響患者的自尊水平從而對患者的感知病恥感產生影響,充足的社會支持可以減少病恥感與自尊水平的負相關性。社會支持中主觀支持、客觀支持以及支持利用度與患者病恥感呈負相關,社會支持越多,社會支持利用度越高,患者病恥感體驗越少。李季等[31]研究顯示,不同婚姻狀況患者中,離異與喪偶的患者病恥感水平高于已婚及未婚患者。
3.5 醫療環境 早在本世紀初便證實精神衛生專業工作者不慎重地做出診斷、藥物副作用、強制治療、忽視患者的權利等是感知病恥感的重要影響因素[32-33]。疾病診斷可以概括疾病的信息,并有助于專業人員交流,這同時也阻礙了非專業人員對疾病的認識,即使是精神疾病的前期診斷,患者也會被貼上“標簽”。但是,經調查顯示,全科醫師與社區居民相比,更認同精神疾病患者具有暴力、危險、不可理喻等特征,專業人員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也影響著患者病恥感體驗。一些歐洲國家的精神科醫師曾經向有關部門申請獲得比其他專業醫師更長的假期以及更高的薪水,原因是他們不得不與具有暴力、危險等特征的精神疾病患者一起工作[33]。66%精神衛生專業人員認為應當將重度精神病患者強制入院治療,47%認為應當取消患者的駕駛執照,41%建議重度精神病患者終止妊娠,40%精神分裂癥患者經歷過不良的住院治療,18%~54%患者受到過不同場合的約束,在經歷過度約束的患者中,71%感覺心里很難受,68%感覺很委屈,24%感到人格受傷[34]。
3.6 文化背景 亞洲人及亞裔美國人更贊同集體主義是早已達成共識的。西方所奉行的個人主義文化中認為別人是在意自己身體健康的,所以自己才獲得來自于別人的社會支持,所以他們不會因害怕遭受歧視而放棄尋求社會支持,與此相反,集體主義中個體之間是相互依賴的,集體目標高于個體目標,因此,在集體主義中人們不愿因自己給別人帶來負擔,社會支持利用度降低[35-37]。Choi等[38]研究證實亞洲人及亞裔美國人因害怕影響與他人關系或給親屬朋友等帶來負擔,通常不會向親友尋求社會支持。在中國文化中精神疾病患者一直被視為道德的失敗,面子觀某種程度上體現著自尊與尊嚴[38-39]。徐云璐等[39]所調查的255例精神分裂癥患者結果表明,面子感強烈的患者,其病恥感水平較高,怕掉面子成為主要的原因。
4 干預對策
4.1 社會聯系干預 公眾病恥感在病恥感種類關系模型中處于核心地位[10],這也就突出了對其干預的重要性。增加公眾對患者的接觸機會對降低公眾病恥感的作用已經被證實[40-41]。近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公眾接觸的兩種形式,一種是視頻短片接觸,另一種是面對面接觸,視頻短片接觸中,參與者觀看了一個有關精神疾病患者的短片,并且有專業人員講述片中患者的疾病及康復歷程。真人接觸中,也是同樣的敘述患者故事,不同之處在于患者和專業人員與參與者面對面交流[42]。
視頻短片的聯系干預方式與面對面接觸方式相比其在受眾的廣泛性上占據優勢,其不受地域、時間限制,依托于各種網絡平臺和電視廣播,受眾人數以指數方式增長,能夠將信息傳遞給相當大的人群,這對面對面接觸方式來說確實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是該方式缺乏受眾人群之間以及受眾人群與患者之間的交流,也無法控制受眾人群對信息的接收程度,即基礎控制較弱[43], 這也造成了視頻短片的聯系干預方式在改變公眾對精神疾病患者態度和行為的效果欠佳[40]。通過借鑒市場營銷策略,通過社交網站將信息傳遞,如臉譜網等,用戶在接收到相關信息后可以在討論平臺交流,可增強效果[43]。
干預實施過程中涉及到患者、受眾、實施者三方面,首先應遵循倫理學原則,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其次確立受眾的目標人群,并保證其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標人群的確定要以精神疾病患者為核心,結合影響患者病恥感的相關因素,將雇主、鄰居、醫療保健人員、立法機構相關人員以及相關宣傳媒體作為目標人群,在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認知改變后,能夠增加患者就業率,營造良好的生活和醫療保健環境,構建良好社會支持系統。就實施者而言,鞏固受眾與患者之間建立起的聯系是聯系干預措施成功的關鍵[43]。
4.2 加強社會支持,營造良好社會環境 Shuler[4]meta分析表明患者接受較高水平家庭成員的聯系,朋友的支持,較持續的專業人員病情管理,能有效增強患者的治療依從性。認知行為療法目前也廣受歡迎,其主要內容為糾正患者錯誤的自我評價、錯誤的疾病認知、疾病不可治愈觀念。Richards等[44]研究證實,認知行為療法對降低病恥感有積極作用。李江嬋等[45]研究也證實了認知行為治療對于減輕或消除患者病恥感以及對于改變應對方式療效明顯。抵抗病恥感活動也得到迅速發展,包括1988年世界精神病學學會主辦的“開放門戶運動”,通過對民眾宣傳精神疾病知識,以降低公眾病恥感[46],1992年世界精神病學協會發起創立“世界精神衛生日”,并將時間定為每年的10月10日。隨后的十多年里,許多國家參與進來,將每年的10月10日作為特殊的日子,以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分享科學有效的疾病知識,消除公眾的偏見。美國心理衛生協會2002年對8個州開展“消除隔閡計劃”,運用發放宣傳冊、播放錄像資料、講座、網絡宣傳等措施增強公眾對患者的理解[47]。加利福尼亞2004年開展“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并在2011年至2014年陸續開展網絡互動、社會互助、能力構建、資源調配、規范娛樂等項目,降低公眾對患者的歧視,增強患者的社會適應能力。
4.3 完善法律,改善醫療環境 加強立法,以政府職能強制性的特點為保障,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權益。我國《精神衛生法》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該法顯示了對精神疾病患者權益的保護[48]。在2013年全國精神病學倫理和法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陳志華律師以1974年發生于加利福尼亞的“塔拉索芙訴加州大學(Tarasoff V.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一案為例,指出精神科醫師不僅有保護患者隱私權的義務,還負有提醒和保護第三方的義務[49]。有國外學者曾為降低病恥感建議更改疾病名稱,我國邱仁宗教授從定義上著手,認為精神障礙疾病的概念應該至少包括兩個要素,功能紊亂和傷害。功能紊亂是指內存機制失去發揮自然正常功能的能力,但唯有這種功能紊亂成為社會負面價值的時候,才能稱為障礙、疾病,從而可以使公眾對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有所改善[50]。
5 小 結
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復過程中,病恥感成為阻礙康復進程的重要因素,是一個涉及醫學、社會學、心理學等眾多學科的復雜問題。病恥感作為一種負性情緒體驗 ,對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及心理、社會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影響,這些影響又間接增強了患者的內化病恥感,從而陷入到一個惡性循環之中。國外自上世紀末就開始了大量針對消除病恥感的活動,并取得一定效果,廣泛贊同增加公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接觸次數,能有效降低公眾病恥感,從發放宣傳手冊和進行知識講座形式發展到以患者自述錄像或現場交流的方式增加公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認識,從而降低公眾病恥感,但是國內針對患者自我病恥感的干預措施較少,而且這也是阻礙精神疾病患者康復的重要一環。目前藝術療法、工娛療法等團體康復訓練在緩解疾病康復患者的負面情緒中廣泛應用,但對緩解精神疾病患者病恥感的應用較少。隨著國家新醫改和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深入推進,在精神衛生服務倡導心理-社會模式、全程治療的理念下,如何緩解患者及家屬病恥感,值得進一步研究。
[1] Cunningham R, Perspectives.Satcher report:Research is key toovercoming stigma and widespread under treatment of mentaldisorders[J].Med Health,2000,54(3):1-6
[2] Gerlinger G, Hauser M, Hert M, et al. Personal stigma in schizophrenia spectrum disorders: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valence rates, correlates,impact and interventions[J].World Psychiatry,2013,12(2):155-164.
[3] Henderson C,Evans-Lacko S,Thornicroft G. Mental illness stigma, help seeking,and public health program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13,103(5):777-780.
[4] Shuler KM.Approaches to improve adherence to pharmac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J].Patient preference and adherence,2014(8):701-714.
[5] 孔 霞,高 燕,翟金國,等.精神分裂癥和抑郁癥患者的家庭負擔對照研究[J].中華腦科疾病與康復雜志 (電子版),2013,3(3):165-168.
[6] 李 娟,李 潔.精神障礙病恥感研究新進展[J].精神醫學雜志,2014,27(3):232-234.
[7] 徐 暉,李 崢.精神疾病患者病恥感的研究進展[J].中華護理雜志,2007,42(5):455-458.
[8] 李 季.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及其與自尊、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D].泰安:泰山醫學院,2011.
[9] Corrigan PW,Wassel A.Understanding and influencing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J].Journal of psychosocial nursing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2008, 46(1):42-48.
[10] Hall JC,Hall BJ,Cockerell CJ,et al.HIV/AIDS in the Post-HAART Era:manifestations, treatment, and Epidemiology Shelton:PMPH-USA,2011,790-806.
[11] 孫思偉,王培玉,劉寶花,等.北京某醫院門診患者及家屬抑郁癥病恥感調查[J].中國公共衛生,2013,29(8):1136-1139.
[12] 呂 穎,王小平.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調查及相關因素分析[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 2012,39(3):137-141.
[13] 徐 暉,李 崢.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及其與服藥依從性關系的研究[D].北京: 中國協和醫科大學, 2008.
[14] 曾慶枝,何燕玲,田 泓,等.精神病患者病恥感評估量表的初步編制[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9,23(9): 634-637.
[15] 呂素紅,張 宣,孫紅俠.精神疾病病人病恥感體驗的質性研究[J].護理實踐與研究,2013,10(13):6-8.
[16] 劉玉蓮,王悅婷.首發精神疾病患者家屬病恥感的質性研究[J].護理管理雜志,2012,12(4):234-236.
[17] Fogley R, Warman D, Lysaker P H. Alexithymia in schizophrenia: associations with neurocognition and emotional distress.[J].Psychiatry Research, 2014, 218(1-2):1-6.
[18] Razali SM,Ismail Z.Public stigma towards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of ethnic Malay: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patients’ relatives[J].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014,23(4): 176-180.
[19] 余 敏,江妙玲,周燕玲,等.穩定期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影響因素分析[J].護理學報,2017,24(7):58-61.
[20] Corrigan PW,Watson AC.The stigma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the gender, ethnicity, andeducation of the perceiver.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7, 43(5):439-458.
[21] 王鶴秋,馮 斌,顧成宇,等.不同文化程度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的差異化研究[A].2013浙江省醫學會精神病學分會學術年會暨浙江省醫師協會精神科醫師分會第六屆年會論文匯編[C].2013:229-233.
[22] 繆 英,練亞芬,章秋萍,等.170例住院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護理學報,2012,19(14):69-71.
[23] 吳志國,苑成梅,王 振,等.心境障礙患者自我病恥感及相關因素研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 醫學版), 2011, 31(11):1527-1531.
[24] 沈瑜君.精神疾病病恥感研究:上海和臺灣的兩地比較[D].上海:復旦大學, 2010.
[25] Reavley NJ,Jorm AF.Associations between beliefs about the causes of mental disorders and stigmatising attitude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 of the Australian public[J].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4,48(8):764-771.
[26] Margeti BA,Jakovljevi M,Ivanec D,et al. Relations of internalized stigma with 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J].Comprehensive Psychiatry,2010,51(6):603-606.
[27] Rüsch N, Corrigan PW, Wassel A,et al.A stress-coping model of mental illness stigma: I.Predictors of cognitive stress appraisal[J].Schizophr Res,2009,110(1-3):59-64.
[28] Lu Ying,WANG Xiao-ping.Correlation between insight and intemalized stigma in patients with schizuphrenia[J].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2012,24(2):91-98.
[29] Chronister J, Chou CC,Liao HY.The role of stigma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societal stigma on internalized stigma, mental health recovery,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people with serious mental illness[J].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3, 41(5): 582-600.
[30] Verhaeghe M,Bracke P,Bruynooghe K. Stigmatization and Selfesteem of persons in recovery from mental illness: the role of peer support[J]. Intem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2008,54( 3) : 206-213.
[31] 李 季,薛雅卓,馮 慧,等.精神分裂癥患者感知病恥感及與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J].現代臨床護理, 2011, 10(3): 8-10.
[32] Schulze B.Stigma an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 review of theevidence on an intricate relationship[J].Int Rev Psychiatry,2007,19( 2): 137 -155.
[33] Stuart H.Reducing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J].Glob Ment Health,2016(3)e:17.
[34] Chien WT,Yeung FKK,Chan AHL.Perceived stigma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illness in Hong Kong: relationships with patients’ psychosocial conditions and attitudes of family caregiver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J].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014, 41(2): 237-251.
[35] 陶慶蘭,黃霞君,寇小敏.精神專科保護性約束對患者的心理影響及護理干預[J].華西醫學, 2008, 23(3):617-618.
[36] Adams G,Plaut VC.The cultural grounding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 Friendship in North American and West African worlds[J].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3, 10(3): 333-347.
[37] Kim HS,Sherman DK,Taylor SE.Culture and social support[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8,63(6):518-526.
[38] Choi JL,Rogers JR,Werth JL.Suicide risk assessment with Asi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 culturally informed perspective[J].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009, 37(2): 186-218.
[39] 徐云璐,徐成敏.精神分裂癥患者病恥感與社會支持、面子觀的相關性[J].山東大學學報(醫學版),2013, 55(11):90-97.
[40] 郭崢嶸. 病恥感對于精神病患者的影響以及文化對策[J].醫學與哲學, 2013, 34(11B):72-74.
[41] Corrigan PW,Morris SB,Michaels PJ,et al.Challenging the public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a meta-analysis of outcome studies[J].Psychiatric Services, 2012, 63(10):963-973.
[42] Thornicroft G, Mehta N, Clement S, et al. Evidence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mental-health-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J].Br J Psychiatry,2015,207(5):377-384.
[43] Clement S,van Nieuwenhuizen A,Kassam A,et al.Filmed v.live social contact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stigma: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r J Psychiatry 2012,201(1):57-64.
[44] RichardsH L, Fortune D G, Main CJ ,et al. Stigmatization andpsoriasis[J].Br J Dermatol,2003,149(1):209-210.
[45] 李江嬋,姚素華,謝秀東,等.認知行為治療對抑郁癥患者病恥感和應對方式的影響研究[J].中國全科醫學,2015,18(4):463-465.
[46] Gaebel W,Baumann AE.“Open the doors”-the antistigma program of the 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MMW Fortschritte Der Medizin, 2003,145(12):34-37.
[47] Clark W,Welch SN,Berry SH,et al.California’s historic effort to reduce the stigma of mentalIllness:th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ct[J].Am J Public Health,2013,103(5):786-794.
[48] 王海容.精神病患者權益受損的法制原因及其對策研究[J].法制與社會,2013(4):265-266.
[49] 胡林英.精神病患者的權利保護與完善立法--全國精神病學倫理和法律問題學術研討會綜述[J].醫學與哲學: 人文社會醫學版, 2014,35(1): 92-94.
[50] Mathern G,Nehlig A.Editorial:Reducing stigma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epilepsy[J].Epilepsia, 2014, 55(3): 383.
050000 石家莊市 河北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賈品:女,本科,主管護師,護士長
王巍
10.3969/j.issn.1672-9676.2017.24.009
2017-07-12)
(本文編輯 陳景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