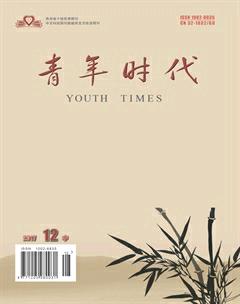淺析宋代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李楠
摘 要:宋代時期,經濟迅速發展,階級矛盾的復雜激化與文學上佛、道教思想受到理學觀點的一定影響,使得宋朝人物畫除在前代人物畫繪制的基礎上又逐步增添了肖像畫、經史題材畫、風俗畫、嬰戲畫等繪畫類別,同時也漸漸擁有了屬于宋代人物畫的民族本色。北宋時期,“翰林圖畫院”的建立,破格錄招了高益、燕文貴、蘇漢臣等一類具有高超繪畫技術的民間畫師,以描繪民間風俗及人物逐漸成為了主流,其中尤以嬰戲題材特色鮮明,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蘇漢臣是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畫家,其作品《秋庭戲嬰圖》生動地描繪了兒童玩耍的情形,表現手法細膩,寫實生動,賦色明快,極富生活氣息,代表了宋代嬰戲繪畫的最高水平。本文以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為例,簡單分析該作品的藝術特色與影響。
關鍵詞:蘇漢臣;風俗畫;秋庭戲嬰圖;藝術特色;影響
一、宋代人物畫的歷史背景
眾所周知,在歷史的長河中,無論哪個朝代,一定時期的社會文化發展由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所決定。在兩宋時期,人物畫的空前發展雖與對前人的繼承與創新脫不了聯系,但更有決定意義的卻是當時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決策。
中國畫一大畫科的人物畫是以人物形象為主體的繪畫總稱,其出現的時間較山水畫、花鳥畫較早。在新石器時間,人物多以紋樣的形式出現在陶器以及生活用品上。在階級社會,社會日常分工日益明確,雖有許多專業畫工的出現,但無論是周代明堂“堯舜之容,桀紂之像”還是漢代的漢墓帛畫都是為統治階層以及貴族所服務。雖已彰顯出線描與平涂為繪畫人物的主要表現形式,但其表現手法欠缺精致的特點也顯示出了人物畫發展的趨勢仍處于稚拙階段。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宋代人物畫除很好的繼承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道教的影響外更多的遵循了唐代強調對人物心理刻畫與細節描寫的人物畫標準。宋代時期,畫院的產生將人物畫的發展推到了新的高度,出現了許多擅長人物畫的畫家,例如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圖》與王居正的《紡車圖》等,而其中具有特色代表性的便是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
蘇漢臣(1094-1172年),汴梁(今河南開封)人,宋代畫家。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任畫院侍詔,南宋高宗紹興年間復職,南宋孝宗隆興初年間任承信郎。在人物、士女、佛道宗教畫等所繪種類中猶擅長嬰戲題材。其所處的時期是人物畫最成熟的時期,城市經濟繁榮,商品流通廣泛,畫師所繪多反映了當地的風土民情,而以描繪孩童為主的嬰戲題材更能反映出人們對平淡寧靜生活的向往。再加上兩宋時期“孝治”的推行,在佛、道教的影響下,人們日常生活中常倡導“多子”的生育觀念。《秋庭戲嬰圖》里描繪的孩童“推棗”游戲更是顯現出“早生貴子”的民俗。社會上所產生的催生禮、三朝禮、滿月禮等禮節的出現更為嬰戲畫的題材氛圍增添了色彩。
二、《秋庭嬰戲圖》的藝術特色
(一)構圖安排妥善嚴謹
南齊謝赫曾在其所著的《古畫品錄》中闡述過畫有六法,其中有一法就是經營位置。而謝赫所言的“經營位置”就是通俗說法中的繪畫的章法構圖。一幅畫的構圖就是整個畫面的骨架,是人們對自身作品進行主觀組織并通過各種繪畫元素的結合所構成的畫面布局。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整幅畫面就相當看重構圖的嚴謹,通過對這幅畫面的分析后可以看出該幅畫作的整體結構是采用了由巨石、人物、圓凳所構成的一個典型的三角形構圖,背景和人物關系有條不紊,主次鮮明,畫面既有穩定性又將整體畫面形象刻畫的恰到好處。
畫面處理最巧妙的部分便是兒童與圓凳的合理安排,讓人眼前一亮。位于畫面右下方的圓凳和雛菊有效遮掩了芙蓉根部冒出枝條的問題。緊接雛菊從畫外引入,在填充畫面空擋的同時讓人體會到整體畫面布局的平衡性,雛菊旁圓凳上所放置的紅色玩具更與兩孩童形成呼應。雖只為一些細節,但僅通過描繪雛菊的一個小部分就讓畫面的立體感和空間感都展露無疑。兒童是整幅畫的核心所在,他們位于畫眼之處,既與右下方圓凳相協調,又彌補了左下方畫面的空洞性。兒童身后巨石所展露的高聳不僅讓畫面增添了許多張力與穩定性,也給人以由前至后的縱深感享受。仔細觀察,巨石底部簇擁了一團雜草,芙蓉葉三三兩兩仿佛長出又似從中穿過,使原本僵硬的石頭充滿了生氣,畫面整體效果也變得生動自然。再與象征團圓的圓凳方圓結合凸顯效果,圓凳為實,巨石為虛,逐步引入,直達主題。《秋庭戲嬰圖》整個畫面的構圖飽滿和諧,疏密得當,給人們以賞心悅目之感。
(二)物態景象刻畫生動
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對于人物動態與配景的描繪也十分講究。僅憑畫作的第一印象就能讓觀賞者體會到一種靜中取樂的氛圍。受畫院侍詔任職的影響,其作品雖具有描繪民間樂趣的風俗性,但他所處的生活環境讓他觀察到了貴族階層小孩的娛樂方式,作品既結合民俗又體現貴族,對研究嬰戲題材人物畫以及反映宋代社會環境具有重要價值。整幅畫作繪畫者用筆細膩,在背景處多采用游絲描,畫面背景中的太湖石也與整體結構相呼應,并不會顯得累贅和刻意反而凸顯了自然無雕琢。“人物衣相要柔中生剛,毫厘分寸,須見筆力,由重大而流暢者,有精潔而縝密者,凡十八楷法。”孩童的皮膚跟大人相比顯得白嫩,細潤,所以在面部和手部都需要采用細線和淡墨進行繪制。在宋代歷史背景下,百姓安居樂業,孩童也會顯得稍胖一些,就需要用一些流暢的線條去刻畫嬰兒肥的臉蛋,肥嘟白嫩的小手等體態特征。畫中的孩童刻畫不管是頭發、眉目,還是一些簡單的服飾配件都是精心創作的。其中,服飾的描畫絲染兼備,具有豐富的變化性。宋代貴族生活奢靡,孩童所著的柔軟細膩的綾羅綢緞需要用細而均勻并且多為圓轉曲線的游絲描與釘頭鼠尾描方能繪畫得出。而在背景花草的繪畫上多采用典型的雙勾法,石與樹枝的刻畫上則運用了頓、挫、皴等手法更加豐富了線條的變化性。蘇漢臣運用熟練的技藝,將幾種不同的筆法優勢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為人物展現提升氣韻,使得畫面栩栩如生。
(三)賦彩雅致凸顯情感
不同的色彩處理方式能夠賦予各個形象不同的韻味,而畫面色彩的處理也是一種情感語言的表達,色彩的冷暖、艷樸、明暗的處理將成為一幅畫作獨特的表現手段,在《秋庭戲嬰圖中》蘇漢臣對色彩的合理安排使得畫面更加和諧與生動形象。在這幅畫中,兒童是主要人物,即使在整幅畫面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卻是點睛之筆。《南宋院畫錄》卷二載:“蘇漢臣作嬰兒,深得其妝貌,而盡神情,亦以其專心為之也”。只見兩孩童全神貫注的盯著桌上小棗,男孩衣衫滑落也無暇顧及,人物面部通過“三白法”提神,使之更加氣韻生動。在衣著方面,以簡單的紅白兩色為主,用厚重的礦物顏料朱砂與白色繪制凸顯主題人物的實,而背景采用薄潤的植物色繪畫,虛實結合,互相輝映。當然,人物旁玩具的刻畫也沒落下。所繪之紅色也與孩童身上紅色的服裝相呼應。而秋季淡粉的芙蓉、潔白的雛菊穿過墨色的巨石在青色樹葉的襯托下更顯得嬌嫩婀娜,惹人陶醉。蘇漢臣對作品靈動的賦色后再次為秋庭嬰戲時添加了嫻靜淡雅之氣,既清新與樸素,又沉靜與活潑。
三、《秋庭嬰戲圖》產生的巨大影響
蘇漢臣是宋代人物畫典型的代表人物,以嬰戲題材的畫作最具研究意義。通過描繪兒童嬉鬧的生活場景,刻畫天真無邪的兒童形象,為宋代人物畫增添了濃郁有趣的筆墨。他筆下所描繪的兒童或純真,或無邪,或青澀,或可愛,把孩童的個性神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兒童的靈性一覽無余,為宋朝的嬰戲畫樹立了典范。《秋庭嬰戲圖》是宋朝兒童繪畫作品的代表,集北宋院體畫中的人物、山水、花鳥于一體。對后世嬰戲題材繪畫在物態、賦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
嬰戲題材在后世多出現在版畫、年畫、陶瓷等眾多藝術門類中。對天津楊柳青年畫的影響頗深。天津楊柳青年畫在年畫領域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至今民間仍在傳頌“天津楊柳青年畫”的說法。《秋庭戲嬰圖》對楊柳青年畫的影響可以從早期楊柳青年畫的娃娃畫里可以探出,娃娃畫構圖飽滿,均衡整齊,嬰孩繪制在保留原有技法的基礎上又創作出連生貴子、麒麟送子、吉慶有余等百姓膾炙人口的題材。的確如此,楊柳青年畫中的多數兒童造型都是參照《秋庭嬰戲圖》中圓臉大頭的可愛造型,符合孩童純真可愛的特點,繪畫內容以孩童的嬉鬧玩耍形態為主。年畫無論在古時還是如今都有裝飾的效果,而象征圓滿意義的兒童形態會多注重體現孩童的樂趣而不是如門神一般的莊嚴凝重。從色彩的角度而言,楊柳青兒童畫進一步的發展了工筆重彩年畫,賦色在工整秀麗的基礎上更加鮮艷明亮。色彩搭配上和諧生動也不會少了喜慶氣調,生動活潑的特點將畫中的兒童的靈氣凸顯出來,既是一種傳承,又是一種創新。在后世人們的賞析中上得高堂,下得市井,雅俗皆宜。
藝術受一定時期的社會環境所影響,并且能動的反映出當時社會的人文精神,一個好的藝術家需要創作出具有時代性的代表作品,賦予繪畫以自身的創造與生命力,代入繪畫者對世間萬物生命的理解,體現自己獨特的表現形式。在繼承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提高自身素質,才能打造出順應時代潮流,符合當代審美的更多更好地繪畫作品。
參考文獻:
[1]史陽春.《秋庭戲嬰圖》研究[J].南京師范大學,2015.
[2]蘇漢臣《秋庭嬰戲圖》研究[J].程沁.美與時代(下半月).2009(06)
[3]淺析宋代嬰戲圖盛行的原因[J].宋春艷.大眾文藝.2012(09)
[4]中國傳統嬰戲圖解讀[J].巫大軍,楊艷.文藝爭鳴.2010(14)
[5]兩宋嬰戲圖像與宗教[J].陳璐.美術大觀.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