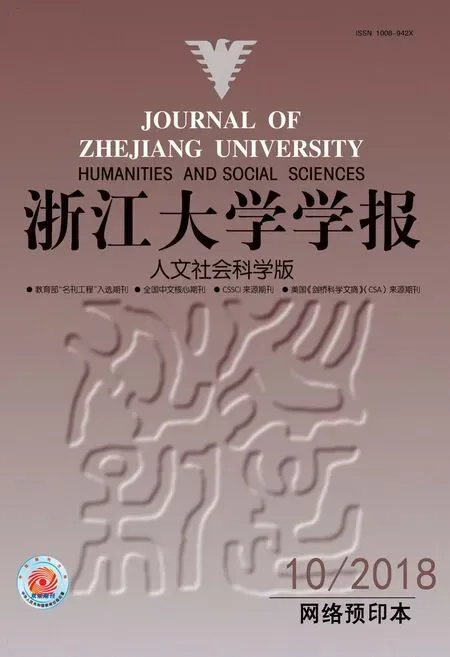“將青年導向德性”:培根青年教育思想新探
肖 朗 李宇亮
(浙江大學 教育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8)
一、導言:從培根關于青年教育的“信稿”說起
長期以來,關于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可謂早已“蓋棺論定”,因為國內外學界普遍認為盡管培根并非教育家,其著作也較少直接論述教育問題,但其教育思想對近代教育乃至后世教育的發展卻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以此認識為基礎,學界對培根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培根的哲學及教育哲學,國內外學者以《新工具》及《新大西島》中的哲學和科學思想為主要依據,論述培根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唯物主義性質,并視之為后世經驗主義教育或科學教育思想的濫觴;二是培根論述各種教育問題的其他思想,這些零散的教育思想被歸納為培根的學問觀、教學法和道德教育觀等,而學者們在論述培根的這些教育思想時多取材于《培根論說文集》和《學術的進展》中的相關內容。
然而,幾乎被學界所遺忘的是早在1600年前后培根曾寫信給時任伊頓公學校長的亨利·薩維爾(Henry Savile),正面闡述自己對青年教育的看法,這便是信稿《致亨利·薩維爾爵士:論理性能力的提高》(后文簡稱“信稿”)①“信稿”被收入 Spedding J.,Ellis R.L.&Heath D.D.(eds.),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Vol.7,London:Longman&Co.,1857-1874。目前對信稿最為詳盡的注釋參見 Vickers B.(ed.),Francis Bacon:The Major Wor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本文對信稿的解讀主要以該書為參照。。英國著名教育史學家博伊德(W.Boyd)和金(E.J.King)曾注意到這份文獻,但只是簡要介紹了信稿的內容[1]234,而事實上這些內容奠定了日后《學術的進展》一書的主體框架。培根在“信稿”中開宗明義地指出青年教育問題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將青年導向德性”,其二是青年“理性能力的提高”。他本欲在“信稿”中專論第二部分,但在圍繞第一部分論述了青年的身體與意志的可塑性后,關于第二部分只留下了零碎的筆記。培根后來將這些內容整合到《學術的進展》中時未再專門討論青年教育,但這并不意味著他遺忘了這一問題。本文以“信稿”的內容為主要線索,通過對培根《學術的進展》《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②《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De Augumentis Scientiarum Libri)一書出版于1623年,該書系1605年出版的英文版《學術的進展》的拉丁文譯本,對后者的許多內容做了重大修改,因而反映了培根思想成熟時期的觀點。及《培根論說文集》等相關著作的解讀,力圖表明培根不僅對“將青年導向德性”這一主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而且主要以歐洲人文主義思想傳統和官能心理學作為其理論依托和分析視角。為此,本文擬從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培根關于青年的基本看法、“將青年導向德性”的教育途徑和方法、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及貢獻等四個方面嘗試對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進行探索,重新梳理和評析這位歷史偉人留下的重要思想遺產③在國內學者中,余麗嫦曾將青年放置在培根道德哲學思想的整體框架中加以審視,但語焉不詳(參見余麗嫦《培根及其哲學》,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夏慧專門探討了培根的道德教育思想,但并未從青年教育的角度出發(參見夏慧《培根德育思想研究》,武漢大學2006年碩士學位論文);戴本博曾關注培根《論青年與老年》一文的教育價值,但未將培根關于青年的論述與其道德哲學聯系起來(參見戴本博《培根論科學和教育》,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第121-122頁);姜文閔、劉海英注意到培根關于詩歌、道德哲學與政治學不適合青年閱讀的告誡,但均未就此進行任何引申(參見姜文閔《培根的所羅門及其教育思想》,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 3期,第 81-88頁;劉海英《論培根的社會歷史觀》,上海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學位論文)。總體而言,國內學界對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尚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和充分的研討。。
二、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歐洲人文主義的思想傳統
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培根對青年教育特別是其道德教育的思考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思想傳統,特別是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等人的觀點。亞里士多德主要從教育與城邦關系的角度來論述青年教育的問題,強調“立法者最應關心的事情是青少年的教育”[2]271,因為城邦公民從小必須通過接受教育來適應其政體的特征和生活方式。同時,他認為青年最重要的特征是激情與欲望旺盛且難以自控,所以青年的道德教育要在法律指導下進行,從而形成良好的習慣,而且在其成年后還要繼續致力于良好習慣的養成[3]313。亞里士多德的道德哲學著作在13世紀被翻譯成拉丁文后即用于教學,文藝復興時期又受到人文主義者的青睞,可以說培根的道德哲學論述在很多情況下是直接以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為理論基礎的。
與亞里士多德不同,身處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西塞羅并未從國家的角度對年輕一代的教育進行整體規劃,但他明確指出當時學習演說之術的人大都為“渴望成名的青年”[4]316,認為演講術的學習者應是已接受過文法教育的學生[5]80,理想的演說家應將雄辯與哲學相結合。關于哲學的教育作用,西塞羅繼承了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想傳統,在《圖斯庫魯姆談話錄》中首次提出“心靈的培養”(cultura animi)這一教育命題[6]196,并將人的心靈比喻為土地,哲學學習則是對土地的耕耘,它能除去惡行并播撒善的種子,收獲德性的果實。在為羅馬年輕一代所寫的《論義務》這本有關義利之爭的名著中,西塞羅闡釋了智慧、公正、慷慨、勇敢、節制等品德,并特別說明年輕人的義務是接受老年人富有智慧的教導,控制情欲并在身心兩方面進行吃苦和忍耐的訓練,以及時刻謹記節制和謙遜;他還提到年輕人謀求名譽的幾種途徑(包括法庭演說和政治演說)[7]375-376,408-412。培根道德哲學思想中“團體的善”優于“個人的善”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又反映了西塞羅的古典共和主義思想[8]221-222,“心靈的培養”則被培根用作其道德哲學實踐部分的拉丁文標題。
(二)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的譜系中,“教育心理學化”的主張由裴斯泰洛齊于19世紀初正式提出,但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就曾嘗試從心理學的視角來分析教育問題,他對受教育者的年齡分期與每一年齡階段的教育安排即以其關于人類靈魂的本質規定為基礎。“亞里士多德的心理學說并沒有從后來流行的客觀物體的角度去解釋靈魂,而是直接采用‘功能’這一術語描述靈魂”[9]148,這種處理方式使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成為后世官能心理學的奠基之作。就其對教育的影響而言,官能心理學此后經歷了兩次重要的發展:其一是斯多亞學派將激情視為靈魂的疾病并將哲學視為對靈魂的治療的觀點[10]244245,在以雄辯與哲學的結合為教育的主要特征的古羅馬時代,這種觀點直接影響了西塞羅、普魯塔克等教育思想家,并在文藝復興時期普遍流行;其二是奧古斯丁在《論三位一體》中確定下來的三分法:他從眾多心理官能中選擇記憶、意志和理解作為統一于人類靈魂的三種官能,并將意志作為統攝所有靈魂活動的官能,這種靈魂官能說后來為夸美紐斯所繼承。
從總體上看,培根的官能心理學以亞里士多德的靈魂論為基礎,同時也受到斯多亞學派和奧古斯丁的影響。他在《學術的進展》中將靈魂或心理的官能分為六種,其中理解和推理與理性相關,意志、欲望和情感與道德相關,而想象則介乎理性和道德之間,這種劃分繼承了亞里士多德關于靈魂的認識功能與意志功能的二分法,并同樣承認想象的中介地位,但與亞里士多德的不同之處在于:(1)培根接受了斯多亞學派的觀點,將情感或激情視為心靈的疾病,這就使“將青年導向德性”的問題被置于治療心靈疾病以保持心靈健康的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之下,這樣的教育分析理路迥異于以道德認知為主導的古希臘德育思想傳統。(2)培根將意志作為獨立的道德官能,這一界定既區別于亞里士多德,也區別于斯多亞學派,而是直接受到奧古斯丁的影響[11]。這種影響在消極層面上的體現,是他在討論“心靈的治療”時為宗教留下一席之地;但就其積極層面而言,這使培根在思考青年德育問題時直接以意志為核心。他在“信稿”中寫道:“至于人的意志,它是最容易得到管控和改變的,能夠治療并改變它的藥方也最多。”[12]Ⅶ,100隨后他列舉了多種能夠改變意志的“藥方”,它們實際上均為“將青年導向德性”的具體途徑和方法。此外,培根的官能心理學還吸收了古典修辭學的若干思想資源,如亞里士多德《修辭學》中有關青年的描寫便為培根分析青年心理官能與行為特征提供了直接參考;更為重要的是,借助古典修辭學的思想資源,在培根那里對青年的道德說教被轉換為通過調動青年的想象以增強其道德判斷,進而對其意志施加影響的心理干預過程。總之,培根通過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將青年的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道德行為整合到一個綜合的思想體系之中,從而使他的青年教育思想呈現出嶄新的面貌和特征。
(三)耶穌會學院教育的啟發
培根是一位信奉新教的大思想家,但他多次對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天主教耶穌會表示贊賞。在《學術的進展》中他寫道:“古代的這種優良傳統(筆者按,指教育與法律并重的傳統)在后代的耶穌會士派的學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復興。這個教派的學者,由于過于迷信,讓人生出‘愈精愈糟’的感覺;但是在教育方面或其他學問道德方面,令我想起阿格西勞斯對他的敵手法納巴祖所說的話,‘您確是善良之輩,可惜不能為我所用’。”①阿格勞斯這句話的原文是“Talis quum sis,utinam noster esses”,《崇學論》將之譯為“君誠良善,惜非吾黨”(見[英]弗蘭西斯·培根《崇學論》,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16頁),《西方教育史》的中譯本翻譯為“他們很好,但愿他們站在我們一邊”(見[英]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任寶祥、吳元訓主譯,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05頁)。[13]15培根之所以稱贊耶穌會的教育,一方面是因為耶穌會致力于當時歐洲的高等教育,它所創辦的學院重視改進教學方法,采用課堂辯論、課外文藝表演等活動來激發青年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美國教育史學家格萊夫斯(F.P.Graves)認為良好的教學法和優秀的教師是“耶穌會高等學校最稱特色的地方”[14]322,宗教史學家穆爾(G.F.Moore)也把耶穌會士譽為“歐洲天主教國家中的教育改革家”[15]274。另一方面,也與耶穌會學院重視青年的道德教育密不可分。眾所周知,這一時期歐洲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極其落后,青少年的教育以家庭教育為主,這對他們形成集體和社會意識非常不利;高等教育在中世紀大學的基礎上雖有了長足的發展,但規模十分有限,而耶穌會學院則遍布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Loyola)在1556年曾令其助手致信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解釋耶穌會致力于教育活動的原因,信中明確寫道:“基督教和整個世界的所有福祉均依賴對青年恰當的教育”[16]209。概括地說,耶穌會學院有以下幾個特征與青年教育特別是其道德教育密切相關:(1)仿照巴黎大學的模式,耶穌會學院采取膳宿制,學院由師生共同組成,由此形成的集體教育較之以博洛尼亞大學為代表的意大利高等教育模式擁有獨特的優勢[17]31,而且耶穌會學院的師生朝夕相處,彼此之間以砥礪品德為重。(2)耶穌會學院教育以分級教學為基本形式,并以學習科目為標準分為低級部和高級部,通常情況下對每一年級的學生均實施獨特的競賽獎勵制度,相鄰年級之間、同一年級學生內部獲得榮譽頭銜者與未獲頭銜者之間普遍存在競爭。(3)在耶穌會學院無論是在教堂、課堂、飯堂,還是在娛樂場所,學生始終處于被監管的狀態[18]378,紀律檢查員(praefect)、助教(bidelli)、級長(publicum censorem)都有直接監督學生的權力,未來將成為修會成員的學生即使訪問其他年級的同學,往返也須結伴而行,他們與修會外就讀學生的交流必須遵守相關規定;修會外就讀學生也被要求謹慎交友,擇善而從。這種教育環境及氛圍契合耶穌會教育所倡導的“德才兼備”的人才培養目標,有助于約束并塑造學生的行為舉止,耶穌會學院遂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培根心目中開展青年教育的理想模式。
三、培根關于青年的基本看法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古代中國教育家相對重視并關注兒童及其教育問題,而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教育家更多討論的是青年及其教育問題[19]26。古希臘流行的年齡階段劃分一般以7年為單位[20]34,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便表示認可這種年齡階段的劃分方法,將 14歲至21歲劃定為“青年期”[2]269。古羅馬人對年齡的劃分雖看法不一,但許多思想家結合教育問題,認為兒童一般從14歲開始經歷青春期的變化,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家也認可這一點[20]11-12。在培根所生活的時代,一般來說“童年與青少年,童年、青少年與青年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人們尚沒有‘青少年’的概念”[21]43。這決定了培根不可能對青年的年齡段進行明確界定,但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他基本接受了古希臘羅馬以來關于青年年齡段的傳統觀點。此外,在歐洲人文主義思想傳統中,關于青年的討論通常與政治生活相聯系,而在這種語境中青年多半被用來與老年人進行對比①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討論城邦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時說:“自然本性……使得同一種屬的人之中一些較為年輕,而另一些較為年長,從而讓其中一些人適合于被統治而另一些人適合于統治。”(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58頁)西塞羅關于不同年齡者所承擔義務的討論將年輕人與老年人相對比,普魯塔克在論述老年人是否應參與公共事務這一問題時同樣觸及青年與老年人的關系。“依年齡將社會劃分為‘年輕人’和‘年老者’兩個階層的做法大概遠遠早于羅馬本身的歷史,甚至可以追溯至遠古的印歐史前時期。”(馬魯《古典教育史(羅馬卷)》,王曉俠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 155頁)。培根同樣繼承了這一傳統,常把青年與老年人對比起來論述,特別在《論青年與老年》一文和《生與死的歷史》(Historia Vitae et Mortis)一書中,以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第二卷中的相關論述和普魯塔克《老年人是否應參與公共事務》一文為主要參考,從道德、政治和認知三個層面對青年的心理和行為特征做了概述。
《論青年與老年》中有兩句話可視為培根對青年的總體看法:“在道德方面也許青年人較為優越,如在世情方面老年人較為優越一樣……年歲多的益處是在乎理解的能力而不在乎意志與感情方面的德性的。”[22]155156可見,青年的優勢表現為在道德修養方面有較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具體而言,相比老年人,“青年謙虛且有羞恥感”,“年輕人友好且有同情心”,“青年有可嘉的仿效與競爭心”而不是嫉妒,“由于熱情和缺乏對邪惡的體驗,青年傾心于宗教和虔誠”,“年輕人的期望是殷切的”,“青年心胸開闊、慷慨、博愛”,“青年自信且充滿希望”,“年輕人溫和易服從”,“青年坦率真誠”,“青年渴望偉大的事物”,“年輕人重視當下”而不是偏好過去[12]Ⅴ,319-320,等等。
但培根指出在處理公共事務或政治事務方面,青年則不如老年人。他舉例道:“青年人在執行或經營某事的時候,常常包攬的比所能辦到的多,所激起的比所能平伏的多;一下就飛到目的上去,而不顧慮手段和程度;荒荒唐唐地追逐某種偶然遇見的主義;輕于革新,而革新這種舉動是會引起新的不便來的;在起始就用極端的補救之法;并且(這是把一切的錯誤加重一倍的)不肯承認或挽救錯誤,就好像一匹訓練不足的馬一樣,既不肯停,也不肯轉。”[22]155這樣的行為方式在政治生活中無疑是非常危險的,因而培根提出青年與老年人在政治生活中需要相互彌補、各取所長,他特別強調:“在年老的人做事的時候,年輕的人可以學習。”[22]155這實際上是參考了普魯塔克的意見,因為后者基于相似的考慮認為老年人必須參與公共事務[23]1448。
與道德可塑性和政治幼稚性相關的,是青年在認知方面的不成熟。培根指出:“青年的發明力是比老年人的活潑;而且想象力也比較容易注入他們的腦筋,并且好像更是若有神助似的。”[22]154但“青年人較適于發明而不適于判斷;較適于執行而不適于議論;較適于新的計劃而不適于慣行的事務”[22]154。與之相對,老年人雖在言辭或思維方面不甚敏捷,但其判斷力強。
綜上可見,如同在亞里士多德和普魯塔克那里一樣,青年及其教育問題在培根那里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中還列舉了關蘇格拉底和老加圖的兩個典故:蘇格拉底因自比“牛虻”的教育活動而受到指控,因為他“削弱了年輕人對他們國家、法律和風俗習慣應有的尊崇”[13]8;而監察官老加圖因視希臘教師為洪水猛獸而說服元老院對其進行驅逐,“免得他(筆者按,指希臘教師卡涅阿德斯)污染和迷惑年輕人的心智和情感,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整個城邦的行為方式和風俗習慣”[13]8。培根固然認為蘇格拉底和希臘教師的學問非但不有害于希臘城邦的風俗教化,反而對之有利,但這兩個典故詮釋了他心中青年及其教育問題與城邦和國家之間的密切關聯。與此同時,培根對青年及其教育問題的論述在相當程度上被置于官能心理學視角下,因為無論是“發明”“判斷”“理解”,還是“想象”“意志”“情感”,在培根看來都心理官能的組成部分。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看,青年雖不適合直接參與政治生活,但在理性官能和道德官能方面卻有著很大的可塑性。正因為青年相比老年人更傾向于追求德性的卓越和信仰的虔誠,“將青年導向德性”遂成為培根重點關注和探討的重要教育課題。
四、“將青年導向德性”的教育途徑和方法
如前所述,培根在繼承亞里士多德靈魂論思想的基礎上又接受了斯多亞學派的觀點,將情感或激情視為心靈即心理的疾病,并由此出發來探討和分析“將青年導向德性”的有關問題。培根指出:“在醫治身體的疾病時,按照順序是先觀氣色查體質,然后診斷疾病,最后是施治。同樣在醫治心理的疾病時,也應當先了解個人天性的不同特點,然后才可以確定病因和心理的缺陷在哪兒。心理的疾病不外是情感所造成的紊亂和失調。”[13]153具體而言,首先需要對人的天性和性情進行歸類和描述;繼而研究對人性有重要影響的內外部因素,培根稱之為“天性的印痕”(impressions of nature),包括性別、年齡、地區、身體狀況、相貌美丑等影響人心理的內外部因素;接著再研究情感的發展與變化過程;最后是研究“在我們的掌握之內,有能力對我們的心理起作用,影響我們的意志和欲望,改變我們的行為方式”[13]153154的途徑和方法。培根所列舉的途徑和方法包括贊揚、反駁、規勸、同伴、友誼、書籍、學問、法律、教育、習慣、訓練、模仿、競賽等,這些途徑和方法一部分是古典作家關于城邦公民德性問題論述中的常見主題,如修辭演說的教化功能、公民友愛等,另一部分源自古典作家探討德性培養問題留下的思想遺產,如天性、習慣與理性的關系等。而培根的貢獻在于將這些思想資源系統整合到青年如何獲得美德這一在他看來尚未予以充分研究的問題中,而且進一步致力于對道德教育方法的經驗研究。
(一)贊揚、規勸和反駁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在西方古典修辭學傳統中,修辭演說一般包括政治修辭(deliberative speech,又譯政治審議性演說)、儀典修辭(epideictic speech,又譯表現性演說),以及與道德教育關聯較小的法律修辭(forensic speech,又譯庭辯性演說)。需要說明的是,政治修辭的功能是“勸說”(suasio)或“勸阻”(dissuasio),作為德性實現途徑的“規勸”(exhortation)即為政治修辭“勸說”或“勸阻”功能的英譯①霍布斯在翻譯亞里士多德《修辭學》時同樣將政治修辭的功能“勸說”(suasio)譯為“規勸”(exhortation),參見Skinner Q.,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43。。儀典修辭雖常用于稱頌君主和統治者,但其贊揚美德和譴責罪惡的社會政治功能卻始終受到重視,因而當政治修辭從羅馬帝國時期逐漸衰落后,儀典修辭便成為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最為流行的文體類型。儀典修辭的功能是贊揚(laus)和譴責(vituperatio),《學術的進展》中作為德性實現途徑的“贊揚”(praise)在《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中即被譯為“laudis”。因此,可以說作為“心靈的培養”途徑的“規勸”和“贊揚”最初指的是政治修辭和儀典修辭的功能。
修辭演說究竟何以實現青年德性的教化?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須考慮《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中一個提綱挈領的概括:“意志由正當理性(right reason)管理,它受惑于表面上的善,接受激情的刺激,以及身體器官和隨意運動(voluntary motion)對意志的執行。”[12]Ⅴ,3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看,青年德性的養成在本質上是對意志的有效調控,但意志容易受到“表面上的善”和激情的擾亂。如果說擁有德性是以明辨是非、區分善惡為首要特征的話,那么判斷力相對薄弱便是青年易為“表面上的善”所迷惑的根本原因。因此,培根建議學習古典修辭學特別是政治修辭時要關注各種“善與惡的色彩”問題,這種觀點源自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指的是關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惡,以及哪種善程度更大,哪種惡程度更小”[12]Ⅶ,77的觀點,較之理想的“善的模型或模式”,對現實的道德判斷產生實際影響的正是這些“表面上的善”或“表面上的惡”。培根還建議,對每一種流行觀點都要盡可能地記下“色彩或表象的謬誤和對謬誤的反駁(elenches)”[12]Ⅶ,77,這樣就可以“通過發現并反駁(reprehend)這些色彩,通過展示它們在何種情況下是合理的,在何種情況下產生誤導……讓聽眾形成清晰的判斷并做出決定”[12]Ⅶ,77。這里有三點需要說明:(1)在文藝復興時期,青年學生并非修辭演說的被動聽眾,他們在接受古典修辭學訓練的過程中首先是演說練習者,其次是他人演說的聽眾,而且他們常常就同一觀點的正反兩面進行演說訓練;(2)按照培根的意見,青年學生道德判斷得以成熟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在演說準備過程中對各種關于善惡的流行觀點進行搜集、分析和反駁,而作為聽眾的學生同樣會在關于善惡觀點的分析中形成判斷力,道德判斷正是在這種交互過程中形成的;(3)作為德性實現途徑之一的“反駁”正是演說中對“善與惡的色彩”的反駁,因為《學術的進展》中的“反駁”(reproof)即為《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中拉丁語“reprehensionis”的英譯,這說明“反駁”即意味著通過對各種有關善惡的流行觀點進行合理評判來促進德性的實現。
然而道德教育并非僅僅是道德說教,斯多亞學派在這一點上為后人提供了教訓,因為他們不顧人們的意志,企圖通過尖銳的辯論和所得的結論來把美德強加給他人,結果反為人們所嘲笑[13]130。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看,除了“表面上的善”而外,理智對意志的管理還受到激情的困擾,后者使人即便掌握正確的判斷,也不能將意志貫徹到實際行動中。雖然“情感如同理性一樣,也帶有向善的欲望(appetite)。但二者的區別在于,情感只看到當下,而理性則看到未來和全局。因此如果眼前之利過多占據了想象,理性通常就會被擊敗;但如果雄辯與說服的力量能夠讓遙遠的未來之物在當下顯現出來,那么理性可借由想象的反抗而占據上風”[12]Ⅲ,410-411。由此可見,在理性與激情爭奪對意志的控制過程中,想象的中介作用極其關鍵,正是在這里,修辭演說的第二個德育功能和價值便顯現出來:“修辭學的責任和任務是把理性應用到想象方面,以便更好地調動我們的意志。”[13]129這對于青年的德性培養無疑非常重要,因為就其自身而言,美德無法直接通過感官展示出來,只有借助想象將其生動形象地展示出來,才能真正激發人們對美德的熱愛之情[13]130;而據前文中培根的解釋,青年的心理特征之一便是具有豐富的想象力,這決定了青年的德性是可以訴諸想象來培養和發展的。例如,如果只是說“這對你有害”,聽者并不會產生很大的觸動,但如果說“你這樣做你的敵人一定喜歡”,效果則會大為不同,因為前者屬于直白的道德說教,后者則促使聽者想象自己行為的后果。培根解釋說,這兩種勸說的效果有著很大的區別,好比用相同的力氣,但分別用鈍禿的工具和銳利的工具來刺穿某樣東西一樣,修辭演說之所以能將理性轉移到想象之中,成功地實現道德勸說,是因為它能夠提供各種修辭形式來對同一觀點加以不同程度的修飾以適應不同的聽眾,并最終實現其對聽眾的感動(movere)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贊揚”和“規勸”分別被培根視為政治修辭和儀典修辭的功能,但他在論述修辭學時并未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將“善與惡的色彩”的使用僅限于政治修辭中的謬誤反駁[12]Ⅶ,77,也未像西塞羅那樣將儀典修辭的功能僅限于“感動”①西塞羅在《論演講術的分類》中界定說,儀典修辭“不使用任何論證,它采用溫和的風格影響聽眾的情感,而不是為了獲取信任的證據”(西塞羅《西塞羅全集·修辭學卷》,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7頁)。,在其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下,政治修辭和儀典修辭同時具有說之以理、動之以情的道德教育功能。通過培根關于修辭演說功能的闡釋,贊揚和規勸這兩種普通的教育方法被賦予獨特的心理學內涵,用來幫助青年“反駁”流行的道德觀念,以及通過激發青年的想象來調和其激情,這些均成為培根筆下的古典修辭學給道德教育帶來的重要啟示。
(二)同伴與友誼
在歐洲古典人文主義傳統中,友愛或友誼一直是重要主題之一。亞里士多德將友愛分為基于善(德性)的友愛、基于快樂的友愛和基于實用的友愛,其中基于實用的友愛最常見于老年人,基于快樂的友愛最常見于青年人,基于善的友愛則最常見于中年人[24]105-108;亞里士多德最看重的是基于善的友愛,他認為人們可以從朋友的品質和活動中發現善,并在其啟發下加以學習[24]238-242。西塞羅進一步認為“德性本身產生并鞏固友誼,沒有德性,友誼便不可能存在”;“友誼的產生主要是由于人的天性,而不是為了滿足需要;主要是由于心靈的趨向加之某種愛的情感,而不是考慮到它會帶來多大好處”[7]289,292。西塞羅還特別珍視朋友之間勸告和責備的價值。除了友誼旨在追求德性這一問題而外,另一個得到關注的是友誼的平等性問題。亞里士多德推崇在德性、財富、權力和地位上平等的友誼關系,并認為社會地位不平等者之間的友誼則需要地位低下者用情感來補償[24]120-129。西塞羅從其關于友誼本質的觀點出發,在強調地位高者與地位低者之間友誼的平等問題時更多強調地位高者的義務,指出在德性和運勢方面享有優勢者應該與親近之人和朋友分享這些優勢[7]307-308。
關于友誼,培根早年的看法更多以政治贊助關系為基本視角,以至于在《論從者和友人》一文中說道:“古人喜夸的那種友誼,世間是很少的,尤其在地位平等之人之間更少。世間所有的友誼都是在上位者與下屬之間的,因為這二者的榮辱休戚是包括在一起的。”[22]176他在晚年時已擺脫政治贊助關系下個人命運或功利的視角,而更多從人性的角度看待友誼:“在沒有愛的地方,人群并不是同伴關系”;“缺乏真正的朋友導致的孤獨是徹底的,也是可悲的;沒有友誼的現世只不過是一片荒蕪……那些就天性和情感的構造而言不適交友的人,無論是誰,其性情都可謂來自禽獸而不是來自人性。”[12]Ⅵ,437有學者指出,從思想層面看促使培根發生上述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是其對古典人文主義思想資源的吸收與借鑒,特別是古典人文主義的友誼觀對友誼的平等獨立性和對德性的追求的強調影響了培根的友誼觀[25]。培根在吸收古典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將友誼的道德價值與其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進一步結合起來,從而為同伴和朋友如何“將青年導向德性”這一問題提供了獨特的解答。
從培根關于友誼益處的論述中,可以發現同伴和朋友對德性形成的作用。他在1612年版論說文集中的《論友誼》一文①《培根論說文集》共有三個版本,即1597年版、1612年版和1625年版,三個版本所收入的文章數量及其內容均有所不同。《論友誼》一文最初收入1612年版中。中對此談得較為簡略:“友誼使歡樂倍增,使憂愁減半”,與朋友的交流“將會拓展自己的理解力,可以消除自己的情緒波動,也有助于籌備自己的社會事務”[12]Ⅵ,558。1625年版論說文集中的《論友誼》進一步闡釋了友誼的三種益處:其一,就情感而言,“友誼的主要效用之一就在使人心中的憤懣抑郁之氣得以宣泄弛放,這些不平之氣是各種情感都可以引起的”。閉塞之癥于人體有害,它們或許有藥可醫,但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打開心結,因為“對一個真心的朋友你可以傳達你的憂愁、歡悅、恐懼、希望、疑忌、諫諍,以及任何壓在你心上的事情,有如一種教堂以外的懺悔一樣”[22]95。“一個人向朋友宣泄私情能產生兩種相反的結果,它既能使歡樂倍增,又能使憂愁減半。”[22]101其二,就理解力而言,友誼能夠促進理解力發展,并能對其進行補救或矯正,這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1)個人的理解和判斷總是被情感和習慣左右,而來自朋友的勸諫則有可能避免情感和習慣的影響而切中要害,正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尤其在涉及德行時,由于“一個人的嚴厲自責是一種有時過于猛烈,蝕力過強的藥品。讀勸善的好書不免沉悶無味”[22]101,“在他人身上觀察自己的錯誤如同照鏡子,很少得到對方的反饋”[26]176,note49,因此“最好的藥方(最有效并且最易服用的)就是朋友的勸諫”[22]101。(2)無論對方是否有能力進行勸諫,“任何心中思慮過多的人,若能與旁人通言并討論,則他的心智與理解力將變為清朗而有別;他的思想的動作將更為靈活;其排列將更有秩序;他可以看出來把這些思想變成言語的時候它們是什么模樣;他終于變得比以往的他聰明,而要達到這種情形,一小時的談話比一天的沉思為效更巨——這些都是沒有疑義的”[22]99-100。其三,朋友能替代并幫助自己完成具體事務。
在闡明同伴及其友誼的益處的同時,培根也告誡青年要謹慎交友,否則無益于自身德性的修養。他在《學術的進展》中談及太過關注行為舉止和外在儀表這一做法時寫道:“在指導年輕的學生時,我們勸誡他們不要交往過多,有這樣一種說法,‘朋友是偷竊時間的賊’。”[13]161可見培根雖然承認同伴及其友誼的德育價值,但他對青年交友仍持保留態度,這看上去與亞里士多德的看法類似,因為后者曾指出青年的友誼主要基于快樂而非德性;培根對青年的態度似乎也殘留著亞里士多德對青年心理特征如欲望強烈而沖動、情緒波動超出自控能力的預設,以至于他在《生與死的歷史》中依然強調“青年善變無常,而老年人則莊重平穩”[12]Ⅴ,320。這就是說,雖然青年比老年人具備優秀的道德潛質,但由于受到年齡的影響,青年自身并不能做到莊重嚴肅、心境平和,所以《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才會強調莊重之人對塑造青年心靈的必要性,《論游歷》一文也才會建議青年在旅行時要有導師或莊重的仆人相伴。總之,在培根看來,過多的同伴交往可能會使青年傾心于快樂的追求而忘卻德性的修養。
(三)書籍與學問
關于知識與德性的關系,以往研究者最常援引《培根論說文集》中的話:“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之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22]5,以及《學術的進展》中的話:“真理與善行的分別正如印章和印跡的區分,真理印出善行;而錯誤的烏云,則只會帶來狂躁激蕩的暴風雨”[13]50,進而強調培根思想中真理與德性的直接對應關系,以至于有學者評論道:“從蘇格拉底提出的知識就是道德,到列寧倡導的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的論斷,說明人類一直重視知識和道德的統一性,從而也證明教學的教育性規律(筆者按,指教學活動是教書和育人相統一的規律)的重要意義。”[27]109-110這種解讀雖正確地揭示了培根看到知識之于德性養成的必要性,但由于未將二者的關系放在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下考察而失之偏頗。
應該說,培根關于這一問題最為詳細的論述是在他于1594年代筆的埃塞克斯伯爵寫給拉特蘭伯爵的第一封建議旅行的書信。他在論及旅行中知識學習的必要性時說:“缺乏知識的人也將缺乏所有的德性:沒有知識就不會有勇敢,因為所有其他貌似勇敢的行為都源自憤怒,而憤怒是一種激情,所有的激情都會向其反面發展。故而當最初的怒火熄滅后,最為憤怒的人通常也是最害怕的人。沒有知識就不會有慷慨,因為這種情況下的給予不是由于缺乏拒絕的勇氣,就是在評價所給予之物的價值時缺乏審慎。沒有知識就不會有正義,因為在缺乏知識的前提下能將其應得者給予某人(筆者按,指能對某人處置公允),不是由于偶然,便是由于主持正義過程中沒有行賄者。沒有知識就不會有恒定或耐性,因為承受苦難而無知識,只不過是愚鈍或是麻木。沒有知識也不會有節制,由于不能正確辨別便不會選擇,我們會把善行連同惡行一起約束起來。”[12]Ⅶ,11顯然以培根之見,對包括勇敢、節制和正義在內的諸多品德而言,知識都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知識之于德性的必要性并不意味著青年德性的培養方式是通過道德說教來把握道德理念,因為培根明確說過完全依賴學問的規則進行判斷是學者才有的癖好,學問本身也需要經驗的完善[22]179。如果道德學說最后使人變得“太過死板、高傲或不諳人事”,這樣的學說也是不值得提倡的[12]Ⅲ,441。他真正重視的是學問在實際經驗中的運用,這種運用主要體現在道德判斷上。清晰的判斷對需要主動施行的德性尤其重要,在此他特別提到慷慨和勇敢:“清晰的判斷之所以能夠讓人變得大方,是因為在評價命運帶來的物品(goods)時,它并不教人評價這些物品的價值本身,否則人不過是這些身外之物的囚徒,而是評價它們的用途,這樣人才能成為它們的主人;它也讓我們知道給予比接受更加使人幸福,給予代表著自主,而接受則象征著服從。清晰的判斷同樣讓我們走向勇敢,因為它教導我們不應該珍視那些我們無法經營的生活,也不應該恐懼我們無法逃避的死亡;高貴死去的人永遠活著,在恐懼中活著的人時時刻刻都在死亡;痛苦與危險的程度只存在于觀念中,實際上除了恐懼本身,沒有什么讓人感到恐懼的了。”[12]Ⅶ,9亞里士多德曾說:“德性是在于行善而不是受到善的對待,在于舉止高尚而不只是避免做卑賤的事情。而行善和舉止高尚也就是給予,受到善的對待和不做卑賤的事也就是接受。”“慷慨的人……不喜歡索取和保有而喜歡給予。而且,他看重財富不是因財富本身,而是因財富是給予的手段。”“勇敢的人是敢于面對一個高尚的死,或敢于面對所有瀕臨死亡的突發危險即戰場上的那些危險的人。”[3]97,98,78相比亞里士多德,培根在論述慷慨和勇敢時更加突出判斷的重要性,但就心智官能而言,青年因涉世未深而遠不及老年人,所以培根贊同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的觀點:“年輕人因為激情澎湃,沒有經過時間和閱歷的調和,是不適合聽道德哲學的。”①此觀點參見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頁。[13]155
同樣基于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培根將詩歌和政治知識排除在青年閱讀書籍的范圍之外。雖然“詩歌似乎適合并有助于彰顯崇高的行為,有助于宣揚道德規范,有助于人們的娛樂”[13]75,但他更贊同詩是“魔鬼的酒”的說法。“因為詩能占據人的想象,然而詩不過是偽說的影子罷了。害人的不是那從心中經過的偽說,而是那些沉入心中,盤踞心中的偽說……然而這些事情,無論其在人們墮落的判斷力及好尚中是如何,真理(它是只受本身的評判的)卻教給我們說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之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22]5事實上,培根關于“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愛求婚),認識真理(就是與之同處),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的論斷旨在從官能心理學的視角闡釋詩歌與真理的區別,他認為詩歌與真理不同,因為詩歌與介乎理性官能和道德官能之間的想象官能相對應,所以不能承載真理。“詩歌并不需要緊隨事物的邏輯,可以把自然狀態中不相干的事物連接在一起,也可能把聯系在一起的事物分割開來”[13]75,故而它只能存在于錯誤的判斷中;詩歌也不能有助于掌控意志,因為它與激情相伴,這才有“真理與善行的分別正如印章和印跡的區分,真理印出善行;而錯誤的烏云,則只會帶來狂躁激蕩的暴風雨”的說法。總之,“詩歌增加了誘惑、混亂和虛榮的想法”[12]26,因而不利于青年德性的養成。
至于政治知識,培根認為“只有等到其道德修為和宗教信仰得到成熟發展之后,年輕人才適合聽講政治事務,否則他們的判斷就會受到污損,情愿相信一切事物除了按照私利和命運加以衡量,再無其他區別”,“這是因為那些在國王的宮廷和國家事務中耳濡目染成長起來的人很少能夠在其行為方式中做到深沉、真摯的誠信,更不用談再給他們施加書籍中規訓的可能了”[12]Ⅴ,26-27。具體而言,有兩類政治知識妨礙青年的德性修養:一類與社交(conversation)有關,即卡斯底格朗《宮廷人物》這類書籍中所描述的紳士與廷臣的社交禮儀,這種知識不能過分推崇,原因之一是“那些精于高雅舉止的人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行為,很少再去追求更高的美德”[13]161;另一類與處世(negotiation)有關,這種知識主要教人對外展示能力與德性以及掩飾個人缺陷的為人處世之學,它們會誤導青年,特別是以馬基雅弗利學說為代表的“邪惡的技藝”教導說,“人們不要去追求道德本身,而只要追求道德的外表就行了。因為有道德的聲譽雖然有幫助,但是真正利用其道德來,卻是一種累贅”[13]182。對此培根評價說,“如果人們拋棄了仁慈正直的法則,他追求幸福的道路的確會更快速更便捷一些”,但追求個人命運者尤其需要了解的是,“所有美德本身就是最大的報酬,所有罪惡本身就是最大的懲罰”[13]182183。培根堅信上述兩種知識都會誤導青年的道德判斷,使他們放棄對激情的調控,因而有悖于磨礪意志的德育目標及要求。
(四)法律與教育、習慣與訓練、模仿與競賽
在1594年創作的宮廷假面劇中,培根借第五個諫臣之口以德性和仁政規勸君主說:陛下應完善法律體系、規范案件審理和監管司法人員,在法制工作完成后,“不要相信陛下的法律會匡正時政,而是要將全部力量用于實現良好的教育;確保陛下的大學和所有神學院對青年進行管理,維護平民家庭的秩序,保證兒童恭敬父母,青年敬畏古人”[12]ⅦI,340。這些并非應景之辭,他在《學術的進展》中同樣寫道:“古時候哲人身處盛世仍能提出合理的建議,批評國家過于偏重法律,忽視教育。”[13]15培根認為雖然法律與教育均為影響意志的途徑,但對政治秩序與宗教秩序的穩定來說,教育更為重要,“因為國家與好政府只是滋養已長成的美德,而不甚幫助美德的種子的”[22]145。培根進一步指出:“習慣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習慣,這是一定的,這個我們叫做教育。教育其實是一種從早年就起始的習慣。”[22]145作為德性培養方法的教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的。近代英國法學者普遍認為法律源于社會習俗,習俗通常被視為不成文的法律[28]93,96,作為資深律師的培根就曾指出法律與習俗的變更是政治動蕩的重要原因之一[22]52。在英語語言體系中,與教育相關的“習慣”和與法律相關的“習俗”原為同一個詞“custom”,培根既在集體層面上也在個體層面上使用這個詞,而其同義詞“habit”與之相比在近代更具個人含義和心理學含義[28]84,98。因此,法律與教育、習俗與習慣對培根而言并無本質區別,不過培根從未正面論述法律對青年德性養成的作用。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思想傳統中就有“習慣為第二天性”的說法。培根在《學術的進展》中論及習慣時即以亞里士多德為參照,他選擇《尼各馬可倫理學》第二卷開頭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根據培根的解讀,亞里士多德錯誤地認為“自然所決定的事物是不能被習慣所改變的”[13]154,他接著以手套、木棍、嗓音和身體忍耐性為反例,試圖論證習慣較之天性更為重要。如此做法有標新立異之嫌,因為亞里士多德緊接著即提出了相同的觀點:“自然賦予我們接受德性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通過習慣而完善”[3]36,培根自己也承認亞里士多德的本意是“道德和罪惡都是基于習慣的”[13]155。對于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普魯塔克等古典作家普遍接受的天性、習慣和理性的關系,培根一方面反復強調習慣對德性養成的決定性作用,如依照“信稿”中草擬的看法,在改變意志的眾多方式對意志施加影響后,“剩下的就由習俗和習慣予以強化和支持了”[12]Ⅶ,101;再如《論習慣與教育》一文中寫道:“人們的思想多是依從著他們的愿望的,他們的談論和言語多是依從著他們的學問和從外面得來的見解的;但是他們的行為卻是隨著他們平日的習慣的。所以馬基雅弗利說得很好……天性的力量和言語的動人,若無習慣的增援,都是不可靠的。”雖有例外,“然而他(筆者按,指馬基雅弗利)的定律依然是不移的,就是,天性與言語上的允諾要約都不如習慣有力”[22]143-144。
另一方面,培根又將理性具體化為習慣培養必須遵守的規則①培根雖然并沒有明確將習慣訓練的規則與理性直接聯系起來,但他在列舉了四條規則后寫道:“所謂的習慣如果經過適當的指引,實際上就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但如果只受運氣的控制,就會變得像原始的猿猴一樣,并產生許多牽強又虛假的東西。”(弗蘭西斯·培根《學術的進展》,劉運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55頁)他強調習慣的訓練必須是理智的、富于技巧的,而不是靠碰運氣,這便使訓練的規則與理性之間建立起了內在聯系。文藝復興時期論述禮儀規范的名著——德拉·卡薩(Giovanni Della Casa)的《禮儀》(Galateo)中闡發了極其類似的思想,該書重復了改變天性的方式,其中包含理性與習慣關系的傳統觀點,而且指出訓練行為的規則來自理性(Della C.G.,Galateo,trans.by Pine-Coffin R.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58,pp.85-89)。,這便涉及作為德性養成途徑的“訓練”(exercise,也可譯為“練習”)的概念。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看,“訓練”既與理性官能相關,也與道德官能相關。培根在談論前者時主要圍繞統括各種理性官能的“心智”(wit)這一概念,而把各種道德官能的訓練統稱為“心靈的訓練”(exercise of mind),并列舉了“心靈的訓練”的四條規則:(1)“我們應當小心在開始時調子不可定得太高,也不可太低。如果太高的話,對于缺乏自信的人來說就會嚇倒他;自信的人反而產生一種輕視的看法,并因此變得懶惰。人們一般常常會一開始期望太高,結果并不能實現。另一方面,如果調子定得太低,也就無法指望人們完成或勝任任何重大的任務。”[13]155(2)“在兩種不同的時間來進行各種練習,一是在心理最合適做事的時候,二是在心理上最不合適做事的時候。利用第一種時間可以得到大的進步,利用第二種時間可以戰勝心理的緊張和障礙,中間的時間你就會覺得更加容易、更加愉快。”[13]155(3)“朝我們天性相反的一端用力,就好像逆水行舟,或者背著樹干自然彎曲的方向扳扯,把它變直一樣。”[13]155這條規則來自《尼各馬可倫理學》[3]56。(4)“如果我們不直接追尋我們的目標,而是在做其他事情時間接地完成,那么我們的心理就比較容易改善,我們就能夠更加心情愉快地達到目的,這是因為人們的心理天然地憎惡必須和束縛。”[13]155在闡述了上述四條規則后,培根強調:“所謂的習慣如果經過適當的指引,實際上就成了我們的第二天性。但如果只受運氣的控制,就會變得像原始的猿猴一樣,并產生許多牽強又虛假的東西。”[13]155由此可見,在這里培根對“習慣為第二天性”的西方思想傳統做了重要的補充和糾正,從而豐富和發展了西方關于天性、習慣和理性的關系的思想。培根在《論人的天性》一文中強調:“天性常常是隱而不露的,有時可以壓伏,而很少能完全熄滅的。壓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壓力減退之時更烈于前;但是習慣卻真能變化氣質,約束天性。”[22]141為了進一步論證通過“心靈的訓練”來養成良好習慣的觀點,他介紹了上述規則的具體內容,并舉例加以說明:“在起始的時候他應當用些幫忙的事務來練習,就好像學游泳的人用浮胞和葦筏一樣;但是過了些時候以后,他應當與困難相搏以為練習,就好像舞蹈家之穿著厚鞋練習一樣。因為,假如練習比實用還難,那么其結果就更為完美了。”[22]141
通過“心靈的訓練”來養成良好的習慣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培根將更多的注意力轉向集體教育環境的作用。他論述道:“假如個體的單獨的習慣其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共有的聯合的習慣,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因為在這種地方他人的例子可為我之教訓,他人的陪伴可為我之援助,爭勝之心使我受刺激,光榮使我得意,所以在這種地方習慣的力量可以說是到了最高峰。天性中美德的繁殖是要仗著秩序井然、紀律良好的社會的;這是無疑的。”[22]145可以說,此處所謂“社會”(societies,也可譯作“社團”)在當時歐洲的原型正是《學術的進展》中所贊賞的耶穌會。培根在《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中進一步明確地指出:“我明確贊同對男孩和年輕人進行一種學院式教育(collegiate education),而非在私人家庭中進行的或僅僅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的教育。在學院,青年彼此之間的相互競爭是在別處遠不能及的;另外,莊重之人的出現則會使青年變得謙遜,并能夠從一開始作為榜樣塑造青年的心靈。簡而言之,學院式教育有非常多的優勢。”[12]Ⅳ,495對《耶穌會憲章》(Constituciones de la Compania de J esus)和耶穌會《教學章程》(Ratio Studiorum,也可譯作《學科計劃》)的考察表明,培根的贊賞是有充分根據及理由的[29]。關于榜樣與模仿,雖然耶穌會并未突出“莊重之人”的榜樣作用,但榜樣示范的作用在耶穌會學院中卻始終被強調:未來將成為修會成員的學生在內心和外表都要保持謙遜,以身作則并示范給他人;修會外就讀學生則必須選擇能夠幫助其學業和德性進步的榜樣和同伴;耶穌會學院中還有由優秀學生組成的學社(academia),學社成員及其主席同樣需要為他人樹立道德榜樣。此外,《耶穌會憲章》強調謙遜是每個學生必須保持的基本品質。至于競賽與獎勵,另據耶穌會《教學章程》,相鄰年級優秀學生之間的競爭每年組織若干次;在各年級學生內部每月或每兩個月組織的榮譽頭銜評選競賽會上獲得頭銜的學生將坐在前排,有時也會得到額外獎勵[30]150。《教學章程》還為教授語法、人文學科和修辭學的教師提供了激發學生競爭的各種教學技藝,并認可教師也有權利用獎勵來刺激學生競爭;耶穌會學院常舉辦不同類型的寫作競賽,每個年級學生的寫作競賽獎勵都有詳細規定。此外,耶穌會學院舉辦的拉丁語戲劇表演也深為培根所欣賞,他認為這種表演能“強化記憶、調節發音的語氣和效果、教人掌握得體的表情和手勢、獲得充足的自信,并且讓年輕人習慣于他人的注視”[12]Ⅳ,496。可見,拉丁語戲劇的價值在于通過表演將語言訓練與道德教育充分結合在一起。有研究者指出,在其教學實際中,耶穌會學院產生了大量出色的戲劇,拉丁語戲劇表演應被視為耶穌會學院文化的組成部分[31]139。顯然,培根通過耶穌會學院了解到戲劇表演的德育價值。
五、結語:培根青年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及貢獻
總體而言,培根所處的文藝復興時期是歐洲走出中世紀、邁向近代社會的重要歷史轉折時期。像這一時期的其他先進教育思想一樣,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主要建立在古希臘羅馬人文主義思想傳統和遺產的基礎上。難能可貴的是,培根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把握和重新定位青年的心理特征,并結合耶穌會學院開展青年教育的實踐經驗,圍繞“將青年導向德性”這一宗旨和目標,較為全面而深刻地闡發了其青年教育思想,并使之達到了一個新的理論水準。
首先,前文的考察表明,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的邏輯起點并非關于人性的抽象理論,而是作為人性影響因素的青年心理特征,他對青年心理的研究擺脫了古典作家筆下青年以情欲為主導的消極形象,從官能心理學的分析視角來看,這主要是由于他更加重視介乎理性官能和道德官能之間的想象的功能及作用。關于想象,都鐸王朝后期的英國文人學者普遍將其視為一種與其他心理官能相關聯的極不穩定的中間官能,因為在理性層面受制于各種影響因素的想象為理性所提供的往往是不能真正反映現實的扭曲表象,而在道德層面這種歪曲現實的表象會刺激相應的激情,二者在擺脫理性的控制后通常會引起不合乎道德的行為。然而,同時代另有部分英國文人學者認為偽造的表象如能得到合理控制,也會帶來各種學科和技藝上的發明[32],可以說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接近培根的想法。當他說“青年更適于發明而非判斷”時,至少是通過訴諸想象的積極功能來更加公允地評價青年的心理特征和認識能力;培根宣稱修辭演說可以促進想象與理性合作來共同掌控情感,這一觀點意味著更容易受到想象影響的青年具有很強的道德可塑性。這些關于青年心理全面而積極的評價大大超越了情欲之說的范圍,發前人所未發,堪稱培根對西方青年教育思想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其次,在審視培根“將青年導向德性”的整體思想構架時可以發現,“心靈的培養”,或更確切地說是“心靈的治療”這一思路源自西方哲學史上與靈魂治療相關的思想傳統①關于這一哲學傳統,相關研究成果中最具影響者為 Nussbaum M.C.,The Therapy of Desire: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中文研究成果可參見石敏敏、章雪富《斯多亞主義》(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 1-28,48-65,256-282頁。[33]。由于這一思想傳統無法被納入“本體論—認識論—社會政治倫理哲學”的一般知識框架中[34],它始終游離于培根研究者的視野之外。該傳統的核心要義是將哲學視為治療靈魂疾病的方法,其中斯多亞學派將激情視為靈魂疾病的觀點對后世影響甚大。培根的創新之處在于將這一思想傳統拓展為包括觀察“體質”(個人性情)、診斷“疾病”(激情)和開具“藥方”(支配意志和欲望的方法)等在內的系統的“治療”方案,他在此基礎上不僅實現了對相關思想資源的整合,而且把與道德教育相關的諸多因素納入自己的經驗研究計劃之中。《新工具》有言,經過改造的歸納法不僅適用于自然哲學,而且適用于邏輯學、倫理學和政治學[35]100。培根認為這種歸納法在人類哲學中運用的前提是相關歷史材料的搜集,而“心靈的治療”同樣需要采用這種研究方法。他本人也是依據這種觀點來進行研究的,如《論學術的發展及價值》指出對個人性情和激情的研究需要訴諸歷史材料,《培根論說文集》中對各種激情的論述更加注重列舉相關史實作為例證[36]271-273,其中特別是《論友誼》《論習慣與教育》和《論稱譽》等文在對“藥方”進行分析時補充了不少歷史示例。雖然培根最終并未對歸納法在人類哲學中的應用提供進一步闡釋,但在“心靈的治療”這一總體思路下,“將青年導向德性”的命題和觀點被賦予更多的實證屬性,這使得培根區別并超越于只停留在規范性論述層面的其他教育思想家。說到底,這也與培根所提倡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和經驗主義教育觀密切相關。
最后,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中也包含了學校教育優于家庭教育的觀點。在這方面培根對古羅馬教育家昆體良和文藝復興時期教育家維夫斯(Juan Luis Vives)的相關思想進行了綜合。昆體良在為學校教育辯護時強調學校中友誼的重要性,并說學生在學校“每天能聽到有許多事受到贊揚,有許多事得到糾正;怠惰的同學受到責備,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警惕;對勤奮學生的贊揚,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刺激”[37]23。他還說“贊許能激起競爭”,并介紹了將學生分成班級,“按照各人的能力輪流發表演講,能力強的就先演講”的做法,稱贊這種教學方法是“一種有益的教學方法”,因為這種方法比教師的規勸對學生的激勵作用更大[38]23-24。為培根贊賞的耶穌會的學院教育可以說是對昆體良上述思想的最好繼承和發揚。另一方面,維夫斯與依納爵·羅耀拉相同也曾就讀于巴黎大學蒙太古學院,但他對當時學院的風氣并不看好,且反對膳宿制。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學院(他稱之為“學園”)培養的學生必須品學兼優,如此才能抵擋來自墮落同伴的影響。維夫斯有兩個觀點為培根所繼承:其一是習慣與模仿的作用,他說童年時代形成的習慣將對人生產生深遠影響,并說孩子就像猴子一樣模仿任何他們認為值得模仿的人[37]259。培根對作為道德教育途徑的“習慣”和“模仿”的論述與這些觀點如出一轍。其二是學校教育中“莊重”的意義,維夫斯要求學園的“莊嚴”和“威望”為所有人尊敬,并提到與此相關的古羅馬傳統:“羅馬人過去為了自己兒子的學習,常常把他們托付給有名的老年人,這些人最為莊重和虔誠。”[39]65“當老年人看到他們的辛勞是有用的,特別是當他感到這對共和國是必需的時候,他們都不辭勞苦;因為,在他們死后,共和國恰恰就是他們遺留給孩子們或青年人的那個樣子。”[38]260正是基于相同的理由,培根也要求理想的學院安排“莊重之人”,并將青年視為共和國中“德性的種子”。眾所周知,近代英國有著悠久而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教育與信仰、思想、言論一樣被視為公民的“私事”,因而普遍不贊同政府干預教育,洛克等英國近代教育家也都偏好家庭教育并大多做過家庭教師,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近代英國的學校教育落后于歐洲其他國家。從這一點來看,培根認為學校教育優于家庭教育的觀點符合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具有比較明顯的超前意識。
正像任何歷史偉人一樣,培根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學界普遍認為培根的教育思想帶有宗教的烙印,這主要是因為他在列舉了所有“藥方”之后,將獻身于良善目標視為“心靈的治療”的“最簡明最概括的一種方法,同時也是最高貴最有效的一種方法”[13]157,并將其與基督教的“博愛”聯系起來。然而在“心靈的治療”的思想構架中,宗教并非道德哲學的附庸,二者的關系可以說頗為復雜。新發現的一份培根手稿表明,所謂“獻身于良善的目標”實際上指《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被稱為“德性之冠”的“大度”。與亞里士多德稍有不同的是,培根在手稿中將“大度”界定為心靈的一種悟性(apprehension)狀態,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凡是人都可以將這種悟性直接轉化為與所需行動相關的德性,因而它本身就是所有德性的綜合,使人遵從并效仿神的意志。這種英雄德性實非常人可及,蕓蕓眾生所能實現的只是通過正當理性和習俗而形成的習慣,習慣培養的“規誡多則多矣,但這些規誡不能直接應用于特定或即時的行動,只是將大量努力用于塑造心智”[40]303。考察培根的后期作品可以發現,培根不僅用基督教的“博愛”取代了“大度”原有的位置,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與“大度”相關的人的天性差異:人性中具有向善(即“博愛”)的傾向,所謂善不過是由此形成的習慣。關于“心靈的治療”的道德哲學基礎,他反復強調單純的習慣訓練或許有助于培養“節制”的德性,但無法培養“慷慨”和“勇敢”等需要主動實施的德性,因為它們需要道德判斷的參與。
如果說近代西方確實存在從神性德育向知性德育的轉變①關于近代西方從神性德育向知性德育的轉變,可參見高德勝《知性德育及其超越——現代德育困境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00頁。,那么培根的德育思想在這一譜系中顯得十分獨特,因為他認為基督教的博愛精神與道德哲學治療心靈的“藥方”都需要道德判斷,也都需要道德習慣的養成。從前文的分析可知,培根始終十分重視道德判斷和道德習慣對青年教育的價值與作用,甚至為青年道德習慣的訓練和培養制定了必須遵守的理性規則,從而試圖將人的“知、情、意、行”四個方面協調統一起來,這便使得培根關于青年的道德教育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同凡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西方近代德育思想和理論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時至今日,培根的青年教育思想并未湮沒無聞,當代受其影響最大者當屬新行為主義代表者斯金納[41]。只是在后者那里,宗教、法律、教育都是控制青年行為的方式,具體來說,學校是為強化其行為而存在的機構,贊許是強化其行為的手段,每一種習慣都可以通過強化來得到改進②關于斯金納的相關思想,可參見樂國安《從行為研究到社會改造:斯金納的新行為主義》,(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24-250頁;斯金納《科學與人類行為》,譚力海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78-386頁;Skinner B.F.,Walden Two,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5,p.25。。這樣的“古今之變”大概是培根在幾百年前所始料未及的。
-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預印本的其它文章
- 健康行為的社會規范性影響和從眾心理
- 從尼采到馬克思:魯迅的思想轉變
- 數字環境下首次銷售原則的適用困境與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