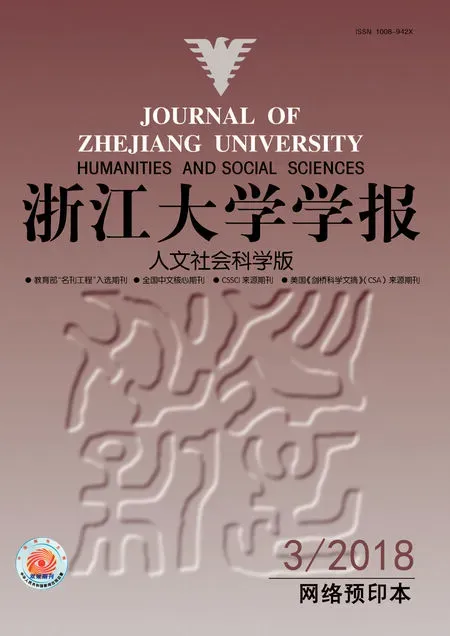比較法視野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
丁相順
(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院, 北京 100872)
當前,中國正在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深化審判體制與機制改革,“核心任務是確保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而讓審判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也是讓審判主體依法獨立地承擔審判責任”。可見,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是尊重司法規律,強化司法裁判活動的專業化,推動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人員的職業化建設,增強職業化的主審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主導地位,使其成為司法裁判的責任主體。另一方面,新一輪司法改革也提出“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的目標。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了“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目標。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通過了《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正在推進和實施該試點方案。該方案分基本原則和改革目標、主要內容、方案實施、組織保障四個部分,提出了司法改革目標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基本架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點工作后,有關部門將提出制度改革方案,因此,站在更加廣闊的視角,從比較法的角度分析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類型,將對建構合理、科學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及實現司法改革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當今世界,讓普通民眾有序參與司法審判,特別是刑事司法審判,已成為各國司法制度改革的一個重要趨勢。“很多國家的改革者一定程度上將‘陪審制’或‘半陪審制’作為推進政治、經濟、甚至社會改革的手段。近年來,世界上的很多國家都通過使民眾參與、融入本國的司法制度,來促進改革、提高公眾參與決策和提升國民主權”[1]。這一趨勢在東亞各國表現得尤為明顯,作為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環,21世紀初以來,日本和韓國先后通過立法在刑事司法中建立了民眾參與司法的制度形式。因此,在司法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應該從歷史發展、國際比較等視角重新審視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設計,厘清司法的專業化、職業化改革取向與司法民主參與之間的關系,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確保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的正確方向。
一、 “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類型與中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定位
所謂“民眾參與司法”,就是讓普通民眾參與司法審判,從而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反映其社會常識,確保案件能夠得到公正的審理,從而實現促進司法民主化等目標。截至2008年,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有55個國家都在刑事程序中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其中大部分都是經濟發達、政治民主和受到近代法文化影響的國家[1]。各國司法制度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同的民眾參與司法審判的模式,學界的歸納和概括也多有差別。
大體來說,各國學界一般將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形式分為兩種類型:“陪審制(Jury)”和“參審制(Assessor)”。兩者在實現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方面具有共性,但在民眾的選任方式、民眾參與審判的形式、庭審中民眾與職業法官的關系、民眾做出決定的效力等方面,則多有差異。一般認為,英國、美國等普通法國家實行的是一種“分工式”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形式(即陪審制),一般民眾在庭審中負責認定事實,職業法官則掌控庭審的進行,并負責法律的適用;而德國、法國等國家實行的是“無分工式”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形式(即參審制),民眾與職業法官共同審理案件,共同決定案件事實,共同決定法律適用。上述差別不僅反映在參與裁判的民眾與法官的權利和作用方面,也表現在法庭的布局上:在陪審制下,民眾一般坐在法庭的側面,不參與庭審調查,處于相對消極的狀態;而在參審制下,民眾一般與法官比鄰而坐,參與庭審進程,作用積極[2]234。為了避免用語不同而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本文使用學界對民眾參與司法形式的一般劃分,即英美國家的陪審制和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采取的參審制。兩者的實質性差別在于:普通民眾的選任方式是采取案結事了的案件擔當制還是任期制;庭審活動中,民眾與法官是否在決定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上存在分工。
社會科學特別是法律科學要依賴概念用語進行建構。中國傳統司法并不存在民眾參與司法的形式,因而也不存在這樣的概念。“陪審”一詞是清末變法之際西方傳教士或日本的媒介對英文Jury制度的中文翻譯。單純從字面意義上看,似乎人民陪審員制度可以追溯到清末變法時期從Jury制度翻譯而來的“陪審”[3]。但近年來,中國學界也注意到了“陪審”一詞名不副實的問題,認為“從制度的歷史、運作程序和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相關內容”來看,“將Jury制度翻譯為陪審團制度是不恰當的”[4]503。“如果要‘咬文嚼字’的話,從日文和中文的表達習慣來看,可能把‘Jury’稱為‘民審團’,把‘Juror’稱為‘審判員’更為貼切”[5]1。因此,從制度的實際內容來看,盡管使用“陪審”的用語,但現行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質上與英美的Jury制度無關。
那么,現行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歷史淵源何在?“人民陪審員”的概念包括“人民”和“陪審”兩個部分。人民成為司法裁判的參與者、主體,與近代以來的民主主義革命密切相關,是民主主義革命者在對幾千年封建等級制度進行嚴厲批判的基礎上,從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中獲得啟發而提出的政治主張,是民主革命的成果。例如,孫中山在對清朝君主專制司法裁判制度提出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平其政刑”的主張,“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之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6]194。中國共產黨也明確提出了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主張,發動群眾,讓民眾參與司法成為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董必武明確指出,“人民陪審員能把人民群眾的生活經驗和法律意識、道德觀念帶到法院里來運用”[7]539-540。可見,人民陪審員制度本身有著高度的中國化色彩,反映的是近代以來民主主義革命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是一種完全有別于英美陪審制度的做法[8]。“人民陪審員制度最早始于革命根據地時期,是我國司法制度的一項優良傳統”*參見最高人民法院答問《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649985.htm, 2016年9月9日。,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中,因為“人民陪審員”的概念用語取自蘇聯的訴訟制度,實行這一制度具有與蘇維埃國際聯盟保持一致的象征意義。1949年后,這一制度理所當然地被確立下來,“中國自1949年以后,除‘文化大革命’時代以外,似乎‘一貫’重視司法審判的‘人民性’。不僅傳統的‘判官’一律改稱‘審判員’,而且通過學習和借鑒蘇聯的法律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審員’制度”[5]4。
盡管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具有濃厚的人民參與司法的政治象征意義,但近代以來,中國長期處于內亂和外戰的狀態,這決定了“人民”的“陪審”制度只能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做法存在,并不能發展成一種精細的司法裁判模式。即使1949年后,甚至在現行的制度實踐中,人民陪審制度也顯得較為粗糙、隨意,是否采取人民陪審員的形式以及人民陪審員在裁判過程中的作用高度依賴于法院和職業法官的決定,盡管這如實地反映了“陪審”的中文字面意義,即“陪同審判”。而陪同審判的做法,在中國的傳統司法文化中也并非無跡可尋。從周代出現的“一曰訓群臣,二曰訓群吏,三曰訓萬民”,到唐末以降的三司會審、朝審、秋審等會審形式,都是由主管司法裁判事務的審判官員主導疑難、重大案件的審理,由相關官員參與陪同,甚至聽取民眾意見[9]。這樣,在清末以來西風東漸和民主革命風起潮涌的形勢下,原本譯自英美Jury制度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形式——陪審,與中國古代固有的“會審”形式自然地結合在一起。
從制度內容方面來看,人民陪審員制度通過任用制選任民眾的做法以及民眾和法官一起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的結構設計,與參審制的民眾參與司法類型相近。允許非司法專業人員參與審判、陪同審判的做法又與中國傳統司法文化高度契合。而普通民眾能夠作為司法裁判的主體參與司法裁判過程,反映了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理念,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成果。由此可見,作為繼受近代民主主義成果的人民陪審制度與起源于英美的Jury制度無論在內容還是精神層面上都有實質性的區別。從制度的本源來說,中國當代人民陪審制度受到近代民主主義革命的深刻影響,是本土法律文化發展的產物。
從類型化的角度對人民陪審員制度進行歷史分析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拓寬視野,更加理性、全面地觀察和審視這一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形式,從而為人民陪審員制度的理論探討奠定基礎。
二、 志同道不合: 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模式的比較法觀察
21世紀初,中國立法機關恢復人民陪審員制度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世界上出現了恢復或創建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潮流。突出的例子是,俄羅斯于1993年通過了《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法典》,正式將陪審制度引入了刑事訴訟程序*關于俄羅斯陪審制度的內容,參見王志華《轉型時期俄羅斯的陪審制度》,載《環球法律評論》,2007年第2期,第106-114頁。;西班牙于1995年5月頒布了《陪審法院組織法》,建立了恢復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陪審制度[10];特別是東亞國家日本、韓國也出現了對民眾參與司法的重大關注,先后恢復和創設了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不同形式。其中,日本于2004年5月通過了《關于裁判員參加刑事審判的法律》(簡稱《裁判員法》),以及與此相關聯的《關于部分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法律》,并于2009年5月正式實施裁判員制度,“裁判員制度就是在那些民眾關心程度高、社會影響大、法定刑較重的案件中,實行以隨機方式抽取一般民眾擔任裁判員,由裁判員與職業法官組成合議庭,共同審理案件,一起決定定罪量刑的制度”[11]。韓國也于2008年1月正式實施《關于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的法律案》(簡稱《國民參與裁判法》),標志著韓國正式在刑事訴訟中建立陪審制。
由于東亞的日本、韓國與中國在法律傳統、法制現代化類型以及成文法為主的法律體系等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將人民陪審制度放在東亞比較法的框架下進行對比和分析,可以更好地認識各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整體態勢,準確把握各國民眾參與司法的特征,厘清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的思路。
(一) 日、韓兩國創設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的背景
日本、韓國創設的“裁判員制度”和“陪審員”制度,都是21世紀初開展的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在1928年至1943年間,日本曾經實行過英美模式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即陪審制,由于這一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限制陪審案件的范圍,治安維持案件和選舉案件不在陪審范圍之列;即使陪審員做出裁決,但如果該裁決不符合法官意圖,法官可以多次要求重新陪審;如果被告人要求實行陪審,在陪審團做出被告人有罪的判決的情況下,被告人須承擔陪審的部分或全部費用。,陪審制度被中止適用,但并沒有被廢止[12]。但二戰以后,日本的司法制度并沒有恢復陪審制度,也沒有采取任何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形式。20世紀末以來,日本內外出現了新的形勢:美國等國家施壓要求其進一步開放市場,國內結構性改革要求由事前規制的行政主導型社會管理模式向事后救濟的司法救濟模式轉變。因此,20世紀末以來,日本開始進行司法制度改革,司法裁判的主體制度改革是其重要內容。此次司法制度改革有兩個重要內容:改革法律職業結構和培養制度,讓普通民眾參與司法。兩者都與司法的主體相關,屬于所謂的“踐行者”*參見[日]田口守一《日本裁判員制度的意義與課題》,付玉明譯,載《法律科學》2012年第1期,第195-200頁。田口教授指出,日本司法改革涉及兩個主體性問題,“一個是法制度的直接推行者——‘法律職業者’,即裁判官、檢察官及律師等專門法律人才的培養問題;第二個與‘踐行者’有關的問題是,裁判員制度的引入”。。創設一種能夠讓民眾參與司法的制度,一直是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的重要議題。2001年6月,負責提出改革建議方案的“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提交的意見書明確提出:“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應建立廣大普通國民與法官共同分擔責任、相互配合,主動地、實際參與決定審判內容的新制度。”主張強化刑事司法的國民性基礎(國民參加司法),讓一般國民分擔法官的責任,能夠主體性、實質性地參與刑事案件的審判*參見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意見書——支撐21世紀日本的司法制度》,中文譯本參見丁相順譯《司法改革報告——日本司法制度改革意見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在此過程中,律師聯合會主張采取二戰以前日本曾經實行過的陪審制。但代表司法行政勢力的法務省認為,陪審制以英美法為基礎,英美法關于犯罪成立的要件不如大陸法系嚴格,如果采納陪審制將動搖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基礎,并且尚無法確定日本國民是否具有應付陪審制度的能力。而法院方面也主張裁判權為法院專屬,傾向于采取法官和民眾組成混合裁判組織體的形式[13]86。最終,折中的裁判員制度被采納,從而創設了一個完全不同于二戰前陪審制的新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
“韓國的情況大體與日本相同,主要是由于兩國的法律體系有著很強的相似性,并且在進行著相同的司法改革——盡管兩個國家的改革有著不同的推動力而在制度上設計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4]。20世紀90年代發生在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結束了軍人獨裁,新的民選政府不得不響應民眾提出的民主化要求。同樣,在國際上,日美自由貿易談判使韓國不得不進一步開放法律服務市場。這要求韓國改革司法制度,提高法律職業人員的專業能力,克服法律職業內部存在的“自我服務”“前官優待”——即法官對曾經擔任過法官的律師給予特殊關照的現象。無論是2003年在最高法院下設的“司法改革委員會”,還是2004年成立的“司法改革推進委員會”,都以促進民眾司法、提高司法民主化為要務,以實現司法程序中的民主化,監督和制衡職業法官在刑事裁判中的專斷,提高司法的透明性和公信力。這種司法民主化要求最終促成了韓國國會于2007年通過《國民參與裁判法》。
(二) 相同的取向,不同的道路
從上述日本、韓國建立民眾參與司法制度的過程來看,盡管中國與日、韓兩國都是朝著司法民主化的方向改革,但背景多有差異,制度本身的發展道路也多有不同。中國恢復和規范人民陪審員制度與日本、韓國差異更甚。就日本、韓國而言,其制度形成的道路也有所差別。
在中國,完善人民陪審制度的動議最初來自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司法機關。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頒布決定,重新恢復和完善陪審制度,并不是進行制度的創設,而僅僅是對這項制度加以規范和完善。而且,立法機關并沒有對實體法和訴訟法做相應的變革,人民陪審制度被看作一種在既有司法審判框架下進行的局部改革措施。這種態勢即使在最近的訴訟法修訂中,也未見任何改變。無論是新的刑事訴訟法,還是新民事訴訟法,都沒有為適應人民陪審員制度而進行任何的程序調整。也就是說,人民陪審員制度被設定為既與訴訟法修改前的制度相適合,也與訴訟法修改后的框架相匹配。
盡管日本二戰后建立的司法制度受到美國的很大影響,攝取了很多對抗庭審的要素,但美國的陪審制度并沒有產生任何作用,被束之高閣的戰前陪審制度也沒有得到恢復。日本司法走上了法律職業化和精英化的道路。通過嚴格的司法考試選任的職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成為司法訴訟程序的主角,職業法官主宰著庭審程序、決定判決結果。日本司法表現出由職業檢察官起訴、職業法官決定庭審的“精密司法”狀態。所謂“精密司法”就是實行徹底的偵查,在與正當程序不正面沖突的限度內,對拘禁的犯罪嫌疑人實行最大限度的調查。不僅警察,而且檢察官也非常重視偵查,一般要在確定充分的證據基礎上起訴,起訴要有完全的把握。在審判中,經常是在征得對方同意的前提下,或者以證人喪失記憶、陳述矛盾為由,使用偵查過程中制作的陳述筆錄作為證據。在許多案件中,口頭辯論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來朗讀證據文書(或者敘述其主要內容)。在這種“精密司法”模式下,法院甚至做出了超過99%的有罪判決。“這是一個使外國研究人員感到吃驚的數字。但另一方面這也確實表明了司法的精確度。并且,也要看到在這一數字背后,相關人員表現出的追求案件真實的熱情。”[15]17與這種過分重視審前偵查相關,法庭上的庭審活動經常流于形式,刑事司法中出現了庭審程序“空洞化”的現象,從而導致審判程序前置,作為偵查機關的警察和檢察官在刑事司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法官的庭審只不過是對檢察官起訴的案件進行確認而已。由于刑事司法過度強調發現實體真實,強調公訴的精確性,這種精密司法模式架空了“罪疑應有利于被告”的現代刑事訴訟原則。在刑事訴訟中,高達99%以上的有罪比例并不能必然保證案件的準確率,其中也出現了一些冤案,引起了民眾對完全由法律職業家主導的刑事司法的強烈不滿。“直接的契機是再審程序導致不少死刑案件平反,律師們質疑法官是否過于輕信檢察官之類的批評逐漸響亮。公眾傳媒還主張,即使在一般民刑案件中,深居簡出的法官的正義感和判斷也越來越與普通民眾的要求脫節,需要通過開放的方式矯正偏頗”[16]。因此,日本開始對壟斷的精英化刑事司法模式進行修正,建立由隨機挑選的一般民眾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的裁判方式。
韓國在二戰前曾經長期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其法律制度也深受影響。二戰以后,盡管殖民主義得到了清算,但通過日本之手建立起來的歐陸樣式的司法制度仍然得以保存。與日本不同的是,韓國在歷史上未曾實行過任何正規的民眾參與裁判形式,而且在2000年以前,對民眾參與司法的學術討論也極少[14]。與日本一樣,韓國也在二戰以后實行嚴格的司法考試和司法研修,控制法律職業人員的人數,形成了由法律職業家壟斷的精英化階層。這種由高度精英化的職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主導的司法程序也同樣表現出精密化的特點,偏離社會民眾。20世紀90年代韓國實現民主化以后,對司法制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改革和更加有效地發揮司法對社會的救濟功能,成為韓國民選政府的重要議題。同時,日本在21世紀初進行的司法改革也對韓國產生了重要影響,關于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各種討論也引起了韓國的關注,裁判員制度的立法過程、背景等被迅速地介紹到韓國,對韓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的建立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日本和韓國將民眾參與司法的范圍限定在刑事審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刑事案件涉及人身權利的處分,刑事錯案不僅會對當事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而且容易引起更廣泛的社會批判,甚至引發對司法裁判制度的不信任。因此,日本、韓國建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民眾參與來克服高度精英化的司法官僚所導致的司法高度形式化問題。但是,日本和韓國建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的初衷有所不同: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主要是為了提高公眾對司法制度的理解,強化司法的透明性,防止法官單獨做出的判決脫離社會常識;而韓國建立陪審制的民眾參與司法的形式,主要是目的是強化司法程序的民主正當性,牽制和監督職業法官,促進司法的公開和提升公信力。
(三) 中國與日、韓兩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的內容比較
傳統上,亞洲國家并沒有表現出對民眾參與司法的偏好,甚至有人質疑“亞洲是否能夠成功地實踐那些‘西方化的民眾參與司法’”[17]。但是,東亞司法改革進程中正在發生的變化使人們相信,民眾的司法參與可以在長期尊崇官憲文化傳統的東亞司法實踐中生根發芽。文化背景、成文法傳統似乎都不是阻礙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因素。但是,制度的成效如何,卻與其生成路徑和制度內容具有極大關聯。中、日、韓三國的具體制度設計存在極大的差別。
第一,在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案件的適用范圍方面,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適用于民事、刑事以及行政一審案件,而日本的裁判員制度和韓國的陪審制度僅僅適用于重大刑事案件。很明顯,日本、韓國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案件的適用范圍較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要窄。對于個案是否采取民眾參與的形式,三個國家都采取由法院決定和當事人申請的形式,但法院和當事人的決定權比重在三個國家具有明顯的不同。在日本的制度下,法院對法定裁判員審理的刑事案件具有絕對的決定權*日本《裁判員法》第2條、第3條。,除非法院認為無法采用裁判員審理的形式,或者采用裁判員審理會對相關人員造成危害。而在韓國,在刑事案件中采取民眾參與的陪審形式,是對當事人公正裁判權的特殊保障。是否需要這一保障,取決于當事人的意志,當事人對是否采取陪審形式審理具有絕對的決定權。這一點,韓國的做法與日本截然相反。而在中國,是否采取人民陪審員審判形式取決于人民法院和當事人兩方。但雙方權限的界限在何處,實際上并不明確。由于當事人的申請最終取決于人民法院的批準,從這個角度說,人民法院對是否采取人民陪審員參與審理具有最終決定權。
第二,在民眾的選任方式上,在當前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前,中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要求人民陪審員除了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資質外,還要具備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并具備一定的法律知識。人民陪審員需要經過基層法院院長提名,由地方權力機構任命,實行任期制。各個基層人民法院實行人民陪審員名單制,每個案件的人民陪審員是法院從該名單中選任的,因此,對法官裁判的個案而言,可以遴選的范圍是確定的。而日本采取的是從所在區域選民名單中隨機抽取的方式,擔當案件結束,其參與司法的任務也就完成。韓國的制度與日本大體相同,采取的也是案件擔當制,民眾參與的規模與人數根據案件情況隨機選任。日本、韓國的檢控方、辯護方參與民眾的選任過程,通過提問和觀察,排除那些可能對己方不利的候選人,控辯雙方有權對若干名候選人無條件加以排除,這些做法都反映了英美陪審制度的特點。從民眾參與范圍來看,每個案件可能選任的民眾范圍極廣,具有不確定性。
第三,在司法裁判中民眾與職業法官的功能分擔方面,韓國的陪審員負責案件事實的認定,在庭審結構中獨立于主審法官;日本的民眾與職業法官更多的是一種參與和合作的關系,共同決定案件事實和法律適用;在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之前,中國的做法與日本的制度有較多的相似性。
日本在審判組織中吸收裁判員參加,確立了一種“參與—制衡”的關系模式。具體來說,六名民眾在參與審判時與職業法官并排而坐,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裁判員參與評議,必須發言陳述意見,在這一過程中,如擔任審判長的法官認為有必要,應該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裁判員解釋相關法律和訴訟程序,使裁判員能夠更好地履行職權。案件評議不是采取簡單的多數表決原則,最終的裁決意見必須包含和體現法官的意見。這樣的制度設計凸顯了法官對裁判員的制衡,保障了裁判員的決議不脫離司法理性的軌道。在案件審判過程中,對法律的解釋屬于法官的專屬特權。
韓國則采取了與日本完全不同的做法,盡管在選任民眾的方式上兩者高度相似。韓國的陪審員在法庭上獨立于法官,只承擔事實認定工作,不負責對犯罪人量刑。因此,韓國的做法相當于“分工—制衡”的關系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陪審員在法庭上的位置面對當事人和證人,可以對案件事實做出更好的觀察和判斷;但陪審員不能直接對證人進行提問,必須通過法官來向證人發問。主導庭審進展的是法官,而不是陪審員。盡管在法庭上,法官對陪審員負有說明義務,但陪審員做出決議是獨立的。不過,這種獨立做出的決議最終是否對案件裁決結果產生拘束力,又要取決于法官的審查和判斷。在不采納陪審員決議的時候,法官必須開示理由。只有理性的陪審團決議才能夠被法官所采納,成為裁判的最終依據。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發現,在人民陪審員與法官的作用方面,中國的做法與日本的裁判員制度相似,屬于大陸法系的參審模式。但在合議庭組成方面,現行中國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人民陪審員與法官的構成,合議庭包括一名還是兩名人民陪審員往往取決于法院的決定,當事人無法參與選任人民陪審員的決定過程,這一點有別于日本、韓國的制度。從總體上看,人民陪審員與法官在參與司法過程中,其相互關系屬于一種“參與—協作”模式。人民陪審員更多地被看作法院的組成成員來發揮作用。
三、 比較法視野下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規劃了司法改革的三個重要任務:“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是“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的重要內容,涉及裁判權行使問題,并且與是否能夠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密切相關。因此,需要從理論上厘清人民陪審員制度與其他各項制度的關系,處理好審判獨立、法律職業化以及民眾參與司法裁判之間的關系。推進司法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確保個案的公平正義。實現個案的公平正義,需要建構一個能夠讓司法裁判者獨立、公平、公正地進行審理和判決的制度環境,需要完善相關制度保障措施,讓人民群眾能夠實質性地參與司法裁判過程,并且通過參與提升司法裁判的質量,實現司法裁判的公平、正義。
“國民參與司法必須在不損害審判公平且公正的前提下進行”[18]122,司法改革的民主化固然是當今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發展趨勢,但維護司法正義、保證案件審判質量更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永恒目標。司法民主化改革應該加強而不是削弱司法裁判的質量。任何司法民主化的措施都應該尊重司法規律的民主化,即法律職業與參與民眾合理平衡的民主化,程序保障的民主化。因此,在推進司法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從比較的視野出發,厘清民眾參與司法裁判與司法裁判職業化、專業化改革的關系,建構更加科學的人民陪審員制度。
1.優先確立司法的職業化改革目標
“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重頭戲是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19],“這是因為我國司法欠獨立的實踐對司法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權威性造成了極大的損害”[20]。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著眼點是尊重司法規律,強化司法裁判活動的專業化,推動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人員的職業化建設,增強職業化的主審法官在司法裁判的主導地位,使其成為司法裁判的責任主體。這是由司法“等待合法的起訴,在適當的程序下對有關法律解釋、適用的爭端作出終局性裁決”[21]339的本質屬性決定的。
“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建立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真正行使裁判職權,同時也切實承擔審理和裁判的責任,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追究,”[22]這是本次改革提出的具體任務。解釋法律、掌控程序、認定證據、做出實體決定等,都是高度專業的職業活動,只有受過專業訓練、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身份得到保障的職業法官才能得心應手,才能制作出有說理性的裁判文書,才能真正承擔相關責任。由于法官獨立行使職權的制度建設不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在實踐中出現了異化的現象,特別是在“案多人少”的形勢下,人民陪審員實際上發揮了補充法院人手不足的功能,變相地承擔了部分法院工作人員的職責,“普通民眾志愿性地廣泛參與,演變為專職化和依靠司法資源支撐的法院雇員;其主要功能從參審轉變為法院輔助功能(書記員、特邀調解員、助理法官等);實現司法民主和公正方面的功能,讓位于減輕法院壓力(包括在組成合議庭和調解方面人力或能力的不足)的功利的作用”[23]。因此,要解決司法能力和司法資源不足的問題,不能再依靠擴大人民陪審員的規模、增加人民陪審員的數量的方法,而應該從完善司法制度、提高法律職業能力、強化法律職業化的角度出發提出良策。“民眾參與司法等以司法民主理念為基礎的制度,是與法官的職業化和獨立相輔相成的。司法人員的職業化和獨立程度越高,民眾的參與越具有獨特的功能和價值。”[23]當前司法改革開展的許多舉措,如強調司法的獨立性(擺脫司法的地方化)、專業化(法律文書要說理),都切中了當前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問題要害,表明了司法改革的正確方向。
《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和承擔功能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路:將人民陪審員的任職年齡從23歲提高到28歲,旨在吸收具有社會閱歷的人士擔任人民陪審員;降低了人民陪審員的學歷條件,一般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學歷即可擔任,且在農村地區和貧困偏遠地區,公道正派、德高望重者不受學歷要求限制,從而擴大了人民陪審員的參審范圍;在人民陪審員功能方面,“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第三條。,充分發揮了人民陪審員富有社會閱歷、了解社情民意的優勢,提高了人民法院裁判的社會認可度。
改革前相比,新的試點方案提高了縮小了人民陪審員在合議庭中的職能。但是,對“參與”的范圍和程度則指代不明,在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的前提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決定案件事實,以及在司法裁判中發揮司法民主的作用,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特別是在中國的庭審模式下,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問題難以區分,必然會帶來合議庭的法官和參與審判的人民陪審員功能模糊、責任不清的問題。
而且,從世界司法民主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為了防止民眾參與司法裁判中出現事實認定的謬誤,在民眾的選任、證據交換、庭審中法官與民眾的功能分擔、庭審中發問的規則,甚至在庭審中參與裁判的民眾與輿論的隔絕和人身保護等措施上,都有明確和精細的規定。也就是說,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是在司法專業化和職業化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對專業化、精細化司法的糾偏。而現行的人民陪審員改革方案與強化司法專業化、職業化改革并行。在法律職業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這種改革方式無論是制度基礎、程序保障還是實際效果,都存在一定的瑕疵,在一定程度上與司法裁判的專業化、職業化改革趨勢存在矛盾。如果沒有建立合理、科學的程序規則,單純擴大人民陪審員參審的范圍,會導致其應用范圍過于廣泛,參與程度過于深入。司法權的真正主體是職業法官,因此,建立能夠保障法官獨立、公正地履行裁判職能的制度環境,應該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首要目標,要避免出現因強調擴大人民陪審員審理范圍而弱化專業法官司法裁判作用的現象。
2.拓展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的形式
人民群眾參與司法裁判,有權對案件事實、法律適用做出最后決定,是人民群眾享有的最大程度的司法民主權,但絕不是唯一的形式。隨著人民群眾對司法民主、司法公開和司法公正的新要求,“體現司法民主的方式已經主要不是通過陪審方式來實現,而是通過諸如審判公開、輿論監督、由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職業法官的任免、改革和完善審判程序以使訴訟主體等的訴訟權利得到有效保障等方式”[24]。在司法訴訟程序中,在不同的環節設計不同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一方面可以彌補職業法官視野狹窄、脫離社會生活的缺陷;另一方面,可以積極發揮民眾在認定和判斷案件事實方面的作用,特別是在某些專門領域的訴訟案件中,由專家擔任人民陪審員可以起到幫助法官準確認定事實的作用。
各國的民眾司法參與形式是多樣化的,可以在不同的訴訟階段采取多樣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例如,為了防止檢察官在審查起訴環節中的擅斷,日本建立了由民眾組成的“檢察審查會”,可以彈劾檢察官做出的不合理的起訴或不起訴決定;為了在知識產權訴訟中發揮某些在特殊專業領域具有專業特長的民眾的優勢,有些國家的知識產權法院建立了“專家委員”制度,以幫助法院更好地查明知識產權糾紛的事實爭點;在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日本法院任命的調解委員參與案件審理的某些過程,在原告、被告之間斡旋,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提出解決糾紛方案,這也是一種重要的民眾參與司法的形式。
司法審判實踐中,我國人民陪審員發揮的重要作用是提供專業知識和參與糾紛調解。考慮到司法改革的專業化、職業化方向,對廣泛地賦予人民群眾司法裁決權要采取審慎的態度,防止不恰當地夸大民眾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增加其負擔和責任。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否定和限制民眾參與司法,相反,應該進行制度改革,加強頂層設計,拓展多樣化的人民群眾參與司法的合理形式,建立包括專家委員、司法調解委員制度等更加科學、合理的民眾參與司法形式,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優勢,通過民眾參與提高審判質量,使民眾能夠量力而行,科學參與司法,提升參與司法裁判的能力和水平。
3.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視角
在《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出臺之前,就有學者指出,“人民陪審制目前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實亡,即使存在,也常常作為減少職業法官占用從而提高法院工作效率的一種辦法,陪審員并不能很好發揮影響司法的實效性作用”[25]。這些問題即使在《決定》實施以后,也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人民陪審員制度在設計之初就顯示出很多的矛盾和不確定性,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人民陪審員的來源、學歷、選任方式、任期、適用范圍等的規定,顯示出非平民化或精英化追求;而參審方式和范圍等方面的模糊設計則使其很難應用于重大刑事案件。”[23]對此,《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也提出了“降低擔任人民陪審員的條件”,“探索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等舉措*《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第二部分第一項、第五項。。但是,讓這些舉措真正落地發揮作用,還需要從認識上、制度上轉換視角,弱化人民參與司法的政治性意義,強化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司法功能。“司法既是政治的組成部分,但整個司法的歷史實際上也是司法不斷擺脫、獨立于政治的歷史”;“司法能夠從政治中剝離出來就在于其自身所持有的基本規律。這是司法能夠作為糾紛解決手段的重要原因”,因此,“尊重司法規律應當成為衡平政治與司法關系的一項標準”[20],必須樹立人民陪審員制度建構和功能發揮應該主要服務于提高司法裁判公平、公正的目標的理念。
其次,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應該通盤考慮,要合理設定民眾選任的方式方法、適用范圍、針對民眾的特殊訴訟程序、參與民眾的權利和義務;也要合理考慮相關主體與參與司法裁判的民眾之間的關系,例如人民陪審員與法官的關系,人民陪審員與案件當事人的關系,人民陪審員權利與義務的關系,人民陪審員與工作單位(雇主)的關系等;特別是要尊重司法規律,科學合理地確定人民陪審員在庭審中的功能。通過對各國民眾參與司法改革的比較研究可以發現,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涉及法律職業化和司法民主化的復雜理論關系,制度改革往往需要統合考慮。當前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與大力推動司法職業化目標是同時推進的,因此,僅僅依靠降低選任條件、擴充陪審員規模、擴大適用范圍以及由民眾專事事實認定,是無法解決實踐中出現的“人民陪審員職業化”以及“陪而不審”等問題的。2015年4月以來,盡管人民陪審員制度試點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出現了因理論準備不足而致使改革目標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申請延長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期限。在延期理由說明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了試點存在的三個問題:一是缺乏事實審和法律審區分的有效機制;二是全面實行隨機抽選,難度較大且不盡合理;三是大合議庭陪審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參見沈德詠《對〈關于延長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試點期限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04/27/content_2020928.htm, 2017年4月27日。。這些問題的發現和解決固然可以進一步通過試點和實踐來找到適合的道路,但實際上,這些問題是各國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通過系統的比較法研究,找到各國制度改革的共性,分析差異性,從司法改革的整體方向上來考慮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功能,厘清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理論關系,可以為建立科學合理的人民陪審員制度提供理論參考。
最后,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做法既不專屬英美法系,也不為大陸成文法國家所獨有。各國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設計了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模式。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反映了當今世界司法制度改革的總體趨向,因此,對各國建立和實施民眾參與司法裁判的特征和規律進行認真梳理和總結,有利于我國吸收借鑒世界法治文明的發展成果,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為建立適合中國需要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貢獻智識。從比較法的角度分析世界各國,特別是鄰國日本、韓國正在實行的民眾參與司法裁判制度,對理性分析當前中國司法改革的任務、目標、推進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鑒和參考作用。
[參考文獻]
[1] Matthew W.J.,″Prime Time for Japan to Take Another Step Forward in Lay Participation: Exploring Expansion to Civil Trials,″ http://dx.doi.org/10.2139/ssrn.2063269, 2016-09-09.
[2] [日]田口守一: 「刑事司法改革の新局面――刑事手続きと市民との新しい関係をめざして」,須網隆夫ほか: 『司法改革と市民の視點』,東京:成文堂,2001年,第234頁。[Taguchi Morikazu,″A New Situation of the Criminal Judicial Refo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and the Citizens,″ in Takao Suami,JudicialReform&thePerspectiveofCitizens, Tokyo: Seibundou, 2001, p.234.]
[3] 段曉彥、俞榮根: 《“陪審”一詞的西來與中譯》,《法學家》2010年第1期,第40-53頁。[Duan Xiaoyan & Yu Ronggen,″Jury: The Word from the West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TheJurise, No.1(2010), pp.40-53.]
[4] 云鳳飛: 《試論英國Jury制度的翻譯問題》,《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502-505頁。[Yun Fengfei,″Translation Problems of the Jury System in Britain,″Journalof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5(2012), pp.502-505.] [5] 孫長永: 《普通民眾參與刑事審判的理念和路徑》,見施鵬鵬編: 《陪審制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頁。[Sun Changyong,″The Idea and Path of Ordinary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Criminal Trial,″ in Sun Pengpeng (ed.),TheJurySyste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7.] [6]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ed.),TheCompleteWorksofSunYat-sen:Vol.1,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7] 董必武: 《正確區分兩類矛盾,做好審判工作》,見《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Dong Biwu,″Distinguishing Two Types of Contradictions Correctly to Do a Good Job in Trials,″ inCollectedPoliticalandLegalWorksofDongBiwu, Beijing: Law Press·China, 1986.]
[8] 熊秋紅: 《司法公正與公民的參與》,《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第47-64頁。[Xiong Qiuhong,″Judicial Justi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ChineseJournalofLaw, No.4(1999), pp.47-64.]
[9] 謝冬慧: 《中國古代會審制度考析》,《政法論壇》2010年第4期,第86-97頁。[Xie Donghui,″The Ancient Chinese Joint Hearing System,″TribuneofPoliticalScienceandLaw, No.4(2010), pp.86-97.]
[10] Thaman S.C.,″Europe’s New Jury Systems: The Case of Spain and Russia,″Law&ContemporaryProblems, Vol.62, No.2(1999), pp.233-259.
[11] [日]田口守一: 《日本的陪審制——裁判員制度》,丁相順譯,《法律適用》2005年第4期,第91-94頁。[Taguchi Morikazu,″The Jury System of Japan: The Referee System,″ trans. by Ding Xiangshun,JournalofLawApplication, No.4(2005), pp.91-94.]
[12] 丁相順: 《日本“裁判員”制度建立的背景、過程及其特征》,《法學家》2007年第3期,第140-146頁。[Ding Xiangshun,″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feree′ System of Japan,″TheJurist, No.3(2007), pp.140-146.]
[13] 吳景欽: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日本裁判員制度為例》,臺北:麗文文化事業公司,2010年。[Wu Jingqin,CitizensParticipatingintheCriminalJusticeSystem:TakingtheJapaneseRefereeSystemforExample, Taipei: Liwen Publishing Group, 2010.] [14] Lee J.H.,″Getting Citizens Involved: Civil Participation in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Korea,″EastAsiaLawReview, Vol.4, No.2(2009), p.177.
[15] [日]松尾浩也: 《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卷),丁相順譯,金光旭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Matsuo Hiroya,CriminalProcedureLawofJapan:Vol.1, trans. by Ding Xiangshun, proof. by Kim Guangxu,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 季衛東: 《日本司法改革:民眾參審的得失》,《南方周末》2009年8月19日,第E31版。[Ji Weidong,″Judicial Reform in Japan: The Gain and Loss of the Assessor System,″SouthernWeekly, 2009-08-19, p.E31.]
[17] Munger F.,″Constitutional Reform,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ailand,″CornellInternationalLawJournal, Vol.40, No.2(2007), pp.455-476.
[18] 洪英: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憲政分析——以參政權的權利性視角之分析為主》,見許崇德、韓大元主編: 《中國憲法年刊2009》,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18-138頁。[Hong Ying,″Constitutionalism of the Referee System of Japan: Focusing on Analysing the Political Right in the Rights Perspective,″ in Xu Chongde & Han Dayuan(eds.),YearbookoftheChineseConstitution, 2010, Beijing: Law Press·China, 2010, pp.118-138.]
[19] 齊文遠: 《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路徑思考——兼論人民陪審制向何處去》,《現代法學》2014年第2期,第20-29頁。[Qi Wenyuan,″The Way to Improve the Credibility of Criminal Judicature: And Is the Direction of the People Assessor System,″ModernLawScience, No.2(2014), pp.20-29.]
[20] 陳衛東: 《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研究》,《中國法學》2014年第2期,第20-49頁。[Chen Weidong,″Judicial Organs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and Powers Independently According to Law,″ChinaLegalScience, No.2(2014), pp.20-49.]
[21] [日]高橋和之: 『立憲主義と日本國憲法』,東京:有斐閣,2006年。[Takahashi Kazuyuki,ConstitutionalismandtheJapaneseConstitution, Tokyo: Yuuhikaku, 2006.]
[22] 江必新: 《深化審判體制與機制改革》,《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4年第1期,第34-38頁。[Jiang Bixin,″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Mechanism,″ChineseCadresTribune, No.1(2014), pp.34-38.]
[23] 范愉: 《人民陪審員制度與民眾的司法參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50-55頁。[Fan Yu,″The System of People’s Assessors and the Judi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People,″Journalof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sEdition), No.1(2014), pp.50-55.]
[24] 王敏遠: 《中國陪審制度及其完善》,《法學研究》1999年第4期,第23-46頁。[Wang Minyuan,″The Chinese Jury System and Its Perfection,″ChineseJournalofLaw, No.4(1999), pp.23-46.]
[25] 龍宗智: 《論我國陪審制度模式的選擇》,《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第118-125頁。[Long Zhongzhi,″The Choice of Jury System in China,″AdvancedEngineeringScience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 No.5(2001), pp.118-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