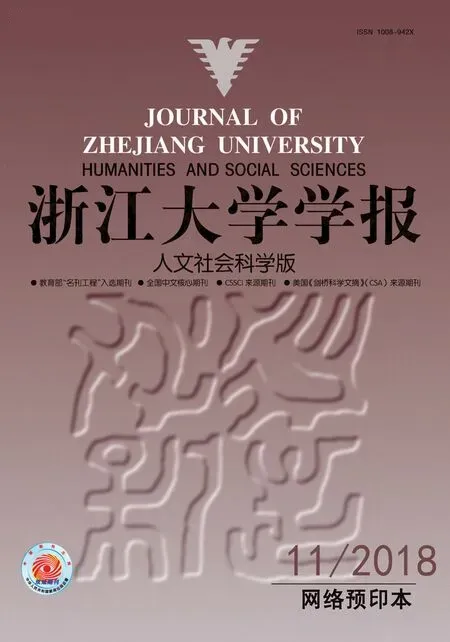清代學者學術(shù)信息獲取方式初探
——以乾嘉時期為中心
陳東輝
(浙江大學 漢語史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清代學者在考據(jù)學等領(lǐng)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少方面堪稱“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筆者長期從事清代學術(shù)史研究,閱讀了大量清人文集、筆記、日記、年譜等,發(fā)現(xiàn)不少清代學者消息靈通,往往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取相關(guān)學術(shù)信息,“閉門造車”的情況并不是很多。本文所言之學術(shù)信息主要是指新的學術(shù)信息,諸如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在做什么研究,刊行了哪些新的論著,同時也包括相關(guān)學者以前尚未寓目之典籍(尤其是珍本秘冊)。在那個通信、交通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的清代乾嘉時期,學者們是通過何種方式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當屬一個非常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此前的論著很少涉及這一問題,更未見關(guān)于此問題的專文。當然,一些論著的某些部分與此問題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如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Elman)的《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周紹明(Joseph P.McDermott)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又如:王華寶的《段玉裁年譜長編》、王章濤的《阮元年譜》和《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涉及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等與同時代學者的交游;陳居淵的《清人書札與乾嘉學術(shù)——從〈昭代經(jīng)師手簡〉二種談起》,著重強調(diào)了函札對學術(shù)交流的重要作用;羅檢秋的《士人交游與文獻傳播》涉及清代學者借閱圖書之若干情況①[美]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趙剛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葛兆光《清代學術(shù)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對艾爾曼的觀點有所闡發(fā),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年第 1期,后收入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xù)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143180頁;[美]周紹明《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何朝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王華寶《段玉裁年譜長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版;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揚州)廣陵書社 2006年版;陳居淵《清人書札與乾嘉學術(shù)——從〈昭代經(jīng)師手簡〉二種談起》,載《漢學研究》(臺北)2007年第 25卷第 2期,第 265294頁;羅檢秋《士人交游與文獻傳播》,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第913頁。。不過上述論著均非專門研究此問題,只是有所涉及,缺乏系統(tǒng)性。筆者經(jīng)過長時間的考察,認為清代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方式大體上可以歸納為以下五種:一是通過當面交流獲取;二是通過往來函札獲取;三是通過撰寫序跋獲取;四是通過購買、借閱圖書獲取;五是通過相互贈書獲取。以下詳論之。
一、當面交流
當面交流最為直接,尤其在沒有電話更沒有網(wǎng)絡(luò)的清代,其作用是其他交流方式無法取代的。大量的學術(shù)信息正是在當面討論相關(guān)問題乃至閑聊中獲取的。
當一些學者長時間在同一個城市時,當面交流通常較多。如道光十四年(1834)春夏,俞正燮在嚴州(今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鎮(zhèn))期間,曾多次與許瀚①許瀚從道光十一年(1831)開始在杭州學署校文,歷時三年。一同拜訪當時在嚴州任建德教諭的嚴可均。俞正燮在《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中提到:“道光甲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嘆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司馬出所攜金石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大笑。”[1]卷一二,487又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朱筠由安徽學政調(diào)任翰林院編修,此后在北京的數(shù)年乃其一生中交游最廣的時期。當時朱筠與紀昀、翁方綱、錢大昕、程晉芳、任大椿、戴震、姚鼐、王昶、邵晉涵、周永年、蔣雍植、章學誠、蔡嘉等著名學者經(jīng)常見面并交流[2]。另據(jù)翁方綱《復(fù)初齋文集》卷三一《跋朱性甫珊瑚木難手稿》記載,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初八,羅聘、桂馥、吳錫麟、趙懷玉、馮敏昌諸學者在北京翁方綱的寶蘇室一同觀看明代朱理存(字性甫)的《珊瑚木難》手稿[3]卷三一,647。不過當時學者們在茶館、酒樓的聚會很少,而是大多在某一位學者家中,并且總體上聚會比較少。因此聚會并非乾嘉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這一點與清末和民國時期不同。
當學者不在同一城市,專程赴外地拜訪同人大多是距離比較近的。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段玉裁自金壇至常州,以所著《古文尚書撰異》囑臧庸為之校讎;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臧庸從武進到蘇州,與錢大昕、段玉裁、王昶等相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當時僑居蘇州的段玉裁到了杭州,與丁杰相識。
因清代的交通與今天相比顯得十分不便,故距離較遠的異地專程拜訪的事例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情況是路過某地時順便拜訪。如乾隆十九年(1754),全祖望赴揚州養(yǎng)病,途經(jīng)杭州時,與故友趙昱之子趙一清共同研討《水經(jīng)注》。
另外,由于不少清代學者同時是官員,在赴任、離任途中,他們往往有交流。如阮元作為清代中后期號稱“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元老”的封疆大吏,曾任山東學政、浙江學政、兵部侍郎、禮部侍郎、戶部侍郎、工部侍郎、浙江巡撫、江西巡撫、河南巡撫、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內(nèi)閣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等,長期在全國各地為官。在無數(shù)次赴任、離任途中,常常與師友、門生等晤面、交流。在這一過程中,雙方都能夠獲取一些最新的學術(shù)信息。
又如,嘉慶元年(1796),桂馥獲選云南永平知縣,是年七月啟程遠赴滇南上任。是年八月,桂馥路過天津,與翁方綱等會面。嘉慶二年(1797),桂馥路過杭州,與丁杰相見時,丁杰還將梁玉繩的《漢書人表考》贈予丁杰。由于路途遙遠,加上一路停頓,直至嘉慶二年(1797)四月,桂馥方才到達云南②參見張毅巍《桂馥年譜》,哈爾濱師范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69-72頁。。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當時學者當面交流之不易。再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段玉裁由四川巫山縣令致仕,返回故鄉(xiāng)金壇途中路過南京,到鐘山書院拜訪了錢大昕。另外,道光元年(1821)十月,王引之赴杭州主持浙江鄉(xiāng)試結(jié)束之后,返回京城途中路過揚州,與顧廣圻見面,并將新刻的《讀書雜志·淮南內(nèi)篇》贈送給顧氏。
有時路過某地,由于時間有限等原因,學者不一定前往友人寓所晤面,而是采用致函的方式①因為同在一地,距離近,所以很快就可以寄到。,邀對方到其所乘之舟車中相見。如乾隆六十年(1795)十月末,阮元在赴任浙江學政途中經(jīng)過蘇州,因獲悉段玉裁居所“距城頗遠,本當親詣高齋,奈皇華期迫,不能久延”,故致函段玉裁,并且附其近刻數(shù)篇,又碑刻一種,“謹令縣中人備輿奉迓,至弟舟一談。大著《說文讀》及諸《漢讀》、《詩、書小學》稿本,務(wù)必攜來”[4]743。
學者相見時所獲取的信息并不僅僅限于對方的學術(shù)動態(tài),往往還會涉及他人,相互交流自己所知曉的他人的學術(shù)動態(tài),品評他人之作。如陳鴻森《〈錢大昕年譜〉別記》乾隆五十八年(1793)條提到:“鈕樹玉來訪。先生與論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得失。”[5]931
書院也是清代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重要場所。如嘉慶年間阮元在杭州創(chuàng)辦的詁經(jīng)精舍,不僅是一所教育機構(gòu),而且也是學術(shù)研究的重要基地。精舍創(chuàng)建初期,除了阮元和主講王昶、孫星衍之外,尚有講學之士等教學人員。據(jù)孫星衍《詁經(jīng)精舍題名碑記》記載,當時汪家禧、陳鴻壽、陳文述、錢林、胡敬、孫同元、陸堯春、王述曾、吳文健、嚴杰、周誥、查揆、李富孫、孫鳳起、吳東發(fā)、朱為弼、周中孚、嚴元照、徐養(yǎng)原、何蘭汀、周師濂、汪繼培、徐鯤、周治平、洪頤煊、洪震煊、金鶚、吳杰等著名學者都曾在精舍講學,共計 92人[6]卷下,545-547。另外,蘇州紫陽書院也匯集了一大批學者,如“吳中七子”錢大昕、曹仁虎、王昶、趙文哲、王鳴盛、吳泰來、黃文蓮就曾在書院一同肄業(yè),時在蘇州的惠棟作為長輩,對錢大昕等也給予了指導(dǎo)。書院為學者之間的學術(shù)交流提供了重要平臺。
游幕同樣有助于學術(shù)信息的獲取。尚小明在《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shù)》中論述了幕府賓主間學術(shù)上的相互影響、幕府內(nèi)的學術(shù)爭論、游幕與學術(shù)傳播等問題。作者認為:“在幕府內(nèi),最普遍的學術(shù)交流方式是就某些學術(shù)問題或某一方面的學術(shù)問題進行討論,交換研究心得、研究信息或研究成果。這方面的例子很多。”[7]293林存陽的《乾嘉四大幕府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以盧見曾、朱筠、畢沅、阮元等四個具有代表性的幕府為研究對象,從中可以看出幕府乃學術(shù)交流之重要場所。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朱筠擔任安徽學政,“一時人士會集最盛,如張布衣鳳翔、王水部念孫、邵編修晉涵、章進士學誠、吳孝廉蘭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炘、瞿上舍華,與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jīng)中,亦時至”[8]289-290。另外,凌廷堪曾在謝啟昆幕府中與盧文弨一見如故。
還有,清廷的修書活動,如《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明史》《續(xù)通典》《續(xù)通志》等大型圖書的編纂,以及各省的方志修纂,均匯聚了一批學者,并且編纂時間往往較長。如負責《續(xù)通典》《續(xù)通志》《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等編纂的三通館,就集中了錢大昕、彭元瑞、孫星衍、邵晉涵、王昶、紀昀、齊召南、陳昌齊等著名學者。學者們可以由此獲取不少學術(shù)信息。
此外,參加科舉考試也是清代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好機會。如阮元與郝懿行,錢大昕與邵晉涵、李文藻就相識于科場。乾隆三十一年(1766)三月,王念孫赴京師參加會試,會試前后,王念孫拜謁朱筠,得與朱筠弟子任大椿多有交往。復(fù)獲見江永《古韻標準》,始知顧炎武所分十部尤有罅漏[9]15。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學者之間的初次見面大多在京師北京,后來的當面交流也大多在北京。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章學誠與戴震初見于北京休寧會館;乾隆二十八年(1763),段玉裁與戴震在京師相識;乾隆三十四年(1769),段玉裁第三次入京參加會試,與戴震確定師生關(guān)系。乾隆五十四年(1789),段玉裁與王念孫在京城首次晤面。此外,戴震與秦蕙田、錢大昕、紀昀、王鳴盛、阮元、王昶、朱筠,錢大昕與紀昀、朱筠、盧文弨、畢沅、趙翼、程晉芳、翁方綱、陸錫熊,阮元與王念孫、桂馥、邵晉涵、任大椿,陳奐與王念孫、王引之、郝懿行,凌廷堪與孔廣森、武憶,王念孫與程瑤田,段玉裁與陳鳣等,最初也都是在北京相識的。京城的初次晤面往往對學者以后的發(fā)展乃至終身學術(shù)方向的選擇具有重大影響。
王汝豐主編的《清代宣南人物事略初編》收錄了一百多位曾經(jīng)在清代“宣南”①當時京城宣武門以南一帶之泛稱,大體上屬于原北京市宣武區(qū)的管轄范圍。居住的知名人士,包括顧炎武、趙吉士、朱彝尊、徐乾學、閻若璩、陳廷敬、汪懋麟、萬斯同、李光地、查慎行、黃叔琳、齊召南、盧文弨、程晉芳、王鳴盛、戴震、紀昀、王昶、錢大昕、朱筠、畢沅、翁方綱、陸錫熊、王念孫、洪亮吉、黃景仁、凌廷堪、阮元、王引之、包世臣、陶澍、徐松、錢儀吉、陳奐、龔自珍、何紹基等[10]26-359,其中有不少是同一時期住在此地,堪稱大家云集。學者生活在同一區(qū)域,交流自然多了。
此外,當時的一些中心城市如蘇州、杭州、揚州等,也成為清代學者之間初次見面的地點。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段玉裁因避禍僑居蘇州,在此結(jié)識黃丕烈、顧廣圻、王鳴盛等,并因錢大昕與藏書家周錫瓚相識[11]222-223。據(jù)劉盼遂的《段玉裁先生年譜》,嘉慶二年(1797),程瑤田到了蘇州,與僑居于此的段玉裁初次相見,“登其堂,促席論難,匆遽之間,雖未能罄其底蘊,然偶舉一端,必令人心開目明”[12]462。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張文虎校書于杭州文瀾閣,得識胡培翚,后經(jīng)胡氏介紹,在八月十七日與陳奐相識于杭州汪氏水北樓[13]393。阮元與凌廷堪、汪中等,江藩與凌廷堪的初晤之地點在揚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戴震離開北京赴揚州,入盧見曾幕府,在此與惠棟相識并深入交流。這次晤面對戴氏以后的學術(shù)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至今有不少論著認為,蘇州、徽州、揚州、常州乃乾嘉時期之學術(shù)中心,這固然沒有問題,但當時最重要的學術(shù)中心應(yīng)該是相關(guān)論著沒有提及的北京。因為所謂學術(shù)中心,應(yīng)該是學術(shù)交流最為頻繁、學術(shù)信息最為集中之地區(qū),具備影響全國的實力,就此而言,北京無疑居于首位。并且,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集中于京城,有力地促進了南北學術(shù)的互動和交流,從而進一步促進了清代學術(shù)的發(fā)展。這一點是在其他城市難以做到的。
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中提出了“江南學術(shù)共同體”這一概念。學術(shù)信息獲取是學術(shù)共同體得以逐漸形成和鞏固,并且得以持續(xù)存在的重要保證。可以說,如果沒有學術(shù)信息的及時、不斷獲取,學術(shù)共同體將是支離破碎的,甚至不復(fù)存在。學術(shù)信息的交流堪稱維系學術(shù)共同體之紐帶。
筆者注意到,學術(shù)共同體的地理分布并不僅僅局限于江南,北京也是清代學術(shù)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京城的學者無論居住時間長短,大多來自江南地區(qū),京城、江南二地的學者學脈相通,互動頻繁,遙相呼應(yīng)。因此,北京、江南堪稱清代學術(shù)共同體的兩大核心地區(qū),而江南地區(qū)又以蘇州、揚州、杭州、常州等城市為支撐點,點面結(jié)合,以點帶面。這一學術(shù)共同體的范圍不宜使用半徑來表述,而是以核心地區(qū)為基礎(chǔ),同時其影響力擴散到周邊乃至邊遠地區(qū),從而形成疏密不一的學術(shù)網(wǎng)絡(luò)。
當面交流尤其是多位學者集中一處交流時,信息量往往較大,內(nèi)容也比較豐富。這種交流是直接的、面對面的,相關(guān)學者所獲取的學術(shù)信息數(shù)量總體上應(yīng)該超過函札,從而對交流雙方的學術(shù)研究更容易產(chǎn)生影響。一些初步的學術(shù)見解通過當面切磋、碰撞而逐漸趨于成熟、完善,有助于學術(shù)共同體的形成。學者晤面時的相互鼓勵、幫助、啟發(fā)、質(zhì)疑以及相互交換資料等皆是清代學術(shù)發(fā)展的催化劑。
通過以上論述,筆者認為以前的某些觀點存在偏頗之處,可以補充、修正。如梁啟超曾曰: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講學,又非如今之歐美有種種學會學校為聚集講習之所,則其交換知識之機會,自不免缺乏。其賴以補之者,則函札也。后輩之謁先輩,率以問學書為贄。——有著述者則媵以著述。——先輩視其可教者,必報書,釋其疑滯而獎進之。平輩亦然。每得一義,輒馳書其共學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嘗不盡其詞。凡著一書成,必經(jīng)摯友數(shù)輩嚴勘得失,乃以問世,則其勘也皆以函札。此類函札,皆精心結(jié)撰,其實即著述也。此種風氣,他時代亦間有之,而清為獨盛。[14]64
梁氏充分關(guān)注到函札對清代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重要作用,這當然是十分正確的。不過這一論述不夠全面,除了函札之外,清代學者之當面交流不容忽視。
美國學者艾爾曼指出:“18世紀,考據(jù)學者接受了官方贊助,擔任官員的幕賓,不論這些官員是在何時何地聘用他們。他們嚴肅認真地承擔起編著經(jīng)注、史書、方志的任務(wù),除此之外,就在書院任教。這種學術(shù)發(fā)展模式持續(xù)到 19世紀,直到太平天國起義突然中斷學術(shù)事業(yè)發(fā)展時,才告結(jié)束……反之,學者到全國各地漫游尋找贊助時,必須具備完成其學術(shù)研究必需的專業(yè)知識,也必須隨時準備校勘經(jīng)籍,收集地方史志材料,校勘經(jīng)史典籍中的錯訛之處。而這種學術(shù)體制也為考據(jù)學者創(chuàng)造了相互交流、查閱善本文獻、參預(yù)重要課題的機會。”[15]79艾爾曼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他所說的這種學術(shù)體制應(yīng)該并非當時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之主要途徑。
二、往來函札
清代學者之間的往來函札大多不是一般的問候、閑聊,而往往帶有較強的學術(shù)性。如段玉裁與王念孫之間有大量的函札往來。乾隆五十四年(1785)段玉裁與王念孫在京城相識之后,主要通過函札交流。胡楚生的《段玉裁與王念孫之交誼及論學》對此有較為充分的探討[16]。
段玉裁《與劉端臨第十三書》曰:“訓(xùn)詁之學,都門無有好于王伯申者。陳仲魚新刊《論語古訓(xùn)》已成,弟之《說文》,亦寫刻本二卷,囑江艮庭篆書,剞劂之工,大約動于明冬。顧抱沖刻宋本《烈女傳》,黃蕘圃刻宋明道二年《國語》未成,明道本影抄在黃處,與鄉(xiāng)時臨本不同,臨本失之疏略也……”[12]401這封函札字數(shù)雖然不多,但提供的學術(shù)信息十分豐富。
道光三年(1823)三月二十五日,王念孫的《答江晉三書三》內(nèi)容同樣很充實。在函中,王念孫對江氏在來信中所提到的問題一一作答,并專門就四聲問題闡述了己見,同時還提到:“《廣雅疏證》一書,成于嘉慶元年,其中遺漏者十之一二,錯誤者亦百之一二,書已付梓,不能追改,今取一部寄呈,唯足下糾而正之。”[17]89
乾隆五十九年(1794),阮元致函孫星衍,就孫氏《問字堂集》提出若干商榷意見[18]9-12。嘉慶十四年(1809)十一月十三日,郝懿行致函王引之,其中有云:“某近為《爾雅義疏》,《釋詁》一篇,尚未了畢。”[19]卷一,5238嘉慶十六年(1811)五月,臧庸致函王念孫,就《小學鉤沉》相關(guān)之三個問題請教王氏,王念孫隨即復(fù)函,闡明自己的觀點。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王引之致陳奐函中曰:“《荀子雜志》已刻完兩卷,大約明年夏秋間方可畢。拙刻《經(jīng)義述聞·通說》已刻一卷,弟二卷須俟正、二月方可蕆事。”[20]卷四,395道光十年(1830)正月二十五日,王紹蘭致王引之函中曰:
向嘗從事《說文》,實無心得,自茂堂大令書出后,早經(jīng)中輟,今惟取其闕者補之,誤者訂之,謂之《說文段注補訂》,已積有百余條,但段書可商榷者尚不止此,當再為之卒業(yè)。然亦不能自信果否?此是彼非。俟暇日錄寄,以求折中焉可耳。袁宏《后漢記》補證三十卷,業(yè)經(jīng)脫稿,尚未付抄。[21]181
這類函札有時很長,其內(nèi)容往往厚重、精彩,有些類似學術(shù)論文。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戴震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撰寫了長達六千多字的函札《答段若膺論韻》[22],涉及古音學中的諸多問題,其中將古韻定為九類二十五部,堪稱戴震關(guān)于古韻分部最重要的成就。此后,鑒于《答段若膺論韻》學術(shù)價值甚高,段玉裁將其置于孔繼涵刻《戴氏遺書》中的《聲類表》卷首,并為《聲類表》這部戴震考證古音的絕筆之作寫序。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四十二年(1777),戴震、段玉裁論韻達15年。戴震去世后,嘉慶十七年(1812)段玉裁結(jié)識江有誥,又繼續(xù)討論古音問題[23]。而這些討論大多是通過函札進行的。函札使他們能夠及時了解近期對方的研究內(nèi)容、學術(shù)觀點等,這樣的交流對學術(shù)問題的深入討論極有助益。
此外,收入中華書局1980年版《戴震文集》卷三的《與王內(nèi)翰鳳喈書》《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與盧侍講召弓書》《再與盧侍講書》《答江慎修盧侍講書》,卷九的《與是仲明論學書》,中華書局1998年版的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三的《與焦里堂論路寢書》《與胡敬仲書》《與阮伯元閣學論畫舫錄書》,卷二四的《答孫符如同年書》《與孫淵如觀察書》《復(fù)錢曉徵先生書》,卷二五的《與阮伯元侍郎論樂書》《與阮中丞論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的段玉裁《經(jīng)韻樓集》卷六的《答丁小山書》等,篇幅都較長,學術(shù)含量甚高,相當于一篇專文。
當學者身處邊遠地區(qū)時,當面交流不便,更加依賴函札往來。據(jù)《雷塘庵主弟子記》(即《阮元年譜》)“道光九年己丑六十六歲”條記載:“十二月,粵東將刻成《皇清經(jīng)解》,寄到滇南。福案:是書大人于道光五年在粵編輯開雕,六年夏,移節(jié)來滇,乃囑糧道夏觀察(修恕)接理其事,嚴厚民先生(杰)總司編集。凡書之應(yīng)刻與否,大半皆是郵筒商酌所定。”[24]165
函札也有托人轉(zhuǎn)遞的。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春,王念孫在《與劉端臨書(三)》中有云,“若膺、容甫札俱祈轉(zhuǎn)致”[25]卷四,153。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二十七日,顧廣圻《致王引之書(二)》曰,“獻歲由南雅學士付下手書”[21]408-409。
較之于準備公開的序跋,當初無意公開的函札時常指出對方論著的不足之處。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錢大昕的《與段若膺論尚書書》對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中今古文經(jīng)字的劃分提出不同見解[26]卷三三,539-540。乾隆五十八年(1793)四月,臧庸在《與段若膺明府論校爾雅書》中,跟段玉裁商榷段氏所校《爾雅》疏誤之處[27]卷二,123-124。嘉慶十四年(1809),段玉裁的《與黃蕘圃論孟子音義書》,指出黃丕烈所刻《孟子音義》中的誤字[12]84-85。嘉慶十六年(1811)五月九日,宋翔鳳致函王引之,將自己關(guān)于《尚書》的最新研究心得與王氏討論。王引之對宋翔鳳的卓見十分認可,將這封篇幅長、學術(shù)性強的函札略作改動并題名為《某孝廉書》,收入《經(jīng)義述聞》[28]卷四,264-269。
與當面交流類似,函札也會涉及他人的學術(shù)動態(tài),評價他人之作。如乾隆六十年(1795)三月二十日,焦循在《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jù)著作書》中說:
本朝經(jīng)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黜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shù)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jīng)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jù)”者混目于其間乎?[29]卷一三,245-247
這段文字言簡意賅,對清代著名考據(jù)學家進行了點評,可以視為重要的學術(shù)信息。
又如:嘉慶十四年(1809)十一月,段玉裁在致孫星衍函中提到,陳鳣的《鄭康成年譜》引用了《唐會要》和《孝經(jīng)正義》中關(guān)于鄭玄自序之材料,而未引其所本的《文苑英華》所收的劉知幾《孝經(jīng)老子注周易傳議》。段玉裁謂此乃“逐杪而忘本,泳沫而忘源也”[12]卷五,100。嘉慶十四年十一月,段玉裁在《與梁曜北書論戴趙二家水經(jīng)注》中用兩千多字詳細論述了自己對趙一清、戴震《水經(jīng)注》相襲之事的看法,極力替其師戴震申辯[12]卷七,172-174。道光元年(1821)八月,王引之《致王紹蘭書(一)》[20]卷四,392和《致王紹蘭書(二)》[20]卷四,392-393以及王紹蘭《致王引之書(一)》[21]161-162中,均提到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的某些疏誤。道光十年(1830),王引之在《與陳奐書(七)》中提到:“段茂堂先生《詩經(jīng)小學》考訂精審,而所引它人之說間有不足存者。如王中丞汝璧之解‘日居月諸’,穿鑿支離,而乃見采擇,似擇焉而不精矣。想尊著內(nèi)必不守此曲說也。金誠齋考訂三禮,頗為精核。”[20]卷四,396
有的函札還蘊含著重要的學術(shù)理論。如盧文弨在《與丁小雅(杰)進士論校正方言書(辛丑)》中指出:“大凡昔人援引古書,不盡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定。況未有雕板以前,一書而所傳各異者,殆不可以徧舉。今或但據(jù)注書家所引之文,便以為是,疑未可也。”[30]卷二○,389此系精湛的校勘學理論,乃盧氏長期治學經(jīng)驗之總結(jié),堪稱厚積薄發(fā),非常值得重視。
通過函札往來,清代學者可以較快獲悉對方最近在從事哪些研究。這在當時是簡單、經(jīng)濟、有效的信息交流方法,有時比當面交流更加深入、具體。并且,不少富有價值的學術(shù)成果是在函札中首次公布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函札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學術(shù)交流的空間,對乾嘉時期知識共同體的形成助益極大。并且,函札往來不受地域、時間等因素的限制,堪稱流動的學術(shù)媒介,在本文所提及的五種學術(shù)信息獲取方式中最為便捷。
清代學者函札數(shù)量十分龐大,其中大部分未收入相關(guān)文集并刊刻,而以各種方式經(jīng)過整理點校后公布的,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清代著名學者劉文淇的后人曾于1984年將珍貴的《青溪舊屋尺牘》(計2409頁)和《通義堂尺牘》(計2153頁)捐贈給上海圖書館收藏。《青溪舊屋尺牘》系劉文淇與225人之間的函札,《通義堂尺牘》系劉毓崧與241人之間的函札,二者合計5000余通,價值甚高,目前正在由海峽兩岸的相關(guān)學者進行整理識讀,準備正式出版。我們熱切期待更多的這類函札能夠盡早與讀者見面,這對本文所涉及之問題的深入研究亦具有重要意義。
三、撰寫序跋
清代學人的著述一般都有序跋,大體上可以分為詩文集之序跋、學術(shù)著作之序跋,其中學術(shù)著作之序跋是學術(shù)交流的重要方式,往往比函札更加系統(tǒng)、深入。序跋除了對相關(guān)著作進行評價之外,有時還會就某些學術(shù)問題做進一步發(fā)揮。一些學術(shù)著作有多篇序跋,其中不少出自名人之手。如阮元等撰集的《經(jīng)籍籑詁》,分別有王引之、錢大昕、臧鏞堂(即臧庸)之序;郝懿行的《爾雅義疏》,分別有宋翔鳳、胡珽之序;凌廷堪的《校禮堂文集》,分別有盧文弨、江藩之序;劉淇的《助字辨略》,分別有盧承琰、國泰之序和劉毓崧之跋。
清代學者、文人在著作完成之后往往會向友人索序。如嘉慶十一年(1806)四月二日,段玉裁在《致王念孫書(二)》中有云:“《說文注》近日可成,乞為作一序。”[21]17于是有了后來著名的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該序共計439字,言簡意賅,堪稱清人序跋的典范之作。同時,段玉裁的《廣雅疏證序》、阮元的《經(jīng)義述聞序》、錢大昕的《廿二史札記序》等字數(shù)也不多,但都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
阮元作為清代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一生中為他人著作撰寫了大量序跋,如為段玉裁《周禮漢讀考》、王引之《經(jīng)傳釋詞》所撰之序,學術(shù)性極強。又如嘉慶十六年(1811)六月十五日,王念孫讀臧庸《拜經(jīng)日記》畢,為之作序。此外,桂馥的《說文統(tǒng)系圖》,程瑤田、盧文弨、翁方綱、張塤等多位學者為其作了題跋。
作序者大多可以在索序者的學術(shù)著作完成之后、刊布之前,利用作序的機會,在第一時間先睹為快,成為相關(guān)學術(shù)信息的首先獲取者;而索序者常常也可以從剛剛撰寫完畢的序中了解新的學術(shù)信息。如嘉慶二十年(1815),王引之將自己的力作《經(jīng)義述聞》之手訂全帙寄給阮元,阮元將其交給南昌盧宣旬刊刻,后來又為該書作序。
學者之間常常相互作序。如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六日,盧文弨為凌廷堪作《校禮堂初稿序》;同年,凌廷堪為盧文弨撰《儀禮注疏詳校》寫序。
清人論著中還有一種體裁是“書后”,這是題跋的一種,相當于讀后感,類似于現(xiàn)在的書評。“書后”大多比序跋、函札更為具體、深入,往往會對原書做一些補充,有時還提出一些不同意見。如王念孫的《六書音韻表書后》、顧廣圻的《書毛詩故訓(xùn)傳定本后》、方東樹的《書徐氏四聲韻譜后》、江藩的《書夏小正后》、胡培翚的《儀禮集釋書后》和《儀禮經(jīng)注校本書后》等,各有千秋,價值甚高。
清人文集中,序跋等往往占有較大的比重。如盧文弨的《抱經(jīng)堂文集》共計三十卷,主要內(nèi)容是序跋、函札以及傳記、墓志銘、題辭、對策等,其中序五卷,跋九卷,書(函札)五卷。但這并不等于說《抱經(jīng)堂文集》的學術(shù)水平不高。正如王文錦在其所點校的《抱經(jīng)堂文集》之“前言”中所云:“盧氏的序跋書信,在文集中占很大比重,這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作者古籍知識豐富,見解高明,特別是他的校理經(jīng)驗,最值得注意和借鑒……盧氏的經(jīng)驗之談,對今天古籍整理工作者來說,很有指導(dǎo)意義,不能忽視。”[31]前言,3-5整體而言,《抱經(jīng)堂文集》堪稱清代一流學術(shù)文集,筆者在主編《盧文弨全集》之過程中對此深有體會。
毋庸諱言,作序者與原書作者基本上是友人或師生關(guān)系,因此序中有時不乏溢美之詞。不過,這并不影響相關(guān)學者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
四、購買、借閱圖書
清代學者大多本身擁有較多藏書,主要靠自己的藏書獲取相關(guān)學術(shù)信息,同時也注重利用他人的藏書。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朱彝尊以及乾嘉學派中的吳派代表人物惠棟曾大量購書,收藏甚豐。一些貧寒的學者如汪中、周永年等也節(jié)衣縮食,想方設(shè)法買了不少書,以便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許瀚《涉江采珍錄》記載了他所購買的大量典籍,有的還具體注明購買處所、時間及支付的書款等。如:“仿宋《韓非子》二十卷附顧廣里《識誤》三卷,四冊。辛卯臘,二十八日,蘇州閶門買。京錢千文。”[32]1
朱彝尊除了大量購書之外,還抄錄了大量書籍。他在京參修《明史》期間,經(jīng)常從史館借抄,并借抄于宛平孫氏、無錫秦氏、昆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塘龔氏、寧波范氏等明末清初的藏書世家。歷年所抄達三萬余卷,占其全部藏書的近四成。又如錢大昕的個人藏書并不是太豐富,但他在治學過程中曾多次向黃丕烈、袁廷梼、盧文弨、周錫瓚、顧之逵、戈宙襄、嚴元照、何元錫、劉桐、吳騫等人借抄圖書[33]卷一,527-557,從而獲得了更多的學術(shù)信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善本錢大昕未曾寓目,從而使其個別考證的精確性稍受影響。如傅增湘在為張元濟的《校史隨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竊惟史籍浩繁,號為難治。近代鴻著,無如王氏《商榷》、錢氏《考異》、趙氏《札記》。三君皆當代碩儒,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其考辨精深,征引翔實,足為讀史之津寄。然于疑、誤、奪、失之處,或取證本書,或旁稽他籍,咸能推斷,以識其乖違,終難奮筆以顯為刊正,則以未獲多見舊本,無所取證也。第舊本難致,自昔已然。錢氏曉征博極群書,然觀其《舊唐書考異》,言關(guān)內(nèi)道地理于今本多所致疑,似于聞人詮本未全寓目。明刻如此,遑論宋、元。[34]序言,1-2
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糾正了正史刊本中的諸多訛誤,水平甚高。然而,由于他們未能見到更多的宋元善本,致使個別考證失誤①參見張元濟《校史隨筆》“金史·考異所指有誤”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8-139頁。。同時,錢、王憑借個人學識指出的《五代史記》時本中的某些錯誤,在張元濟所見之宋慶元刊本中不誤,并且尚有不少未及指出者②參見張元濟《校史隨筆》“五代史記·錢大昕考異所指此不誤”條、“五代史記·王鳴盛商榷所指此不誤”條、“五代史記·時本訛奪多可糾正”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 119-122頁。。從某種意義上說,錢、王的上述考訂變成了無效勞動。如果他們當時能見到更多的宋元善本,就不會出現(xiàn)上述問題了,《廿二史考異》和《十七史商榷》的質(zhì)量也將更高[35]。這一事例從反面說明了學術(shù)信息之于考證的重要作用。
學者之間還相互借書,如朱彝尊與王士禛之間就是如此。當然,也有由于種種原因不愿出借藏書(尤其是珍本秘籍)者。如段玉裁在《與劉端臨第三書》中提及:“黃韶圃孝廉所購宋本好書極多,而慳不肯借,殊為可憾。”[12]393這同樣也從反面說明了學術(shù)信息之于研究的重要意義。
清代學者利用官方藏書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情況不多,所占比重甚小。這與當時官方藏書數(shù)量有限并且集中在重要城市(尤其是京城),難以被分散居住在全國各地(包括不少鄉(xiāng)村)的學者利用直接相關(guān)。同時,與今天相比,學者治學所需要的資料數(shù)量有限,在很多情況下利用自己的藏書就已經(jīng)夠了。還有,在交通不便并且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圖書館的當時,學者要靠利用圖書館為主來治學也不現(xiàn)實。因此,在當時圖書館并非治學之必需。而進入民國時期,直至20世紀末,各類論著與清代相比呈幾何級數(shù)增長,并且此時學者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圖書館的重要性顯得十分突出。近年來,隨著數(shù)據(jù)庫、電子書的大規(guī)模普及,E時代的學術(shù)信息獲取方式大大改變,圖書館(此處指實體圖書館)的重要性沒有以前那么大了。
清代學者購買書籍主要是通過固定書鋪,也有部分書籍購自臨時書攤、流動書船等。北京琉璃廠堪稱當時固定書鋪最為集中之地,無論是常住京城,還是臨時赴京的清代學者,琉璃廠往往是他們的必到之地。翁方綱在四庫全書館供職期間,通常是上午校閱圖書,午飯之后便攜帶應(yīng)考證之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查。另有錢大昕、朱筠、桂馥、丁杰等四庫館臣,也經(jīng)常與翁氏一同去琉璃廠訪書。可見琉璃廠書肆乃參與《四庫全書》編纂之學者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重要渠道。
像琉璃廠這樣的學者經(jīng)常光顧的書店街既是購書之處,也是學者晤面、交流之場所。此處還留下了中外學者交流之史實。如黃丕烈就是于嘉慶六年(1801)在琉璃廠陶正祥、陶珠琳父子經(jīng)營的五柳居書坊,與朝鮮著名的“北學派”代表人物和“詩文四大家”之一的樸齊家(1750—1805)結(jié)識的[36]。
同時,人文薈萃的蘇州、南京、杭州等地也是書鋪林立,為清代學者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提供了很大便利。
書肆中不但有學者之間的交流,還有學者、店主之間的交流。清代書肆主人由于每天接觸各類典籍及學者,耳濡目染,在學術(shù)信息方面有時比學者還靈通。他們往往知道某位學者喜好某類書籍,另一位學者最近關(guān)注哪些書、做哪方面的研究等等。因此,與店主的閑聊,也常常使學者多少有些收獲,甚至知曉意想不到的重要學術(shù)信息。此外,少數(shù)學者還充分利用在書肆當伙計的機會,刻苦學習,搜集資料。如年僅十四歲就進入書店當學徒,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汪中即為典型代表。
此外,為他人刻書期間通常可以第一時間獲取相關(guān)信息。如阮元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能力,曾經(jīng)刻印了錢大昕《三統(tǒng)術(shù)衍》三卷、孔廣森《儀鄭堂文集》二卷、彭元瑞《石經(jīng)考文提要》十卷、胡廷森《西琴詩草》一卷、張惠言《周易虞氏易》九卷和《周易虞氏消息》二卷,以及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其中一卷)等多種當時學者的著作。在幫助他人的同時,阮元自己也及時獲取了寶貴的學術(shù)信息。
不過,當學者在邊遠地區(qū)時,購買或借閱圖書較為困難。如嘉慶九年(1804),桂馥《上阮中丞書》提到:“馥所理《說文》,本擬七十后寫定,滇南無書,不能復(fù)有勘校,僅檢舊錄簽條排比付錄。”[37]卷六,697
五、相互贈書
如果說一般的傳世典籍主要來自于購買,那么新近刊布的同時代學者的著作除了購買、借閱之外,學者之間的相互贈送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著名學者獲贈的機會更多,這使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讀到同行的著作。《經(jīng)義述聞》堪稱一部大書,王引之將其贈送給翁方綱、段玉裁、朱彬、王紹蘭、焦循、阮元、許宗彥、陳壽祺、張澍、陳奐、許瀚等多位學者。部頭不大的著作,贈送就更為普遍了。
贈書可以有多種方式,有拜謁時當面贈送的,如:嘉慶二十一年(1816)冬,王引之拜謁翁方綱,以所刻《經(jīng)義述聞》就正,翁方綱“覽至《周易》‘噫!亦要存亡吉兇’一條,以讀‘噫’為‘抑’,為不易之論。又告以說經(jīng)當舉其大者”[20]卷三,391;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鮑廷博將《知不足齋叢書》一至五集贈送給同在杭州的盧文弨。也有托人轉(zhuǎn)遞的,如:嘉慶二十三年(1818)三月初四,許宗彥致函王引之,謝春歲經(jīng)由阮常生轉(zhuǎn)遞書信及饋贈《經(jīng)義述聞》;嘉慶二十五年(1820)二三月間,陳壽祺接到經(jīng)由孫爾準轉(zhuǎn)遞的王引之贈送的《經(jīng)傳釋詞》;道光十一年(1831)正月,王念孫在致朱彬函中告之收到由其子朱士達轉(zhuǎn)遞的書信及贈送的大著《禮記訓(xùn)纂》,王氏讀之以為有功經(jīng)學甚巨,唯有獻疑者數(shù)處,故附簽28條寄示朱氏求正[9]321-322。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十年(1830)九月,王引之在《與陳奐書(八)》中說:“《儀禮管見》及致胡主政書已送交。《管見》學力深而用心細,實不可少之書,便中仍望見賜一部。”[20]卷四,396可見王引之利用為陳奐轉(zhuǎn)遞陳氏本人所著《儀禮管見》及書信給胡培翚之機會,先睹為快,趁便希望陳奐也贈送一部給自己。
因為當面贈送和托人轉(zhuǎn)遞的機會較少,所以贈書更多是采用郵寄的方式。贈書往往伴隨著函札往來。如:嘉慶八年(1803),阮元寄贈《經(jīng)籍籑詁》《浙江圖考》給凌廷堪;嘉慶十一年,阮元寄贈《經(jīng)籍籑詁》《十三經(jīng)注疏校勘記》給黃承吉;道光十年,王引之將王念孫的《荀子雜志》寄送給陳奐。
郵寄時還有一種較為特殊的情況,就是并非著者本人寄出,而是經(jīng)過著者委托,從著作的刻印地直接寄出。這在當時可以節(jié)省不少費用和時間,也更有利于受贈者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如段玉裁《致王念孫書(三)》云:“拙著《說文》,阮公已為刻一卷,曾由邗江寄呈,未知已達否?”[21]20
托人轉(zhuǎn)遞和郵寄(不含從刻印地寄出者)一般同時附有函札,這樣的函札大多涉及與所贈之書相關(guān)問題的探討,因此學術(shù)含量往往很高。受贈者也大多有復(fù)函,除了致謝之外,主要篇幅通常是對所贈之書的評價以及相關(guān)問題的闡發(fā)、補充、商榷等,當為研究清代學術(shù)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如嘉慶二十三年(1818)三月,張澍收到王引之寄贈的《經(jīng)義述聞》和《廣雅疏證》后復(fù)函王引之時提到:
曩歲作《姓氏五書》,內(nèi)有《姓氏辯誤》二十六卷,討論前人言姓氏之舛錯者,妄自謂精審。而閣下《經(jīng)義述聞》中頗言及姓氏,往往與愚說不合。竊又自疑其說之未必當,恨無由面質(zhì)之于大雅也。茲略舉數(shù)條言之,冀得是正為幸……凡此數(shù)端,雖于經(jīng)義無關(guān),然實事求是,則閣下之說或有未諦當者,敢獻其疑,并望恕其直而教之以所未聞焉,則幸甚。[38]卷一五,600-601
關(guān)系特別密切的學者還有機會獲得摯友贈送的珍貴的初印本。如阮元《與王伯申書一》曰:
蒙示《經(jīng)義述聞》,略為翻閱,并皆洽心,好在條條新奇,而無語不確耳。見索拙論曾子一貫之義,詳在《詁經(jīng)精舍文集》內(nèi)。今以一部奉寄,其言“郵表畷”似亦有可采者。拙撰《曾子注釋》出京后又有改動,因今年正月鳩工刻雅頌集,工已集而書未校寫。不能眾工閑居,因即以此稿付刻,其實不能算定本,其中講博學一貫等事,或可少挽禪悟之橫流。至于訓(xùn)詁,多所未安,頃翻《經(jīng)義述聞》“勿”“慮”等訓(xùn),尚當采用尊府之說,將板挖改也。《注釋》一本呈覽,初印不過三十本,概未送人,乞秘之,勿示外人,緣將來改者尚多也。[21]223-224
這段文字內(nèi)容豐富,除了涉及《曾子注釋》初印本之外,還可以獲悉阮元翻閱王引之贈送的《經(jīng)義述聞》之后,覺得《曾子注釋》中的個別訓(xùn)詁當采用《經(jīng)義述聞》之說,故函中有“將板挖改也”之語。此例充分表明了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重要性。另外,初印本之贈送者未必都是著者本人,有時也可以是刊行者。如嘉慶九年(1804)六月,馮鷺庭將其剛剛刊刻的惠棟的《后漢書補注》寄贈給阮元[39]卷七,385。
贈書不僅僅限于刻本,還有稿本、未定本等。如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朱彬致函王念孫,并呈上剛有成稿的《禮記訓(xùn)纂》①參看朱彬《致王念孫書(五)》《致王念孫書(六)》,見賴貴三編著《昭代經(jīng)師手簡箋釋——清儒致高郵二王論學書》,(臺北)里仁書局 1999年版,第45-48頁;王章濤《王念孫·王引之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6年版,第319-320頁。。又如,陳奐《師友淵源記》有如下記載:
江諱沅,字子蘭,一字鐵君……若膺師著《經(jīng)韻樓文集》未定本,切屬弗借予人。奐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為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fù)借予人邪?”師猝無以應(yīng),唯曰:“我館陳徒好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圈記乃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奐因是得識若膺師。[40]200
這段文字說明了段玉裁將《經(jīng)韻樓文集》的未定本給了江沅,陳奐因從江沅受學而得以選錄該未定本,獲取了從業(yè)已刊行的著作中無法獲取的學術(shù)信息。同時,段氏“切屬弗借予人”,也可以理解,畢竟是未定本。
贈書并不僅僅局限于本人的著述,也包括他人作品。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邵二云以先生(引者按:指段玉裁)《韻譜》稿本示錢竹汀,竹汀以為鑿破混沌,為制序”[41]460。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阮元致王引之函中提到:“茲瀆者,在山東尋得吳中珩《廣雅》本,特為寄上老伯校正《廣雅》之用。”[21]270道光元年(1821)八月,王引之致函王紹蘭:“兩承芳訊下頒,并快讀尊著,及拜賜《經(jīng)韻樓集》。”[20]392道光十一年(1831)春,陳壽祺致王引之函附有其子陳喬樅的《禮說》和《毛詩箋說》之書稿。再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五月間,阮元致王引之函中曰:“春間,曾將吳中珩《廣雅》本寄上,未知曾收到否?曾校畢否?”[21]244這應(yīng)該是阮元將吳中珩所校的《古今逸史》本《廣雅》寄贈給王引之,供其父王念孫撰寫《廣雅疏證》時使用。當時阮元正在山東學政任上,此函是從濟南發(fā)往北京。這說明當時函札傳遞時間較長,有時也存在郵寄過程中遺失的情況。
另有代他人索書之事例。如嘉慶元年(1796)元月初九,段玉裁《與邵二云書二》有以下內(nèi)容:“蘇州有博而且精之顧廣圻,字千里。欲得尊著《爾雅疏》一部,望乞之為禱。即交小壻郵寄可也。”[12]389又如王引之在為《讀書雜志》中的顧校《淮南子》各條所撰之說明中提到:“歲在庚辰,元和顧澗蘋文學,寓書于顧南雅學士,索家大人《讀書雜志》。乃先詒以《淮南雜志》一種,而求其詳識宋本與《道藏》本不同之字,及平日校訂是書之訛,為家刻所無者,補刻以遺后學。數(shù)月書來,果錄宋本佳處以示,又示以所訂諸條。其心之細、識之精,實為近今所罕有。非熟于古書之體例而能以類推者,不能平允如是。”[42]2498這段文字充分反映出索書、贈書帶來的及時的學術(shù)交流。
也有當初有幸見到了某書,但由于某種原因未能及時獲取并利用的情況。如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條記載:“是年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后,孔戶部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奧。”[43]附錄,228
六、結(jié) 語
清代學者總?cè)藬?shù)有限,做相同領(lǐng)域研究的則更少,學人圈較小,并且做相同領(lǐng)域研究的學者往往互有聯(lián)系。再者,當時學術(shù)著作數(shù)量也不多。因此,上述學術(shù)信息的獲取方式基本上與清代(尤其是乾嘉時期)的學術(shù)、文化、經(jīng)濟、交通等發(fā)展水平相適應(yīng)。以上五種獲取方式并行不悖,互為補充,信息獲取呈現(xiàn)出多元化、立體化的狀態(tài)。中國古代十分講究師生關(guān)系,同門聯(lián)系較多。不過從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學者的交流絕不僅僅局限于同門。不同學派、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地位之學者相互獲取學術(shù)信息,大大開闊了視野,從而構(gòu)成了一個較為完整而系統(tǒng)的、立體化的清代學術(shù)圈。多樣且較為有效的學術(shù)信息獲取方式,使得清代學術(shù)圈的范圍擴大了,聯(lián)系增多了,交流豐富了,活力增強了。此類縱向、橫向相結(jié)合的知識群體互動也促進了知識傳播,對清代學術(shù)的發(fā)展頗有助益。
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的最大好處是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的重復(fù)性和片面性,同時充分利用已有的相關(guān)成果。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段玉裁開始撰寫《說文解字讀》,王念孫也在同年開始為《說文》作注。當王氏完成兩卷之后見到了段氏《說文解字讀》,為了避免重復(fù),于是不再繼續(xù)作注了。這一點對崇尚考據(jù)學的乾嘉學者尤為重要。當時的學者普遍重視實證研究,從而很關(guān)注學術(shù)研究中的發(fā)明權(quán)。學術(shù)信息的及時獲取顯然有助于學術(shù)規(guī)范的建立和自覺遵守。
總體而言,清代學者之所以能夠及時獲取學術(shù)信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相對完備的函札傳遞渠道,同時也得益于當時發(fā)達的私家藏書體系。不過,清代的交通相對于現(xiàn)在還是極不便利的。即便是距離不遠的鄰省鄰府乃至鄰縣,交流都不太方便,更不用說相距數(shù)百里乃至上千里的兩地。因此,當學者處于偏僻地區(qū)時,學術(shù)信息獲取有時是比較困難的。同時,由于條件所限,清代學者學術(shù)信息的獲取在總體上未能系統(tǒng)化,尤其是尚未進入核心學術(shù)圈的中底層學者及初學者等,難以及時獲取相關(guān)學術(shù)信息。因此,我們也不能過分夸大清代學者學術(shù)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