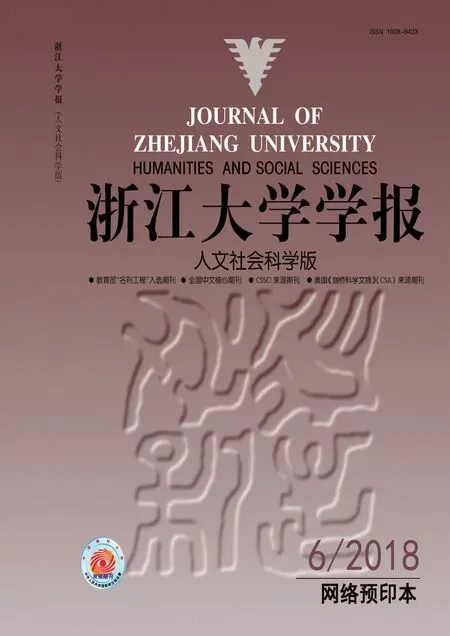隔代照顧研究述評及其政策討論
林 卡 李 驊
(浙江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 引 言
在中國,兒童福利議題常常處于社會福利研究的邊緣。這不僅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使人們形成了將兒童照顧視為家庭事務的觀念,也因為目前的社會政策體系對兒童照顧的公共財政支持十分有限[1]。要推進對兒童福利的理論研究,隔代照顧是一個很好的議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正隨著目前中國社會變化給家庭照顧帶來的挑戰加劇而不斷提高。近二十年來出現的農民工進城浪潮使農村地區出現了許多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2],因而隔代照顧現象在農村更為普遍。在城市,隨著過去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和家庭規模的縮小,城市家庭在兒童照顧方面的人力資源日漸衰竭,加之有限的公立幼兒園和托兒所等正式照顧資源常常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處于正常上班狀態的父母又無力照顧子女,這就迫使許多家庭中的祖輩承擔起了照顧孫輩的責任[3]。
盡管如此,國內社會政策研究領域對隔代照顧問題的討論迄今為止還十分缺乏。其阻礙因素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傳統照顧觀念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把子女照顧僅僅看作家庭事務,老人提供的隔代照顧往往被視為家庭義務,其社會價值常常被低估甚至忽視;二是研究者對隔代照顧的國際研究狀況(如研究范式、基本理論假設和相關政策討論)不熟悉,難以在理論層面上展開深入研究。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國外研究經驗,多維度、多視角地對這一議題進行探討,以便更好地理解隔代照顧的特點和性質及其與其他因素的關聯。
廣義上來講,隔代照顧具有雙重含義,既包括祖輩照顧孫輩的勞動,也包括孫輩照顧祖輩的活動[4]。但在實際運用中,多數研究都把隔代照顧主要看成祖輩照顧孫輩的活動,即由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等上一輩老人參與照顧孫輩子女的服務,包括祖輩對孫輩的經濟支持、生活照顧及精神支持等。一些研究者對隔代照顧與隔代撫養的概念進行了比較和區分。隔代撫養是指父母把孩子寄放在祖輩家中,由祖輩代為養育,側重于祖輩進行的教育和培養活動[5];而隔代照顧的內涵則更為廣泛,既包含老人對兒童的生活照料,也包括對兒童的教育和培養。
國外學者多采用社會調查的數據庫資料來分析隔代照顧狀況。有的研究采取橫截面數據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和Logistic回歸分析,也有的使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比較研究以描述受訪者在隔代照顧方面的情況。常用數據庫有德國的“歐洲健康、老齡化與退休調查”數據庫(Survey of Health,Ag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SHARE)、美國的“全國家庭與住戶調查”數據庫(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NSFH)以及英國的“英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庫(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BHPS)。這些調查資料描述了照顧者及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居住地點等方面的特征,從而反映出各地隔代照顧的特點。
本文將從國際比較的視角切入該議題,通過回顧國外相關研究,考察不同社會隔代照顧的狀態及其特點。為此,我們在Google Scholar中將“grandparents”和“child care”作為關鍵詞進行文獻搜尋,獲得相應的論文213 000篇。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了解該議題的研究現狀和國際發展趨勢提供了豐富的文獻。以此為基礎,本文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來回顧有關隔代照顧問題的國際研究:一是各種社會因素對隔代照顧的影響,二是隔代照顧對被照顧者(孫輩)和照顧者(祖輩)身心健康的影響,三是社會政策與隔代照顧的關系,四是歐洲國家隔代照顧狀況的比較研究。最后,本文將總結分析這些研究對中國社會政策制定的啟示。
二、 各種社會因素對隔代照顧的影響
各國隔代照顧的狀況首先取決于各國社會的代際關系模式、社會資本網絡的特點[6]。代際關系模式與人們的行為和社會文化模式密切相關,照顧兒童涉及孫輩、祖輩和子輩三代人的利益。一些學者強調,在中國、越南、緬甸、泰國等國家,延續家族血脈、傳宗接代的文化規范直到今天仍起著強有力的作用[7],這種觀念鼓勵老人把隔代照顧當作一種樂趣而非壓力[8]。而在另一些國家的文化觀念中,祖輩照顧孫輩的責任意識較為淡薄,這使祖輩在閑暇時更愿意追求自身的發展而把兒童照顧看作負擔而非義務[9]。這種現象揭示了文化視角對理解隔代照顧活動十分重要。
隔代照顧的狀況也取決于勞動力市場的狀況。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隔代照顧現象與勞動力市場狀況密切關聯。一些研究者指出,當兒童的父母或許因就業而無法充分履行其照顧責任時,隔代照顧可以作為替代方式來緩解父輩在家庭照顧方面的壓力[10]。這種內在的聯系使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探討勞動力市場與照顧市場、正式勞動力市場與非正式勞動力市場以及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等問題。譬如Lin等強調,在工業化社會中家庭作為福利單位的功能正日漸衰退[11]。為了照顧子女,父母可以通過就業獲得報酬來雇傭保姆,也可以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孩子(如家庭主婦),還可以采用隔代照顧的方式[12]。因此,Viitanen強調,隔代照顧問題和家庭與工作平衡問題相關聯,發展隔代照顧有助于工作的父母實現家庭與工作平衡[13]。
隔代照顧問題與性別關系問題也密切關聯。一些學者通過對比不同性別照顧者參與隔代照顧意愿的調查數據,揭示了男性與女性照顧者所占的比例和他們的活動狀況。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生物社會學視角,從基因層面的親緣關系來解釋隔代照顧者的性別差異。例如Coall等采用親緣關系指標來闡釋隔代照顧的機理,包括被調查者孩子的數量、是否自己親生、是否配偶親生、是否領養等因素[14]。Bishop等從某高校選取140個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結果支持了這一親緣選擇假設的合理性[15]。Danielsbacka等也通過歐洲調查數據來檢驗親緣選擇理論,研究表明,女性母系祖輩通常是最積極的隔代照顧者,其次是男性母系祖輩,再次是女性父系祖輩,最后是男性父系祖輩[16]。同樣,Tanskanen等的研究發現,在隔代照顧中外婆比奶奶所花的時間更多,外公也比爺爺花費的時間更多[17]。而Leopold等采用SHARE數據庫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和比較后發現,男女雙方的祖輩退休之后參與隔代照顧的時間差異在縮小[18]。
以上研究涉及一系列相關指標,包括有哪些人給兒童提供了照顧幫助、他們給予了哪類幫助、照顧者的就業狀況、每周照顧的時間、被照顧者父母的就業情況等。這些指標可以反映出代際間家庭責任的變化、社會資本的多寡和代際變遷對隔代照顧的影響[9]。在這些討論中,也有研究以互惠主義為原則,采用社會交換理論來比較不同國家的隔代照顧狀況。總之,在影響隔代照顧的因素中,我們不僅要關注家庭關系和代際互惠方面的因素,也要關注經濟、政策和社會文化等因素。
三、 隔代照顧對被照顧者和照顧者身心健康的影響
對隔代照顧問題的討論難以避開對其效應的評估。一些學者指出,一些祖輩對兒童的溺愛會給兒童成長帶來消極影響[19];也有學者指出,隔代照顧意味著父輩在子女照顧方面的缺位,因而對兒童身心健康是不利的。盡管在一些極端情況(如嚴重酗酒、吸毒和在監獄中服刑)下,一些父母會因無力照顧子女而使祖輩照顧成為替代的選擇,但這無法改變父母缺位給兒童身心健康造成的不利影響[20]。然而也有一些學者發現了相反的證據,認為隔代照顧對兒童身心健康并沒有顯著的不利影響。例如Pearce等對英國12 354個3歲兒童的調查表明,祖輩照顧與雙親照顧對兒童肥胖的影響的差別并不顯著[21]。但總體而言,學者們通常認為隔代照顧對兒童身心健康的影響是消極的。
但對祖輩而言,隔代照顧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的影響是復雜的。一些研究指出,參與隔代照顧會使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參加活動,有利于老年人健康;但也有研究指出,照顧兒童會給老年人的生活帶來額外負擔,不利于老年人健康。針對這些困惑,一些學者采用健康指標和生活質量指標進行了測量和驗證。例如Hayslip等對86個參與隔代照顧的老人的生活情況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的健康水平有所下降[22]。Hughes等使用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數據庫對美國12 872個調查對象(50至80歲)進行了分析,發現參與和持續參與隔代照顧的老人群體情緒低落的可能性比不參與的老人群體高出1.47倍與0.77倍[23]。同樣,Muller等采用SHARE數據庫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認為隔代照顧對祖輩的心理健康狀況有明顯的負面影響[24]。
相反,一些學者認為參與隔代照顧的老人可以享受與孫輩的親密關系進而增進其幸福感,因而身心更為健康。Gessa等使用SHARE數據庫展開研究,也發現參與隔代照顧的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比未參與的老人更好[25]。還有研究者通過對42個參與孫輩照顧的老人進行調查,發現他們在照顧中所獲得的來自他人的物質和精神支持較多而精神壓力較小,因而健康狀況較好[26]。又如Buber等對12個歐洲國家的研究發現,不照顧孫輩的老人比照顧孫輩的老人情緒更容易低落[27]。也有學者認為參與隔代照顧使老人具有較高的社會參與程度,降低其孤獨感,從而增進了健康狀況[28]。
當然,要深入地解釋這種正面或負面效應,我們需要具體考察照顧者的社會參與狀況。有研究者認為,由于老人在隔代照顧中耗費了大量時間,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參與程度會隨之降低[29]。Arpino等研究了參與隔代照顧的祖輩在五種基本的社會活動中的參與情況,包括志愿活動、教育活動、體育和俱樂部活動、政治活動和宗教活動,以及參與這些活動的頻率。研究發現,參與隔代照顧對女性祖輩參與社會活動的影響較小,對男性祖輩的影響較大[30]。這說明參與隔代照顧活動對老年人社會參與情況的影響是復雜的,兩者間或許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四、 社會政策與隔代照顧的關系
以往,隔代照顧活動被認為是一家一戶的事,由家庭中三代人之間的關系所決定。但隨著福利國家的出現和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對隔代照顧的研究就需要討論公共服務體系的特點和家庭政策的制定等問題[31]。代際變遷及文化變遷的狀況會影響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公共服務的提供。解釋這種影響需要考察政策發展及公共服務體系的特點,研究照顧形式的變化[32],把隔代照顧問題的討論引向社會政策與社會服務領域,從而把微觀的個人照顧與宏觀的社會體系和社會服務政策結合起來。
在社會政策和公共資源的支持方面,一些研究強調,在當代社會中家庭照顧服務已經成為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必要內容[33]。許多發達國家制定了支持社會再生產進程的社會政策,包括普惠的兒童津貼、母親照顧津貼和兒童教育津貼等。有研究采用社會調查的數據來考察社會政策項目(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各種類型的長期護理保險及其他社會保險項目等)對兒童照顧的影響,從而揭示這些福利國家的社會照顧體系與隔代照顧的內在聯系[34]。
此外,也有些研究從社會救助角度分析社會政策項目對隔代照顧的影響。譬如英國反兒童貧困小組分析了蘇格蘭反兒童貧困組織的案例,考察了英國“兒童稅收積分”和“工作稅收積分”項目對不同家庭選擇兒童照顧方式(包括隔代照顧)的影響[35]。也有一些研究者論證了對單親家庭和未婚母親家庭的隔代照顧活動進行社會支持的必要性。他們認為在父母至少有一位缺位的情況下,祖輩照顧孫輩的負擔會比較重,需要給他們一些幫助。同時,一些祖輩因自身身體情況不佳而不能很好地履行照顧責任,這會使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產生行為方面的問題[18]。
同時,這些對兒童照顧的社會支持政策也為女權主義者所倡導。他們強調婦女從事兒童照顧工作是為社會培養新一代公民,因而隔代照顧問題應放在人口再生產體系中去理解[36]。有學者通過比較不同福利國家體制中的照顧模式來揭示隔代照顧、照顧模式與福利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及變化,并探索公共服務體系干預家庭照顧的正當性和積極性[37]。按照這一“社會照顧”的邏輯,如果要求祖輩承擔起兒童照顧的責任,那么這些照顧工作就應該得到公共機構的支持,甚至給予一定的報酬。為此,我們需要把隔代照顧的討論與社會政策(特別是家庭政策)的研究關聯起來,并進一步考察如何通過發展社會政策和提供社會服務來支持隔代照顧活動。
作為結果,社會政策特別是家庭政策的研究者都強調社會政策對于人口再生產的意義。Thomese等的研究表明,在荷蘭家庭中,祖輩參與兒童照顧能夠顯著促進生育率的提升[38];Rindfuss等的研究也發現,祖輩對孫輩非正式照顧的增加提升了挪威人的生育意愿[39]。而社會政策對隔代照顧的支持既能夠保護兒童權利,又能夠提高照顧者的生活質量,也能夠緩解人口再生產的壓力。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政策對隔代照顧進行一定的支持將有助于提升一個國家的生育率,從而維持人口數量的可持續性。顯然,社會政策應該考慮到老人的照顧行為可能產生的長期影響。
五、 歐洲國家隔代照顧狀況的比較
為了豐富以上討論,下面通過回顧有關歐洲國家隔代照顧狀況的研究來探討隔代照顧與社會政策的關系。隨著福利國家體系的發展,歐洲各國都發展起了社會照顧體系,但隔代照顧這種家庭照顧形式在這些福利國家中仍然十分流行。譬如Igel等在分析了歐洲11個國家的情況后指出,超過50%的被調查的歐洲家庭采用隔代照顧的方式。在21世紀初,這些國家中老年人群體參與照顧孫輩的比例從37%到59%不等。其中,中歐和北歐國家(如瑞典、丹麥、法國和荷蘭)的比重較高而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較低[40]。這種觀察與人們通常的假設相矛盾,一般認為南歐國家的家庭規模較大,隔代照顧可能較為普遍;而北歐國家發達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照顧體系可能會減少對隔代照顧的需求。
針對這一理論假設與實際數據形成反差的狀況,一些學者對隔代照顧情況進行更為細致的考察。他們把老人參與率與照顧兒童的強度(每日的照顧時間)結合起來考察,發現在南歐國家,參與隔代照顧的祖輩在老年群體中所占比例較低,但他們照顧工作的強度比中歐及北歐國家高。在兒童照顧公共服務水平較高的北歐國家中,家庭所負擔的兒童照顧壓力較小,因而照顧強度較低。這種狀況容易使老人把兒童照顧看作一項社會贈予,對兒童照顧活動持有積極態度,從而帶來了高參與率;但在兒童照顧公共支持水平較低的國家,隔代照顧被看成社會負擔,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義務和責任,因而老人在兒童照顧方面所面臨的壓力也較大,這就導致了較低的參與率[41]。
在性別關系上,北歐國家和南歐國家之間的差異也較為顯著。根據Leopold等對10個歐洲國家隔代照顧數據的比較,這些國家中的女性祖輩都比男性祖輩更愿意為照顧孫輩而放棄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18]。但在北歐國家對尚未退休的祖輩的意見調查中,選擇照顧孫輩和選擇工作的男女比重相當。與此不同,南歐國家中選擇照顧孫輩的女性比重較高。在西班牙,祖輩夫婦用于工作的總時間中,男性祖輩占72.95%,女性祖輩占27.05%;在照顧孫輩的總時間中,男性祖輩占30.48%,女性祖輩占69.52%。與之相比,瑞典的男女祖輩花在工作上和花在照顧孫輩上的時間最為接近。男性祖輩花在工作上的時間為42.70%,女性祖輩為57.30%;而花在照顧孫輩方面的總時間中,男性祖輩為41.19%,女性祖輩為58.81%。在已經退休的祖輩群體中,意大利的祖輩為照顧孫輩所花的總時間中,男性花的時間僅占30.81%,而女性占69.19%。比利時男性祖輩的這一比重為45.16%,女性祖輩為54.84%。南歐國家與北歐國家的這種差異表明,北歐的社會照顧體系可以通過支持隔代照顧而促進男性與女性照顧任務分配的均衡。
從社會政策和公共財政支持的視角來看,一些學者借用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資本主義三個世界的分類來分析隔代照顧的狀況。研究指出,對社會照顧領域的公共投入較低的南歐國家,其隔代照顧模式是“低參與率、高照顧強度”,高公共投入的北歐國家則屬于“高參與率、低照顧強度”,歐洲大陸國家則介于兩者之間。基于SHARE數據庫(2004年)的調查數據,Albertini等人指出,在南歐國家,有45%的祖輩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顧在內的照顧支持,其人均照顧時間為每年1 647小時;北歐國家丹麥的情況是60%的祖輩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顧在內的照顧支持,但人均照顧時間僅為每年382小時;在其他歐洲國家,法國50%的祖輩為子女提供包括隔代照顧在內的照顧支持,人均每年花費742小時。這些數據從特定的視角反映出隔代照顧現象與公共服務支持體系之間具有內在聯系[37]。
六、 總結及政策啟示
在社會政策視野中對隔代照顧現象展開討論,需要探索工業化社會中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及其對家庭照顧和非正式照顧體系的影響。通過上述研究回顧,我們看到隔代照顧現象在這些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階段國家中仍然十分普遍。根據Albertini等人的研究,歐洲國家的隔代照顧情況是,老人們平均每人每年給予子女(包括照顧孫輩在內)的照顧支持為902小時[37]。這就打破了人們以往的一個認識誤區,即在農業社會中,家庭照顧是兒童照顧的主要形式,但這種形式在發達工業化國家中會隨著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而退化。借鑒歐洲的經驗來反思家庭照顧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的作用和定位,我們需要回答公共服務體系和家庭照顧是否可以相互支持。如果這種相互支持的邏輯關系能夠成立,那么各國政府或許可以通過發展家庭政策來支持家庭照顧活動,并強化非正式照顧體系的作用。
另外也要考慮文化觀念和社會政策項目的作用。對歐洲各國關于隔代照顧態度的調查發現,有的地方(如北歐)對隔代照顧持較積極的態度,而有的地方(如南歐)則較為消極[40]。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觀念和社會關系的不同。在中國,儒家文化倡導在代際互惠的基礎上發展家庭照顧。但是,要推動隔代照顧的發展,需要改變把隔代照顧僅僅理解為家庭內部事宜的觀念,要把它放到更為宏觀的社會再生產體系中去看待。祖輩參與對孫輩的照顧目前在中國十分普遍,但對照顧孩子的祖輩提供的社會支持還十分缺乏。為此,在充分肯定老年人隔代照顧勞動對社會所做貢獻的價值的同時,也要探索如何通過社會津貼、補助等方式支持隔代照顧活動,為從事隔代照顧的老人提供一定的回報(“社會工資”),從而把這一私人問題轉變為公共問題。如何通過發展社會政策項目以支持非正式照顧體系的發展,促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動,是我們要面臨的重要任務。
在目前中國的兒童照顧服務方面,發展機構照顧常常被看成是目前發展兒童照顧體系的基本方向,而隔代照顧被認為是一種不得已的家庭照顧方式,會隨著公共服務體系和照顧機構(托兒所、幼兒園、學前班、小學等)的發展而弱化或被替代。但根據歐洲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的經驗,隔代照顧與兒童入學、入托、入園的權利并行不悖。采取社會政策手段尤其是家庭政策手段(包括提供育嬰補貼、兒童照顧津貼、單親母親社會救助津貼等)來支持隔代照顧,可以強化對隔代照顧和非正式照顧體系的支持,也可以緩解照顧者的壓力,鼓勵他們積極參與。
在效果的評估上,學者們關于隔代照顧對兒童身心發展影響的看法是模糊的。有的強調父母缺位對子女發展的不利影響,有的則討論祖輩照顧對兒童發展的積極影響。至于對老人的身心影響,一些研究主張隔代照顧對老人健康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取決于隔代照顧的頻率和強度。這啟示我們要把隔代照顧的影響與其強度和參與率聯系起來考察。同時,隔代照顧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體系運作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生育決策和照顧行為,為子輩多生孩子、提高生育率提供了有利條件。在面對目前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力老化和不足的問題時,我們有必要鼓勵發展隔代照顧以緩解工作父母的照顧壓力,支持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使年輕父母在制定多生孩子的計劃時無后顧之憂,從而促進生育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