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歸舊里無故人
■文/傾顧圖/畫畫的小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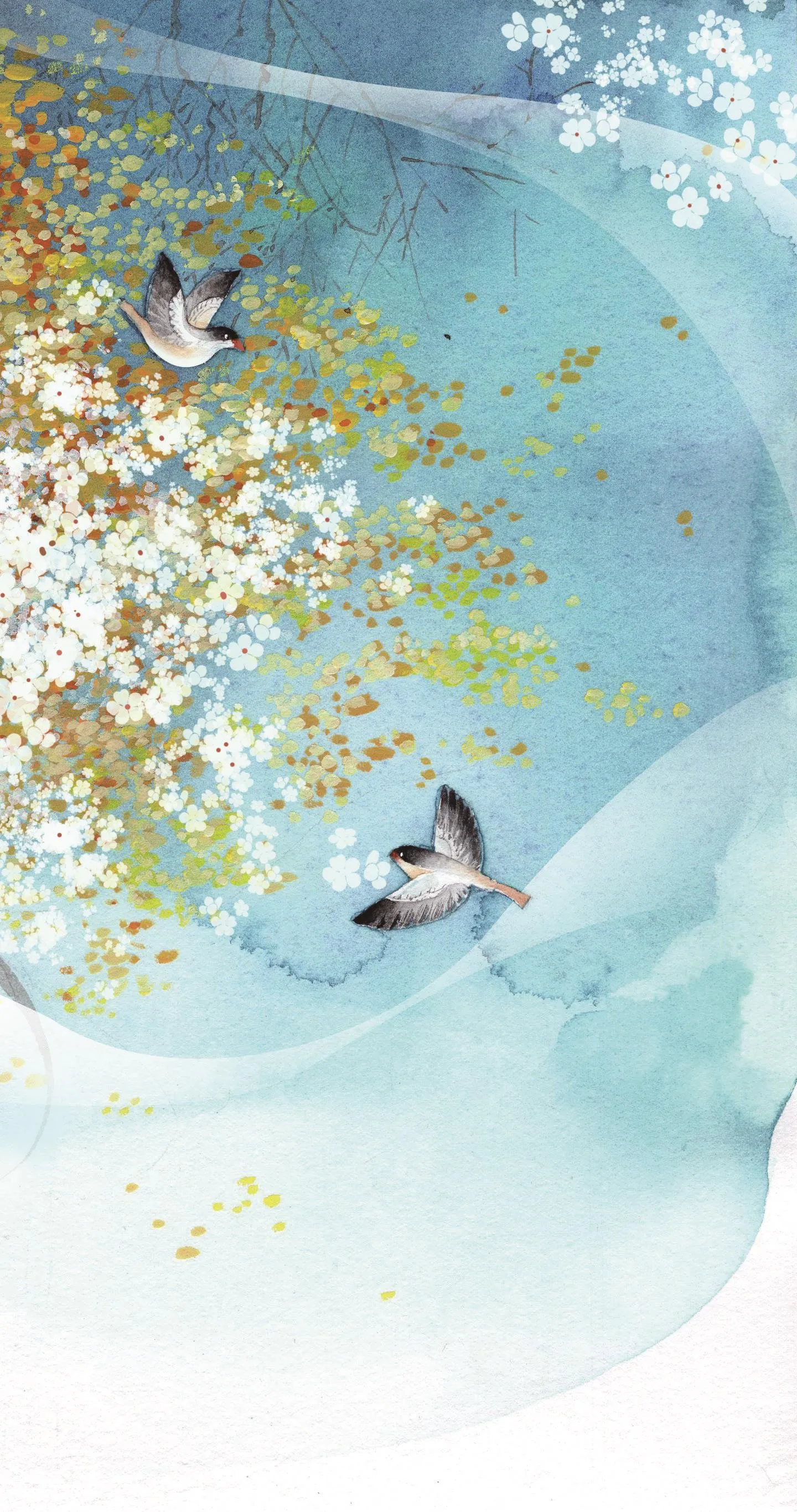
壹
我護著當朝皇帝和皇后躲到了一座破廟里。破廟極破,鴿籠大小,地上散落著發了霉的稻草,我默不作聲地把稻草攏到一起,脫下大氅鋪在上面。
阮阮開心地坐到了上面,皇帝卻一臉面癱,龍臀猶豫半天也沒往下坐。
我知道,他擔心有蟲子,這樣嬌滴滴的皇帝,當真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我冷眼瞧他猶豫半天,總算瞄準了大氅往下坐,然后一屁股坐到了發霉的稻草上。
阮阮嫌棄地把大氅扯開,又凝出一臉笑容對我說:“師兄,你坐到我身邊。”
皇帝的臉綠了綠,他若無其事地從地上爬起來,自己賭氣一般坐到一邊,一副“我很生氣快來哄我”的悶騷樣子。
他這樣的舉止,讓我想起當初,他錦衣玉食,還要吹毛求疵,朝上一臉正經,下朝卻嬌氣又幼稚,有張靜若好女的面皮,便真把自己當作了個小姑娘,要人哄,要人疼,做了錯事撒嬌裝傻,當真嬌俏得緊。
而如今,他的皇后給他添堵,他的將軍懶得哄他,他就自己靜靜地坐在那里,像一尊美人像,我卻疑心他被氣得頭頂正在冒煙。
這已經是極大的進步了,至少他沒被氣哭。我坐到阮阮身邊,不敢嘲笑皇帝,阮阮卻老大不客氣,開口道:“陛下,您這嬌弱的身子,小心被風刮跑了。”
他斜睨了阮阮一眼,狹長的眸子里波光粼粼。我疑心他要哭了,攔住阮阮不許她多言。阮阮住了口,他也低下頭,修長的手指不知在膝上擺弄什么。過了片刻,他站起身,掌心托著一只紙疊的鴿子,風拂過,鴿子打著旋順著風被吹走。他眸中亮了亮,有些得意,像是藏著秘密的小孩子。
我心里“咯噔”一聲,我知道他藏著的秘密是什么。
當初他還是小太子時,大他五歲的異母哥哥嘲笑他是個文弱的娘娘腔,他忍著不哭,卻把自己氣成個圓滾滾的小包子。我氣不過,替他打了那個小混蛋一頓,然后就被罰跪在后花園一個時辰。
被欺負時他沒哭,看我跪的時候他卻哭得淚流滿面,一邊哭還一邊扯著袖子替我擋太陽。
我跪得筆直,還有心情跟他說笑:“別哭了,等你當上皇帝,我就當你的將軍,保護你一輩子。”
他哭得更兇了。我苦惱地想了想,掏出一只妹妹疊的紙鴿子塞到他手里:“阿穹,下次你不開心,就疊一只鴿子,對它說悄悄話,然后讓風把它帶走,它會把你的愿望告訴神仙,替你實現的。”
小小的鴿子停在他小小的掌心里,他總算笑了起來,梨花帶雨,美不勝收:“那我要許愿和你一直在一起,我做一輩子的皇帝,你做我一輩子的大將軍,一輩子不分開。”
風卷著小鴿子飛上了天,天上的神仙卻沒收到小太子的愿望。如今,他成了末路的皇帝,我成了手無寸兵的將軍,便是一輩子,大概也做不到了。
貳
只是他不該記得這些的。
初春時,傅丞相與雍王勾結,攻下了皇城,將他趕下皇位。我護他出逃時,因為一些意外,他失去了記憶。
就是這么爛俗,他失去了記憶,忘了自己是個皇帝,也忘了自己姓甚名誰。猶記得他睜著美麗的眼睛,茫然無措地望著我,我嘴動了動,還沒說話,阮阮冒出個頭來,軟軟喚道:“陛下,您忘了嗎?您出生時,國庫空虛,您父王為您取名‘正窮’,寓意皇家貧困,沒有余糧。”
他臉色變了,不可思議地瞪大眼:“所以……堂堂一國之君,叫‘正窮’?”
阮阮快樂地點頭,他卻郁悶至極,不敢相信自己的父皇取名如此沒水準。我被逗笑,在一邊輕笑出聲,他看了我一眼,眼中生出驚艷之色:“這位……好眼熟。”
他猶豫一下,又說:“這位姑娘是我的皇后,那你莫非是我的……男寵?”
我和阮阮一道沉默。他臨水自照,瞧了瞧自己的臉,又瞧了瞧我,大驚失色:“莫非我是你的男寵?”
很好,他確乎長得綺麗動人,而我也五大三粗,所以我揍他應該沒人有意見。
緊要關頭,他忽然開竅,雙眼一閉又暈了過去。阮阮戳戳他,問我:“師兄,以后我們怎么辦?”
當時正是暮色四合,一片織金如醉。我望了望前路,又瞧了瞧歸途,前路野草蔥蘢,卻也有一線生機,而歸途隱沒在皇城的繁華中,危機四伏,血腥殘忍。
我問阮阮:“你認識回淮江的路嗎?”
她點點頭,我苦笑一聲:“那我們就去淮江,投奔你爹,找我師父去。”
若不是萬不得已,我不會選擇這條路,當年叛出師門時,我一路跪過了刀山火海,傷得在床上躺了幾個月。我曾賭咒,龜兒子才會回去,沒想到如今時移世易,我卻要披荊斬棘地重新回去,做一只神志清醒的龜兒子。
李正穹昏在地上,一張曾經水潤白皙的小臉如今卻蒼白消瘦。我嘆了口氣,覺得如今的世道,能活著做只龜兒子也是件不易之事。
叁
一路上,雍王派出的殺手層出不窮。
雍王清君側之后,皇帝龍體不適,一病不起,如今已一命嗚呼了,而他以正統的名義登基為帝。
以上為篡位的雍王放出的偽官方說法,為了化偽成真,他一路上都不消停,一撥撥的殺手循著我們的行蹤前來刺殺,簡直像是春日里拔苗的韭菜,一茬接著一茬,茬茬都不是好打發的貨色。
時間久了,我難免力有不逮,竟在一次被人暗算中傷了手臂。
這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阮阮眼淚汪汪地捧著我的手臂替我包扎,李正穹卻瞧著倒了一地的尸體若有所思。我忍痛問:“陛下,別看了,太臟。”
李正穹歪著頭思索一陣,驚喜道:“我似乎想起來什么事。”
阮阮替我包扎的手緊了一下,我疼得齜牙咧嘴,掩蓋了不安的神色:“哦,想起了什么?”
我狀似無意地問,李正穹閉了閉眼,睜開時神色變得有些陰郁:“我似乎想起逃出皇城時的事情。”
他不開心是應該的,猶記當時,叛軍里應外合攻入禁宮,到處都是哭喊殺戮之聲,我在一片血雨腥風間艱難奔走,終于在他的寢宮里找到了他。
寢宮里濺了一地的血,他靜靜地坐在龍床上,手中一柄長劍染血,如玉面修羅,艷麗惑人。看到我來,他起身緊緊抱住我,我感覺到有冰涼的水滴滴落。他聲音哽咽,卻不肯放開我:“你來了,我就知道你會活著來找我,我想去找你,可是……”
話音落在一聲嗚咽里,他哭得有些顫抖,我也在顫抖,我摸到他背后長長一道刀傷,它提醒著我,我差一點就失去了他。
而我帶他出逃時,場面更加血腥。我們幾乎是踏著血海走出了宮門,我將他背在背上,他的血和淚一起滴下來。阮阮在我們身邊泣不成聲,只有我在笑,笑得咬牙切齒。
“阿穹,”我說,“我會幫你回來奪回你的一切,到時傷了你的人都要死。”
這是我這輩子說的最酷炫的一句話,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自己帥得令人心醉。只是現在,我這個帥得驚人的將軍,卻成了一個烤叫花雞十分了不起的高人,這個認知在李正穹和阮阮狼吞虎咽、贊不絕口時更加明晰。
我殘著一只手,解決了一只山雞,又將它拔毛放血,精心烹飪成一只芳香四溢的叫花雞。阮阮對我進行了數千字的贊美,我滿意地撕了只雞腿遞給她,坐在一邊的李正穹“哼”了一聲,我連忙撕了個雞翅給他。
他面色不虞,拿著雞翅問道:“為什么不給我雞腿?”
我奇怪地回道:“你不是從來只喜歡雞翅嗎?”
他這才心滿意足地吃自己的雞翅,吃完之后,他又和阮阮一番明爭暗斗,搶來了最后一只雞腿,阮阮氣呼呼地走到一邊。他獻寶般地將雞腿遞給我,嘴上卻傲嬌萬分:“瞧你受傷了,給你吃只雞腿補補。”
我猶豫一下,接過來啃了一口,感覺這只雞腿確實美味不凡,雖沒抹蜜,吃到嘴里竟甜滋滋的。
肆
阮阮問我:“師兄,我還要裝多久的皇后?”
她問的時候,我們正在過河,我先攙扶著李正穹走過了湍急的河面,又轉回來背著阮阮往對面走去。
阮阮伏在我身上,聲音悶悶的,我腳下頓了頓,又把她往上背了背。她將頭埋在我肩上,不開心地說:“師兄,我不喜歡他,況且他也不喜歡我。”
她說得對,她與李正穹分開看郎貌女貌,擺在一起卻貨不對版,怎么瞧都不似恩愛夫妻。
流水急急,帶著寒意一路漫流,我嘆了口氣,感覺自己這幾日嘆的氣趕上往昔數年的分量:“阮阮,師兄沒有辦法。”
阮阮的父親淮江王是本朝唯一一個異姓王爺,他一直想將自己的獨女嫁給李正穹,且也差點讓他成功了。而如今,李正穹是落架的鳳凰不如雞,想要得到淮江王的協助重回皇城,自然要許下重酬,比如娶阮阮為妻,立她為后。
若是李正穹沒失憶,這事想來做不到,幸好他失憶了,我與阮阮商議好,要她假扮皇后。因我知道,李正穹是個有擔當的男子,只要他想不起過去的事,他便會好好對自己的“妻子”,不說多么恩愛,至少能白頭偕老。
這事有些對不住阮阮,我又嘆了口氣,阮阮在我背上哭了起來:“師兄,你別嘆氣了,是我任性,我知道你也是為我好,我爹給我找的相公不是個好東西,還不如這個小皇帝。”
少女的眼淚晶瑩而美麗,我沒說話,沉默著渡過江去。江對岸站著的李正穹正翹首以盼,見我們平安歸來,“哼”了一聲解下身上披著的大氅丟過來,說道:“裹上吧,瞧你凍得臉白唇青的。”
這大氅帶著少年暖暖的體溫,我瞧瞧仍含著淚的阮阮,抬手披在了她的身上:“陛下,阮阮是您的妻子,您的好應該給她。”
李正穹似是沒想到,臉色幾變,最終沉了下來:“朕知道了。”他又說道,“將軍操心的事情真是多。”
阮阮生氣地替我說話,兩人話不投機,又吵了起來,我只覺得頭有點疼,晃了晃,暈倒了。
我竟變成了個弱不禁風的病包,這簡直荒謬。我與李正穹之間,從來是他負責貌美如花,我負責鐵骨錚錚。
記得當初,月下花前,他拈一本詩集,若一汪奢艷的影,映得一群美人心波蕩漾。而我就在一邊舞刀弄劍,不是舉大錘,就是舞長刀。
一次,我剛舉起長劍,他就生氣地把書重重一摔,我問:“陛下,怎么了?”
他瞪我一眼,像只鬧人的小貓,刁蠻得迷人:“以后你不準耍武藝!”
我挑眉不解,他卻忽然紅了臉,將眼神轉開:“那些小宮女都夸你又俊俏又英武,簡直搶了我的風頭!”
英俊瀟灑不是我的錯,我看看他,識相地把真相咽進了肚里——如李正穹這般美麗的男子,想來沒幾個女子會喜歡,因為沒人會愿意自己的夫君比自己還要動人。除非,那個女子是個傻瓜。
伍
我醒來的時候瞧到面前有張大臉。臉其實不大,只是湊得太近,我嚇了一跳。仔細一看,是李正穹正緊張地看著我。見我醒了,他綻開個笑臉,又記得在和我鬧矛盾,想收卻收不回去。
我被他逗笑,一咧嘴,只覺得唇上干澀。他見微知著,把水遞來,細心地喂入我口中:“你真是胡鬧,傷口化膿也不與我們講,現在發燒病倒了,讓我……們多擔心。”
他口上說得嚴肅,手下的動作卻格外溫柔,我不由得笑了。他也忍不住,傻瓜一樣又笑了起來。笑著笑著,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有點尷尬地清了清嗓子,問道:“那個……我一直不好意思問,你叫什么名字啊?”
笑容僵在我臉上,他緊張地說道:“我知道我們從小認識,只是我什么都不記得了,不是故意忘了你的。”
我倒慶幸你忘了我,我凝視他,半晌,垂下眸子輕聲說道:“我姓傅,傅離衣。”
他的笑容同樣僵住,有點傻乎乎地皺皺眉:“你姓傅,和你與我講的造反的傅丞相一個姓。”
“不錯,”我聽到我的聲音,干澀而凝重,“那個造反的傅丞相是我爹。”
我姓傅,是個將軍,我爹也姓傅,原職丞相,兼職造反。
雍王這個傻瓜,做了我爹的傀儡還不自知,天天開開心心地做著君臨天下的夢。我也是個傻瓜,好好的榮華富貴不享,護著個小皇帝逃出皇城,去投奔鬧翻了的師父。
若是他誤會我的身份,那我便先離開,再暗中保護他吧。
我正心酸地想著,李正穹卻忽然攬我入懷,摟得緊緊的:“你真是個傻瓜,離衣,我本不該說這些話的,可是你為我做了這么多,我要告訴你,我喜歡你。”
啊?畫風轉得太快,我愣住了,他卻一鼓作氣,想要再接再厲把我氣死:“縱使對不住列祖列宗,對不住我的皇后,我也要講,我喜歡你,就是當個斷袖,我也要喜歡你,離衣,你不準離開我。”
阮阮找水回來后偷偷問我:“師兄,你和陛下是不是鬧別扭啦?”
我微笑:“沒有呀,你怎么這么想?”
阮阮一臉不信,指著縮在角落的李正穹說:“他臉上那么明顯的巴掌印,不是你打的,還是他自己拍的不成?”
我略心虛,小聲說:“我幫他打蚊子。”
這話阮阮不信,我也不信,這樣揍當朝天子的事,放在當初我是萬萬做不到的。只是當他說他要當個斷袖時,我只覺自己腦子中有根筋斷了,三觀也碎了一地,這才做出這等犯上之事。
從這天起,我便有些躲著李正穹,他看出來后,一開始用“你這負心人”的眼光瞧我,過了幾日換上“你無情你無理取鬧”的神色,最后卻只傷心而克制地偷偷瞧我。
這讓我覺得自己真的成了個負心漢,阮阮也說:“師兄,我覺得小皇帝最近有點可憐。”
可憐也沒辦法,我總不能真讓他成了個斷袖。
陸
我硬起心腸,帶著他們披星戴月,一路神擋殺神,佛擋弒佛,終于到了淮江。
踏上淮江梅山那日,天下著小雨,阮阮開心地蹦了兩蹦,李正穹也稍稍放松了些。
淮江王將自家府邸修在高高的梅山山頂,居高臨下地望著自己的屬地,我一撩衣擺,跪在了山腳。
阮阮為難地說道:“師兄,你跪在這里做什么,爹爹早就原諒你了。”
我笑笑:“阮阮,別騙我了,我壞了山里的規矩,現在想回來,自然有別的規矩等著我。”
可能想表揚我說得對,山上幾道身影飄飄蕩蕩,向著我們逼近。阮阮一跺腳,說:“我去找爹爹,讓他親自和你說。”
這正合我意,我笑笑,忽然叫了聲:“阿穹。”
這么些日子沒有理他,聽我喚他,他竟露出受寵若驚的神色:“離衣,你有什么事?”
我示意他低頭,他就樂呵呵地半跪在我身邊,然后被我一掌打暈了過去。
阮阮連忙接住他,我說:“乖,帶著他去找師父吧,我和師弟們敘敘舊。”
山上的影子飄到了身邊,幾個青年站在我們面前,一色的故人,一色的面無表情。
我說:“師弟們,好久不見。”
他們互相交換個眼神,向著我斂衽而拜:“師姐,好久不見。”
小師弟帶著阮阮走了,我嘆了口氣:“給我上琵琶鎖吧,也好去給師父他老人家行個禮。”
大師弟卻道:“師姐說笑了,您身中奇毒,師父最疼您,又怎么舍得廢了您的武藝呢?”
我被帶上了梅山山頂,師父像往常一樣坐在院子里,面色慈祥地拈著棋子下一局殘棋。我有些恍惚,像是從來不曾離開這里,自己還是梅山大弟子,學藝有成,師徒和睦。
只是那都是癡心妄想,梅山不收外姓女子,便是像我這樣天賦異稟、俊朗不凡的女子也不收。當初我年少輕狂,穿了男裝,取了佩劍便上了山,坑蒙拐騙,總算入了師門,學了師門絕學,自覺得意非凡。
只是這是大錯,我越是學藝有成,越是罪孽深重。發現我是女子那日,師門震動,百年門規因我而破,師父怒不可遏,差點一掌拍死我。還好一群師弟跪地替我求情,而阮阮更是以死相逼,我方才留下一條生路。師父開護山大陣,我赤腳走過九十九尺炭火路,空手越過三十三尺白刃山,血灑梅山,卻贖不了這欺師滅祖的大罪。
師父忽然問我:“你護著他來,是想求我助他奪回皇位?”
我不語,師父卻笑了:“你要幫他奪你爹的權?”
“求淮江王揮兵北上,除反王,扶社稷,救江山。”我跪在地上,沖他深深叩頭,“李正穹才是正統,是天命所歸,我不是幫他,我是幫正義。”
師父摸摸胡子,還是那么祥和:“你們兩個,一人服下‘相思’,一人服下‘相忘’,為師很感動。你去讓小皇帝對你死心,我便幫他,如何?”
還能如何?我重新叩頭,心悅誠服地道謝:“師父的大恩大德,徒兒沒齒難忘。”
柒
我好好休養一夜,泡了個澡,吃了頓飽飯,又踏踏實實睡了一覺。
第二日,天光晴好,梅山之上百里梅花灼灼綻開,李正穹羞羞答答地舉著一枝白梅在我門口徘徊,我猶豫一下,推門而出。
薄薄的光照進院中,他站在一片光芒璀璨中,笑容溫柔,卻又頓住。
他瞪大眼瞧我,說道:“你竟是個女子?”
我理了理自己長長的袖,又撫了撫鬢邊正紅的牡丹,沖著他嫣然一笑:“對呀。”因著阮阮自幼喚我“師兄”已成習慣,哪怕當年事發之后也未曾改口,是以一路上李正穹從未懷疑過我男子的身份,所以現在他這般反應,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他徹底呆住,我卻在仔仔細細打量他,也許每一眼都是最后一眼。我想,我是這樣喜歡一個人,萬死莫辭,卻不能說給他聽。
還好,他也喜歡我。
我伸出手來,接過他手中的梅花,而后說道:“你那天說你是個斷袖,我打了你,是因為我斷不會愛上一個斷袖。”
“你的意思是……”他的眼里爆出光芒,像是落了滿天的星,“我不是斷袖的話,你就會喜歡我?”
我笑而不語,輕輕嗅了嗅白梅,他又紅了臉,有點羞,有點惱,有點竊喜,像是當初大婚時,他用喜秤輕輕挑起我描金繪鳳的大紅蓋頭,紅燭下,他的臉上染著薄紅,如緋似霞,倒比我這個新娘子美上不少。
自己的夫君美得如此如魔似幻,我心生不悅,干脆捏起他的下巴,色瞇瞇道:“哪里來的小娘子,這么美,小心被人輕薄了去。”
他呆了呆,似是不信竟被自己的娘子輕薄了。我得意揚揚地展顏一笑,正要放開他,萬萬沒想到,他忽然眼波流轉,上前壓倒了我:“回官人的話,奴家是來找奴家負心的夫君的,她姓傅,名離衣,乃奴家的皇后,不知官人可有見過?”
少年好聞的氣息布滿我的鼻端,我僵住,臉上飛快地蔓延開紅暈。他似我之前得意一笑,卻萬分溫柔,而后他輕聲喚我:“娘子。”
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日,我們當著滿朝臣子,上告知天,下通于地,結發為夫妻,皇帝和皇后恩愛永年。
只是這幸福終結于叛亂,我爹謀權篡位,我與李正穹會合后寡不敵眾,雙雙被俘。
爹問我:“傅家滿門都比不過一個李正穹嗎?”
我不語,只是一下下地叩頭,叩得額頭染血。
翻云覆雨的傅丞相長嘆一聲,示意下人端出兩只瓷瓶。“離衣,”他一手支額,一手拿過一只瓷瓶遞給我,“一顆‘相思’,一顆‘相忘’,你和李正穹一人一顆服下,我便放你們走。”
“相思”和“相忘”是相生相伴的奇藥,服“相思”必死,嘗“相忘”忘情。爹爹拍拍我的頭,親手把藥放入我手中:“離衣,爹希望你做出正確的選擇。”
捌
我被送入李正穹關著的牢里,瞧到他被雍王打得遍體鱗傷。他們兄弟倆從小就不對付,小時候我還仗著力氣大替他揍過雍王,長大了卻無能為力。
我扶起他,將頭埋在他肩上哭了。他疼得齜牙咧嘴,還笑著安慰我:“傻瓜,哭什么哭,我可是你爹的女婿,你爹怎么也不會殺了我的。”
我被他逗笑,眼淚卻簌簌掉下來,我說道:“你還記得小時候許的愿嗎?”
他說:“記得,我做一輩子皇帝,你做我一輩子的將軍。唉,當初太傻了,怎么沒想到讓你做我的媳婦呢?”
牢外監視的人不耐煩地咳了一聲,我把一顆藥塞到他嘴里,說:“那你改改愿望,我們白頭偕老好了。”
我看懂了我爹的暗示,分辨出了哪顆是“相思”,就把“相忘”塞給了李正穹,自己服下了“相思”。我知道這和他理解的正確不同,卻是我心底的正確。
后來,我們被來皇城游玩的阮阮從牢里救了出來,殺出一條血路,總算踏上了逃亡的道路。“相忘”藥效發作,李正穹失了記憶,“相思”卻深埋心底,未曾要了我的性命。
這一路走來,他重新愛上了我,這是我的幸事,亦是我的痛苦。
我抬起頭來,沖著李正穹微微一笑,而后在他唇上深深烙下了一吻。這是最后的一個吻,我點了他的穴道,告訴他:“阿穹,我要走了,一路護送你,算是成全了你我的君臣之情。只是生恩難報,我終究要回到我爹身邊輔佐他,憑我爹的權勢,沒準能撈個公主當。”
他瞪大眼,不可置信地瞧著我,我別開眼去,轉身想要離開。
“離……衣……”身后他叫我的聲音斷斷續續,我沒想到他竟能沖開啞穴。回頭時,我瞧見他又哭了,流了一臉的淚,唇邊沾著血,烈烈的,像一枝開謝了的紅梅。
唉,都要分開了,還是注意點形象吧。我忍住淚,沖他笑了笑,只覺心口有把尖刀戳來搗去,又像是春花成灰,零落成泥卻也無處可訴的相思之苦,磋磨得人如怨如慕。
“相思”竟然在這個時候發作,我同他一樣,嘔出一口血來,卻終究沒有停住步子。
我沒騙他,我本就打算好了,將他送到淮江王身邊后,便要回去皇城。這世間之事真是難說,當初我以為只有傻瓜會喜歡李正穹,后來我以為我會一輩子和他在一起,想想轉頭都成了空。
身后的少年聲聲泣血,而我步步行來,亦淚如泉涌。我想,我服了“相思”,終究要死,為什么死之前不替他最后做一點事呢?
玖
重回皇城那日,天有小雪,如絮輕沾。
皇帝站在城頭上,遙望遠方。四野無邊,寂靜空闊,有雪的味道送入鼻端。皇帝恍然間,似是看到城墻下,有人容色艷烈,如長刀染血,美且肅穆。
只是不可能,他想看到的那人早在三年前便已死去。三年前,他還在淮江毫無斗志,得過且過。一日,忽有一紙死訊傳來——傅丞相之女刺殺雍王,又在群臣面前怒斥傅丞相身負皇恩,無君無父,而后大笑三聲,自城墻一躍而下,當場斃命。
阮阮將死訊告訴他時,他不肯相信,阮阮給了他一記耳光,自己卻哭得比誰都傷心。
“你若不奪回皇位,怎么對得起師兄對你的一番情意?”
阮阮這樣說,他卻沒聽到心里去,只是想,她來了又走了,瀟灑如風,卻把他的心填得滿滿的。而如今,她死了,他的心里也空了,便是江山如畫,又與誰人共賞呢?
自然是無人共賞了,只是她的一片心終究不能辜負。
他振作起來,揮軍北上,三年間,不知多少艱難險阻,每一次他以為自己要死了,便疊一只小鴿子放入風里,只是想許愿,死后能再見她一面。可惜她大概不想重逢,每次他都化險為夷,終究重新登上了皇位。
他也曾遍尋良醫,想解開“相忘”,期間斷斷續續記起一些事來,記得多了,便也知道自己曾多愛慕一個女子,縱使她不溫柔、不嬌俏,只愛舞刀弄槍,自己卻義無反顧地愛上了她兩次。
記憶最深的卻是一次他的生辰,她單膝跪地,青絲淌了滿背,而她眸中溫柔閃亮,直直看向他的心底,說道:“青史翻涌,史書成誦,若過百年,又是哪家稱王,哪家稱帝。只是愿我王史上一筆,只留英名,不見污跡,臣愿以此身,助陛下肋生雙翼,直上九霄。”
那一刻,滿堂皆靜,而他的心卻在她的視線里歡呼雀躍,自此心無旁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