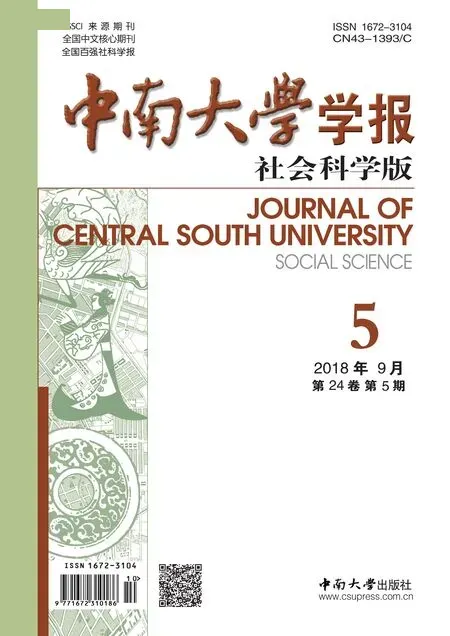論監察留置的適用條件
王飛躍
?
論監察留置的適用條件
王飛躍
(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湖南長沙,410004)
盡管公職人員的犯罪、違法、違紀乃至不道德行為,都屬于監察的范圍,但適用留置需以“貪腐瀆職”來劃分監察機關與偵查機關查辦犯罪案件的權限,因而“貪腐瀆職”是適用留置的前提條件。“涉嫌犯罪”作為留置適用的決定性條件,是區分針對不同性質的監察案件采取不同類型的監察調查措施的核心因素。“涉嫌犯罪”包括與職務有關行為的危害程度已經涉嫌犯罪以及相關的證據或者線索可以證明或者指向涉嫌犯罪的事實兩個方面。“逃避追責”是留置適用的選擇性條件,是區分針對不同類型的被調查人采取不同類型的監察調查措施的主要依據,其目的在于在保證案件調查得以順利進行的同時,能夠使被調查人的人權得到最大化的保障。
監察留置;貪腐瀆職;涉嫌犯罪;逃避追責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以下簡稱為《監察法》)第22條規定了留置的適用。刑事法學界普遍認為,適用逮捕時應考慮嫌疑人同時符合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等三項要件[1?3]。由于留置作為最為嚴厲的監察措施,其強度與逮捕相當,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并涉及機關權限[4],且從淵源上來看,監察委員會對職務犯罪的調查權所承接的是以往屬于檢察機關的自偵權,因而在適用留置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監察措施時,應當重視《刑事訴訟法》有關刑事拘留、逮捕的成熟規定和長期實踐[5]。逮捕的適用條件雖有助于留置適用條件的理解,但并不能照搬,因為留置的適用面臨如下問題:第一,在公職人員涉嫌犯罪的情形下,究竟是由監察機關適用留置還是由刑事偵查機關適用拘留、逮捕,涉及到監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職責劃分。第二,從《監察法》第22條的規定來看,對于“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也可以適用留置,是否無需參照刑事訴訟過程中逮捕適用的刑罰要件。第三,羈押必要性審查是限制羈押性刑事強制措施適用的重要手段,監察留置的應否考慮留置必要性。
一、貪腐瀆職:留置適用的監察調查權限條件
《監察法》第3條規定監察委員會“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以下稱公職人員)進行監察,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第15條通過列舉的方式對第1條規定的“公職人員”和有關人員(以下簡稱監察對象)的范圍進行明確:①中國共產黨的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民主黨派各級組織機關和各級工商業聯合會機關的公務員,及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管理的人員。②法律、法規授權或者受國家機關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務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③國有企業管理人員。④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⑤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集體事務管理的人員。⑥其他依法履行公職的人員。《監察法》第34條第2款還規定“被調查人既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又涉嫌其他違法犯罪的,應當由監察機關為主調查,其他機關予以協助。”《監察法》的前述規定,是否意味著只要是公職人員涉嫌犯罪就可以由監察機關適用留置?這涉及監察調查與刑事偵查的權限劃分。因而首先得明確監察機關調查犯罪案件的范圍,只有在監察機關調查犯罪案件的范圍內才可以適用留置,這是留置適用的前提條件。
《監察法》第3條以“身份”為依據確定監察范圍。但不能將監察范圍作為劃分監察調查與刑事偵查權限的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40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公安機關是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雖然監察全面覆蓋公職人員,但不能由此得出公職人員的犯罪全部納入監察調查范圍,因為:
第一,監察范圍大于監察調查范圍。《監察法》第3條確定了監察范圍,《監察法》第11條規定監察委員會具有“對公職人員開展廉政教育,對其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從業以及道德操守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法作出政務處分決定;對履行職責不力、失職失責的領導人員進行問責;對涉嫌職務犯罪的,將調查結果移送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提起公訴;向監察對象所在單位提出監察建議”的職責,這一規定從行使“監督”“調查”“處置”等三種不同類型的監察職權對監察范圍事項的處理權限進行劃分,其中只能“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也即調查范圍明顯小于監察范圍。
第二,監察調查的中心任務是反腐。監察機關的核心使命決定了留置的范圍為“貪污瀆職”。雖然,一方面,《監察法》將公職人員的犯罪、違法、違紀乃至不道德行為,都得納入監察的范圍,因為監察權應當成為促進權力善治并提升權利保障的基礎,因而不僅應當具有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制止權力腐敗運行的消極面向,同時也應當具有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國家善治的積極面向[6]。另一方面,正如王岐山指出的那樣——監察委員會實質上是反腐敗機構[7],國家監察委員會的核心使命是反腐敗[6],而貪腐瀆職犯罪“嚴重破壞公共權力的運行秩序,侵害社會公平正義,損害國家和政府的威信與公信力,阻礙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社會穩定構成現實的危害與威脅”[8]。《監察法》第39條規定:“經過初步核實,對監察對象涉嫌職務違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責任的,監察機關應當按照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辦理立案手續。”“監察機關主要負責人依法批準立案后,應當主持召開專題會議,研究確定調查方案,決定需要采取的調查措施。”可見,只有針對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才能通過立案開展調查 工作。
第三,牽連管轄規則并未改變監察調查與刑事偵查的職能。盡管《監察法》規定“被調查人既涉嫌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又涉嫌其他違法犯罪的,應當由監察機關為主調查,其他機關予以協助”,但是,一方面,由于監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調查權是由以往屬于檢察機關的自偵權劃轉而定,而以往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職能管轄的分工是以罪名為標準進行劃分的,因而劃分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各自管轄的范圍依然應當遵循以罪名為標準進行劃分這一規則。另一方面,以往刑事偵查過程中也存在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牽連管轄問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2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偵查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涉及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應當將屬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機關。在上述情況中,如果涉嫌主罪屬于公安機關管轄,由公安機關為主偵查,人民檢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屬于人民檢察院管轄,由人民檢察院為主偵查,公安機關予以配合。”因此,不論是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為主”與“配合”或者監察機關與公安機關的“為主”與“協助”,并非對職能管轄的改變,而只是解決如何分工合作的問題。因此,只有涉嫌“貪腐瀆職”犯罪的案件才由監察機關管轄,公職人員涉嫌其他犯罪的,仍由公安機關管轄,“貪腐瀆職”是監察調查與刑事偵查權限劃分的依據。對于公職人員的性騷擾行為、婚外情行為、公職人員雇傭他人報復阻礙自身職務升遷或威脅自身現有職務的犯罪等行為、對于公職人員的嘴亂吃、手亂拿、腿亂走以及打牌、酗酒等不良嗜好等行為,盡管都屬于監察的范圍,因為《公務員法》將“模范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紀律,恪守職業道德,模范遵守社會公德”、《中國共產黨章程》將“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提倡共產主義道德,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等作為一項義務和紀律進行要求,但如果不屬于貪腐瀆職,哪怕涉嫌強奸罪、賭博罪、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這些均屬于刑事偵查機關的職責范圍)等等,也不能適用留置。
二、涉嫌犯罪:留置適用的案件類型條件
《監察法》第22條規定的留置條件中有“被調查人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監察機關已經掌握其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這一內容,是否意味著對于“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也可以適用留置?答案是否定的。
(一) 對于單純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不能適用 留置
如果根據《監察法》第22條的規定認為留置可以適用于職務違法案件中的被調查人,實際上誤解了該條規定含義。因為:
第一,對于職務違法案件中的被調查人適用留置沒有賴以依存的制裁基礎。與逮捕類似,留置剝奪了被調查人的人身自由。但不論是逮捕還是留置,均屬于保障性措施(保障監察調查或者刑事偵查工作的順利進行),而非制裁性措施;而剝奪人身自由的保障性措施只有在存在剝奪人身自由的制裁性措施具有適用可能性的情形下才有合法性基礎。刑事訴訟過程中適用逮捕的條件之一是“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即逮捕期限可以折抵將來適用的羈押性刑罰,這是逮捕這一保障性措施賴以依存的制裁基礎。而對于職務違法案件的被調查人,根據《監察法》第45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對違法的公職人員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決定”,并沒有適用羈押性制裁措施的可能性,留置期限也就不具有折抵相應政務處分的可能性,因而對于職務違法案件的被調查人適用留置不具有賴以依存的合法制裁措施的基礎。
第二,對于“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適用留置有違處罰法定原則。由于留置并非法定的處罰措施,而是法定的保障性措施,但留置又剝奪了被調查人的人身自由,因而即便職務違法行為屬于“嚴重”的情形,對被調查人適用留置也不符合處罰法定原則,因為被調查人在最終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政務處分”之前,已經因為適用留置而被剝奪了人身自由,而法定的職務違法處罰措施并不包含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使得被調查人實際受到的處罰超越了法定處罰的范圍。
第三,對“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適用留置須同時符合附加條件。《監察法》第22條規定的對“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適用留置,是以“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為附加條件的。“嚴重職務違法”與“仍有重要問題”的合并必須達到涉嫌犯罪的程度。因而對于單純的“嚴重職務違法”,即便“仍有重要問題”,如果沒有達到涉嫌犯罪的程度,不能適用留置。因此,在監察案件的調查過程中,只有對涉嫌犯罪案件的被調查人才能適用留置,對于“嚴重職務違法”的被調查人只有在“仍有重要問題”使得被調查人涉嫌犯罪的情形下,才能適用留置;對于單純的職務違法案件中的被調查人不得適用留置。
(二) 涉嫌犯罪包括危害程度與證據充足程度
“已經掌握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以及“涉及案情重大、復雜的”同為“涉嫌犯罪”條件中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危害程度,即與職務有關行為的危害程度已經涉嫌犯罪,二是證據充足程度,即有相關的證據或者線索可以證明或者指向涉嫌犯罪的事實。
留置只能適用于涉嫌與職務關聯的犯罪案件,對于雖與職務關聯,但僅僅屬于違法、違紀以及不道德的行為,不能適用留置。在理解涉嫌犯罪時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涉嫌犯罪存在三種類型,其一是“已經掌握的事實”涉嫌犯罪,也即“已查事實”涉嫌犯罪;也可以是“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涉嫌犯罪,也即“待查事實”涉嫌犯罪;此外,已查事實與待查事實均涉嫌犯罪。第二,涉嫌犯罪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事實方面,即存在涉嫌犯罪的事實;二是指危害程度方面,即相關事實的社會危害已達到犯罪的程度。第三,涉嫌犯罪是一個綜合判斷——既可以是“已查事實”涉嫌犯罪,也可以是“待查事實”涉嫌犯罪,還可以是“已查事實”與“待查事實”綜合起來判斷涉嫌犯罪,如已經掌握涉嫌受賄2萬元的事實,另有線索指向涉嫌受賄2萬元的事實。
對于證據充足程度,應當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已查事實”應當有相應證據。留置適用于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犯罪,這些違法犯罪適用留置時應當有相應證據予以證明,但適用留置的每一個案件不應當采用完全一致的證據標準,而應當采用“求同存異”的證據標準。所謂“求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所有的適用留置的案件都應當有最基本的統一的證據標準——能夠證明違法犯罪事實存在,能夠證明違法犯罪事實與職務關聯,能夠證明有不正當履職的事實存在;二是指涉嫌相同性質的違法犯罪在證據標準方面應當有一定的共同要求,如對于所有受賄犯罪,在受賄事由、賄賂的給予與收受、賄賂與職務的關系方面的證據都應大體保持一致。所謂“存異”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不同個罪的證據類型可以適當區別,比如受賄與貪污,一般情況下,受賄犯罪的主要證據是言詞證據,貪污犯罪的主要證據是書證。二是指不同個案的證據狀況可以適當區別。如對于新近發生的賄賂行為與年代久遠發生的賄賂行為,在對待口供客觀真實性的把握方面可以適當區別,一般情況下,對于僅憑口供認定年代久遠的賄賂行為應當更為嚴格。第二,在“已查事實”涉嫌犯罪的情形下,“待查事實”只要有可靠的線索指向相應的涉嫌犯罪的事實即可。因為已經掌握相應證據證明“已查事實”存在,也即意味著被調查人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即便“待查事實”最后不能查明屬實,對其適用限制人身自由的留置措施也具有相當的正當性。第三,在“待查事實”涉嫌犯罪的情形下,“已查事實”是前提。如果“已查事實”單獨評價尚未達到犯罪的程度,而是“待查事實”達到犯罪的程度,或者“待查事實”與“已查事實”綜合評價達到犯罪的程度,必須以掌握部分違法事實的證據為前提。因為如果僅僅有線索指向相應的涉嫌犯罪的事實,這只是符合監察案件的立案條件,畢竟監察立案與留置適用是兩個不同的階段,在僅夠立案條件的情形下,貿然適用留置措施,不利于人權保護。《監察法》已將這里的“違法”限定為“被調查人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當然不包括獨立于職務范圍之外的賭博、吸毒、酒駕等行政違法行為,更不包括獨立于職務范圍之外的違反合同約定等民事違法行為、見死不救等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有觀點認為,公務員、法官、檢察官等人員違反內部工作規則的行為,應當由其所在國家機關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力,不應該由監察機關進行監察,也即“職務違法”不包括違反內部工作規則的違法行為[9]。這一觀點不敢茍同,就如該學者列舉的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法》第101條規定的“不按編制限額、職數或者任職資格條件進行公務員錄用、調任、轉任、聘任和晉升的;不按規定條件進行公務員獎懲、回避和辦理退休的;不按規定程序進行公務員錄用、調任、轉任、聘任、晉升、競爭上崗、公開選拔以及考核、獎懲的;違反國家規定,更改公務員工資、福利、保險待遇標準的;在錄用、競爭上崗、公開選拔中發生泄露試題、違反考場紀律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開、公正的”等行為,情節嚴重的構成犯罪,當然屬于監察委的監察范圍。第四,在“待查事實”涉嫌犯罪的情形下,“待查事實”與“已查事實”應當具有關聯關系。如果“已查事實”雖有相應的證據但未達到犯罪的程度,而“待查事實”雖達到犯罪的程度但與“已查事實”沒有關聯關系,則不能適用留置,因為“待查事實”屬于適用其他罪名的犯罪,也僅夠立案的程度,此種情形下不能采取留置措施。關聯關系包括以下情形:一是同一事實之間具有關聯關系。被調查人因同一事由先后多次收受同一行賄人的賄賂,其中有一次受賄的證據已經掌握,其余幾次受賄有相應線索,其余幾次受賄與已經掌握證據的事實之間有關聯關系。二是同類事實之間具有關聯關系。同類事實的部分事實已經掌握相應證據,如被調查人在前后幾個建設項目中先后收受了甲乙丙丁四個人的財物,被調查人收受甲財物的證據已經掌握,收受乙丙丁財物有相應線索,被調查人收受乙丙丁財物與收受甲財物之間有關聯關系。三是“已查事實”是“待查事實”的結果。雖然獨立于職務范圍之外的賭博、吸毒等行政違法行為不屬于職務違法的范疇,但如果賭博、吸毒等行政違法行為已經查實,而且賭資、毒資的來源與職務有關的,那么“已查事實”是“待查事實”的結果,二者之間具有關聯關系。四是“已查事實”是“待查事實”的表現形式。如部門或者單位違規發放津補貼,而這些津補貼并非來源于財政撥款或者并非由單位財務支出,在已經掌握違規發放津補貼的相關證據的情形下,必然可以指向貪污、單位受賄等待查事實,此種情形下,違規發放津補貼就是貪污、單位受賄等待查事實的表現形式,二者之間具有關聯關系。需要說明的是共同犯罪案件、職務犯罪中的“本案”與“原案”、瀆職犯罪與“后案”之間并非此處的關聯關系,因為共同犯罪案件以及互涉案、瀆職犯罪的“本案”與“前案”、職務犯罪與“后案”的事實和證據在很大范圍內是相同的,可以直接適用“已查事實”涉嫌犯罪的規定①。
三、逃避追責:留置適用的被調查人類型條件
在“對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的人”以及“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已經掌握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的情形下,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適用留置,是否適用留置還取決于被調查人是否存在“可能逃跑、自殺的”“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情形,對此,我國刑法學理論在討論逮捕制度時一般稱之為“社會危險性”,但適用留置的社會危險性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關于逮捕的社會危險性存在區別,逮捕的社會危險性除了前述情形外,還包括“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的情形。不過有學者認為,“可能實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不應作為逮捕的理由,理由在于:在沒有證據證明的情形下,所謂的“可能”或者“現實危險”都是主觀推測,以其為依據適用逮捕極其隨意;而如果有證據證明前述情況客觀存在,則完全可以憑據“可能實施新的犯罪”將其予以逮捕[2]。“可能逃跑、自殺的”“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可以歸結為“逃避責任”,因為前述“逃跑”“自殺”等情形是在貪腐瀆職等犯罪事實敗露后,企圖逃避承擔刑事責任,而“串供”“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等情形,則為企圖通過阻止相應犯罪事實得以查明的方式逃避承擔刑事 責任。
“逃避責任”作為留置適用的條件,目的在于通過區分不同類型的被調查人限制留置的適用范圍,以避免這一監察措施過多地限制剝奪為憲法所保護的人身自由權利;同時避免因為長期羈押被調查人導致的“刑期倒掛”現象——法院對因為偵查(監察調查)、審查起訴階段超期羈押而對被告人“關多久,判多 久”[3,10,11]。在理解“逃避追責”條件時,應當注意以下方面:第一,應當嚴格區分“逃避責任”與“避免麻煩”。一般情況下,被調查人知道自己可能接受調查,即便明明知道自己無罪,也擔心因為頻繁的接受問話甚至會被限制人身自由而心生恐懼,從而產生“惹不起躲得起”的心理,以致產生逃跑的想法,因而應當嚴格區分“逃避責任”與“避免麻煩”。二者的區分還是取決于留置適用的決定性因素——有證據證明“涉嫌犯罪”,如果沒有證據證明“涉嫌犯罪”,不能單憑被調查人有逃跑的跡象而對其適用留置。第二,對于輕罪案件堅持“留置適用例外原則”。對于涉嫌犯罪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被調查人,一般情況下不適用留置,其理由在于:一是被調查人具有適用緩刑的可能,對其適用留置,很大程度上剝奪了其適用緩刑的可能,因為一般審前羈押的嫌疑人、被告人適用緩刑的比率很小,特別是羈押一年半以上的罪犯,適用緩刑的意義不大。二是避免“刑期倒掛”的現象,如前所述,法院“關多久,判多久”的根本原因是被告人被長期羈押,使得原本刑期可以短于羈押期限的被告人被判處與羈押期限相同的刑期。三是體現懲治貪腐犯罪中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②。在貪腐案件中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方式之一就是對于犯罪輕微的被調查人,可以通過不適用留置來落實這一刑事政策。確有證據證明被調查人有逃避責任可能的,如被調查人有關閉手機、與外界斷絕聯系、收拾行李或者購買車票等情形的[10],可以認定其有逃跑的可能,如被調查人存在書寫遺書、有悲觀厭世、抑郁等情形 的[12],可以認定其有自殺可能。第三,對于重罪案件的“逃避責任”可以適用推斷。由于調查初期本來任務重、時間緊,如果在調查被調查人涉嫌違法犯罪事實的同時,還要求辦案人員花費很多時間精力去收集證明被調查人有“逃跑”“自殺”“串供”“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等證據,顯然違反辦案規律。因而一般情況下,對于涉嫌的犯罪可能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調查人,結合我國貪官外逃、自殺的現狀③,只要其涉嫌犯罪的事實有相應的證據予以證實,運用依據經驗法則以現存事實為基礎推斷發生某一未來事實可能性的間接證明方法[13],可以合理推斷其具有逃避責任的可能[14]。
四、留置適用中三個條件的關系
我國學界關于適用逮捕的三項要件之間的關系存在分歧。近些年逮捕存在“審前羈押率偏高”“審查方式司法程度低”“逮捕把關不夠嚴格”的問題,導致了“冤假錯案讓司法蒙羞,嚴重損害了法治和司法公信”[3],因而不少學者在將冤假錯案的“罪魁禍首”歸結為逮捕的同時,也對證據要件、刑罰要件和必要性要件在逮捕適用中的作用進行了分析,不少觀點認為社會危險性是適用逮捕的決定性因素[15,3],進而提出了證明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的證據包括兩種類型——“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和“專門用來證明社會危險性的證據”,如證明犯罪嫌疑人“有吸毒、賭博惡習”“曾經自殺、自殘或者逃跑的”等[15]。我國不少地方檢察院專門就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嘗試了風險評估機制,如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的未成年人非羈押措施可行性評估制度、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檢察院的《逮捕必要性評估參考標準(試行)》、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檢察院開展的對流動人口輕微刑事犯罪不捕的風險評估,等等[16]。更有學者提出了應當用品格事實而非犯罪嫌疑涉嫌的犯罪事實來證明社會危險性的存在[17]。這些理論探索與實踐嘗試都是以社會危險性系逮捕的決定性因素作為基礎的。與此類似,就留置適用的“貪污瀆職”“涉嫌犯罪”以及“逃避責任”也存在三個條件的關系問題,是否應當以“逃避追責”作為留置適用三個條件中的決定性條件的問題。
本文認為,留置適用中的決定性條件應當是“涉嫌犯罪”,理由如下:
第一,目前一些錯捕案件之所以被法院宣判無罪或者由檢察機關的公訴部分作出不起訴,恰恰是因為證據條件沒有把握好,而不是因為社會危險性的判斷錯誤,因為社會危險性的判斷錯誤與宣告無罪、檢察機關公訴部分作出不起訴的結論沒有任何關系。有學者提出錯誤的偵查并不必然導致錯誤的審查逮捕、錯誤的審查逮捕并不必然導致錯誤的審查起訴,錯誤的審查起訴也并不必然導致錯誤的有罪判決[18],筆者深以為然。如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有1.4%的案件捕后不作犯罪處理(包括判處無罪、絕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存疑不起訴、撤銷案件),有6.5%的案件捕后判處徒刑以下刑罰(包括拘役、管制、單處罰金)[3],恰好證明: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是查明事實真相、正確適用法律最基礎性的工作,只要在偵查、批捕、審查起訴等任何一個環節能夠把好證據關,錯誤的偵查、錯誤的逮捕和錯誤的提起公訴都將不是“錯誤”[18]。
第二,過于關注社會危險性,而忽視證據條件、刑罰條件,恰恰是導致超期羈押乃至導致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如依據社會危險性,嫌疑人翻供當然不具有如實供述的情節,而不論是審查逮捕還是羈押必要性審查,對于不具有如實供述特別是翻供的嫌疑人,顯然認為其具有社會危險性。此時,不論是審查逮捕的檢察官還是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的檢察官關注的是因為嫌疑人翻供而具有社會危險性,因而需要予以逮捕或者繼續羈押,而不是從嫌疑人翻供這一情形出發重點審查該案在證據方面存在哪些問題,并由此不予逮捕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故而造成了超期羈押乃至冤假錯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危險性理論恰恰是導致超期羈押乃至冤假錯案的危險所在。因而對于留置的適用,決定性因素不是“可能逃跑、自殺的”“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銷毀、轉移、隱匿證據的”“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等社會危險性情形,而應當是“涉嫌犯罪”的判定。
因此,在留置適用中的“貪腐瀆職”“涉嫌犯罪”“逃避追責”三個條件當中,“貪污瀆職”作為監察機關調查涉嫌犯罪的權限依據,是留置適用的前提條件;“涉嫌犯罪”作為監察機關區分職務違法與職務犯罪兩種不同類型的案件以及是否存在犯罪事實、犯罪證據的案件類型依據,是留置適用的決定性條件;“逃避追責”作為監察機關區分不同類型被調查人的依據,是留置適用的選擇性條件。
注釋:
① 關于職務犯罪中的互涉案、瀆職犯罪的“本案”與“前案”、職務犯罪與“后案”的關系,參見向澤選:《職務犯罪關聯案件偵查管轄的完善》,《河南社會科學》2011 年第4 期,第18-19頁。
② 貪腐犯罪中適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可參見何家弘:《寬嚴相濟與中庸反腐》,《法學家》2015年第5期,第16-28頁。
③ 關于我國貪官外逃,可以參見陳雷:《當前我國貪官外逃 的基本特點及預防措施》,《政法論壇》2009年第1期,第175-185頁。
[1] 劉計劃. 逮捕審查制度的中國模式及其改革[J]. 法學研究, 2012(2): 122?142.
[2] 陳永生. 逮捕的中國問題與制度應對[J]. 政法論壇, 2013(4): 17?35.
[3] 孫謙. 司法改革背景下逮捕的若干問題研究[J]. 中國法學, 2017(3): 22?48.
[4] 鄭賢君. 試論監察委員會之調查權[J]. 中國法律評論, 2017(4): 111?121.
[5] 趙曉光. 規范監察留置程序[J]. 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2018(4): 114?121.
[6] 魏昌東. 國家監察委員會改革方案之辨正: 屬性、職能與職責定位[J]. 法學, 2017(3): 3?15.
[7] 施鵬鵬. 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偵查權及其限制[J]. 中國法律評論, 2017(2): 44?50.
[8] 趙秉志. 中國反腐敗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現實問題研究[J]. 法學評論, 2014(3): 1?17.
[9] 胡錦光. 論監察委員會“全覆蓋”的限度[J]. 中州學刊, 2017(9): 64?73.
[10] ]陳衛東, 徐貞慶. 論逮捕中社會危險性的判斷方法[J]. 湖北警官學院學報, 2015(9): 117?120.
[11] 吳丹紅. 刑罰的“實報實銷”[J]. 人民檢察, 2009(13): 37?38.
[12] 楊凱. 逮捕中社會危險性審查裁量之規范[J]. 人民檢察, 2014(17): 43.
[13] 萬毅. 逮捕程序若干證據法難題及其破解——法解釋學角度的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5(2): 83?91.
[14] 金璐. 淺析《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中arrest與我國逮捕制度的差異——兼議arrest的翻譯[J]. 法學雜志, 2016(3): 124?132.
[15] 孫茂利, 黃河. 逮捕社會危險性有關問題研究——兼論《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逮捕社會危險性條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的解讀[J]. 人民檢察, 2016(6): 28?34.
[16] 王貞會. 審查逮捕社會危險性評估量化模型的原理與建構[J].政法論壇, 2016(2): 70?80.
[17] 洪浩, 趙洪方. 我國逮捕審查制度中“社會危險性”認定之程序要件——兼評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關于逮捕社會危險性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5?9條[J]. 政法論叢, 2016(5): 116?123.
[18] 陳衛東. 審查逮捕應堅持證據核心主義 貫徹非法證據排除規則[J]. 中國檢察官, 2015(2): 3?6.
On requirements of detention of supervisory commission’s cases
WANG Feiyu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4, China)
All public officials are within the range of being supervised if they break the law or the regulations or the moral norms, but application of detention should take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or dereliction of duty as the distinction for supervisory organs and investigation organs in dealing with the cases. This means that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or dereliction of duty should be the prerequisite for applying detention. Suspected crimes should be the decisive condition of detention, functioning as the core factor in distinguishing and adopting different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cases of different nature. Such crimes include both those actions related to a certain position whose harm has been involved in committing crimes, and those relevant evidences or clues which can testify or directly refer to the fact of suspected crimes. Escape of responsibility is the alternative condition for detention, functioning as a major basis in distinguishing and adopt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igation measur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the persons investigated, aiming to ensure that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investigated can be protected to the utmost,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ensur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can proceed smoothly.
detention; involvement in crimes of embezzlement and bribery or crimes of dereliction of duty; suspected of a crime(or crimes); escape of responsibility
2018?03?01;
2018?09?21
王飛躍(1969—),男,湖南洞口人,博士,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政法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刑事法學,聯系郵箱:wfeiyue2005@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06
D922.11
A
1672-3104(2018)05?0040?07
[編輯: 何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