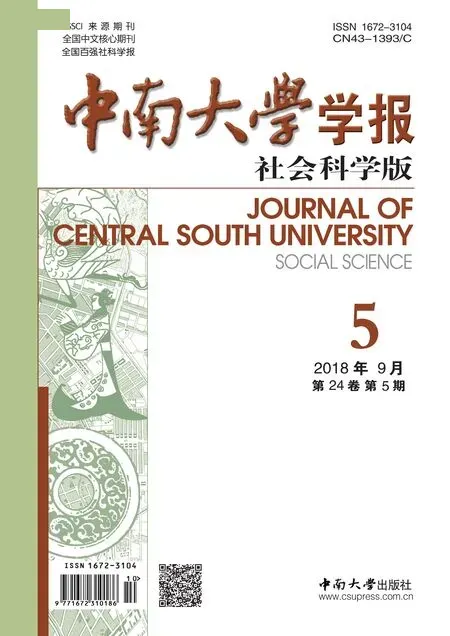從政策引導到法律主導——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問題研究
劉長秋
?
從政策引導到法律主導——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問題研究
劉長秋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上海,200020)
保障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基本醫療服務是我國新醫改的基本目標,也是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提出的一項基本要求。我國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問題高度重視,但在推進和保障方面卻還主要依賴政策而非法律。政策與法律的關系決定了法律應當成為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主要路徑。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已經起步且具備了一定基礎,但與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實際需要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需要采取相應的立法對策予以補正。
政策;法律;基本醫療服務;法律化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堅持醫藥衛生事業為人民健康服務的宗旨,以保障人民健康為中心,以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從改革方案設計、衛生制度建立到服務體系建設都要遵循公益性的原則,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努力實現全體人民病有所醫。”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堅持為人民健康服務的方向,堅持預防為主、以農村為重點、中西醫并重,按照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要求,重點推進醫療保障、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藥品供應、監管體制綜合改革,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不難看出,保障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已經成為今后我國醫改乃至整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方向與目標。然而,在法治已經成為我國當代社會主旋律,而社會治理亦已越來越依賴法律治理的宏觀背景下,基本醫療服務的享有和實現還必須依賴法律的保障。就目前來看,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和保障更多的是以政策來推動,法律保障問題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而學界對于基本醫療服務方面的法學研究成果也還不多見。基于此,本文擬從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的現狀分析入手,對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問題淺作 探究。
一、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的現狀分析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醫療是一個以治療身體以及心理疾病以恢復健康為目的的服務活動,它不僅包括現代意義上的醫療,也包括人類早期社會以巫術為手段的治療活動。但人類醫學科學的發展使得醫療的概念被不斷加以準確化和科學化,并形成了現代醫療的概念。現代意義上的醫療一般指對于疾病的診療,即以診斷和治療(diagnosis and treatment)為中心,實施各種檢查、措施、手術等醫療服務而取得的結果、成果和產出[1]。它排除了巫術意義上的醫療概念。而基本醫療則是現代醫療的一部分。所謂基本醫療,或稱基本醫療衛生,直白地說就是一個人患上了常見的普通疾病之后,能夠得到專業化的醫療機構所能提供的、患者自身能支付得起的或者國家能夠免費提供的、具有普適意義的適宜的診斷、治療或公共衛生保健。基本醫療服務,過去也稱初級衛生保健服務[2],是指由政府負責全部籌資或者部分籌資的公共衛生服務和醫療服務[3]。基本醫療服務是保障醫療衛生資源公平分配從而確保人們在患病時得到必需治療的客觀要求,是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底線,也是公民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正如德沃金所指出的,“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分配醫療衛生服務。即使在財富非常不平等甚至藐視平等的社會里,也不能因為一個人太窮,無力支付費用而不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治療”[4]。立基于此,“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5]。而基于這一責任,我國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視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和保障的問題。我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努力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出發點也正是保障廣大人民群眾享有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保障人們的生命健康權。
1993年1月15日,時任衛生部部長的陳敏章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的報告中首次提及了“基本醫療”的概念,他指出,“基本醫療服務必須給予保證,提供醫療質量和服務效率,體現政府對全體社會成員的一定的福利性照顧,而特殊醫療應采取放開的方針,擴大服務領域,供服務對象靈活選擇,以適應社會多層次需求”[6],從而將“基本醫療”與“特需醫療”相區分,作為一種政策方向提了出來。自此之后,基本醫療服務的問題便逐漸被提上了國家議程。在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與保障及其推進方面,我國一直以來都極為關切、高度重視,并在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過程中不斷強化。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發〔1997〕3號)提出“不斷深化衛生改革,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包括衛生服務、醫療保障、衛生執法監督的衛生體系,基本實現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國民健康水平進一步提高”,而衛生改革與發展的基本原則之一則是“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為中心,優先發展和保證基本衛生服務,體現社會公平,逐步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求”。1998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1998〕44號) 明確指出:“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即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據財政、企業和個人的承受能力,建立保障職工基本醫療需求的社會醫療保險制度。”這實際上為我國實現基本醫療服務的推進邁出了重要一步。之后,我國又在基本醫療服務工作方面穩步推進。2009年3月17日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09〕6號)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的總體目標;2009年3月18日發布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提出“2009—2011年重點抓好五項改革:一是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建設,二是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四是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五是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在此基礎上,2009年8月18日國家發改委與衛生部等九部委發布了《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這標志著我國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工作正式實施;而2015年9月11日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70號)則使我國基本醫療服務工作的推進又向前邁進了重要一步。
除以上重要文件之外,我國還相繼出臺和頒布了大量政策性文件,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1999年頒布的《關于貫徹兩個條例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加強基金征繳工作的通知》(勞社部發〔1999〕10號)、2004年10月9日發布的《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醫藥價格監管減輕社會醫藥費負擔有關問題的通知》,2011年7月1日頒發的《國務院關于建立全科醫生制度的指導意見》(國發〔2011〕23號),國務院2012年3月24日印發的《“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國家發展改革委、衛生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民政部、保監會2012年8月24日聯合發布的《關于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發改社會〔2012〕2605號),2013年9月28日發布的《國務院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3〕40號),2015年1月5日發布的《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全面加強衛生計生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國衛法制發〔2015〕1號),2015年4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民政部、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計生委、保監會等部門《關于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全面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5〕30號)及《中醫藥健康服務發展規劃(2015—2020年)》,國家衛生計生委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五部委2015年10月27日聯合發布的《關于印發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若干意見的通知》(國衛體改發〔2015〕89號)以及國家衛計委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于2015年11月17日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社區衛生服務管理和提升服務質量的指導意見》(國衛基層發〔2015〕93號),等等。這些文件都對基本醫療服務問題有所涉及。由此不難看到,在逐步將醫改推向深入,并通過醫改將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問題納入政策引導的軌道方面,我國迄今已經做了大量努力。
總體而言,對于我國公民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工作,黨和政府是極為重視的,也因此出臺了大量政策,涉及醫療機構建設、藥物保障、中醫藥發展以及醫療保險、疾病救助等在內的眾多領域。這對于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提升其健康水平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在法治已經成為當代社會主旋律,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已經將依法治國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高位的宏觀背景下,關涉我國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問題的“幾乎所有主要的醫改措施都停留在政策層面,基本法律制度的缺位,使得公民對健康權的合理期待無從落實”[7]。而從法理上來說,為了創造出使人們過上更為健康、更為安全的生活條件,法律乃為不可或缺的手段[8]。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與保障及其健康水平的提高固然離不開政策,但更需要法律。在目前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更多的還是在依賴政策引導而非法律保障的宏觀背景下,基本醫療服務要實現法治化,得到法律之保障,必須要將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有步驟地加以法律化,使我國日益成熟的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上升為法律,獲得法律的強制力,從而實現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由政策引導逐步向法律主導轉變。否則,“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為群眾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就很可能會成為一句 空話。
有關這一結論,我們可以以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貫徹落實為例進行闡釋。在我國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方面,盡管國務院發布的《“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各級政府在安排年度衛生投入預算時,要切實落實“政府衛生投入增長幅度高于經常性財政支出增長幅度,政府衛生投入占經常性財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的要求。但由于基本醫療服務并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在以國內生產總值為綱的政績觀下,缺乏明確法律制度約束的地方政府很容易會想方設法將中央的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資金截留甚至挪用,從而進一步加劇基層基本醫療服務供需矛盾。顯然,“欠缺法律權威的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難以為公民健康權提供有力保障”[9],廣大人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依舊無法得到根本性解決。所以,將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借助法律的權威來推進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勢必將成為今后我國在貫徹落實國家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以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權方面的必然歸向。
二、政策法律化何以必要和可行?
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權的保障及其健康水平的提高,客觀上需要將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而要實現我國基本醫療政策法律化,一個邏輯上的前提就是: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有必要被法律化且能夠被法律化。而這顯然涉及政策法律化何以必要與可行的問題。從邏輯上來說,政策之所以被法律化,是基于其必要性與可行性。亦即:政策在理論上存在被法律化的必要且客觀上具備政策法律化的可能。
(一) 政策法律化的必要性分析
立法政策學理論認為,法與政策是實現法治的兩種最重要的正式制度安排,也是對經濟社會進行管理的最主要手段。作為實現法治的兩種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策與法律各有其特點。法律有其特定的邏輯結構,內容的規定往往相對詳盡、具體,能給人們提供具體的行為指引,規范性突出,權威性顯著,穩定性較強,是防范和避免行政或司法專權的重要手段;而政策作為“國家或政黨為實現一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目標任務而確定的行動指導原則與準則”[10],則多是宏觀的、原則性的、依據社會發展需要及時出臺的,具有更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應時性的特點。然而,法律與政策也各有其缺陷。具體而言,法律盡管相較于政策更具有權威性和穩定性,但立法程序等方面的要求(即它要經過嚴密的立法論證、立法規劃、起草、審議、通過、頒布等繁瑣程序,且不能朝令夕改、經常變動),客觀上容易令其產生法律過于僵化與滯后的問題,即“法之對體系起穩定作用的連續性也常常使法落后于社會觀念的變遷”[11]。政策盡管具有相對靈活性和適應性的便利,卻也容易因其易變性而帶來穩定性不足和權威性欠缺的弊端。正因為如此,現代社會治理往往既需要法律,又離不開政策,需要二者之間多一些借鑒與轉化。即:在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上,需要重視政策向法律的轉化,使政策多一些類似法律的穩定,并“讓法律多一些政策考量”[12],易言之,就是要重視政策的法律化。政策法律化可以借助政策的靈活性來強化法律對于現實社會的適應性,使之更契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政策法律化也可以借助法律的權威來增強政策的剛性,使政策產生更高效的執行力。政策法律化是在協調政策與法律關系的基礎上實現二者有效銜接的方式[13]。“法律化尤其為社會過程引入了行為導向的安定性和穩定性。在關于何為正義與公道的多元化的觀念沖突中,法規范提供了可靠的、可貫徹的行為指南。在時間維度上,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穩定性和持續性。”[11]就此而言,政策法律化是彌補政策缺陷以及提高法律適應力,從而使法律與政策能夠發揮合力的重要路徑。在當代社會治理既需要法律又離不開政策的宏觀背景下,政策法律化已成為提高國家社會治理能力,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選擇。
不僅如此,依法治國的客觀需要也決定了政策法律化的必要性。法治是當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征,也是實現社會治理的必由之路。而法治的實質是令法律這種相對更具穩定性和可預見性的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居于主導地位,亦即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盡可能地被納入法律規范的軌道。與法律相比,政策的制定一般缺乏嚴密而規范的民主程序,其內容規范性少。因此,盡管政策具有靈活性和應時性等特征,但同時也具有不穩定性和易變性的缺陷,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容易淪為潛規則或暗箱操作,從而危害社會的健康發展。而政策法律化則是將原本易變的政策借助立法的形式穩定下來,令政策成為更為穩定和可預見的規則,從而更有效地滿足社會治理的客觀需要,是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
(二) 政策法律化的可行性探討
政策法律化不僅需要具備現實必要性,更需要具備理論上的可行性,亦即:政策和法律具備一些自身特質,從而使得政策與法律具有由此及彼的基礎與可能。筆者以為,政策法律化的可行性主要來自政策與法律的同質性。
1. 政策與法律都是旨在強化社會治理的社會行為規則
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政策和法律作為制度,都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國家等公共權威應社會之需要而向社會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且最終通常都會在國家層面上實施。政策作為國家機關、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等公共權威在一定歷史時期為達到一定目標而制定的、具有普遍權威性的行動方案和準則,其目的“在于調整和規范社會利益結構,以促進社會經濟健康、快速發展”[14];而法律作為“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維護秩序的手段”[15],其存在的目的顯然也是為了調整和規范社會利益結構,以“使每一個社會階層及其利益群體享有利益的權利都將受到其他社會階層及其利益群體的權利的約束”[16],從而保障社會的有序發展。作為公共產品,無論是政策還是法律,它們都能夠滿足社會的某種需求。從理論上講,政策與法律的社會需求決定制度供給,當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對政策與法律產生需要并積極謀求政策與法律對其利益的維護時,就必然要求相應的制度供給發生[17]。換言之,政策與法律都是應因社會治理的需要而產生和存在的,其存在、發展與變遷都是為了滿足特定的社會需求。政策與法律在社會調控上具有同樣性質的功能。國家通過頒布法律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規范,同樣,國家也通過實施政策對社會生活進行調節和管理[13]。在當代社會中,政策與法律具有相同的使命。很多時候,政策會成為法律的前奏,而法律則需要為政策的推行和深化提供保障。
2. 法律與政策具有密切的聯系
在法律與政策關系上,學界存在著很大爭論。以德沃金(Ronald W. Dworkin)為代表的政策觀認為,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政策是包含在法律之內的,是法律的組成部分;而以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為代表的政策觀則認為,政策和法律是兩碼事,法律之中并不包含政策,從方法論的角度說,政策是法律獲得合理解釋的推理和論證的依據。在我國,學者們多認為,法律與政策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二者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然而,二者之間實際上又存在著密切聯系。首先,站在公共政策的角度上加以考察,法律是公共政策的一種類型。在某種意義上,法律法規即是擁有立法權的政治家制定并為政府和法院執行的公共政策[18],是作為公共權威的立法者以國家強制力推行的、承擔特定公共職能的國家政策。其次,站在法律的角度上來看,政策實際上是一種軟法。法律依照其在社會運行中的強制力的不同可以被劃分為硬法與軟法,前者是指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國家法,后者則是指在國家法之外發揮著類似于法律約束力的社會規范,亦即那些原則上沒有法律拘束力但有實際效力的行為規則[19]。如行業規章、技術標準、單位規章以及鄉規民約等,而政策也在其中。政策作為國家法之外的一種軟法,是法律的制定和運行過程中的輔助和支撐。它不僅可以成為法律制定和執行的依據,而且還能夠以其靈活性彌補法律過于僵化的先天不足,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往往起到“試行法”的作用[20]。可以說,政策是當代社會治理過程中所倚賴的一種不同于國家法律但又具有特定約束力的軟法。這為政策在特定條件下轉化為法律提供了可能的空間。
三、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法律化何以必要與可行?
政策法律化并不是政策與法律的簡單疊加,而是法律對于政策的認可與保障。為此,政策法律化必須滿足特定的條件,需要具備必要性與可行性。作為政策法律化在基本醫療服務領域的一種實踐,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否則,就無法法律化。
(一) 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之必要性 分析
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是一種公共產品,而產品的市場需求是該產品存在和發展的前提[21]。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深入,“看病難,看病貴”已經成為困擾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生存與發展的一個重大顯性問題。“鋸腿自救事件”“詐騙救妻案”“自制鋼腎事件”……,因公民生命健康問題而招致的各種社會熱點事件的不斷發生,極大地刺激著社會的敏感神經,彰顯著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缺失。在此背景下,人們對于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的需求已經日益強烈。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以保障其生命健康,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項基本權利需求。
從法理上來說,權利“是規定或隱含在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的,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15]。立基于此,法律的認可與保障顯然是實現公民權利的內在需要。當前,在基本醫療服務方面,我國已經出臺了包括《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等在內的大量政策性文件,將公民基本醫療服務問題納入了政策引導的軌道。這在表明了黨和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問題上的態度與立場之同時,也對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和保障及其健康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一方面,目前我國旨在推進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制度規范——無論是醫療機構分級診療,還是基本藥物制度,抑或是全科醫生制度——基本上都是以政策引導為主,形成法律制度的還不多見。應該說,在有關人們的基本醫療服務方面,政策引導具有必然性,尤其是在國家的醫藥衛生改革的方向與目標定位尚不明晰,而相關體制機制也尚未理順的情況下。而且,我國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漸進性改革。基于政治等多方面考慮,改革往往從醫藥衛生方面的具體問題著手,尤其需要以靈活性的政策指導為主,而不是以剛性和普遍性的法律規范為先。法律自身的僵化性決定了衛生法律在改革過程中必然有其難以克服的缺陷。這一點注定了政策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手段在推進醫改以保障人們基本醫療服務方面的必要性。政策引導可以很好地發揮其自身的靈活性與適應性,能夠根據實際需要及時地修正和完善,使其更符合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現實需要,避免法律保障必然引生的僵化性而帶來的社會不適。但另一方面,政策自身所固有的易變性、模糊性及剛性之不足決定了單純的政策引導必然難以完全適應保障人們生命健康權利的客觀需要。因為單純依賴政策來保障人們基本醫療服務的模式很容易使人們的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受到行政權力的隨意干預和制約,從而令人們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和保障陷于一種不穩定、不確定的狀態,使人們生命健康權的實現演化成為充饑之“畫餅”。在此情形下,作為權利最可靠保障的法律就需要及時介入,以為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和保障提供最有效的支撐。顯然,提供并保障基本醫療服務以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在生命健康方面的權利需求,使得加強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立法成為國家的一種本能反應,也就是要將現行的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使基本醫療服務得到法律的保障。
(二) 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之可行性 探討
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不僅具有法律化之理論上的必要性,就其現實性而言,也具有轉化為法律的可行性。原因在于:
1. 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與法律具有同質性
首先,在推進醫改以保障人們的生命健康方面,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具有與法律相同的目標定位。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 衛生服務”“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為基本目標,而 法律則以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為最高法益,至于醫療衛生法,更是以保障人們的生命健康為己任。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的確立實際上是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權的必然要求。很顯然,二者具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標定位,無論是從政策層面上來說,還是從法律層面上來說,基本醫療服務的實質都是健康服務,它所關注的是公民的健康 權[22]。這使得二者具備由此及彼的基礎,尤其是由政策到法律的基礎。其次,基本醫療服務政策發揮了“試行法”的作用。在醫藥衛生資源分配方面,我國目前還存在著明顯的立法缺失。現行的醫藥衛生立法,無論是《執業醫師法》與《藥品管理法》,還是《獻血法》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抑或是《醫療事故處理條例》,都只是在調整醫藥衛生領域的個別法律關系,都沒有涉及醫藥衛生資源分配這一核心問題。而醫藥衛生資源分配又是國家醫藥衛生事業健康發展的基石,直接關涉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在此背景下,以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為目標的公共政策實際上早已成為我國基本醫藥衛生法的“試行法”,成為指導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指針以及我國醫藥衛生法獲得合理解釋的推理和論證的依據。一言以蔽之,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與醫藥衛生法律具有同質性,在實現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上是可行的。
2. 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符合政策法律化的限度要求
立法政策學認為,法律與政策可以借助于政策法律化而實現連通,從而得以彌補各自的缺陷與不足,最大可能地發揮政策與法律兩種制度手段的合力,提升社會治理的能力。政策轉變為法律是客觀現實的必然要求,社會生活的復雜多變與發展,要求將具有長期穩定性的政策、對全局具有重大影響的政策、成功和成熟的政策立為法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促進其完善[23]。然而,政策法律化作為一種立法建制活動,本身并不是毫無限制的,相反,它必須滿足特定的要求并需要遵循一定的限度。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作為將國家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的一個立法過程,顯然也在此列。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并不是將基本醫療服務政策與法律簡單地融合。作為一種政策法律化的活動,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是一個需要遵循特定限度的立法活動。
一般而言,法律化的政策首先應該是具有正當性的政策。而所謂正當性政策是指合乎公共利益需要的政策[24]。而在健康直接關涉個人幸福以及社會發展的情況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作為以保障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以提升人們的健康水平為目標的公共政策,顯然完全合乎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此而言,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是具有正當性的公共政策,是應當被法律化的醫藥衛生政策。除了正當性這一要求之外,法律化的政策還必須具有全局性以及相對穩定與成熟性。法的調整對象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關系,“法在很大范圍內調整著國家和社會一切重要的發展過 程”[25]。為此,法律化的政策必須是關涉國家發展全局的政策。只有那些對國家發展全局有重大影響的政策,直接關系到大部分社會關系的調整,才有必要轉化為法律,即具備立法的必要性[26]。法律化的政策還必須是經過實踐證明是科學可行從而是成熟的且具有一定穩定性的政策。法律與政策的一個重大區別在于法律具有穩定性,它必須保持相對的穩定,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因為國家個別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政策法律化的實質是使政策成為法律,從而具有法律的穩定性,并獲得法律的權威。只有那些已經被證明科學可行且相對較為成熟的政策,才具備法律所要求的穩定性,從而獲得被法律化的可能。而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作為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長期探索且經過醫患關系由相互信任到最終裂變之考驗與洗禮的一項成果,不僅代表了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發展的必然方向,且已成為一項相對較為成熟、穩定和科學的公共政策,完全具備法律化的基礎。
3. 國外經驗宣示了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可行性
從國外尤其是那些所謂的福利國家的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實踐來看,出臺相關政策并在這些政策成熟后將其升格為國家法律,是各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一般進路。作為世界上首個建立社會政策框架的福利國家,英國于1882—1948年期間即已形成了社會福利制度、專門化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與政策框架結構,并于二戰后相繼頒布了包括規定組織和提供國家衛生服務的《國家衛生服務法(1946)》等在內的有關社會保障的五大立法,將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與政策框架等納入了法律保障之中。而《國家衛生服務法》頒布后,立法者始終圍繞國家衛生服務的基本政策而不斷對其加以修改、補充和完善,將與國家衛生服務相關的公共衛生、藥品、社會服務和保障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逐步納入該法調整范圍[28]。在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理查德·斯科頓(Richard Scotton)和約翰·迪布爾(John Deeble)于1968年提出建立全民醫療保險(最初稱為Medibank)的設想,并得到了工黨領袖愛德華·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的政治支持而成為一項政策。惠特拉姆上臺后,積極推動該政策的法律化,加快落實全民醫療保險的立法過程,并于1975年通過了《健康保險法》。此后歷經多次變革,澳大利亞又通過了《全民醫療保險法》(1984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為其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政策進一步提供了立法支持[29]。在加拿大,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實現了全民醫療保險,加拿大人都以此為豪。可以說,加拿大的全民醫療政策不僅僅是一種醫療保險,它已經變成了一種國家象征,成為體現加拿大社會平等、公正的重要標志[30]。而20世紀40年代萌芽并于20世紀50年代形成政策的加拿大全民醫療保險主要是通過1957年的《醫院保險和診斷服務法案》以及1966年的《醫療保健法案》得以確立的,并由1984年最終出臺的《加拿大健康法案》固定下來。在德國,以保障人們基本醫療服務為目標的醫療改革政策更是直接通過立法來加以推行,從2004年生效的《法定醫療保險現代化法》到2007年實施的《法定醫療保險強化競爭法》,從2011年頒布的《法定醫療保險護理結構法》再到2014年通過的《進一步發展法定醫療保險資金結構與質量法》……,可以說,德國每次醫療衛生改革都是先依據國家確立的醫療衛生改革政策,由議會制定或修改相關法律,然后再推進改革。這不僅保障了醫療衛生改革的科學性、民主性,也確保了這一改革的連續性。至于美國,其對于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與保障更是以醫療服務政策的法律化為前提的。盡管美國提供著世界上最好的醫療保健,它的衛生體系是碎片化的、不公平的、過分昂貴的以及——用CBS新聞主播沃爾特·克朗凱特(Walter Cronkite)的話來說——既不健康和富有福利性,也不是一種體系[31]。為此,2010年3月,奧巴馬總統簽署了旨在推動美國醫療保險改革以擴大基本醫療服務覆蓋范圍的《病人保護與低價醫療法案》……。總體來看,依據本國相對成熟的醫療服務政策而制定相關的立法,并在立法中明確國家在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方面的義務,是將各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通常進路。以此為基點,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顯然也需要走這樣一條道路。
當代社會治理實際上是一個既需要政策引導又離不開法律保障的發展過程。政策與法律對于社會發展而言就像自行車的兩個輪子,其中作為政策的前輪重在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作為后輪的法律則主要是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在政策與法律這兩個推動社會發展的前后輪之間,政策法律化就像是自行車的車鏈,連接著前后兩個車輪,保證著社會這輛自行車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前行。基本醫療服務是保障人們生命健康權的必需,是當代社會治理必須予以關注和重視的一個重點問題。作為當代社會治理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基本醫療服務也需要政策與法律的雙輪驅動。而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就是整合政策與法律的制度手段,發揮二者對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功能互補優勢的必然選擇,也是完善我國醫藥衛生法治的客觀需要。
四、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具體操作與對策建議
政策法律化是指具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依照立法權限和立法程序,將成熟、穩定又有立法必要的政策轉化為法律[27]。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就是將國家的基本醫療服務政策依照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從而實現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由政策引導到法律主導過程的轉化,使基本醫療服務政策獲得人人可以遵守的法律效力以及國家強制力的保障,增強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執行的有效性,使該政策在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權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我國多年以來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實踐基本上都是圍繞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權的保障展開的,并在醫改過程中逐步確立了“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目標,而為了保障這一政策目標的實現,我國一直都比較注重相關立法建設。就目前來看,我國在醫療衛生方面已經出臺了包括《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母嬰保健法》《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條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中醫藥條例》以及《艾滋病防治條例》等在內的多部重要法律以及法規,已經邁出了醫療服務甚至是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初步步伐,使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法律保障具備了一定基礎。然而,目前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步伐還比較緩慢,現有立法與當前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基本醫療服務的法律需求相比,還相差較遠。具體而言:一是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基本醫療服務方面的核心法。我國盡管頒布了大量的醫療衛生法規,但保障基本醫療服務的基本法律制度尚付闕如,且迄今還沒有出臺一部《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法》,沒有對政府基本醫療服務方面的供給和保障義務進行統一、明確的規定。這使得“看病難,看病貴”依舊是我國廣大人民群眾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公民健康權的行使缺乏有效法律依據之保障。二是政策引導而非法律治理在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由于立法的滯后性,在基本醫療服務的制度建設方面,我國目前主要還是以政策引導為主,法律保障還沒有到位,如在基本藥物制度保障、大病醫保、醫療機構分級診療、因病支出型貧困家庭社會救助等方面,基本上還都是依靠政策在推動,立法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在法治已經成為社會主旋律而依法治國也已經被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之歷史高位的宏觀背景下,我國基本醫療服務制度建設急需通過立法來加以推進。三是我國現行關涉基本醫療服務的立法更多的是在供給醫療服務方面發揮作用,直接涉及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的比較少見。從理論上來說,醫療服務的可及性是人們獲取基本醫療服務的前提,沒有醫療服務的可及性,人們獲取基本醫療服務只能淪為空話。但基本醫療服務顯然不止于能夠獲得醫療服務這樣一種比較低的層面,它實際上是一種相對更高的要求。形象一點說,二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前者重在解決“有病無處醫,有病不能醫”的問題,而后者則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后者需要以前者為基礎,其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前者,但其要求卻遠高于前者。就目前來看,現行的衛生法律法規盡管都是人們獲得基本醫療服務所不可或缺的,客觀上也都有助于保障人們獲得基本的醫療服務,但明確在立法中規定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的并不多見。迄今為止,在國家層面上只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條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這兩部行政法規明確提出了保障基本醫療服務(初級衛生保健)的立法目標,而在《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母嬰保健法》以及《中醫藥條例》等立法中則并沒有對基本醫療服務的問題進行明確規定①。這使得除《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條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這兩部行政法規之外的現有醫療衛生法更多的是在提供醫療服務方面發揮作用,而難以在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方面有大的作為。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將我國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醫療服務保障之軟肋暴露于法治視野的情勢下,我國已有的醫療衛生立法顯然還需要在推進基本醫療服務方面更進一步。
國務院《“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提出:“積極推動制定基本醫療衛生法,以及基本醫保、基本藥物制度、全科醫生制度、公立醫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及時將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成功做法、經驗和政策上升為法律法規。”這實際上為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亦即基本醫療服務立法指出了目標與方向。筆者認為,在目前我國醫療衛生法律領域尚沒有一部作為整個法律群之基本法且公民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立法尚付闕如,而現有立法又難以真正承擔起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使命的情勢下,我國應當制定《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法》這樣一部能夠承擔基本醫療服務保障功能且又能夠擔當我國醫療衛生法基本法使命的法律,以便在統領我國醫療衛生立法并使其理念與原則保持一致的基礎上,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保障提供立法依據與引領。應該說,這是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首要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國還應當圍繞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制定包括《基本醫療保險法》《基本藥物供應保障法》《醫療機構分級診療條例》《社區醫療服務管理條例》《因病支出型貧困家庭社會救助辦法》等法律、法規或規章,以作為《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法》的細化與補充,切實將公民的基本醫療服務供給納入法律保障的范圍之內。同時,對于我國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應當明確政府在其中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義務。例如,應當在《執業醫師法》《藥品管理法》《母嬰保健法》《艾滋病防治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政府、執業醫師、藥師以及病患者等在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方面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尤其是要明確政府在承擔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方面的責任與義務,使我國現有的衛生法律法規也承擔必要的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任務。也就是說,要依據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的需要構建我國的醫療衛生法律體系,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享有的基本醫療服務能夠得到法律的切實保障。
為了保障我國新一輪醫改的順利推進,確保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及其健康水平的提高。我國已經著手制定基本醫療服務法方面的一系列工作,作為承擔著這樣一種使命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已經于2017年12月22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正在逐步推進之中。盡管該法無論在名稱上還是在內容上都還存在著一些不足,其正式出臺還需要經歷一些磨礪,但可以預見的是,在目前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與保障依舊更多的倚賴政策引導而依法治國又已被提到一個前所未有之歷史高位的情勢下,我國基本醫療服務需要且必然會經歷一個由政策引導到法律主導的發展階段,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將是未來我國基本醫療服務供給和保障方面的最主要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法律化并不是要將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政策的全部內容都上升為法律,而是要將其基本理念以及那些已經比較成熟可行的重要制度法律化,從而使法律在推進基本醫療服務政策深化和落實方面發揮應有作用,切實保障我國基本醫療服務的供給。畢竟,在法治社會中,政策和法律各有其獨立存在的空間與價值,政策法律化不能完全取代政策,更不能消滅政策。我們必須正視政策與法律之間的辯證關系,“無視政策對法律的補充作用,毫無限度地推進政策法律化,妄圖以法律替代各種政策,其最終結果將導致政策在法治社會中的消亡”[33]。無視并抹殺基本醫療服務政策與法律之間的制度功能差異,將基本醫療服務政策的全部內容盡行法律化,最終勢必會導致我國基本醫療服務泛法律化。
注釋:
① 《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條例》第1條規定:“為保障城鎮從業人員的基本醫療,合理利用醫療資源,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結合本省實際,制定本條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第1條規定:“為了提高鄉村醫生的職業道德和業務素質,加強鄉村醫生從業管理,保護鄉村醫生的合法權益,保障村民獲得初級衛生保健服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以下稱執業醫師法)的規定,制定本條例。”
[1] 樸志镕. 醫療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法學上的醫療概念的理解[C]// 金玫, 易繼明. 私法. 武漢: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16: 80.
[2] 徐國平. 糾正概念大力發展我國基礎醫療衛生服務事業——從“初級衛生保健”中文誤譯說起[J]. 中國全科醫學, 2014(25): 2911?2914.
[3] 汪建榮. 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45.
[4] 羅納德·德沃金. 至上的美德: 平等的理論與實踐[M]. 馮克利, 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 126.
[5] 劉鑫, 連憲杰. 論基本醫療衛生法的立法定位及其主要內 容[J]. 中國衛生法制, 2014(3): 23?28.
[6] 陳敏章. 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摘要)[J].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 1993(2): 63?67.
[7] 陳云良. 基本醫療服務法制化研究[J]. 法律科學, 2014(2): 73?85.
[8] 勞倫斯·戈斯廷. 公共衛生法的理論與定義. 趙曉佩, 譯. [C]//馬克斯韋爾·梅爾曼, 等. 以往與來者——美國衛生法學五十年. 唐超, 等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12: 241.
[9] 陳云良, 何聰聰. 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法律規制研 究[J]. 法商研究, 2014(6): 17?25.
[10] 段鋼. 論政策與法律的關系[J]. 云南行政學院學報, 2000(5): 51?54.
[11] 萊因荷德·齊佩利烏斯. 法哲學[M]. 金振豹, 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79.
[12] 肖金明. 為全面法治重構政策與法律關系[J]. 行政管理論壇, 2013(5): 36?40.
[13] 陳庭忠. 論政策和法律的協調與銜接[J]. 理論探討, 2001(1): 64?66.
[14] 陳標, 夏道明. 試析公共政策執行失靈[J]. 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5): 83?86.
[15] 張文顯. 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理論、方法和前沿[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26, 289.
[16] 朱未易. 中國社會階層利益沖突的法律調整機制[J]. 江蘇社會科學, 2008(4): 158?164.
[17] 劉長秋. 法律視野下的中國生物產業政策研究[J]. 上海財經大學學報, 2013(6): 40?47.
[18] 肖金明. 為全面法治重構政策與法律關系[J]. 行政管理論壇, 2013(5): 36?40.
[19] SNYDER F. Soft law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C]//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198.
[20] 劉長秋. 當政策遇到法律[N]. 大眾日報, 2014-12-03(10).
[21] 楊斐. 法律修改研究: 原則·模式·技術[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14.
[22] 許中緣, 翁雯. 論基本醫療服務權的救濟[J]. 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2): 91?98.
[23] 埃德加·博登海默. 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 譯.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402.
[24] 朱最新. 珠三角一體化政策之法律化研究[J].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2(5): 9?15.
[25]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學[M]. 丁小春, 吳越, 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41.
[26] 張國慶. 公共政策分析[M].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4: 202.
[27] 黃清華. 英國衛生體系基本法研究[J]. 法治研究, 2012(8): 46?59.
[28] 蔣露. 澳大利亞全民醫療保險解析[J]. 當代經濟, 2009(6): 37?38.
[29] 季麗新. 公平視角下加拿大醫療衛生政策剖析[J]. 山東社會科學, 2007(11): 77?81.
[30] FAGUET G B.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 missed opportunity, a better way forward[M].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13: 8.
[31] 陳振明. 政策科學[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8: 258.
[32] 屈振輝. 試論公共政策法律化的限度[J]. 蘭州商學院學報, 2007(6): 112?115.
From policy orientation to law leading:On China’s legalization of basic medical service policy
LIU Changqiu
(Research Institute of Law,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It’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China’s new medicare reform to let most people enjoy the basic medical service, which is also a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the Report of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asic medical services of most people, but the promotion and guarantee of such services depend on policy rather than on law.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cy and law determines that law rather than policy should be the main approach for China to provide and guarantee basic medical services. The legalization of China’s basic medical service policy has been on the way and has laid certain foundation. Bu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actical need in our country, it is still insufficient with a huge gap, with which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pe.
policy; law; basic medical service; legalization
2018?03?07;
2018?04?24
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重點基金項目“基本醫療服務保障立法研究”(13AFX026)
劉長秋(1976—),男,山東萊蕪人,法學博士,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山東省高校證據鑒識重點實驗室兼職教授,上海市法學會生命法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生命法學、生命倫理學、黨內法規學,聯系郵箱: shangujushi@sina.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5.008
D922.161
A
1672-3104(2018)05?0058?09
[編輯: 蘇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