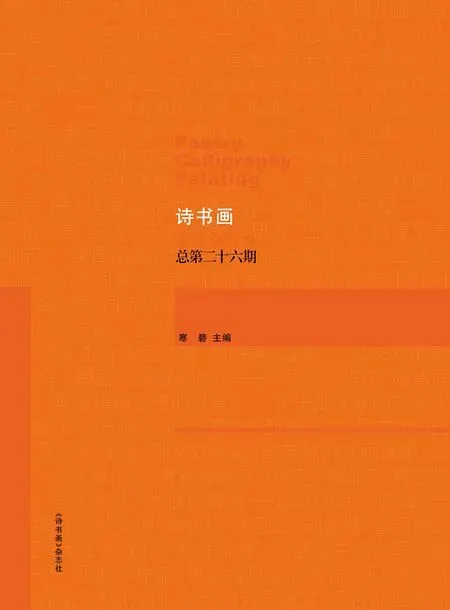前羅王時代清金石學的變化大勢與理論自覺
——一個學術史的考察※
潘靜如
一般來說,史學/知識與藝術之間并沒有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鴻溝,但從各自的主體性而言,二者的精神相去絕遠。在中國傳統的學術史或藝術史領域內,我們時常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其中,濫觴于宋、盛極于清的金石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考察這一現象的范本。作為關聯著“史學/知識”與“藝術”的金石,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清三百年學術史上,金石學由附庸而蔚為大國,是很可矚目的事。隨著乾隆中“西清四鑒”的頒行及畢沅、阮元、王昶等人的表率與提倡①清代金石學肇始于顧炎武等遺民,但使其成為“顯學”的還有賴于乾嘉間巨師碩儒的倡導,其中阮元的影響最大。清人已明確指出這一點,初不待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揭破。參褚德彝《清儀閣藏古器物文》序、徐鈞《清儀閣藏古器物文》序、嚴保庸《寶鐵齋金石文跋尾序》、宋祖駿《枕經堂金石跋書后》、宗稷臣《枕經堂金石跋書后》、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序》、孫詒讓《古籀拾遺序》、《古籀遺論序》、吳云手札,桑椹編《歷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錄》(以下簡稱《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8、339、341、346、347、416、447、452、1074頁。,學士大夫們對金石的癡迷近乎瘋狂:它的聲勢和規模之大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時代。這與清代小學、經學和考據學的發達有關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盛行可以在清代實證學風的脈絡里找到內在邏輯(inner logic)。換言之,明人金石學雖承自兩宋,但偏重碑帖賞鑒一途②羅振常就說:“至有明斯學(金石學)寖微,蓋明人喜論書法,所考求在帖不在碑。”見羅振常《碑藪》序,民國二十五年蟫隱廬石印本。,可說是一種娛樂(pastime)或珍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式的古董主義(antiquariannism)③此僅就大體而言,明人當然也有考古功深的著作。本文“娛樂”(pastime)和“古董主義”(antiquariannism)兩詞參Shana J. Brown, Pastimes: From Art and Antiquarianism to Morde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珍奇柜”,原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收藏古物的儲存室的一種,它與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興緊密相聯,就外在形式來說,是為了滿足篤古者的好奇心,參The Origins of Museums: The Cabinet of Curiositis in Sixteenth-and Seventeenth-Century Ue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清人則一面耽于此樂,一面積極通過金石來解決學術問題,筆者曾杜撰“目的金石學”(teleological epigraphy)一詞來指稱它。由附庸而為大國,它在發展過程中呈兩種趨勢:一種是粗放的外向拓展,即從最受矚目的帶字的鐘鼎碑碣逐漸延伸到磚瓦玉器壁畫陶瓷封泥等領域,另一種則是內在發掘和深入,這涉及到其最終的自我價值和本位的確立,而在實踐過程中形成理論是其標志之一。所謂理論只能在歷史語境中去理解,不能繩以現代銘刻學(epigraphy)、考古學(archaeology)、古文書學(paleography)等專門概念,盡管適當的類比是可行的。本文試就嘉道咸同之際的金石學發展作一個學術史的梳理。論述時,會根據清金石學自身的脈絡而延伸至光緒年間。因此可以這樣說,本文試圖勾勒出“前羅王時代的清金石學簡史”—當然是理路意義上的,而非全景意義上的。
一、金石范疇的流變
宋人的金石學著述中,鐘鼎(彝器)、碑碣而外,銅鏡、玉器、貨幣、瓦當、陶器等已見著錄,并間有摹寫或考釋,像王黼《宣和博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拾遺》還錄有“雜器”一類,來安置彝器以外的青銅器,比如生活用具、車馬器等。這表明宋人雖然沒給金石學下一科學或明確的定義,但從一般的處理方式來看,其包孕范圍是很廣泛的。④朱琰給替張燕昌《金石契》所做一序頗能體現這一點,有云:“芑堂張子,博雅好古,……積十馀年,裒成若干冊,其中錢范、古磚、瓦頭似為創例。然鄭漁仲《金石略》載金幣、貨布,趙明誠《金石錄》有漢陽朔磚,采擇亦有元本,乃因錢及范,不襲不倍,其意固欲與前人并傳也。”見《歷》,第247、248頁。不過,金石二字,無疑還是偏指彝銘碑刻,例如鄭樵《通志》“金石略”一門惟強調“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⑤鄭樵《金石略序》,《通志》卷七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就透露著這樣的消息。明人碑帖篆刻之學十分發達,賞玩所及,各類古董也頗受垂青,像古琴、古硯、玉器、象牙、窯器、漆器之類進入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論》就可見一時風會。這偏于鑒賞一途,不能得出金石學明確拓展了范圍的結論。總的來說,這是乾嘉以后的事。這一方面有賴于新的出土,像清中后期瓦當、陶器、封泥的大規模發現就是,另一方面也有賴于金石學本身的急劇發展。本文著力揭示出后者在此過程中充當的作用。
先來看乾嘉以后的清人敘述中有意無意間對金石概念及其范疇的界定。

《考千甓亭古磚圖釋》

《陶說》
今世嗜古者,輒搜古有文之磚瓦而著錄之,非玩物之謂,將以補金石之闕也。
金石之學至我朝而集其成。至于磚石之馀也,自有宋洪文惠始著于錄,后之言金石者,皆略焉。
金石文字之可貴,以其可以考古事,證異文,故學者多耆之,而于古甓亦然。①李枝清《竹里秦漢瓦當文存》序、陳用光《浙江磚錄》序、陸心源《千甓亭古磚圖釋》序,《歷》,第1092、1060、1076-1077頁。
上引文字有些費解。金石二字似偏取其狹義的一面,而在敘述過程中,又隱隱將古磚甓作為一分子囊括進去。乾嘉而后,搜考金石之風極盛,由彝碑而及于其他,是再自然不過的。儒宗碩學的提倡是一個原因,比如阮元以“以八磚分題課士”后,出現了士人競相搜訪古磚,并借以矜尚夸耀的局面②吳云《手札》,《歷》,第1074頁。。但金石熱的內在推動無疑更值得關注,士人寢饋于斯,會不自覺的由此及彼,于是磚瓦、玉器、泥造像、畫像或各類雜器等都有了層出不窮的專書。甚至于“奇物”一出,蓋過了彝碑的風頭。當時一個學者偶獲瓦當,竟至于“不輕示人”,引起士人的瘋狂蒐求,連錢大昕都不惜出重金,購瓦三十馀,來跟他抗衡。③程敦《秦漢瓦當文字》卷首,乾隆間刻本。一時風氣如此。參以嘉道間人的敘述,程瑤田說:“毅堂之從事于此也,得鐘鼎尊彝諸器有款識者甚多。好之不已,浸假而及于泉布,其在三代者尤多古文奇字。”④程瑤田《看篆樓古銅印譜序》,《歷》,第960頁。瞿中溶說:“予自弱冠留意金石文字之學,因旁及印章,手摹古今譜錄,又博訪搜藏之家。”⑤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證》自序,同治十三年刊本。一個使用了“浸假”,另一個使用了“旁及”,這驗證了我們的觀察。
如果,這僅意味著金石學熱下自然而然的兼收博取的話,那么下引帶有“抗議”或“正名”意味的論述,則昭示了金石門類中各子類不斷的自我獨立意識。
裘曰修(1712-1773)《陶說》序:
嗜古之士,類及鐘鼎尊彝之屬,多有記錄。董逌、劉敞、洪邁諸君子而外,《宣和博古圖》致為大備。獨窯器并無專書,近世《格古要論》一編,亦寥寥數則,觀者莫能厭飫。⑥裘曰修《陶說序》,朱琰《陶說》卷首,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5年,序第1頁。
劉寶楠(1791-1855)《退庵錢譜》序:
吾友夏君遐庵,嗜學好古,以金石之學儒者多通,而刀幣獨略,世所傳圖志,驗諸正史,往往不合,于是是網羅泉貨,權衡母子,得古錢若干品,為之辨真贗、別良苦,考其年世,核其異同,折衷至是,成《前譜》八卷。①劉寶楠《退庵錢譜序》,夏泉《退庵錢譜》卷首,民國八年《海陵叢刻》本。
鮑康(1810-1881)《鮑臆園手札》:
古泉之學,至嘉道時始有確識。前人著錄,皆不足信。②鮑康《鮑臆園手札》,《叢書集成新編》49冊,第555頁。
龔自珍(1792-1841)《印說》:
瘁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為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即錄,錄副鐘彝之末簡。……小學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為一門,固有說乎?夫苕泖之士愛古甓,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制,吉祥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為一門,儲印豈不愈于是?③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6頁。
楊峴《千甓亭磚錄續錄序》:
耆古者之僻也,鼎鐘彝器而外,至于漢魏唐晉之磚之有文字者,亦罔不蒐獲焉。或謂點畫奇肄,偏旁增損,足以推見由篆變分之始,與刻符、摹印、幡信、署書之大凡于《說字》不無小補,猶淺也。夫古之磚者,紀年代,著姓名,皆一時實跡,非若史乘出自后代篹輯,容有傳聞之異也。循是以證歷代之史乘,往往引磚文而得其訛謬,豈非讀書之助哉?④楊峴《千甓亭磚錄續錄序》,《歷》,第1075—1076頁。
陶器、貨幣、印章、磚甓乃是自宋以來就被不斷著錄或賞鑒的,只是一直居于附庸的地位罷了,然而嘉道以后卻要求重新評估自己的價值,這意味著整個金石學發展的迅速。
為了進一步證明,先以印章為例。印章向來被視為小道,有明一朝,篆刻復興,漢魏六朝的印譜被不斷蒐集和刊行出來,但人們看重的乃是其“書法”。又往往以“寶玩”、“異寶”視之。⑤例如張所敬《集古印范序》:“好古君子得而藏之鄴架,又何假商彝周鼎夏后氏之璜乃稱寶玩哉!”李日華《題周九真〈印問〉》:“今天下之徒,慕古耳……古鼎彝入玩,踴貴如異寶,然多贗濫,獨古文字存耳。其存也,碑碣金石盡而縑素,縑素盡而榜署,榜署不振而章記滋行,其為物,不受陰陽二氣、劫運三災之淪蝕,而一寄于靈人之手。”都是例子。引文見韓天衡編《歷代印學論文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2005年第446、48頁。但是嘉道以后,情形大變。宋書升《齊魯古印后序》云:“聞阮文達公輯吾鄉金石志,凡豐碑桓碣,鐘鼎盤敦之倫,莫不備載,其中古印亦甄賞至確,然非專書,所收之數,不過數十,覽者嗛焉。”袁寶璜《瞻麓齋古印徵序》云:“可以辨璽檢官私之制,可以窺篆籀形聲之變,可以考姓氏名字之異同,可以證地名官名之沿革,可以補經學史學之支流。”馮桂芬《三百蘭亭齋古印考藏序》云:“鼎彝尊卣盤敦之屬,往往可資以定經史之訛,而補所不及,印章亦其類,而官印尤足以證古官制。”⑥分別見《歷》,第1009、1017、938頁。當然,這里不必拘泥,只看其大勢。像元人揭汯《漢晉印章圖譜序》就說過“當時設官分職廢置之由,亦從可考焉”之類的話,參《歷》,第199頁。凡此,皆足為證。再如貨幣,自梁詩正而下,不再安于金石一門中的邊緣地位。梁詩正《錢錄》序云:“今單行于世,號為完書者,惟南宋洪尊《泉志》一編而已。……列朝政事之大端者畢著于此,《通典》,《通考》參差互見之處,亦得以探討其源流,而究其詳略,子亦考鏡之林也。”孫衣言《古今錢略序》云:“然則泉法雖國計之一端,其因革利病,亦古今得失之林矣。”姚覲元《古今錢略序》云:“固將與鼎彝款識,比崇類尊,可以察滄籀之異同,研形聲之正假。”⑦分別見《歷》,第841、864、866頁。金石門類的擴張,宛然可睹;其功用的多樣化,不限于小學一途,也不言而喻。
隨著清季古陶、封泥的出土,金石門類愈加壯大;尤其是陶文乃先秦古文字(時人多謂籀文),更增添了其分量。⑧例如吳大澂做《說文古籀補》就頗得益于新發現的陶文。劉鶚甚至說:“近年出土陶器,多三代之古文,可駕彝鼎而上。”見劉鶚《劉鶚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下冊第219、220頁。按照時人孫文楷的說法是“函圓錢方,別傳九府之制;泥封磚范,莫非三代之珍”,“陶器復傳,籀文大顯”。他總結道,金石各子類“一時分道揚鑣”。⑨《歷》,第993頁。
結果是,金石學一詞似乎越來越不足以盡斯學,最終逼出了羅振玉的“古器物學”:
考宋人作《博古圖》,收輯古器物,雖以三代禮器為多,而范圍至廣。逮后世變為彝器款識之學,其器限于古吉金,其學則專力于古文字,其造詣精于前人,而范圍則轉隘。古器物之名,亦創于宋人。趙明誠撰《金石錄》,其門目分古器物銘及碑為二;金蔡珪撰《古器物譜》尚沿此稱。嘉道以來,始于禮器外兼收其他古器物,至于李燕庭、張數味諸家,收羅益廣,然為斯學者率附庸于金石學也,卒未嘗正其名。今定之曰古器物學,蓋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學,金石學固不能包括古器物學也。①羅振玉《與友人論古器物書》,《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冊一,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68年,第75-78頁。
他以類別和流傳來涵蓋古器物學。流傳分而為四:鑒定、傳拓、模造、撰述。類別則一十有五:禮器、樂器、車器馬飾、古兵、度量衡諸器、泉幣、符契鉩印、服御諸器、明器、玉器、古陶、瓦當磚甕、古器范、圖畫刻石、梵像。
這還是“金石學”么?羅振玉根植于傳統金石學的脈絡作了新的嘗試,但還是稍嫌曖昧地補充說“殷墟之古骨角蚌甲象齒之類,并可考求古器物學”。那么,它們到底是屬于還是不屬于古器物學?羅振玉沒有說明。民國不少學人由于不甚接觸或接受考古學、現代史學和古文字學這樣的學科體系,希望在傳統脈絡中加以整合,因而有類似的思路或困惑。②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筆者另文撰述。但不妨拈幾個例子于此。馬衡主張“金石學”包容一切磚瓦、陶器、封泥乃至甲骨、明器等,認為“物質名稱(金石學)雖不足以賅之,而確為此學范圍以內所當研究者”,稍晚一點的朱建新也認為“雖不盡屬金石之范圍,而皆得以金石之名賅之也”。分見馬衡《馬衡講金石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3頁;朱劍新《金石學》,1938年,第3、4頁。但像陸和九這樣的金石學家則根本不贊同,理由是不能把甲骨陶玉竹木一股腦塞盡金石學范疇類,這是以現代考古學的名義扭曲金石學的本義。其實他忽略了一點,這一現象并不始于晚清民國,也不由于考古學概念的輸入。參所著《金石學講義》。
二、從有字之物到無字之物:以《漢武梁祠畫像考》、《簠室古甬》為例
金石學興起的內在動力與清代的實證學風有關,因此,毫不奇怪,它是以羽翼小學和經史之學的姿態出現或復興的。就其最初傾向來說,又與小學的關系尤密。清人鄒柏森、伍崇曜各有一句斬截醒豁的話,“金石之學,本于考據小學也”,“金石以款識為重,此古今通例”,陸和九也總結為“金石學者,以文字為主干”,頗能說明這一點。③鄒柏森《嚴州金石錄序》,民國《嘉業堂叢書》本。伍崇曜《南漢金石志跋》,《歷》,第275頁。陸和九《金石學講義》,北京圖書館出版公司,2003年,序1頁。這仿佛是不證自明的。古磚瓦的被重視就是個極好的例子。張廷濟曾慨嘆道:“瓴甋謂之甓,致頑物也,而求古者廁諸古鐘鼎碑碣之列,文字洵足重哉!”李兆洛也說:“嗜古者之不遺一字也,雖殘磚零甓,皆著于錄。或曰猥矣,然深求秦漢瓦當遺文,其偏旁損益,行筆曲直,咸有意理,可尋藉,可推見。”④《歷》,第 1064、1070頁。晚清之際,俞樾把它與鐘鼎碑碣并列,也是因其能“明小學”的一面。⑤俞樾《慕陶軒古磚圖錄》序,《歷》,第1069頁。可見物以字貴,其來尚矣⑥古代金石學家注重有字之物,并不全以古文字而言。這里的“字”字還有更廣泛的意義,即謂一切古器物上的“文字”。這一點需要澄清。它實際涉及到一個民族的文化審美心態。。
民初,法國人色伽蘭(Victor Segalen)也觀察到中國歷來偏重銘文字,輕視無字之物。⑦色伽蘭《中國西部考古記》,馮承鈞譯,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第19頁。帶著現代考古學的眼光看傳統金石學,當然覺得詫異。算起來,現代考古學源頭之一是十五至十八世紀興自意大利的“古物學”,從教廷到民間都在搜求希臘羅馬的珍奇古物。這極大影響學術界,初期不必說,像后期的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格外注重搜集古貨幣,并考證各種銘刻,稍晚的伯克(August Boeckh)、蒙森(Theodor Mommsen)更是編纂了希臘、拉丁語等銘文集成。⑧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5-13頁。張廣智《西方史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61、173、176頁。雖然西方古物學與中國金石學的預設任務不同,但有可比之處。西方古董主義盛行時,學界雖鉆研古希臘文或搜集銘刻,但大體來說,并不偏重有字之物。表面看,中國金石學似與之迥異。但若非清小學、考據學空前發達,是不會出現如此局面的。事實上,如果將眼光放到小學考據學尚未成為中心的宋代,我們會發現,那時的人們固然于金石文字表現出很深的喜好,但絕不能謂之偏重,像《考古圖》、《博古圖》等的大體精神就表現了這一點。
然而,色伽蘭詫異歸詫異,從清代金石學的發展來看,并非等到現代考古學的輸入,學人們的目光才從“字”轉移到“物”,盡管金石文字始終處于顯著的位置。這表明金石學對于古文字學的發展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們注意到的是,嘉道而降金石學內部蘊育著一股頗為強勁的思潮:考字不是金石學天經地義的任務,甚至羽翼經史之學也在內涵上發生了一定變化。這在下兩節將有更細致的論述。這里只以畫像、古傭兩個個案來揭示其方法和思路上的典型意義。
瞿中溶是嘉道間一個極有成就的金石學家。如果以考證作為標準,那么其《集古官印考》算是開山之作,可視為嘉道而后金石發展和流變過程中代表作之一。這里討論他的另一部著作:《漢武梁祠畫像考》。自序云:
翁覃溪閣學、畢秋帆尚書先后以此刻載之《兩漢金石記》及《山左金石志》,皆愛其文字而錄之,于畫像多忽,未為深考。

《漢武梁祠畫像考》
“皆愛其文字而錄之,于畫像多忽,未為深考”一句值得標出。又云:
后王蘭泉司寇又以其圖縮刻《金石萃編》中,亦不加一語辨之。予十年來恒以此圖置之案頭……近代博古家鮮知其出處,《山左金石志》并誤以李善為李固。……所畫男女容飾,衣冠帶履及宮室京灶、刀劍車馬、器械雜物等,雖未必今合乎古,而要不外漢代所遺之制。予故摘擇四十圖,別為一卷附后,以為考古者之助。①瞿中溶《漢武梁祠畫像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4-6頁。
武梁祠建于東漢桓、靈時期,位于山東省嘉祥縣。宋《金石錄》《隸續》已有與祠堂畫像相關的記載。乾隆中,黃易發現了這一遺跡,并推考了石室之制。嗣后,清人續有關注。②巫鴻《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柳揚、岑河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第11-57頁。與翁方綱、畢沅只注重祠中文字不同,瞿中溶敏銳地發現這些畫像對于考訂衣冠宮廷車馬一類的名物制度有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他對只注重文字風氣的反省及陳述的方法和目的,其象征意義不可小覷;咸同間張寶德的《漢射陽石門畫像匯考》,按說也是并不多見的畫像專著,然而大致內容不過是彙錄前人有關石門畫像的題跋文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微不足道。③張寶德《漢射陽石門畫像匯考》,《叢書集成初編》1618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總的來說,相較于馬邦玉《漢碑錄文》、端方《陶齋藏石記》仍然只關注畫像石題記、造像題名一類文字上的東西,這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延至光宣,王襄出了一部《簠室古甬》,也很值得注意。王襄是第一批接觸和研究甲骨文字的人,本文把他的《簠室古甬》作為個案來討論,是基于傳統金石學的脈絡。晚清河洛一帶墓穴發現不少明器,按當時一般學者的意見,自然屬金石學范疇。這本書著錄了俑、獸、井、灶等六十多件明器,各系以說明與考證;值得一提的是,各明器是以攝影的圖像著錄在冊的。王驤自序中注意墓穴、墓坑的長短高下,頗有現代考古學的影子,末有云:
以襄平素所見聞,證諸往籍所載,記足為考訂史家掌故之資。嗚呼!古俑之可寶,不第發前人未見之奇,識古之葬禮已也。其衣裳冠履,可考歷朝之服色焉;其跪拜立肅,可考歷朝之禮節焉;其裝飾、其制作,可考歷朝之習尚與美術焉。有是數者,得之者當如何珍惜也!①《歷》,第1100頁。
古俑上很少有文字,王襄卻很看重它的考古價值,其精神正與瞿中溶同。不同的是,武梁祠的畫像仍附有不少題記文字,為瞿中溶所一一按考,而古俑一類的東西則缺乏這樣的條件。也許,正因為古俑上沒有文字,王襄才會格外注重古俑本身及其巨大價值。
以上所舉僅是兩個極細小的例子。惟從有字之物而轉向無字之物,體現了清金石學內在變化的一端,所以有單獨拈出的必要。但是,如果真的要考察金石學的內在變化,那么必須放在一個更宏大的視野中才行。
三、轉向:從“生產過剩”到“主體凸顯”
首先必須申明,本文強調“轉向”,并不是說金石學將擯棄考證小學、經學的角色,這始終是它的任務之一。然而,就像上文論及的,對畫像、古俑的關注已和它最初被期待的角色有了出入。最終,金石學不斷轉向史學和古器物本身。探討所以然之故,宜從整個金石學發展的歷史中去尋找。
乾嘉而后,搜求金石的風氣極為狂熱。粗略統計,現存的金石學著作中,屬乾隆以前的不足七十種,之后的近二百年中則多達九百馀種。②容媛《金石書錄目》,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0年。容媛:《金石書錄目補編》,《考古通訊》1955年3期。這與我們的印象相合。本文第一節提到乾嘉時士人瘋狂搜購古磚、瓦當只是兩個極小的例子,“寒暑風雨,奔走高語”,“重寶奇器,往往朝出墟壟,夕登幾席”③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同治三年刻本,序言頁。端方《陶齋吉金錄》自序,光緒石印本。是相當普遍的。《金石萃編》、《寰宇訪碑錄》系列或更專門的彙編就是典型的產物。相應的,作偽之風大盛;雖然古器作偽始于宋,然而正如《宣鑒彙釋》所稱,“自乾隆后”才蜂起。此后,幾乎全國各地都有作偽能手。④朱劍新《金石學》,第169、170頁。按所引商承祚《古代彝器偽字研究》是節略文字,原載《金陵學報》三卷二期。士人一面憤慨“市井作偽之徒,又復窮極工巧,千慮之失,賢者不免”,“近時所傳鼎彝銘,托名商周,每多贗作”,“古器無文不惡,偽字則惡矣”⑤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后序、毛鳳枝《關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序》,《歷》,第266、807頁。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第7頁。,一面不得不提高警惕,像老向友人哭窮而又酷嗜金石的趙之謙免不了疑神疑鬼的,自以為有打假義務的陸增祥還趕作了《祛偽》一卷⑥趙之謙《趙之謙尺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2年,第149頁。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附有《祛偽》一卷,吳興劉氏《希古樓叢書》本。。
作偽的流行和辨偽的必要,正說明有市場。可是,研討金石變成一場“全民運動”,難免會滋生流弊。章學誠就責難“于今習為風氣”的外表下掩藏的是“驚博者侈其名目,鑒賞者炫其評騭”,陸增祥也以為“今之言金石者,大都矜尚紙墨,爭事新奇而已”,有人干脆說這是“葉公之好龍”或“流風相扇,拱璧求之,甚有目不識丁,脫所藏得以居奇,亦儼然自接於文雅”。⑦章學誠《江寧金石記》后序、陸增祥序《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后序,《歷》,第694、306、266頁。傅春官《漢射陽石門畫像彙考序》,《叢書集成初編》1618冊。其實,這還只是金石學最表面的亂象。深入追究一點,乾嘉而后,金石著述雖多,但大多只是著錄性質的。樊增祥于同治間謂“著錄之家,本朝極盛”,標舉了各種著錄體例,限以時代、一省、時代兼一省、一郡、一邑、域外、名山、一人、一碑的,或別以體、表、圖的,可謂粲然大觀。據當時人自省,就是考訂一途,也有“好深”、“好異”二弊,“往往以一得自喜,而全文不照”。⑧樊增祥《金石續編序》,《歷》,第294、295頁。王闿運《獨笑齋金石文考二集》序,民國十八年慧業堂石印本。
金石學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迅速掙得了自己的獨立地位。閻若璩、王鳴盛就曾各舉若干例子來追認五代以前的金石學者。如果說這是金石學興起之際,學人一時偶舉聊作談資的話,那么李遇孫著《金石學錄》考錄從漢代到有清的四百多位金石學家,就不免有建立譜系的意味了。⑨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歷》,第326、327頁。李遇孫《金石學錄》,民國二十三年《百爵齋叢刊》本。按,不久,陸心源撰《金石學錄補》又增添三百多人,有《潛園總集》本。入民國,褚德彝復作《金石學錄續補》,增考清末民初金石學家二百多人,有石畫樓刻本。此外,民國間田士彝別傳《金石著述名家考略》,得七百一十八名金石學家,與前三書重復甚多,有民國二十三年山東省立圖書館本。約略同時,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分圖書為十二類,金石獨為一類,與經學、小學、史學等并立。這尤有象征意義,仿佛在說金石學從附庸走向大國。⑩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3頁。目錄流略之學確有“辯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作用,但是不是絕對的。《漢書藝文志》“六略”中分類的混亂,很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學術性質考慮,而是考慮了六略書目數的平衡。因此,孫星衍的新分類,可能也是部分地基于金石著述的繁復,但不論如何,這并不妨礙金石學成為不可忽略的一門學問的事實。追溯起來,雖然鄭樵《通志》早就新立“金石略”,但自晁公武、陳振孫以至乾隆中修四庫全書,金石著述七零八落,幾乎散在經史子集各部里,而尤以經部小學與石經類、史部目錄類、子部譜錄類為多。[11]容庚《金石書錄目序》,《金石書錄目》,第4頁。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3、294頁。此外,羅振常也提過同樣的問題,見羅振常《碑藪序》,《歷》,第155頁。這時金石著述忽然“鬧獨立”,當然是有了底氣。孫的主張未被學界主流接受,其意義卻值得關注。同光之際,張之洞《書目答問》終于別辟了“金石”一類,雖然隸之史部,到底算是正了名。①張之洞的做法是一種權宜折中之計。有的金石著作,他仍入經部的“小學類”“石經類”,并不放在金石下。大約在他那里,經部仍具“優先選擇權”。見張之洞《書目答問補正》,范希曾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3頁。但是,為什么是史部?拿什么來自立?
清金石學興起之初,頗與考證一途相關,然而其功能是羽翼他者。就像張德容總結的:“我朝自顧炎武、南原、朱竹垞諸老,以金石佐經術,于是金石之學日盛。”那么如何“佐”經術?陸心源說:“書為六藝之一,金石又書之一端,金石而名之為學,猶諸子之別為九流,流之中又別有流焉。”②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序,《歷》,第263頁。陸心源《金石學錄補》序,光緒十二年《潛園總集》本。“書”指小學而言,不待贅言。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大多數金石學家注重的都是有字之物。因為清人治經精神為“經學即理學”,在方法論上則是“讀經自考文始”,“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小學成為經學的媒介和津逮。③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203-211頁。金文產自兩周,足以昌明小學,服務于經學;石刻除了有不少古文字,更有自漢至宋歷代的官刻石經,可與傳世經文相比勘。循是而論,學者在論及金石學的功用時或單舉其有益經學的一面,而不及小學,并不是忽略考字之用,而是經學包含小學之義,比如錢大昕謂“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里”、汪鳴鑾謂“金石者,經與史之旁支也”就是這樣的。④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14頁。應該說,“以金石佐經術”是卓有成效的,直到晚清,學者們還通過金文訂正了《尚書》“寧王”的一個訛誤;同時,金石學也促進古文字學的極大發展,吳大澂還看出了《說文解字》所收古文的真實時代。⑤裘錫圭《談談清末學者利用金文校勘〈尚書〉的一個重要發現》、《吳大澂》,《文史叢稿:上古思想、民俗與古文字學史》,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158-166頁、167-176頁。
金石學與古文字學的關系之緊是千真萬確的,即便在羅、王以前,古文字學已經在金石學的推動下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可以說是突破。⑥潘靜如《金文考訂與近代學術思潮—以莊述祖、吳大澂、孫詒讓的〈說文〉古籀研究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4年3期。這正是它不必假重經學的獨立價值所在。但是,就事實來看,金石學與經學的關系是被夸大了。之所以金石學家強調這一點,可能一是因為這確是它興起的原動力之一,再是不妨借經學以自高。雖然如此,在金石學極盛之時,已有違言。王鳴盛云:“金石之學,青主雖并稱有益經史,實惟考史為要。”法式善云:“余嘗謂金石文字足以備讀史者之采擇,此其功較專論小學者為更大也。”⑦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法式善《金詩文鈔序》,《歷》,第328、277頁。兩人不約而同強調金石學對于史學的作用,很可玩味。金石有益經史,自清初顧炎武已標為鵠的,為以后學人所繼承。但格外強調對于史學的作用,卻是乾嘉以來的新變化。所以乾嘉間章學誠撰《史籍考》在目錄部設金石一類,而道光間許瀚撰《史籍考》更進一步,辟金石為一門。逮張之洞撰《書目答問》,于史部專設金石一門,也就水到渠成。
從某種意義上講,不管是強調有益經學還是史學,金石學都不過是羽翼之而已。然而卻又有微妙區別。金石的有益經學⑧名物制度、世謚等暫不在內,詳后論。,除了石經而外,乃是一種迂回的方式,即通過考字、釋字的間接方式來實現的,故清人謂之“佐經術”。表面看,金石的有益史學也不過是補史文之闕而已,但金石文字及金石本身在客觀上即是史學研究的一部分。對于各個地方的金石來說,它們甚至構成了地方歷史或史學的主體:這與金石學家泛稱的“有益經史”有別。⑨這個“史”字,往往僅謂文字記載的歷史。吳方文稱“嘗考金石文字不獨可以證經典之訛,補史文之闕,而都邑之興衰沿革,往往志乘所不能言,言之而未盡者,每於碑刻中見之”、孫星衍稱“金石實一方文獻,可以考證都邑、陵墓、河渠、關隘、古今興廢之跡”,就是例子。⑩吳方文《括蒼金石志序》、孫星衍《京畿金石考序》,《歷》,第731、677頁。胡聘之更是舉出“可考者”八端:地域、戎備、官制、物產、水利、鹽法、封置、故實。[11]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序》,《歷》,第795-797頁。倘說,“佐經術”能夠給金石學以較崇高的地位,那么當金石學極盛之后,轉而強調自我與史學的關系,可說是主體精神的體現。
另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似乎被大部分清金石家所忽略:金石并非只有文字。一九一四羅振玉刊刻了吳大澂的《權衡度量實驗考》,他說:“考古禮器百物制度,蓋肇于天水之世,至國朝一變,而為彝器款識之學,專力于三古文字,不復措意于器物制度,其途徑乃轉隘于宋人。逮程易疇先生作《考功創物小記》……百余年來,寂無嗣響。”誠所謂慨乎言之,可與前引他標舉古器物學的文字參看。一九三八年謝國楨《吳愙齋尺牘跋》也說:“有清考據之家,率以聲音訓詁,疏通經義。自程易疇乃以古代器物,考證名物制度,然途徑雖啟,運用未宏。……先生深湛許學,博識名物,由古籀、陶文以訂補《說文》之未備,律度量衡古器之流傳,可實驗于今日。”[12]羅振玉《權衡度量實驗考序》,上虞羅氏《永慕園叢書》本。謝國楨《吳愙齋尺牘》跋,民國二十七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那么,羅振玉說“途徑乃轉隘于宋人”是什么意思?考宋人劉敞云:“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能為盡之。”①劉敞《先秦古器記》序,《歷》,第71頁。宋金石學的精神,于此可見;王國維據甲骨文考訂商王世系,實也在“譜牒次其世謚”理論的范圍內,此是后話。由于清小學發達,清金石學偏得其考字一途。程氏《考功創物小記》算是有清名物制度的開創之作,惟他所見的古器物還是有限。在金石學發展過程中,不是沒有學者發現金石學對名物制度考證的絕大作用,像吳云就意識到這一點,且謂“使易疇(程瑤田)當日得見余所藏二器,正可不煩而自解”②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序,同治十一年刻本。。只是相比于考錄文字,古器物圖錄的著述并不多,圖釋就更少了。但隨著金石著述的堆積,學者漸厭惡“侈其名目”,“爭事新奇”的現象,從而思于考字之外,別啟新宗。吳云做《兩罍軒彝器圖釋》就隱逗消息,至吳大澂則專精而系統地撰述了《古玉圖考》、《權衡度量實驗考》,可視為宋金石學精神的恢復。實際上,古玉、權衡度量而外,像官印、貨幣包括前舉的畫像、古傭等古器物都陸續有了相當于名物制度研究的專著,因此毋寧把它視為清金石學發展中轉向自我的一個象征。當然,就像吳大澂自己說的,從古玉可以考見的是典章制度、宗廟會同祼獻之禮、君臣上下等威之辨。③吳大澂《古玉圖考》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頁。這仿佛仍只是資考經學或史學而已。不過,我們知道這與通過古器物上的古文字或文辭來考證經史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因為它是從古器物自身出發。后來,馬衡講金石學分為金石文字之學與古器物學二途,并非全然承自宋人緒論或受新學影響,清金石學中后期的轉向亦有以致之。④馬衡《馬衡講金石學》,第4頁。

張之洞

吳大澂

羅振玉
清金石學轉向的征兆其實不止于此。例如在金石極盛的嘉道時期,有個叫黃錫蕃(1761-1851)的還作了《刻碑姓名錄》來考錄歷代刻工姓氏:“金石之學,自歐趙以來,著作大備,體例不同,撰人、書人無不詳載,惟鐫刻姓氏,往往闕如,而不知書之妙尤賴刻之精。”⑤黃錫蕃《刻碑姓名錄》自序,民國三十七年《咫園叢書》本。雖然他這樣做一是為了發明體例,二是看重“書之妙尤賴刻之精”,并不宣稱有何深遠的意義,但是如果金石學的價值只是在“佐經術”而已,他大可不必這么做。放在比較視野下,西方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興起的針對十六、十七世紀圖書排字工的研究,頗足相與映發。一個叫托馬斯·薩切爾的人懷著對“排字工態度”的興趣展開了莎士比亞的文本研究,不用說,它的根本興趣在莎士比亞,不在排字工,但卻不經意間打開了書志學(bibliography)中制作線索研究的一個重要窗口。⑥G·托馬斯·坦瑟勒《分析書志學綱要》,蘇杰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8-85頁。回到黃錫蕃那里,他的興趣固在“體例”和“書之妙”上,但考證出的“有一人而刻數碑,數人同刻一碑”等結果,卻為石刻文本的互相校勘和石刻制作研究提供了可能。

《積古齋鐘鼎彛器款識》

《權衡度量實驗考》
四、考據話語與藝術話語的歧途
截止目前,我們的論述都是依金石學自身的脈絡而展開的。換言之,我們的論述全然從清代考據學推動了金石學的發展這一事實出發。但如所周知,金石本身還是一門藝術。也許是巧合,歐洲與中國古器物崇尚熱潮的極盛期出奇的同步。①前些年美國bard學院發起了“歐洲和中國的古董主義與知識生活”(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的一個比較研究,筆者未獲一手文獻或成果。白謙慎《西方學術視野中的黃易及清代金石學》,《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序二,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年。更巧合的是,同在十九世紀,那個編有《希臘銘文集成》的伯克在古代度量衡上有了革命性的發現②伯克《古代度量衡考》(Metr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über Gewichte,Münzfüsse, und Masse des Alterthums)出版于1830年代末。,遠在東亞的吳大澂也完成了他的《權衡度量實驗考》。只是這樣的個案比較很難被賦予任何昭示性的意義。但是,如果從各自的原動力及表現出來的形態和結果出發,不乏互資鏡鑒的地方。
自趙宋學者就認識到金石有助于考訂名物制度、小學、君臣世系。現存最早的金石著述作者歐陽修也說:“可與史傳正其闕謬。”③歐陽修《集古錄目序》,《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叢刊》本。這是極自然的。清金石學家同樣強調金石學對于經史小學的考訂作用,像“辨經史之疑,訂傳注之失,考古文、篆、隸、行楷訛俗遞變之由”,“夫金石所以重者,以其有關經史小學耳”,“古人之事跡,以及姓氏爵里名物足以考證經史小學”,“有足證文字之源流者,有足辨經史之訛舛者”,“研究金石之學,說古文形義,舉證經史”,“足以訂經注之疏,補史傳之闕,備小學之考”這樣的表述隨處可見。④吳玉搢《金石存》自序、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陸增祥《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序、張鳴珂《從古堂款識學》跋、陳祖范《中州金石考》序,分見《歷》,第272、308、306、398、445、765頁。
不過,金石學是不是只有考訂一途?吳受福說:“金石之學有二:曰考訂,曰品騭。”⑤吳受福《清儀閣金石題識序》,《歷》,第333頁。好像并不自限于考訂。但這樣忠恕的論調,在其他人著作中很少看到。觸目所及,都是“但評詞章之美惡,點畫波磔之工拙,何裨實學乎”,“墨妙萃于一亭,蘭亭至八千匣,卒歸湮沒,無補遺文,是為好事家;又如品評優劣,講求書法,名跡有書賈之目,寶章有待訪之編,是為賞鑒家,皆于金石無與焉”,“翁覃溪一輩,雖名金石家,實與董思翁、孫壯海、王箬林之流鑒賞家無異”,“絕無考證,尤無與于金石之學”,“以商周遺文,而乃與晉唐隸草絜其甲乙,其于證經說字之學,庸有當乎”這樣的話語。①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序》、張德容《二銘草堂金石聚》自序、)潘祖蔭《二銘草堂金石聚》序、陸增祥《二銘草堂金石聚》),《歷》,第327、263、260、262頁。孫詒讓《古籀拾遺序》,《籀庼述林》,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128頁。很顯然,不但古物收藏、藝術鑒賞一途不在定義范圍內,便是詞章義例之學也被輕視。②張之洞《書目答問》細分金石為四科,曰目錄、圖像、文字、義例。但是,在大多金石學家的眼里,義例一科算不上金石學。或許就像芬利(M. I. Finley)主張將史學家(historian)與好古家(antiquarian)相區分一樣,清學者也亟思將金石學家與古玩愛好或鑒賞者劃清界限。③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N.Y. : Viking, 1986, p.6.有趣的是,若按照芬利的標準,清代以摭拾考訂為宗的金石學家恰恰也只能算是好古家一列,只有黃宗羲、王夫之、趙翼一流人物勉強夠得上史學家的資格。由此可知,清人承認的金石學只是考據一途。
這當然好理解。同治年間,楊守敬曾說過:“金石之學,乾嘉間為最盛,蓋自一二碩儒,標厥風旨,承學者遂爭趨焉。大抵江、浙、兗、薊之士為多,非必好尚之獨異也。”④楊守敬《激素飛清閣評碑記》,《歷》,第5頁。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甲于天下,乾嘉間最著名的金石學家差不多都來自這里,他們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共同體”,流風所被,漸及山東、直隸乃至全中國是自然而然的事。⑤關于“江南學術共同體”的提法也許還有一定的爭議,但仍不失為一個詮釋或理解清代學術發展的有效路徑。參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最重要的是,考據學風的興起,也正源自江南地區。這樣看來,不管是從因字通經的內在理路來說,還是從業已形成的崇尚實證的學風來說,清金石學最終似乎只能入于考據一途。
比較起來,從十五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復活了人們對古典世界的興趣,其中就包括對古器物的搜藏、古遺址的探尋。所謂珍奇柜就是源于此時的古物收藏者尤其是教廷和皇室的權勢階層。盡管最初的收藏基于興趣或趣味,但研究活動繼踵而來,逐漸萌生了諸如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學問,與并時的校勘學、古文書學、古文獻學桴鼓相應。人文主義極盛之后,約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迎來了一個湯普森所謂的博學時代(Age of Erudition);圣摩爾派是這一時代的典型,值得注意的是此派人物如馬比昂、蒙福孔等無不精于古文字學。⑥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77頁。關于“博學時代”源流始末的簡單介紹,可參張井梅《淺論西方史學史上的“博學時代”》,《史學史研究》,2008年,3期。截止這里,外在形態與乾嘉而后的金石學十分相似:知識淵博被推崇和追求,針對古器物的學術活動毋寧說是搜集、整理和考訂。盡管如此,在古物學興起伊始,西方于古器物(不管有字無字)而外,也相當重視古遺址,由意大利而波及英國,甚至逐漸發展出了田野考古學。⑦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5、6頁。這顯出二者的不同。然而更重要的不同也許是,源于對古典文化的熱情,歐人并不放棄對古代藝術(古物是其載體)的膜拜與探索,盡管約在十六世紀從中分化出了“歷史古物學”。約略說來,歐洲古物學的興起與追尋失落已久的人文精神緊密相聯,在發展中才分流到各種學術體系里。而清金石學,如本文開篇所說,是一種目的金石學,從根本上把藝術鑒賞排除在外,只實踐、鞏固了考據學家的話語,體現出一種智識主義傾向。⑧徐復觀以為清人沒有發掘出中國藝術根源、把握藝術精神的關鍵,是他們在八股影響下的長期墮落所致,恐怕并不確切或完整;這實際與清代的實證主義學風關系極大。但他說古代藝術(品)只能在古玩家手中,保持一個不能為一般人所接觸所了解的陰暗角落,則是昭然的事實。參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序第2頁。
當博學時代過去后,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史學相繼迎來了被稱作理性時代、浪漫主義、客觀主義、實證主義等的階段。這與早先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發展都息息相關。這里僅關注它們與古物學之間的線索。按照西方學者的意見,近代興起的古典學術研究要混合不同領域來進行,不但靠歷史文獻和其他書面文獻,也要依靠大量的銘文和紙草文獻。這個龐大的計劃需要各領域的細致研究,像對重寫本(palimpsest)、銘文(inscription)或古物(Antiquities)的研究都屬于這一類工作。這種項目自然會導致古代史研究要采納很嚴肅的現實主義觀點,遷流衍化,最終在某一階段表現為實證主義。由于枯燥僵硬的實證主義對學者著作的逐漸浸染,學者把他們的視野局限在狹窄的專業之內,在古代史方面越來越只見其木、不見其林。⑨休·勞埃德-瓊斯《導言》,維拉莫微茲《古典學的歷史》,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序第8、9頁。這與清金石學極為相似:“實學”達到了一個相當的水準,但缺少積極的會通精神。然而,歐洲實證主義很快引起了歷史主義與它的抗衡。很明顯,在歐洲古物學發展過程中,實證主義只是流,而不是源。但在漢學、考據學的引逗或籠罩下,清金石學家從一開始就抱著“金石之學,本于考據小學”的宗旨和實證主義的態度,宋、明時代的古器物研究和藝術精神探索無形中成了被壓抑或不受歡迎的偏門小道,盡管這一行為并未絕跡,事實上,也不可能絕跡。因為承認也罷,不承認也罷,清金石學家雖然宣稱金石學是要考字證經的,但士大夫式的趣味賞玩始終是一種客觀存在,一如在歐陽修或趙明誠那里所表現的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