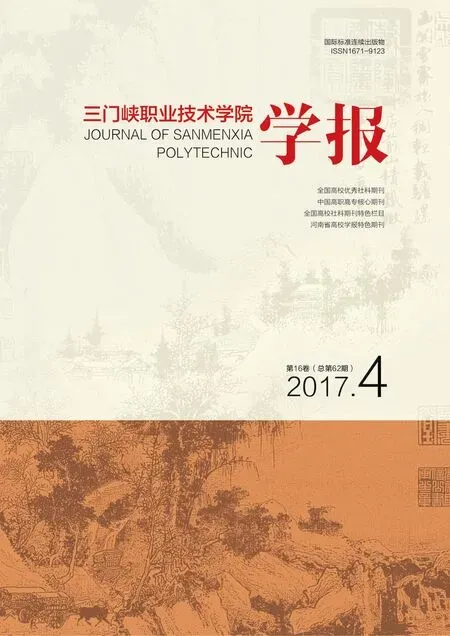試論“底柱隘”對三門峽漕運的影響
——從“鐫廣”治河與“砥柱山崩”談起
◎祝昊天
(陜西師范大學 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西安 710062)
自先秦以來,河、渭水道上即有“泛舟之役”,作為連接東西之間的重要通道,如漢初“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1]但凡有建都于關中者,必然要予以高度重視。但眾所周知,黃河水道尤以三門峽段最是險要,受阻于此,沿途漕運其實并不暢通,從而極大限制了東西之間的運輸往來。有鑒于此,歷代居于長安的統治者皆為之所困擾,不計成本地投入到河道修治,只為疏通這條關乎都畿供應的經濟動脈。
事實上,關于三門峽漕運的問題已有不少論著,[2]常言漕運艱險,但就河道狹隘的問題,卻鮮有關注,仍有待作進一步討論。
一、“底柱隘”與“鐫廣”治河
有漢一代,三門峽漕運始初成規模。自武帝執政起,就不斷增加關東漕糧的輸入,最多時“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1]其后仍有“歲漕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之“故事”。[3]然而,如河東太守番系所述:“漕從山東西,歲百余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1]基于運輸損失嚴重的事實,當時已有感到“砥柱之限”的影響。

圖1 三門峽形勢圖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三門峽漕運遺跡》,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2頁。
其后,據《漢書·溝洫志》載:成帝初,因“屯氏河塞”,導致黃河泛濫,至鴻嘉四年(前17年),“從河上下,患底柱隘”,為緩解下游河防的壓力,丞相史楊焉提議“可鐫廣之”,意欲將河道拓寬,以疏緩水勢;但“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反倒造成大量碎石壅塞河道,“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于故”,結果適得其反。[3]于此時,曾明確指出“底柱隘”的存在。
又以酈氏注《水經》所述,有詳細描寫此段河道的情況: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辟,尚梗湍流,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4]
就地質構造而言,“三門峽北為太行山系,南為秦嶺山脈,南北兩山夾持,使三門峽成為黃河水系東流入海的重要通道”,[5]因兩側山地持續抬升,水流下切侵蝕加劇,發育成深切峽谷;又以黃河地塹不斷下降,構成盆地底部,表現出了較為顯著的堆積作用。據此,與《水經注》文字描述聯系,如“河水翼岸夾山”語,河道經三門峽段已明顯收窄,加之從上游攜帶下來的河流堆積物沿途沉積,在河床上堆積成了諸多深淺不一的河灘,讓原本就并不寬闊的水域更顯“擁堵”(參見圖1所示);而受此影響,河水也收束成“閼流”,每每經此峽谷隘口,水勢稍有增大,極易形成洪流沖下,這點尤其對逆流而上的漕船構成嚴重的安全威脅。
同例,引《后漢紀》所載:興平二年(195年),獻帝逃亡至陜,遭李傕所部圍攻,于此危急形勢下,別將李樂“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登也。”宗正劉艾亦曰:“臣前為陜令,知其險。舊故有河師,猶有傾危,況今無師。”[7]就其所述,可見東漢時已有設置專門負責導航的“河師”,但即便如此,航行仍“猶有傾危”,以至于連一般航行都不能保證,可見通行條件確實惡劣。
另據酈氏注《水經》所引《五戶祠銘》:
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以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眾五千余人,修治河灘。[4]
可知魏晉時期已“歲常修治”,當是利用枯水期時間,對河道堆積物進行清理。只不過,這些工程多“功卒不集”,故“雖世代加功,水流漰渀,濤波尚屯”,效果并不明顯,而“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眾峽諸灘之言”。[4]
那么,誠如番系所言“砥柱之限”一語,砥柱勢必對三門峽漕運造成限制。
二、“砥柱山崩”導致“壅河”
值得注意的是,類似于漢代情況,隋初也有對砥柱進行過一次穿鑿。據《隋書·高祖紀》載:開皇十五年(595)六月戊子,隋文帝“詔鑿砥柱”,[8]并下令修復沿線的棧道,意欲重新疏通三門峽漕運航道。但遺憾的是,限于《隋書》未修《溝洫志》文,有關此次工程的記載已不甚詳細,僅《食貨志》有載:開皇時,“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于路,晝夜不絕者數月”。[8]似是東西之間運輸暢通的表現。
然而,這種情況并未能持續太久。此前,一般以隋末動蕩作解釋,但卻很可能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史實,即“砥柱山崩”導致“壅河”。據《隋書·五行志》所載:大業七年(611),“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8]這本是一次災異記錄,但卻與“底柱隘”有著直接聯系:按“砥柱山崩”所述,勢必會產生大量碎石落入黃河中,只因河道狹隘,積塞住水口,形成“壅河”現象,致使河水倒流數十里之距。無獨有偶的是,《史記》中也有類似于“山崩”、“壅河”的記錄,據《魏世家》所載:(魏文侯)二十六年(前 400),“虢山崩,雍河”。 按正義注所引《括地志》云:“虢山在陜州陜縣西二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余也。”[1]如是說,這次“虢山崩”應與大業七年“砥柱山崩”的情況基本相同,那么類似情況的發生也就絕非偶然。
事實上,三門峽所處正當汾渭地震帶活動范圍,參照《中國歷史地震圖集》統計,[9]這里歷史地震活動頻繁而強烈,僅有記載的破壞性地震就達87次。[10]有鑒于此,自是常有“壅河”現象發生,對河道形成不同程度地堵塞;所以,也就有“歲常修治”的需要,若不及時進行清理,恐怕只會使“底柱隘”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直至航道徹底斷絕。顯然,經過這次“砥柱山崩”,三門峽漕運再度中斷,隋代為修治河道所付出的努力幾乎作廢。
至唐初,經行砥柱已被往來船只視作畏途。據《新唐書·藝文志》載:武德五年(623),“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11]同引《歷代名畫記》述,此行還有“兩都秘藏之跡,維揚扈從之珍”,包括大量珍貴書畫在內,皆“忽遭漂沒,所存十亡一二”。[12]考慮到這次運輸的特殊性,行船時必定十分小心,在排除人為因素后,仍不可避免傾覆損失,則只能證明航道確實早已殘破不堪,甚至根本無法安全通行。
面對如此情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唐朝都只能“自洛到陜皆運于陸,自陜至京乃運于水”,等同于放棄了三門峽漕運,“以避底柱之險也”,[13]但這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三、“底柱隘”對運輸效率的限制
繼前文所述,既以“底柱隘”的存在,僅就運輸而言,最直接的影響莫過于對效率的限制:經此峽谷隘口,不僅“閼流”為險,航道也相應收窄,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門峽漕運單位時間內漕船通行的數量。對此,可試以數據推算來進行初步論證。
首先,是對漕運運量進行估算。以唐代漕運為例,主要以玄宗時期作參照:開元二十一年(733),按裴耀卿所提“節級取便”方案,[14]開辟“北運”線路,“凡三歲,漕七百萬石”,[11]年均約 230萬石;而“開元初,河南尹李杰始為陸運使”,設“八遞”用車,“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后至一百萬石”,[15]是為陸運數額;至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但遭安史之亂破壞以后,唐后期漕運狀況已大不如前,僅“水陸運每歲四十萬石入關”,[16]尚且不能保證。據此分析,在扣除陸運部分后,推算運量可達到130-200萬石左右。同理,按度量衡標準折算,[17]漢代運額亦在此范圍內。
其次,是對漕船載重與數量的計算。據《宋書》載:劉裕率水軍主力西進,經陜城至潼關,以“龍驤將軍王鎮惡伐木為舟,自河浮渭”,直攻長安。考慮到“鎮惡所乘皆蒙沖小艦”,[18]可見砥柱一段并不通大船。但即便是一般漕船,卻也有明確的載重限制,如人門棧道摩崖題刻(人Ⅵ段T6)記載:
大唐貞觀十六年四月三日,岐州郿縣令侯懿、河北縣尉古城師、前三門府折沖侯宗等奉勑造舩兩艘,各六百石,試上三門。[6]
就這次試航所見,較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所述,[19]應與實際大體相符。若按此計算,則以往對漕船的需求量當在2000-3000艘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另引《新唐書·食貨志》所載:
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
為確保漕運的恢復,劉晏曾在揚州定制“上門填闕船”,載重可達1000石,幾乎是一般漕船的兩倍。很明顯,之所以要更大的容量,只能是為縮減船只的數量:
考慮到“底柱隘”的存在,經行漕船在數量上必然受到限制,若是容量太小,導致所需數量過多,就會在砥柱之側造成擁堵;所以,這才要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增加單次通行的運量,是為提高運輸效率所用。
再次,是對通行時間的推算。據載:宋初為營建汴京,曾在岐、隴以西采伐大量木材,彼時“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渭達河,歷砥柱以集于京師”。[20]相較之,冬季本是明顯的枯水季節,如“此冬閑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19]常整治河道;而夏季則有伏秋夏汛,引裴耀卿描述:“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21]可見于汛期航行確實危險。所以說,僅春秋時節才相對適宜運輸,則每年也只有五個多月時間可供通行。
那么,何以在限定時間內完成相當數量的運輸,也就成了三門峽漕運所必須要面對的難題。對此,引唐人李繁所撰《鄴侯家傳》記述:
唐時運漕,自集津上至三門,皆一綱船夫并牽一船,仍和雇側近數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門常有波浪,每日不能進一二百船。觸一礁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渦中,更不復見……故三門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近百日方畢,所以漕運艱阻。[22]
據考,此處“一二百船”似將“十”誤寫作“百”,[23]按數量計算,則與《新唐書》記載大體相符:時以“運舟入三門”,而“一舟百日乃能上”,稍不慎,即“覆者幾半”。[11]就實地所見,假以人力纖挽,漕船只能逐一排隊通過三門,考慮到纖引的過程并不輕松,若真是按“每綱上三門,無損傷,亦近百日方畢”來推算,則數千艘船只必定會擁堵于三門之下。
實際上,在相對理想的狀況下,每日漕船過砥柱者尚且不足20艘,即便是按單程運輸,在限定時間內,全年通行量至多也就3000艘,這與之前推算的數字基本相符。但是,對河道的清理難以長期維持,何況還不時會有“山崩”導致“壅河”;在更多時候,河道擁堵反倒是三門峽段漕運所要面臨的常態,像安史之亂后,河工廢棄已久,而運量也就萎縮到不足40萬石的規模,可見運輸效率已降至低點。所以說,因“底柱隘”的存在限制了運輸效率,實乃三門峽漕運不暢的根本原因。
四、輔助線路的開辟
有鑒于此,基于對“砥柱之限”的認知,當低效率的運輸不能滿足需求時,就只能選擇另辟線路。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11]在唐玄宗統治下,為擴大運量,至少開辟過三條輔助線路:
其一,“北運”線路。如前文所述,按裴耀卿所奏,開元二十二年(734),在“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經此船漕車轉,過十八里陸道,“以避三門之水險”;事實上,正是由于這兩處倉址均在黃河北岸,故“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至貞元時,為恢復漕運,陜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與前作十八里陸道并行,專“治上路以回空車”,而另設下路以行載重,如此形成對流運輸,更進一步提高了效率。
其二,“八遞”南路陸運。開元二年(714),自“河南尹李杰為水陸運使”算起,即“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長四十里”,[15]其間“用車千八百乘”,往來于各“遞場”轉接,是為黃河南岸主要的陸運線路。及裴耀卿罷相后,“北運頗艱”,“八遞”運輸自是更加繁忙;然而,“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為減少運輸對畜力資源的占用,“乃為交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仍是借以船漕車轉的方式進行漕運。
其三,“開元新河”。顯慶元年(656),“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意欲直接在人門左岸開辟出一條道路來,無奈“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可見這在工程設計上仍有不小難度。繼其后,開元二十九年(741),又有“陜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漕”,如“開其山巔為挽路,燒石沃醯而鑿之”所述,這是難度和規模最大的砥柱整治工程,[24]用工著實費力,這才好不容易穿鑿出來一條人工石渠,史稱“開元新河”。經此“新門”,漕運得以“辟三門巔,逾巖險之地,俾負索引艦,升于安流”,[21]從而省卻不少轉運勞煩。
總體而論,這三條輔助線路的開辟不僅是為改善運輸條件所用,除繞行砥柱以求安全外,更大意義還是在于拓寬漕糧運輸的渠道,以增加運量。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增運線路的開辟往往因時所需,受條件所限,與預期尚且存有一定的差距:僅以“開元新河”為例,按《唐會要》所述,工程自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始,至天寶元年(742年)正月二十五日“渠成放流”,[25]工期僅三個月的時間,不免略顯倉促;雖已完工,“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這與楊焉“鐫廣”治河情況較類似;此外,由于人工石渠穿鑿的深度明顯不足,實際上僅容黃河水流漫過,卻無法載舟承重,只得“候其水漲,以人挽舟而上”,還是需要借助于人力纖引;故此,“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只因“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11]最終不了了之,但僅數年過后,石渠便因“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26]可見這條新開辟的線路其實也未能使用多久。
五、結論
綜上所述,“底柱隘”是造成三門峽漕運一直不暢的根本原因。
就環境構造而言,因水流的下切侵蝕作用與周邊山地持續抬升,遂有在三門一帶發育出深切峽谷,由于黃河河道經此開始明顯收窄、比降趨緩,導致從上游攜帶而下的大量河流堆積物沿途沉積,占據原本就不寬闊的水域,使河道更顯“擁堵”;受此影響,河水收束成“閼流”,加之“砥柱山崩”影響,于砥柱之下形成激流險灘,已為經行于此的船只所視作畏途。
對此,考慮到河道航行過于艱險的存在,為確保關內漕運的輸入,古人或修棧道以供纖挽,或設門匠沿途導航,或用河師定期清理,幾乎想盡辦法;然而,雖使漕船得以安全渡過砥柱之險,卻仍不能改變三門峽漕運不暢的現狀。歸根到底,還是因為河道狹隘的存在,從客觀上限制了運輸通行的效率,這才是關乎整個三門峽漕運的“瓶頸”所在,即“砥柱之限”所指。
所以說,正是基于實踐積累中的認識,才會有楊焉“鐫廣”治河的想法,所言“底柱隘”者,亦是對三門峽地勢的準確描述,只是受限于當時的工程技術水平,尚且難以達到預期效果,故雖有大力投入,但還是難以解決實際問題。有鑒于多次穿鑿砥柱的工程失敗,唐代漕運開始轉變思路,通過船漕車轉的方式,靈活轉運,繞行于砥柱之側,另行開辟輔助線路運輸,水陸并行,從而拓寬了運輸渠道,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效率,最終實現了運量增加的目的。
[1]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2]李久昌.崤函古道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3]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4]酈道元.水經注校證[M].陳橋驛,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5]王均平.黃河中游晚新生代地貌演化與黃河發育[D].蘭州:蘭州大學,2006:12.
[6]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三門峽漕運遺跡[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7]袁宏.后漢紀[M].北京:中華書局,2002:544.
[8]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9]國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國歷史地震圖集[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
[10]馮興祥.三門峽盆地的新構造運動與地震活動[J].河南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82(1):53-59.
[11]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2]張彥遠.歷代名畫記[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10.
[13]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M].北京:中華書局,2005:2101.
[14]何汝泉.唐代轉運使初探[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10.
[15]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92:224.
[16]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3:35.
[17]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233-236.
[18]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9]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0]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4:633.
[21]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2]王汝濤.類說校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46.
[23]姚漢源.黃河三門峽以下峽谷段兩岸的堆臺[J].人民黃河,1982(4):52-54.
[24]王雙懷.唐代水利三題[M]//王雙懷.古史新探.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3:155.
[25]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1598.
[26]王若欽.冊府元龜[M].北京:中華書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