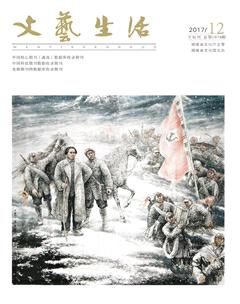女媧圖像演變之管見
摘 要:女媧是中國最古老的女神之一,她補天治水、創神造人、創設婚姻、制簧置笙,對人類活動做出了重大影響,其神話成為中國上古神話傳說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關于女媧神話的研究在中外學術史上從未中斷,本文試圖從其形象的演變進行細致研究。
關鍵詞:女媧;形象;演變
中圖分類號:K87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36-0074-02
一、女媧的敘事演變
中國神話傳說豐富多彩,被后人千古傳誦的女媧傳說就是其中精彩的一篇。據考證,古籍中女媧一詞最早出現在屈原的《楚辭·天問》:“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之后,在許多典籍中出現了對女媧傳說的記載。
如《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記載:“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晉郭璞注《山海經》時這樣解釋的:“ 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化七十化,其腹化為此神。”這些神話傳說的初始階段,人首蛇身的女媧神性色彩濃厚。她創世造神,化生萬物;摶黃土做人,貧富有別;煉石補天,疏導洪水;創制婚姻、嫁娶有禮;創制音樂,始作笙簧。于是女媧以祖神形象、救世神形象、媒神形象以及樂神形象展現在人們面前,作為母系社會女性崇拜的極至,女媧成為三皇之一,以“圣王”形象受人膜拜。
但隨著時代變遷,一方面蒙昧時代的逝去和文明程度的深化,遠古的神話人物不再廣泛受到人們頂禮膜拜,人們也不再從宗教祭祀的角度和崇拜的心理來敬仰神話人物和故事,轉而客觀地認識到它們只是虛構的神話現象。
另一方面,主要作為遠古母系氏族社會階段社會生活反映的女媧傳說,在父系社會中男權夫權主義處于主導地位的形勢下,在中國封建社會最根本的皇權觀念影響下,漸漸弱化,淡出政治統治領域,于是,女媧傳說轉而在文學領域異彩紛呈。
例如曹植在《女媧贊》中從文學的角度,將女媧置笙簧這一神話題材做了藝術的描繪:“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靈。”這一過程中,女媧的形象也漸漸褪去獸性,朝著更為人性化的方向發展,并最終衍化成為美麗的人形女神。其功能也從創世神圣女皇的宗教意義逐漸被文學作品中的社會意義所替代。在曹植的美文《洛神賦》中,女媧造笙簧這一神話傳說被藝術加工為清歌漫舞的美妙姿態:“于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云車之容裔。鯨鯢踴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
二、女媧的圖像演變
神話傳說中遠古神的形貌,大部分都是恐怖的半人半獸形象,例如西王母,最早出現正在《山海經》中的形象呈獸人、神人的混合體,她外形似人,身綴豹尾,口含虎齒。這些神話形象都是遠古時代人類原始宗教信仰中圖騰崇拜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原始宗教圖騰誕生之初反映了先民們對難以戰勝的猛獸的恐懼,以及對大自然神秘力量的畏懼與崇拜。女媧人面蛇身的形象亦體現于此。
女媧傳說出現在許多的歷史典籍中,它們雖然分散,但我們依然能從中看到這位傳說中人類始祖的豐功偉績,但是這些典籍中缺乏關于女媧外在形象的具體描述。根據文獻考證,直至戰國中后期,女媧尚未形成像漢代那樣較為固定的人首蛇身形象,這一點,從成書于戰國中后期《山海經·大荒西經》的記載中可以反映出來。東漢王逸注《楚辭章句》:“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這些是目前被認為最早的關于女媧外形記載的文字,但是除了人首蛇身之外沒有其它更具體形象的描述。隨著考古發掘成果的不斷擴大,可供參考的資料愈來愈多,反映女媧外在形象資料的載體形式亦豐富起來(木漆彩繪衣箱、彩繪帛畫、畫像壁畫、畫像石等)。文獻與考古發掘出的成果相結合,使女媧的形象及變化過程變得日漸清晰。
(一)女媧早期以獨立神形像出現
呂微先生認為,在絕大多數先秦典籍中,言伏羲者不同時言女媧,言女媧不同時言伏羲。這一點長沙馬王堆墓的帛畫似乎可以佐證。其一號墓與三號墓中均有彩繪帛畫。此畫T 字形的橫幅和豎幅分為天國、人間、地府三部分。上段居中位置的日、月之間,端坐著披發的人首蛇身的女媧,其人首處理上,披長發,垂下的發梢搭在蛇身的位置,人面描繪清晰;服飾上,為藍色衣;形態上,紅色蛇身部分環繞盤踞。在女媧的左、右上方,分別繪有太陽與月亮,且太陽中繪有金烏,日下有扶桑樹。月中繪有玉兔和蟾蜍,月下是奔月的嫦娥。
可見,在漢初的墓葬中已出現單個的人首蛇身圖像,而且女媧人首蛇身的形象塑造已較為細致,具有圖騰形象的特點。帛畫中女媧與日月組合,象征著生生不息的生命世界,體現出女媧創世神、造物神的形象。此時的女媧在發飾與服飾均上帶有人的特點,且多見于女性的墓葬。這類型的例子還有,山東昌樂縣三冢子村出土的女媧畫像石,女媧人首蛇身,一手執矩,雙肩有羽翅,身后立一女侍,尾下是獸面的銜環鋪首。陜西綏德出土的女媧畫像石,畫像為女媧的側面,有頭飾,此外無其他飾物,造型古樸簡潔。
從史料看,在大多數先秦典籍中,女媧出現時并未與伏羲相提并論。女媧與伏羲分言的事實,說明兩者最初是分屬于兩個不同的神話傳說系統,而且就女媧形象而言,早期只是一個造物女神的形象,還沒有被納入到漢代“三皇”的系統之中,經過兩漢時期的不斷改塑,才最終完成女媧從“女神”到“圣母” 的形象演變。
(二)女媧伏羲的相對而立不交尾,或相對交尾圖像形式
1.西漢中晚期的女媧圖像多以伏羲、女媧人首蛇身相對或是交尾的構圖出現,此時的伏羲、女媧被視為人類始祖或是古代圣王形象,在伏羲、女媧交尾的圖像中,多是將伏羲、女媧塑造為偶象組合。漢昭帝至宣帝時期的洛陽卜千秋墓壁畫,是目前在河南文化區見到的早期伏羲、女媧圖。此圖女媧在前,緊接著是青龍、白虎、朱雀、仙女和卜千秋夫婦,最后是伏羲。伏羲女媧位于壁畫的首尾兩端,相對而立,均為人首蛇身。女媧位于畫面左側,上身人像,面目清秀,長發,大髻盤頭,著女服,拱手面向月中蟾蜍,下身蛇尾殘損一半,僅存上翹尾部,與頭等高。其右側為一圓形白色月亮,四隅用白、綠兩色繪制山字形光芒,以紅色鋪地。圓月中繪有蟾蜍與桂樹,蟾蜍身上有墨色黑斑,四肢舞動,面向女媧。桂樹則以濃重的赭石畫出樹干,樹葉以紫色平涂的方法體現。伏羲位于畫面右側,上身人像,短發,頭戴王冠,長須,五官清晰,衣著男相,側目與金烏相視。下身蛇尾上翹,略低于冠。右側為一圓形的紅色太陽, 四隅用紅、綠兩色各繪出一山字形火焰狀光芒,紫色涂地,紅日中心上部有一黑色金烏面向伏羲,含物疾飛。endprint
西漢晚期的南陽唐河針織廠的墓畫,伏羲位于北側,女媧位于南側,伏羲女媧均人首蛇身,以相對的形象出現,未出現交尾。山東長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與肥城欒鎮村畫像石墓為齊魯地區早期的伏羲女媧圖像,伏羲女媧均為人首蛇身,分別執規矩,相對而立。
2.女媧伏羲相對交尾的圖像形式
1995年文物普查時在河南商丘永城太丘蔡莊一村民院內發現一塊漢代女媧伏羲畫像石,該石高1.46米,寬0.93米,厚0.15米,出土于該村西北100米處一古墓內。畫像石畫面伏羲女媧人首蛇身,伏羲身著長襦,頭戴三尖帽,腰系束帶,龍尾上有兩只爪,雙手托起女媧;女媧頭部向下,頭戴尖帽,下部蛇尾盤繞。該石畫像為浮雕,畫像輪廓線凸出,細部用陰線條勾勒。兩蛇尾相交,動物印跡明顯,反映的是生育圖騰,表現了先民繁衍子孫的信仰。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東室古墓的彩繪衣箱上,繪有人面雙首蛇身的形象,其圖形頭尾倒置,身軀交纏。此墓隨葬的一把五弦琴上也繪有交尾的人首蛇身圖案。
從考古成果來看,至漢代女蝸和伏羲的形象出現的頻率很高,而且造型別具一格,他們或面面相對,或交尾,或聯袂,或接吻,人首蛇身的兩者在整體畫面中的位置以及在形象特征、肢體動作和身體姿態等方面的構圖都是對稱的,除了面部形象和發式能夠分辨出男女性別之外,其他描繪基本一致。這些圖像中女蝸和伏羲手中所持物品也常常相互對應,如伏羲手捧太陽,女媧則手捧月亮,伏羲執規,女蝸則執矩。這里伏羲、女媧以對偶形象分別與日、月形象為鄰組合,是漢代宇宙觀中陰陽對立統一思想的體現,其指向意義象征漢代陰陽二元思想在圖像中的體現。而規矩象征法度,代表禮法,指向“規天矩地”的以法度治天下的文化內涵;也指天園地方的宇宙觀,體現創世始祖的形象。
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墓畫中,伏羲、女媧的形象多為手持華蓋,例如南陽宛城區辛店英莊二號墓、南陽縣辛店鄉熊營石墓。華蓋意為帝王的車蓋,象征著帝王的權勢及威嚴。
東漢早期的墓畫中,伏羲女媧的形象多為手持靈芝,例如,南陽軍帳營營石墓畫像、南陽王寨石墓畫像。
東漢時期,靈芝作為仙草象征著神仙及長壽,女媧圖像中出現靈芝反映出那時人們對求仙的狂熱和延年益壽生命永恒的追求。東漢中晚期,特別在巴蜀文化區,伏羲、女媧的形象多為手執排簫及鼗鼓。例如新津縣的兩幅漢畫石磚、南溪三號石棺的擋頭畫像、合江四號石棺擋頭畫像、江安石棺擋頭畫像、重慶沙坪壩的畫像。
《藝文類聚》卷一引《帝王世紀》:“帝女媧氏,亦風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帝系篇》中有:“女媧氏命娥陵氏制良管,以一天下音;命圣氏為斑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既成,天下無不得理。”樂神女媧創制音樂及樂器的敘事記載,使兩人手持樂器的圖像,符合人文始祖的形象表現。伏羲、女媧與規矩、華蓋、靈芝、簫鼗的組合構圖,指向為世俗文化與皇權思想,女媧由較為單一的創世女神形象,逐漸轉變為圣王形象。
(三)三人的構圖
1958年山東滕縣(今滕州)西戶口出土東漢時期伏羲女媧畫像石。畫像石縱79、橫84、厚15厘米,凸面線刻。畫面共分為三層:
一層:升仙圖。中為西王母,左右有羽人、玉兔、九尾狐等,兩側伏羲女媧蛇尾相交貫穿三層。
二層:起居圖。男女各四人端坐,頭上方有羽人、猿猴等。
三層:狩獵圖。一牛車左向行,車上二人坐,后跟一犬,二人抬一反綁的野獸相隨,后跟一荷弩獵人。
山東省微山縣兩城鎮也出土有類似構圖的畫像石。圖中刻畫的西王母正中端坐,頭上棲息一鳥,身后兩縷云氣,伏羲、女媧分于左右,下身蛇尾絞纏,尾部各連接一朱雀,西王母左肩上榜題顯示“西王母”三字。
河南南陽市區出土的畫像石中,有一幅圖為巨人懷抱伏羲、女媧,構圖為傳說中主司婚姻神靈——赤身的高禖神將伏羲女媧抱在一起。關于高禖神懷抱伏羲女媧的情況,牛天偉先生談及此類圖像是認為:“這種畫像中伏羲、女媧盡管兩蛇尾并未相交,但卻有一位神人作為交合的‘媒介,通過一種外力欲使其交尾,因此也應歸入‘交尾圖像的范疇。”
山東鄒城市高莊鄉金斗山出土的畫像石,構圖為東王公拱手端坐,兩側是伏羲和女媧,他們兩尾相交于東王公身下,尾下有三只正在啄魚的鳥,伏羲和女媧一同舉著位于東王公頭上的日輪。
陜西省藍田縣華胥鎮華胥陵前,漢畫像石描繪的是華胥氏與伏羲、女媧三口之家,圖中:華胥氏雄居于正中,兩側分別是伏羲、女媧,二者蛇尾相交,手中各執規、矩。三人構圖代表著伏羲、女媧神格的下降,在意義的指向上具有多義性。
例如有西王母的三人構圖突出了西王母信仰世界長生的主題,主角是西王母,女媧則降為配角,這與女媧單獨出現的構圖的意義相比較,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伏羲和女媧兩人的共同構圖突出原始先民生殖崇拜亦有所不同。而高禖神懷抱伏羲女媧的構圖,其意義則單純許多,僅僅表現了伏羲女媧人類始祖、生育神的形象。
三、《唐代帛畫——伏羲女媧圖》
從《唐代帛畫——伏羲女媧圖》來看,圖中二者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除服飾唐化痕跡明顯外,其余與以前的伏羲女媧交尾圖大同小異,然而所體現的意義已有所不同。在神話傳說的初始階段,女媧的神性色彩濃厚,祖神形象突出,之后作為“三皇”的圣王受人尊崇。然而在神話流傳延伸的過程中,隨著歷史的發展,遠古神半人半獸的形象已難以保持神所應當具備的莊嚴和神圣。
歲月流逝、社會變遷,人們對于神的敬畏日趨減少,從而使神話人物形象越來越接近普通人。至晉,女媧的傳說已逐漸走出歷史政治的舞臺,步入文學殿堂。進入唐代,女媧的文學敘事更加繁榮。反映在女媧的形象上,以先秦文獻、漢帛畫、漢畫像磚、唐帛畫和明清仕女畫為線索,女媧形象的演變從最初的人首蛇身形象,發展到赤發形象,至明代蕭云從《離騷圖》中窈窕淑女型的仙女形象,清代任伯年《女媧煉石圖》中淡雅清靈的仕女形象,其形像從宗教圖像逐漸轉變為神話傳說中的一位女神。女媧的社會功用亦從原始圖騰的宗教信仰,轉變為文學敘事的對象,這其中的文化元素體現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豐富內涵。
參考文獻:
[1]賴非.中國畫像石:第2卷[ 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
[2]岑小瑩.西王母圖像演變之管見[J].美術教育研究,2014 (05).
[3]程萬里.漢畫伏羲女媧圖像藝術學研究[J].藝術百家,2012(04).
[4]寧稼雨.女媧女皇神話的夭折[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