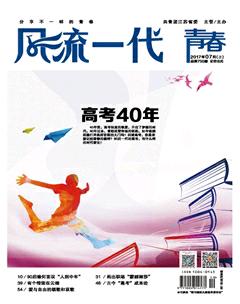古今“高考”成本論
吳聰靈
每年6月,人們的關注焦點都在高考上。這高度緊張的三天終于過去,冷靜思考的時刻到了:倘以投資論,大多數家庭和孩子,在高考上的投資與回報,究竟如何?
當此之際,回看古今諸多實例,或將有利“高考后”諸君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高考成本:從雞蛋到
4萬元,投入無上限
為著特定目標而做事所投入的一切,均可視作投資。當今高考之投資成本,不可謂不大。
以備戰高考的最后一學期來算,一個學生投入在復習資料、補課費、營養費等方面的綜合費用,就十分可觀了,而高考之前的各類小考,更是不計其數。簡單算一下,一個學生從小學到高中12年,要經歷24次期中、期末考試,3次畢業考試,3次入學考,40次季考,120次月考,480次周考……可謂久經“考”場。
以年代變遷來看,從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應考陣容也在擴張——從一個人的高考,到全家人的高考,再到全社會的高考,考前準備越來越豐富,考試配備越來越全面,各種投資也越來越高昂,高考成本一路攀升。
上世紀70年代下放農場的青年們上考場,揣個雞蛋就感覺營養十足了。至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上考場如進課堂;到2000后起,補習課逐漸興起,而今越發重視,補習班、營養餐成為風尚,考前住酒店,爹媽汽車送……陣容日趨龐大。
有人以2011年沈陽某考生為例算了一筆賬,復習資料加補課費、營養食補、沖剌階段就近租房之類,總投入就接近4萬元了。
在高考投入不斷升級的背后,是應考者身心狀態的變化。
40年前的高考生,在生活中吃過很多的苦,知道學習機會來之不易,把學習當作改變命運的機會,為之不懈努力。而今日考生并無生活之憂,易產生“被動式學習”的心理,白天埋在大堆的學習資料里,晚上淹沒在昏暗的燈光里,周末奔波在各類輔導班里。所以對于今天的學生而言,能夠不被學校與家長的壓力打擊信心,可煥發自身動力與學習熱情的,堪稱真正的成功者。
古人趕考:
拼了身家性命上路
與今人高考獲得擇業敲門磚不同的是,古人趕考直接奔的是功名利祿。以其性質論,頗類似于今日之考公務員。所以,古人趕考投入更為高昂。
以曾國藩為例,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他任職禮部右侍郎時曾在北京寓所給四位弟弟寫信:李子山曾希六族伯托我捐功名,其伙計陳體元亦托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垅,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垅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托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為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即發執照與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不可感哉?
大意是,道光十七年(丁酉年),已經兩次會試失敗的曾國藩,準備第三次參加道光十八年的會試。盡管曾家在當地是個家境還算殷實的小地主,但前兩次會試已經幾乎花光了家中的錢,于是只能去族人和親戚朋友家借貸。朱家、王家一分錢都不愿意借,他只好走到栗江找同族的伯叔輩曾希六。曾希六是一個做買賣的人,他和自己的伙計陳體元將錢借給了曾國藩,曾國藩才得以進京趕考,并在第二年的會試中考取進士進了翰林院,從此平步青云。他37歲官至二品,成為大清開國兩百多年來升官最快的湖南人。現在兩位當年有恩于他的生意人讓他幫著在朝廷捐一個官銜,類似于今天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曾國藩墊錢在京中替兩人辦理,辦理完畢后將執照寄回家,并告訴弟弟們,即使曾、陳兩人還給曾家捐官的錢不足額,曾家也應先將官職執照給兩人。
由此信可知曾國藩對人情練達之嫻熟,同時也可見當時舉人進京會試之艱難,與應試成本之高。
所以,古代科舉中江南士子的成績最好,亦不難理解了——不只因為江南文化氛圍好,經濟發達,更因明清時期有江南貢院,大大節約了江南士子的時間與成本。云貴考生跑一次,夠江南考生來回好幾趟了。在自己的地盤上“主場決勝”,發揮優良亦屬正常了。
投資還有應對考試的健康保障上,古往今來也都是一樣高度重視且備受煎熬。
清人龔煒曾作《赴考》一文,描繪自己以孱弱之軀赴考,一路上中暑、暈船,最終無奈半途返回,甚至因此“絕意名場”。《名醫類案》載:“許元公入京師赴省試,過橋墜馬,右臂臼脫。”本已昏迷,幸遇一良醫為之調治,“五日復常,遂得赴試。”雖是意外,可見長途跋涉之風云難測。
為應付惡劣的考場環境,古人會在臨考時服用玉屏風散,以抵御寒邪。古時鄉試多在農歷八月舉行,此時天氣已涼。考生們常服人參、飲棗酒,以求益智強記、養血安神之效。
此外,古人為了防止考場上內急,還在廷試前煮食白果,即銀杏果,取其縮尿之功效。與此相對應,今天一些參加高考的女生通過服藥的方式將經期延遲,亦可算是“人為干預”自然周期,來保障考場上的精力與專注度了。
總而言之,用心良苦。
人生大考場,
持續學習是贏家
大考之后的焦頭爛額,可謂古今一同。然而人生真正的贏家,并不必然是在一張卷子上答出高分的人。
若德行有虧,考上狀元也可能會大難臨頭。比如陳世美,因中狀元而成駙馬,結果呢,因為不認貧賤之妻,竟被送上鍘刀。
戲文故事與史實或有差距,但這故事的傳播卻表達社會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和考取功名比起來,更重要的是做人要講良心,重情義。
現當代的應考者中,亦有因為品德優良而收獲意外驚喜的。有著“萬嬰之母”稱號的林巧稚,于1921年7月前往上海參加北京協和醫院的預科考試。在最后一場考英語時,一位女生突然中暑暈倒,林巧稚趕緊放下試卷,上前急救。結果,她最有把握的英語試卷,竟沒有做完。
原以為這次應試要落榜了,一個月后她卻收到了錄取通知書。原來,監考老師將她樂于助人的事跡寫了一份報告附在試卷后面報了上去。北京協和醫院認為,她的愛心與沉著冷靜,具備了一名醫生的優良品質。
果然,林巧稚所在那一屆的學生中,只有18人順利畢業,而她的成績是第一名。
樂于助人是上德,勤學上進是美德。知名主持人孟非,高中畢業進廠當了工人,也不影響星途坦蕩。
這是表面呈現的順利與幸運。實際上,人家始終如一努力上進,才是成功的根本。而這些,并非考卷所能衡量。
已考上大學的學子中,亦不全是喜劇。因健康出狀況而學業不繼甚至威脅生命的,或進入高校后目標消失、焦慮困頓心理脆弱等釀悲劇的,時有發生。由是可知,高考所能檢測的個人素養,它對于人一生的影響,需要被客觀理性看待。
有時,人們會為著高考而犧牲了親情——或是父母為了子女前程而送其到外地讀書,親情團聚減少,兩頭孤寂;或是家中有親人重病乃至離世時,備戰高考者被隱瞞。筆者曾從事臨終關懷義工服務與培訓工作,見過很多大學生來做義工,都是家中有長輩或父母重病離世時,自己因備戰高考而全不知情。大考后親人不在,滿腹思念與感恩、愧悔之情,只好來向別家老人表達,以解心結。
由是可見,在子女前途與親情維護的沖突之間,還有理性調和的空間。畢竟,人生幸福與否,與太多因素有關。高考固然重要,但也只是人生路上無數考試中的一環。真正具有檢驗能力的試卷,其實是每個人自己出題的——你想在哪個領域有收獲,就可以選擇在哪個領域給自己布置作業。
那些能持續保持學習動力,不斷在身心健康、能力提升、情感滋養等方面提升完善自己,并將其作為日常訓練內容的人,才能擁有更多的自由度與幸福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