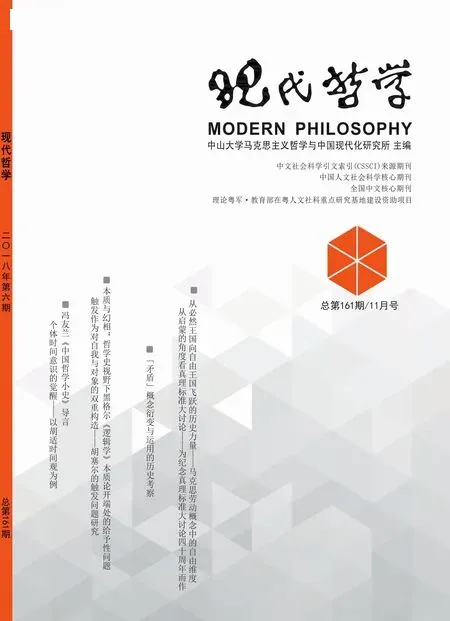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政治-倫理沖突與精神轉向的當代性闡釋
戶曉坤
近年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流變與內部沖突,受到俄羅斯學界的廣泛重視。原因在于俄國被迫通過君主立憲發展有限的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與蘇聯解體后俄羅斯資本主義轉軌具有歷史的相似性,即努力構建符合現代文明樣式的政治-經濟制度與社會秩序。20世紀初俄國政治局勢中各方勢力以及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主張與現實策略錯綜復雜且充滿了矛盾斗爭,這一情勢在21世紀俄羅斯政治生活中依然可見端倪。究其根本,仍然是橫亙百年之久的西方主義和斯拉夫主義、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古老俄羅斯和現代文明之間的分裂與沖突。十月革命似乎在表面上使一切思想沖突走向歷史的終結,然而蘇聯解體后被遮蔽的根源性沖突在今天仍然暴露出來,21世紀俄羅斯學者再次將“二擇其一”的道路探索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將資本邏輯全球化背景下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與俄羅斯現代化的迫切任務內在勾連起來。歷史道路的“抉擇”作為當代性問題被積極地提示出來,向著俄羅斯精神傳統、道德情感與“歷史的真理”回溯,成為理解21世紀俄羅斯社會現實、政治生活及其未來圖景的必要思想進路。
一、1905年:俄國知識分子的分裂與轉向
1905年對于俄國知識分子而言,“相當于歐洲的1848年……是每個人何去何從都必須選擇的年代,是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代”[注]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0頁。,暴力革命還是和平改革、接受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還是維護相對穩定的專制政府?知識分子所面對的恰恰是無法回避或妥協的“二擇其一”。身處歷史岔路口的極端處境鍛造了俄國知識階層作為一個政治范疇的強烈自我意識,用司徒盧威的話來說,他們只是在1905-1907年的革命中才發現了自我。作為區別于從事一般智力活動、掌握著高尚倫理文化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成為俄國歷史傳統與宗教意識形塑下的獨特“道德-倫理現象”,其整體命運深深卷入并嵌于近代以來俄國社會政治變遷與精神文化重塑之中。
俄國知識分子的內在特質“不僅在于其專業品質,而且還在于其對同胞、社會和全人類命運所負有的道德責任。知識,精神性和正直,堅定地遵守道德原則……”。[注]А.А.Галкин, 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ласть,1998,№4.正是基于這一階層自我認同的精神基礎與身份意識,俄國知識分子在復雜的歷史境遇與社會變革中成為審視者和批判者,以先知式的洞見對理性主義、秩序化時代與現代文明保持著精神疏離與道德獨立性,并以某種強烈的價值形式、宗教情感與文化反思捍衛生命個體的內在道德體認、自由、責任與良知。俄國知識分子群體轉型與角色建構中的內在分裂與精神轉向,折射出特定民族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復雜矛盾與內外沖突,而1905之后俄國各方力量的政治博弈、隨之而來的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也迫使這一階層不斷剝離附著于社會表層的激進情緒與立場差異,展開深刻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改造。
1906年俄國在激進的社會動蕩與流血沖突中走上了君主立憲之路。然而依循西方化模式的“維特改革”試圖通過“憲法”與自由派結盟以維持“杜馬君主制”的中間道路左右維艱,并未遏制自由主義反對派徹底革命、瓦解君主制的激進運動,導致改革的支持力量向著杜馬反對派與強硬保守派退卻,在上下、左右無法在體制內妥協的情勢下,斯托雷平作為保守反動右翼使改革轉向了暴力鎮壓的憲政專制:一方面以鐵血手段平復蔓延于城市與農村的混亂和動蕩;另一方面通過土地私有化使農業擺脫傳統村社,加快現代化市場經濟改革。在遭到左翼和自由主義反對派、體制內憲政派與極右翼的反對之下,寡頭專制的改革方向被迫陷入停滯。長久以來俄國特殊社會結構所形成的累積性矛盾、上下階層對立與不公正改革在疾速轉型中促進了社會情緒的“雅各賓化”、“群眾的功利主義”與“革命崇拜”,與當時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政治激進主義迅速融合、嫁接,導致革命情勢不可逆轉。[注]А.С.Ахиезер А.П.Давыдов,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и смысл большевизма,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2,с.175.
按照西方政治文明的邏輯,沙皇俄國具有“父權制政治文化”特征,個人的政治生活在根本上是由倫理責任、對社會秩序以及傳統習俗的忠誠與遵從來規定的,然而在上述情勢下這種服從與隱忍的道德情感轉向了冷漠與殘忍。1905-1907年間,不同陣營的思想立場與政治主張由于當局改革舉措與社會上下層矛盾沖突而發生了深刻轉變。自由主義反對派主導下反對沙皇政府的恐怖攻擊、罷工、農民抗爭、暴動等激進運動釋放出了對社會秩序以及傳統文化、宗教道德的瓦解和破壞力量。暴民政治的毀滅性后果使俄國知識分子開始對“政治的真理”——西方政治制度所依循的自由民主法則——產生了恐懼和質疑,基于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對激進革命及其暴力后果反躬自省、叩問內心,一些俄國知識分子甚至轉向保守主義,正如梅尼日科夫斯基所言:“世界上沒有比俄國知識分子所處的處境更絕望的處境了,——處于兩種憤怒之間:來自上面的、專制體制的憤怒與來自下面的、與其說是仇恨的、不如說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間自發勢力,——但有時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壞”[注][俄]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羅斯》,李莉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知識分子向著自由-保守主義中間道路退卻的深層社會根源與思想根源,成為當今俄羅斯學界反思現代革命不可跨越和回避的思想環節,或言之,必須通過對歷史真理的追溯直面并回應俄國政治激進主義產生的根源性問題。20世紀初自上而下的現代化轉型形成了俄國政治文化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緊張從等級分層社會向現代功能分化社會的過渡,不僅意味著建立新型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與物質生產方式,而且要求重建社會關系的組織原則,并將其鞏固在政治體制中。轉型階段的俄國政治文化內部表現出異質性的沖突結構,即在社會文化實踐、價值取向和道德態度方面是上下割裂的,不斷發展的新興公民社會與統治權力機構、社會的自發活力與保守主義政策之間的沖突增加。
立憲政府因襲歷史傳統的專制統治慣性地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施加控制,對進步的恐懼反而破了統治階層的政治權威與政治認同,“恐懼氣氛在統治階層中占主導地位,于是,由于俄國現實生活的分裂和俄羅斯國家的無組織性,這種氣氛一直在俄國當局那里居主導地位。盡管改革為俄國社會提供了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是在短期內社會生活的許多矛盾不僅無法解決,而且它們還會進一步加深……”。[注][俄]安德蘭尼克·米格拉尼揚:《俄羅斯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29頁。立憲政府因襲歷史傳統的專制統治慣性地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施加控制,對進步的恐懼反而破壞了統治階層的政治權威與政治認同,初期“激進主義政治文化”轉變為與專制主義意識形態相對抗的社會力量和政治運動。“對于以西方輸入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學說雜拌而成的萬靈藥,左翼喪失信心,而以愈加嚴格批判之道看待西方理想,而且如同右派,向國內建制與適合國情的解決法里尋求活法;即令如此,左翼右翼的對立鴻溝仍不斷增闊”[注][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8頁。。針對功利主義、激進主義的政治斗爭與政治行為開展具有深刻精神性的道德反省與自我批判,導致了知識分子群體的內部分裂。
知識分子精神轉向的深層思想基礎在于外來思想資源——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與其自身精神文化根基之間的沖突。20世紀初一部分俄國知識分子從“合法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自由主義者,經濟決定論構成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共識,即將發達資本主義視為構成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在生產力落后的俄國必然經歷較長時期的資本主義階段,司徒盧威、別爾嘉也夫、弗蘭克等路標知識分子基于上述邏輯轉向反對民粹派的社會革命。然而,經濟決定論作為俄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共識基礎,必然與自身的精神文化根基與宗教道德情感形成悖論與沖突,即作為價值準則的個人自由能否通過物質利益或者經濟進步來保障?他們深刻地洞見到:西方資本主義所依循的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內在地消解著個體價值及其社會責任、義務和良心等傳統倫理的實體性內容,導致個體的精神世界陷入空虛與疏離,宗教價值與道德規范被物質利益的無限擴張所排擠驅逐,自由競爭作為人們追求財富的內在動力,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實體倫理關系分崩離析,這種建立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基礎上的消極自由轉變為對于個體生命施加權威的“抽象的權力”。
在陷入內在思想沖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來,建立在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的客觀主義歷史觀成為橫亙在俄羅斯未來的思想障礙,集體的平庸使個體價值與特殊性淹沒于群眾之中。“因此,從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盧威為代表的這些人便出現了從‘唯物主義’轉向‘唯心主義’的趨勢。客觀‘進步’的尺度逐漸讓位于主觀‘道德’的評價……如布爾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視經濟進化的唯物史觀與強調心中良知和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義哲學’必須結合起來,后來就對‘批判唯心主義’的評價越來越高”。[注]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2頁。俄國識分子在經過了1905年革命之后發生了兩個方向的蛻變,一是轉變為支持憲政的保守主義,寄希望于通過與政治精英的聯合實施漸進革命;二是對政治激進行動背后的激進主義文化展開深刻反思,批判拋棄自身精神文化傳統、盲目追隨西方自由主義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摧毀,“抽象的普遍原則”必然戕害生命個體的道德生活實踐,進而訴諸于回歸東正教的精神信仰重建政治生活的倫理根基。
二、在“左”與“右”之間:俄國知識分子政治—倫理沖突的精神根基
對于1905年革命之后知識分子群體面對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政治立場現出的情感困頓、猶疑搖擺、思想沖突與精神轉向而言,當代學者朱可夫認為需要從政治-倫理作為俄國政治制度形成的精神根基這一前提出發方能夠理解。俄羅斯文化傳統的道德形而上學性質決定了其政治實踐的倫理向度,這是現代西方政治文明所依循的抽象法理原則所不能夠解釋的,并構成其“歷史的真理”。[注]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俄羅斯知識分子深刻自省于對民族國家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義務與良心,并試圖給予革命以道德評價,在“俄羅斯是否有未來”的深切憂慮中,努力去理解和澄清“愛國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自由”、“民主”等抽象原則背后的“歷史的真理”——在特定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歷史演進中所形成的、具有內在約束性的法則——而非簡單接受某一終極目標規劃下的制度建構及其抽象的政治原理。對于激進主義的強烈道德批判與向保守主義、甚至專制主義的大踏步倒退,迫使俄國知識分子直面“俄羅斯的命運”以及歷史道路抉擇,迫使其在經歷了思想的出離后重新回到原點,在自身民族的精神文化傳統中為新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行為提供可理解的、具有現實性的道德準則。[注]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
20世紀初俄國的專制反動政策和激進主義革命形成一個悲劇性的悖論關系,一方面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間的互不妥協使追求立憲的中間道路失去了現實的可能性,表現為“維特改革”的不可持續;另一方面,在激進主義土壤中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必然抱有對革命的不切實際的幻想、以及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膚淺理解,他們無法觸及俄羅斯的靈魂,對于西方自由民主之抽象的普遍性毫無批判能力,反而釋放了對社會生活與個體生存的破壞性與反動性,使革命喪失了道德反思和政治-倫理的約束,轉變為騷亂的暴徒。左翼陣營中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出版的《路標文集》正是對激進主義的集體譴責,“在俄國革命的實踐中他們發現,接續了平民知識分子思想傳承的民粹主義運動失敗后轉向恐怖主義的暗殺行為和不擇手段的黑社會組織模式與他們的追求是不同的”[注]金雁:《倒轉“紅輪”:俄國知識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6頁。。
路標知識分子對于革命的后果所產生的強烈內省和懺悔,恰恰產生于俄國貴族和知識階層在古典基督教文化形塑下的傳統道德本能,盡責、無私、正直、誠實,這種個人的道德本能在歷史演進中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倫理,即正義、義務、責任、榮譽、良心、團結以及道德和法律自律原則。路標知識分子深切地洞見到,這種“歷史的真理”正在被“政治的真理”所破壞,前者意味著個體生命實踐的內在質地,它使個體對于自身命運以及共同體承擔起不可推卸的道德責任,而后者作為抽象的普遍原則將社會割裂為孤立的原子個人,并將個體的道德責任轉嫁給國家、階級、歷史的終極目的等無人格的社會整體、未來秩序或烏托邦信仰,從而抽空了個體生命實踐的具體內容。赫爾岑終身所捍衛的自由立場正是對上述差異的具體詮釋,因為“任何遙遠的目的、任何凌掩一切的原則或抽象名詞,都不足以辯解自由之受壓制,或欺騙、暴力以及暴政。人生俯抑動止所寄托的道德原則,須是我們依當下本有處境而實際憑倚的原則,而非我們根據或許有、可能有、應該有的情況而采取的原則”[注][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赫爾岑所謂的“自由”是特定歷史情境中實際個體的自由行動與道德必需,是建立在特殊原則基礎上的絕對價值,無法以應然的方式外在附加于具體內容之上。
在外部局勢的壓力之下,各方社會力量的政治實踐不斷背棄自身的精神根基。當別爾嘉耶夫闡明:“我永遠是極端的敵人,不管這個極端是社會主義還是專制主義”,意味著路標知識分子試圖超出“左”與“右”的政治立場對立,無論是自由主義或是斯拉夫主義都不足以說明或判定其向右轉或向后退卻的性質。俄國的政治-倫理傳統深深扎根于個體的道德本能和具體生命實踐之中,而無西方政治制度得以確立的理性主義原則和知識論傳統,能夠使俄國完成現代化秩序建構的,并非抽象的普遍原則或制度化秩序,而是生命個體的道德責任與內在精神的自覺,如不經歷由此向內而行走的精神性路徑,任何外在的現代化努力(政治的、經濟的或技術的)對于俄國而言都是極其危險的。
這種道德本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倫理不是空洞虛無的主觀主義或個人情感,而是無法剝離、無法舍棄、無法擺脫精神根基或內在靈魂。或者說,俄羅斯民族歷史道路的任何一個發展方向,必定以此為出發點,腳踏根基、由此而發生。與此同時,路標知識分子觸及到了西方自由主義的虛無本質,即將個人自由讓渡于某種形而上學的抽象原則,逃避現實,道德冷漠與敗壞,“這些抽象事物——歷史、進步、人民福利、社會平等——都曾是無辜者被獻祭其上而未引起主事者良心絲毫不安的殘酷祭壇”[注][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06頁。,在路標知識分子宗教哲學外觀下所隱藏的,恰恰是對西方文明最悲觀的直觀,即對于經濟進步、議會改革以及作為算術泛神論的民主政治所許諾之自由的破壞性的深刻直觀。
朱可夫認為,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向著保守主義的退卻,不是政治立場的選擇,而恰恰是超越二元對立政治立場的努力,不是政治行動的權宜之計,而是對政治-倫理之精神根基的捍衛,歸根結蒂是對西方政治文明樣式的審慎與懷疑。正如別爾嘉耶夫所指出的,“俄國歷史造就了具有如此精神結構的知識階層。這種精神結構與客觀主義和普遍主義相悖離,具有這種精神結構則不可能去崇尚客觀的宇宙真理和價值。俄國知識階層不太相信普遍法則,因為他們認為類似的思想和法則將妨礙與專制制度的斗爭和服務于‘民眾’的事業,而民眾的利益則是高于世界的真與善的”[注][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標集》,彭甄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頁。。相隔百年時空跨度與現代化之努力,當代學者依然洞見到兩種政治制度之現實根基的本質性差異,直覺到將西方文明的自由主義原則施加于這個依循宗法倫理傳統歷史建構起來的東方社會的非現實性,并依循自身“歷史的真理”對俄國現代化之路開展出自省式探索。
這一內在精神之路對俄國社會現實與未來圖景的通達,要求對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治行為和政治制度之道德根基或倫理前提進行內在審視。相對于抽象的政治原則與法律制度而言,道德倫理是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精神性實體,它構成“一個民族意識的其他種種形式的基礎和內容”[注][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第48頁。,正如黑格爾所言,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人為主觀制造出來的,“……每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總是取決于該民族的自我意識的性質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識包含著民族的主觀自由,因而也包含著國家制度的現實性”。[注][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91頁。這種現實性對于俄國現代化之路而言是無可棄絕的“活在今天的過去”,對于這一特定民族精神根基的理解和體認,方能使俄國現代化的所有外在努力獲得某種內在的自我約束,并且使之成為能思的和能批判的。
朱可夫由此明確指出,特定社會行動者的政治活動以及社會政治制度中包含明確的(意識形態)或隱藏的(道德直觀)前提,俄羅斯精神文化或宗教認同中的道德理想和價值信念,構成了其尋求政治文明現代化的必要前提。[注]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路標知識分子政治立場的轉向,作為對俄國政治生活之倫理根基的捍衛,迫使之后的改革者們必須直面如下問題:如何對政治現象、政治立場以及政治行為模式的現實性做出判斷?如何為政治生活確立堅實的道德基礎?
三、超越“左”與“右”:自由主義中間道路的政治實踐及當代性理解
俄國知識分子基于對自身歷史傳統與文化根基的深刻洞察與體認,從內在精神向度思慮俄國革命與現代化轉型中政治行為的道德前提以及政治制度建構的現實性問題,“這些制度和價值觀越是具有從外部強加的性質,越是與深入到人民精神深處的東西相脫離,那么精神損失的概率就越大,這一民族對這些制度和價值觀以及它們最初創造者和體現者產生的敵意、自卑或各種畏懼憎惡心理的綜合癥概率也就越高”[注][俄]安德蘭尼克·米格拉尼揚:《俄羅斯現代化之路——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17頁。。十月革命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并未在根本上終結所有的思想爭論與沖突,20世紀20年代被驅逐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流亡歐洲,被稱為“俄羅斯僑民”的別爾嘉耶夫、伊林、米留可夫、司徒盧威等著名流亡者在思想爭論中依然保持清晰度和緊迫感,深懷對祖國的思念承擔起反思俄國革命道德意義與政治責任的使命。具有張力的時空距離使流亡知識分子立足于對現代文明的總體性關懷,開展出對20世紀初俄國兩次革命與自身精神轉向的深層反思,與歐洲知識分子的跨文明對話使其更加理解世界歷史展開進程中俄羅斯民族的獨特命運。
米留可夫與司徒盧威作為行動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保守主義中間路線的思想困頓與斗爭中,試圖通過現實策略或理論建構的政治實踐超越“左”與“右”探索第三條道路。然而較長時間以來,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作為政治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雙重擠壓下的附屬品,其現實性的政治主張往往被忽略與否定。在朱可夫看來,對俄國轉變時期表層社會文化心理的分析,構成了理解俄羅斯當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思想資源,并通過對民族情感與現代國家的關系、政治策略與政治-倫理的區分等問題的當代性理解與闡釋,為特定民族國家的現代化主張積極提示出不可回避的思想環節。[注]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
在1905年革命中米留科夫在主張立憲君主制,爭取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聯合以防止激進革命與保守政府的第三條道路,列寧認為立憲民主黨標志著俄國資產階級“第一次開始形成為一個階級,形成為一支統一的和自覺的政治力量”。[注]《列寧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頁。立憲民主黨的激進策略宣告失敗后,米留科夫調整為妥協策略,“中心思想是‘保全杜馬’、由‘強攻’專制制度轉為‘正確圍攻’,并成為立憲民主黨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的政治策略”[注]張建華:《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35—236頁。。然而斯托雷平在解散第二屆杜馬后開始實行恐怖統治,幻想破滅后米留科夫被迫流亡并刻地意識到,革命已經開始便不可能采取中間立場。在國家對于經濟和社會的調節方式上,他所捍衛的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在俄羅土壤上似乎轉化為某種另類的自由主義。
作為“俄羅僑民”的米留可夫在流亡期間試圖再次尋求中間道路,要求以民主俄國取代舊的統治階級習慣與方法;嘗試通過與社會民主黨聯合加劇俄國內部斗爭的心理基礎,進而從內部反對布爾什維克,“新策略”的其思想基礎包含著與布爾什維克政權走向和解的內在邏輯。其政治立場的轉變遭遇到左翼和右翼學者的嘲諷,然而“事情遠非如此簡單,新策略實質上是米留科夫面對頑固堅持暴力的右翼和趨向與布爾什維克和解的少數思想轉變者之間尋找的一種中間策略……單純的思想轉變者容易屈服于蘇維埃政權,而單方面的革命會脫離俄國,在屈服與脫離之間,應該尋找一種明智的對人們斗爭的成績有益的‘結合體’”[注]張建華:《蘇聯知識分子群體轉型研究(1917—1936)》,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80頁。。米留可夫意識到,政治斗爭現象背后更為深刻的基礎在于俄羅斯的民族情感與國家認同,因此有必要建立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內在統一的國族意識,民族感情不僅不違背國家生活,反而本身就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內在要素。與此同時,米留可夫要求區分國家和民族、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邊界,避免情緒性的愛國主義以及沙文主義。
司徒盧威從俄羅斯文化傳統與“個人生活”理念的結合闡述自由思想,尋求自由文化與俄羅斯宗教傳統價值觀的融合。司徒盧威在1906年便已經完全意識到,“右翼”和“左翼”已成為國家和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大危險,中間道路的信念源于其將自由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整合在自己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經驗之中,并將政治實踐建立在國家與民族統一原則的基礎上,即“民族統一給予任何國家堅實性和穩定性。對自身任務的民族理解、自覺感是公民社會政治、社會統一力量的前提”[注]張建華:《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導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242頁。。司徒盧威放棄歐洲基督教文化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古典自由主義所形成的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對立,而認為民族傳統與國家穩定以及個人的權力、自由之間可以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實現統一。
對于“何為真正的愛國者?”這一問題具有兩個標準: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和政治生活的道德準則。前者的核心要義在于:什么樣的內外政策與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說,“個別與特殊問題沒有全盤解決法,只能通之以一時的權宜處理,而且這些一時權宜之計在根本上必須敏感于各個歷史情境的獨特性,并且善能回應紛雜個體與民族的特殊需求”[注][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ix頁。,后者則回答另一個問題,即政治與精神文化領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具體行動所應遵循的內在真理是什么?司徒盧威認為,俄羅斯文明的內在氣質構成了民族國家結構和社會參與者選擇政治行為與政權類型的思想基礎,任何一種選擇都背負著歷史、俄羅斯、社會、人與神的道德責任,俄羅斯的社會政治經驗、哲學世界觀和價值觀塑造了政治行為的道德責任和倫理內容。在上述前提下,司徒盧威反對簡單地革除一切傳統,而倡導依賴國家歷史文化傳統,通過君主立憲制來實現政治自由,而斯托雷平改革只是在特殊政治時刻的道德技巧上與司徒盧威的政治自由在某種意義重合,向統治階層在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做出適度的讓步與妥協。朱可夫認為,試圖理解自近代以來俄羅斯現代化轉型在精神和政治層面的內在對立必然追溯到20世紀初的思想沖突,這一主題的當代性在于,其積極提示出俄羅斯作為特定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努力需要依循的“歷史的真理”,而非抽象的政治真理,這種基于道德體認的政治選擇,一旦觸犯,所有革命的根基都是極其不穩固和危險的。[注]О.А. Жукова,Проясняя по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ораль и борьба дискурсов в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начала ХХ век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2016,№1.俄羅斯需要用更長的時間實現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重建以及社會關系的協調與和解,即將現代公民國家融入自身的民族文化(以國家主義為核心)、精神思想與政治傳統中。澄清20世紀早期俄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倫理沖突與精神轉向,通過對政治運動背后的道德動機與價值觀念的話語分析,才有可能克服“歷史的真理”與“政治的真理”之間的沖突。
俄國知識分子階層在政治實踐與斗爭策略上表現出“左”與“右”之間的猶疑搖擺與精神轉向,恰恰源于對俄羅斯民族精神根基的深刻洞見以及對西方自由主義原則的審慎懷疑。“所有歷史、心理的文獻證明,俄國知識階層只有在知識與信仰綜合的層面上才能轉向一種新的意識。在將理論與實踐、‘現實-真理’和‘現實-公正’進行有機結合中,這一綜合將真正符合知識階層價值需求”,[注][俄]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標集》,彭甄等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頁。別爾嘉耶夫為俄羅斯文明復興所提示出的這一可能方向,只有在現代西方文明之歷史限度的不斷迫近中方能夠被真正開啟,這種拒絕為實現空泛真理而摒棄一切的道德動機,為文化創造帶來了新的生機活力,并形成人與人之間新的社會結合方式。或言之,只有當人們的精神活動扎根于生生不息的、具體的生命實踐并歷史地開展出來,才能使政治的真理獲得現實性。
對于21世紀思慮特定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而言,俄國知識分子精神轉向的思想性與當代性,遠遠超出了政治立場的表面對立以及政治行為中的權宜之計。這一階層在政治生活領域中以自省式的知覺熱切地關注于道德與社會、信仰與責任的內在質地,以及個體的特殊性與絕對價值的實質性內容、民族情感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現實關系等,上述努力同樣超出了他們所處時代能夠理解的范圍,作為“活在今天的過去”直接回應了現代文明的重大基本問題,其自身所遭遇的困境與沖突、所表現出極端與懷疑,恰恰是現代性自我展開的困境與沖突,“俄國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種特殊的極端方式,表達人類處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許多人也認為,俄國知識階層的歷史意義,在其以病態夸張的形式體現人類對絕對價值的渴求”。[注][英]以賽亞·柏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xiii頁。如果未能將知識階層的政治-倫理沖突與精神轉向上升到對整個現代文明的精神關懷與內在反省高度,那么這一民族獨特的精神結構與道德信仰也將在現代性同質化與客體化的趨勢中湮沒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