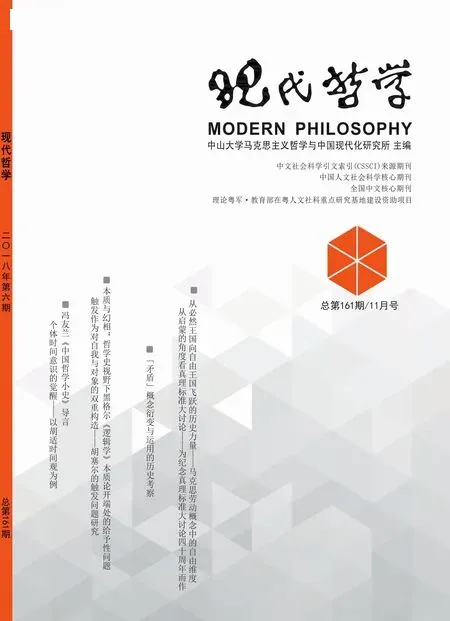東洋哲學的先驅
——井上圓了
[日]三浦節夫/著 [日]深川真樹/譯
一、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的創立
1868(明治元)年,奪取政權的新政府接收江戶幕府的“學校”,即昌平坂學問所、開成所、醫學所,各改稱為昌平學校、開成學校、醫學校后并使其復興。1869(明治2)年6月,決定合并昌平學校、開成學校、醫學校而建立大學校,但“從一開始,因國學家和漢學家抗爭對立而發生糾紛。結果,同年十二月進行若干的制度修正(作者注:大學校改稱為大學本校,開成學校改稱為大學南校,醫學校則改稱為大學東校,而整合為一種綜合大學再開始運營),但混亂并無結束,至翌年二月大學規則被制定,對洋學派的攻擊亦便開始。其間教官與學生互相反目,該當局者彼此分裂,教官與學生均反抗大學當局,大學陷入如此四分五裂的狀態,而且并無收拾的方法,因而明治三年七月,大學本校終于停止了運營”[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通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第112頁。。
1870(明治3)年制定的大學規則,為日本首個整套的近代教育法規,并以教科、法科、理科、醫科、文科為大學五大學科,但由于上述國學家和漢學家之間的對立抗爭,該規則最后沒有得到實施。1871(明治4)年,政府代替大學本校設立文部省,改仍存在的大學東校與大學南校的校名,只稱為東校、南校。11月,為了學制改革,暫停東校與南校的運營,修正學則后再開始運營,重新招生。1872(明治5)年,頒布制定大學、中學、小學的“學制”,東校改稱為第1大學區醫學校,南校改稱為第1大學區第1番中學。然而,第1番中學于1873(明治6)年成為專門學校,改稱為開成學校。1874(明治7)年5月,將第1大學區開成學校與醫學校從大學區獨立出來,各改稱為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1877(明治10)年4月,東京開成學校與東京醫學校兩校合并,誕生了日本首間綜合大學的東京大學。創立之時,東京大學由文學、法學、醫學、理學的四學部,以及由東京英語學校改稱的預備門構成。其中,文學部的學科有二,即第1科“史學、哲學及政治學”、第2科“和漢文學科”。
關于文學部的創設,《東京大學百年史》的作者說:“《東京帝國大學五十年史》將文學部的開設評為:‘不同于法學部及理學部均繼承舊開成學校法學科及理學科的事業,文學部完全重新設置’(上冊,頁六八五)……此觀察不能不說是片面的。也就是說文學部不僅對吸取西洋式的新的學問,亦對保存日本古來的傳統予以關注。”[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413頁。還說從上述第1科與第2科的內容看,“以今日的一般觀念而言,政治學似非歸屬于文學部,而更適合歸屬于法學部,但應是仿效西洋諸大學將政治學置于哲學部中”[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413頁。。但2年后的1879(明治12)年,第1科的史學被取消,代替設置理財學(經濟學),變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 1881(明治14)年9月15日,“文學部的學科組織再度改編,其中將向來與政治學及理財學一同構成第一科的哲學獨立出來,以此作為第一科。政治學及理(財)學科改為第二科,和漢文學科則改為第三科。然而,與從前相同,第一年的課程幾乎是三科共通的”[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415頁。。當進行此改正時,“關于文學部新設哲學與政治學及理財學科一事,大學與文部省之間花了將近三個月的期間,反覆進行函詢-回答-再函詢-再回答的程序”[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通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第455頁。。相較之下,同時進行的理學部的改正申請一次便完成,對比甚為鮮明。另外,1885(明治18)年12月進行的學科改正,將政治學及理財學納入法政治學部,亦將和漢文學科分離出來,故文學部變為哲學科、和文學科、漢文學科的3科。
二、東洋哲學的先導——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是建立近代日本學術、思想的領袖之一。他出生于1836(天保7)年、但馬國出石藩(今日的兵庫縣)甲州流兵學師范的家庭。1843(天保14)年,8歲便開始修習文武。1845(弘化2)年,10歲時進入藩校弘道館。1852(嘉永5)年,17歲隨父到江戶,學習甲州流兵學,并進入佐久間象山的蘭學塾,這是一間研究西洋學術、講授西洋知識的學塾。返鄉一趟之后,1854(安政元)年,19歲時再到江戶,跟坪井為春學習蘭學。后因父親過世而歸鄉,但1856(安政3)年,21歲時三訪江戶,繼續于坪井的學塾學習。1860(萬延元)年,25歲時充當蕃書調所手傳一職,在此首次學德語。
根據加藤回想,他必須研究世代傳承的祖業即兵學,但“世上喜好西洋兵學的人增多了,并且比起兵學我更喜歡研究哲學、倫理學、法學等學科了……認為對社會也有些益處,故遂改志,決定要從事自己喜歡的研究”[注]加藤弘之:《加藤弘之自敘傳》,收入《傳記叢書》88,東京:大空社,1991年,第26—27頁。此書復刻加藤弘之先生八十歲祝賀會編:《加藤弘之自敘傳:附-金婚式記事該略·追遠碑建設始末》,東京:編者,1915年。。1864(元治元)年,29歲時由幕府拔擢為直屬家臣,就任開成所教授職并一職。
時值明治維新(1868年),33歲的加藤由新政府重新任命為開成所教授職并。1869(明治2)年,34歲時就任大學大丞一職。1871(明治4)年成為文部大丞。其后數年間,數次被明治政府任官授職,但皆辭職。至1877(明治10)年,42歲時由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麻呂被任為東京大學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的3學部綜理(起初,醫學部綜理是池田謙齋)。1881(明治14)年有所改正,加藤成為4學部的初代總理(從此年設置學部長一職,外山正一就任文學部長)。
東京大學文學部創立之初,其第1科(史學、哲學及政治學,從第三年為哲學、政治學及理財學科)的全部課程如下:
第1年 英語(論文)、論理學、心理學(大意)、和文學、漢文學、法語或德語
第2年 和文學、漢文學、英文學、哲學(哲學史、心理學)、歐美史學、法語或德語
第3年 和文學、漢文學、英文學、哲學(道義學)、歐美史學、政治學、經濟學
第4年 英文學、歐美史學、哲學、政學及列國交際法[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414頁。
根據以上課程,哲學要講授心理學、道義學(倫理學)、論理學、純正哲學,不包含“印度及中國哲學”(東洋哲學)。由后續情況看,哲學科因1881(明治14)年的改正而獨立后,開始講授新設科目“印度及中國哲學”(東洋哲學)。
總之,將東洋哲學導入東京大學哲學科,使其與西洋哲學并列的,就是加藤弘之。根據井上哲次郎回想,以德語為專業又學哲學的加藤說:“佛教中似乎也有哲學,何不妨在大學也開設佛教課程?”[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東京:冨山房,1973年,第7頁。1885(明治18)年2月12日,加藤在日記中寫道:“自上午十一點半在學校上班,自三點于法文學部召集文學部教員,以就學問述卑見以質諸先生為題演說,是為誡和漢教員不知學問也。”[注]中野實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二月》,《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0號,1992年3月,第77頁。換言之,東京大學哲學科開設后8年,加藤仍感到自己的學問觀與大學教員的落差甚巨。那么,持此學問觀的加藤,如何得到“佛教中有哲學”的想法?在上述略歷中,也沒出現加藤特別修習佛教的事實。根據翻刻《加藤弘之日記》的中野實的解說,加藤日記中頻出的是與家人、家計相關的事,關于與大學相關的事多記述“去學校”“去學校上班”等,并無詳述內容。例如,1880(明治13)年1月7日,他寫給女兒文子之事:
七日 晴
文子自兩三日前罹患感冒,今朝狀況急起直下,故邀請竹內氏診察,同氏立即來臨,是大約九點之事。守候至二點二十分,雖試各種治療,但最后無其效果,后來文子陷昏迷,下午二點二十分左右死去。不過此前,由竹內氏指示派人邀請池田治療,但在外出中,因而邀請東京府病院所雇彪杰瑪(譯者注:Tjaico Wiebenga Beukema)氏,雖同氏立刻來到,但其時死時已到,故不能救命,可悲。齡四年十個月也。即明治八年三月十八日誕生。病名急性腦水腫也。
八日 晴
今日下午二點出殯,葬送至小石川念速寺。但同寺在朱引內(譯者注:日語,讀音:しゅびきうち,即政府規定的東京市區),埋葬被禁,故埋葬于近地同宗新福寺。與前年死去的花子和去年死去的岳母同處。法名命為文操。[注]中野實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一年一月-明治十三年》,《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1號,1993年3月,第141頁。
加藤對家人的情思甚篤。他委托小石川念速寺舉行葬儀,該寺常在日記中出現。根據井上圓了的記錄,“加藤老博士的小孩逝去時,使念速寺舉行葬儀,故同寺平素幸好與加藤老教授親密往來”[注]井上圓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22編第8號,1915年8月,第1頁。。當時念速寺的住持為近藤秀嶺,擔任加藤家的佛教法事。近藤住持是教理學者,“是在東京真宗大谷派(作者注:東本愿寺派)寺院中的佛教學者,大致把握俱舍、唯識、華嚴、天臺等教理”[注]井上圓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22編第8號,1915年8月,第2頁。,與一般住持不同。
似乎為了理解佛教的本質,加藤與近藤住持商量。例如,據《加藤弘之日記》1881(明治14)年2月19日記載:“去學校。拜訪增上寺住持福田行誡,請教佛道問題。先前托念蓮(作者注:速)寺介紹也。”[注]中野實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四年-十五年》,《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2號,1994年3月,第41頁。福田是凈土宗的僧侶、學者,后來成為凈土宗管長,是超越宗派、頗受仰慕為名僧的人物。
根據圓了的記錄,希望增設佛教課程的加藤,與西本愿寺(凈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島地默雷商量,后者是留學過歐美、批判政府“三條教則”、建議信教自由的僧侶。圓了說,大學“決定要聘講師,老博士(作者注:加藤)與島地默雷師商量,同氏介紹了原坦山翁。聽說,由此老博士親自訪問寓居淺草公園的坦山翁,而看到翁租雜耍戲棚的空房并住于此,老博士便一驚了”[注]井上圓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22編第8號,1915年8月,第2頁。。總之,加藤招聘原坦山為佛教的講師。根據《東京大學百年史》的記載,“明治十二(1879)年九月十八日的學科課程改正”,規定“另置佛書講義此一科目,以使文學部各級學生自由選課”[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524頁。,由原坦山擔任。
井上哲次郎說當時他以學生的身份立即申請上課聽講,又說“其課程起初使用《大乘起信論》為課本。上課方式并不能說上乘,但因選擇的課本好,故學生喜歡聽,亦不僅學生,而且各種各樣的人來上課聽講,譬如,當時的綜理加藤博士也起初旁聽,從校外西村茂樹博士等人也來旁聽,此外,外山正一博士等教授也列席,坦山氏的佛典課程如此惹起了當時學界的注目。無論如何,于廢佛毀釋后佛教形勢振的時代在大學講授佛典,以歷史的角度而言,是一件應當注目的事”[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東京:冨山房,1973年,第7頁。。
《加藤弘之日記》1881(明治14)年4月16日記載:“今日為了植物園之事去文部省御用掛伊地知正治那里,但因他身體不適而無以得見。接著去增上寺與行誡見面后回家。六點多去學校聽演說,是原坦山佛教大意的演說,九點左右回家。”[注]中野實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四年-十五年》,《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2號,1994年3月,第45頁。原坦山如此被介紹給大學相關人員。然而,“坦山翁為禪門的悟道之人,并非教相學者,尤其天臺學,完全無所涉獵”,因此,念速寺的近藤聽到加藤決定請坦山作佛教講師,便向加藤“建議招聘另一位以教相為專業的學者,結果吉谷覺壽師,由老僧介紹被任命為大學的講師”[注]井上圓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22編第8號,1915年8月,第2頁;中野實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五年-十六年》,《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3號,1995年3月,第82頁。據1882(明治15)年7月27日記載:“在家○吉谷覺壽真宗僧來。”。吉谷是東本愿寺的代表性佛教學者。
因1881(明治14)年的改正,文學部哲學科獨立了,當時的情形是:
并且哲學科在其科目中新加世態學(社會學)及審美學(美學)的同時,采取了包含“印度及中國哲學”的形態。至此,“哲學”此一概念被擴大,明治十五年增設“東洋哲學”為科目。與此相關聯,在此時期開始使用“西洋哲學”的名稱。
依當時的公文與私文來看,針對新時代的學術偏向于西洋一事,出現要求反省與修正的意見,另一方面存在著擔心其復歸于固陋的見解,也有人提及統合雙方的理念,由此可窺見學問論或文明論與制度上的問題參雜,議論紛紛的樣子。[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6年,第489—490頁。
因中國哲學是儒教、漢學,可以想象其所受到的重視而被設立為科目,實際上已有漢文學的科目,佛教則被稱為“印度哲學”[注]為何不用“佛教哲學”一詞,而稱“印度哲學”?宇井伯壽說明其理由:“當時認為,若用‘佛教哲學’,則在與基督教的關系上有困難,于是,由于佛教為起源于印度的哲學,而最后‘印度哲學’一詞被發明。因此在當時,‘印度哲學’一詞實即指佛教哲學,而后來其成為講座的名稱。”(宇井伯壽:《インド哲學から佛教へ》,東京:巖波書店,1976年,第500頁。),這至今并無在大學教育的相關爭議中成為議題。由此而言,加藤扮演了關鍵角色。
三、井上哲次郎“東洋哲學史”講義
1883(明治16)年9月,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在日本首次使用“東洋哲學”作為課程名稱。擔任講課老師的是東京大學第一屆畢業生井上哲次郎,但規劃開此東洋哲學課的是綜理加藤弘之。
1855(安政2)年,井上哲次郎出生于筑前國大宰府(今日的福岡縣)的醫師家庭,是第三個兒子。1862(文久2)年,8歲開始跟中山德山學習漢學。1868(明治元)年,去博多跟村上研次郎學習英文。1871(明治4)年,17歲時下定決心進入長崎的廣運館。于此受到賞識。1875(明治8)年,21歲時去東京,進入東京開成學校。1877(明治10)年,東京大學創立后,在文學部學習“哲學及政治學”。1878(明治11)年,哈佛大學畢業的費諾羅薩(Ea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赴東京大學就任,擔任哲學及政治學的教師。“于大學,使我對哲學更感興趣,且對我的思想傾向有極大影響者,即是費諾羅薩氏……氏才二十六歲,還可說是青年人,精神煥發地講授笛卡爾(譯者注:René Descartes)至黑格爾(譯者注: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哲學史,其印象至今仍不能忘掉。”[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東京:冨山房,1973年,第6頁。
1880(明治13)年,井上哲次郎26歲時東京大學畢業,取得文學士學位,但并未實現當初的海外留學志愿。此時,“加藤綜理建議我編纂‘東洋哲學史’。因自己原來也對東洋哲學史有興趣,故動心,而進入文部省編輯局而從事之……大約一年左右在此上班,但文部省官僚主義有點強烈,感到不甚適合自己,故某一日訪問加藤綜理訴說這點,綜理便說,我愿不愿意在大學編纂‘東洋哲學史’。其為我所最希望的事,因此立即向文部省辭職而進入大學的編輯所,充當大學的助教授一職,并從事‘東洋哲學史’的編纂……雖我是助教授,但起初并無上課,專門從事編輯,開始講課的是,在上述‘東洋哲學史’的原稿很多部分完成之后”[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東京:冨山房,1973年,第9頁;中野實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記——明治十五年-十六年》,《東京大學史紀要》第13號,1995年3月,第82頁。據1882(明治15)年12月9日記載:“○井上哲二(作者注:次)郎來談。”。1883(明治16)年9月,井上哲次郎“首次開東洋哲學史的課。聽講者為井上圓了、三宅雄二郎、日高真實、棚橋一郎、松本源太郎等十數名也。”[注]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東京:冨山房,1973年,第74頁。根據《巽軒年譜》記載,“東洋哲學史”一課自1883(明治16)年開始。但佐藤將之在《井上圓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國哲學の位置》說:“根據圓了上同科目時的筆記本記錄,第5講即在1月11日,此后一周一次上課。因此,毋庸置疑的,哲次郎自前一年12月便開始上‘東洋哲學史’一課。”可見,哲次郎記錯開始上課的日期。(《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21號,2012年9月,第53—54頁。)1884(明治17)年2月,他被命令修習哲學三年,前往德國。
哲次郎的東洋哲學史一課為人所知,但從沒有研究者論及過其內容。不過,在東洋大學井上圓了研究中心有一本用“和紙”(譯者注:日本傳統的紙)做的筆記本,其封面上有井上圓了所記錄“東洋哲學史卷一”的文字(共96頁),在此將寫出其概略。筆記本的第1頁中有如下記載:
東洋哲學史 井上圓了
井上哲次郎氏口述
儒學起源
義解○儒有二義:一云學孔孟之道者;一以總通諸學者為義。然而爰云儒學者指孔孟之學。
此外,第2頁寫道:
教體○孔子之道決不可云純粹之哲學。全以修身一學為本也。另僅評政治、說宗教,其政治及宗教亦皆本修身一學而立者也。
這個筆記本的前20頁內容為儒學史,但沒有上課日期等。其后記錄日期和第幾講,當初的內容以孔子為中心,其后對象改變。
自明治十六年一月 第五講 一月十一日
第六講 一月十八日
第七講 一月二十五日
第八講 二月一日
第九講 二月十五日
第十講 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一講 三月八日 孔子爰終
第十二講 四月十二日 孟子
第十三講 四月二十六日 孟子
第十四講 五月十 孟子
第十五講 五月十 荀子
第十六講 五月二十四日 荀子
第十七講 六月一日 楊子
由此可知,哲次郎東洋哲學史的課只以中國哲學為對象,并不包含印度哲學即佛教哲學。
四、井上圓了“發現”東洋哲學
1881(明治14)年,東京大學文學部哲學科獨立,井上圓了是此時唯一的入學生,而且是首個兼修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的學生。
1858(安政5)年,井上圓了出身于越后國長岡組浦村(今日的新潟縣)的慈光寺(東本愿寺末),圓了為長子。慈光寺當時已有200年的歷史,是一座在教團中平均規模(門徒數)的佛寺。因有長子要任下一代住持的規定,圓了從住持父親那里受到僧侶教育。10歲時,圓了遇到明治維新(1868年),從此開始在石黑忠悳的學塾學習。石黑為23歲的蘭方醫即西醫,曾于江戶的醫學所擔任助教,由于預測發生戰火,回了家鄉。圓了在此學習初步的漢學和算術,就連下大雪,石黑估計無學生來時都堅持到學塾。9月,長岡藩與新政府軍之間發生北越戊辰戰爭。12月,于佐渡島發生廢佛毀釋。石黑教圓了時代變化、西洋世界等教科書以外之事,使圓了覺醒。江戶的戰火熄滅后,石黑關閉學塾而回江戶。自1869(明治2)年起,以慈光寺為學校,圓了在此師從長岡藩的儒者木村春叟,受到4年的藩校程度的正式漢學教育,并從此時期開始學英文。1871(明治4)年,圓了13歲時得度,即披剃出家。圓了受完漢學教育后,轉向洋學。1874(明治7)年,進入新潟學校第1分校,即祝愿變成廢墟的長岡復興而建立的長岡洋學校后身,以英文學洋學及數學。圓了成為意識到日本文明開化的青年,2年畢業后,被同校后身的長岡學校雇傭為教師助手。
針對在長岡的圓了,京都的東本愿寺命令“立刻上洛”。為了于教團內建構新的教育體制,首先制定對年輕的優秀僧侶施行精英教育而培訓為教員的方針,因此會英文的圓了,在1877(明治10)年進入教師教校英學科。半年后,被選拔為東京留學生,1878(明治11)年4月8日到東京。已20歲的圓了,翌日在小石川的念速寺住1日。在此與住持近藤秀嶺一同“決定訪問加藤老博士(作者注:弘之),數日后近藤老僧帶我至番町上二番町四十四番地,得以初次面謁老博士。是后偶爾拜訪而幸蒙知遇”[注]井上圓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東洋哲學》第22編第8號,1915年8月,第1—2頁。。9月,圓了參加加藤推薦的東京大學預備門的入學考試。幸無落榜,以第2年級(第1屆學生)的身份開始學習[注]關于圓了的考績、生平與思想的詳節,參照拙著:《井上圓了——日本近代の先驅者の生涯と思想》,東京:教育評論社,2016年,第92頁。。制度上,若無預備門畢業則不能進入大學,而且實行極其嚴格的學力考試,甚至每年60至100名以上不得晉級[注]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通史1,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第592頁。。圓了的成績在班上爭取第一,因而順利畢業,1881(明治14)年9月進入文學部哲學科。圓了在念哲學科的4年期間,上過與哲學相關的如下課程:
第一學年(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漢文學-講師為信夫粲。《史記》與一個月二次的作詩。
論理學-講師為費諾羅薩。艾佛雷特(譯者注:Charles Carroll Everett)《論理學》。
論理學-講師為千頭清臣。杰文斯(譯者注:William Stanley Jevons)《論理學》等。
第二學年(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東洋哲學-講師為井上哲次郎。東洋哲學史。
西洋哲學-講師為費諾羅薩。參考斯賓塞(譯者注:Herbert Spencer)《世態學》和摩爾根(譯者注:Lewis Henry Morgan)《古代社會》,講授社會學,并以施瓦格勒(譯者注: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哲學史》(英語抄本)為教科書,講授近世哲學史與康德(譯者注:Immanuel Kant)哲學等。
西洋哲學-講師為外山正一。使用貝恩(譯者注:Alexander Bain)《心理學》、卡彭特(譯者注: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精神生理學》、斯賓塞《哲學原理總論》等講授心理學。
漢文學-講師為信夫粲。唐宋八家文。
第三學年(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哲學-講師為島田重禮。中國哲學。
印度哲學-講師為原坦山。《輔教論》、《大乘起信論》。
印度哲學-講師為吉谷覺壽。《八宗綱要》。
西洋哲學-講師為肥羅諾薩。使用華萊士(譯者注:William Wallace)的英譯本,講授自康德哲學至黑格爾哲學的展開,以及黑格爾的論理學。
漢文學-講師為三島毅。輪流閱讀《左傳》、《荀子》、《揚子》、《法言》(譯者按:《東洋大學百年史》所作“《揚子》、《法言》”應作“《揚子法言》”)等。
第四學年(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因此年度無試業證書而以下為推測)
東洋哲學-印度哲學。講師為原坦山。《大乘起信論》、《唯摩經》。
講師為吉谷覺壽。《天臺四教儀》。
東洋哲學-講師為島田重禮。《莊子》。
西洋哲學-心理學。講師為外山正一。以達爾文(譯者注:Charles Robert Darwin)、斯賓塞、彌爾(譯者注:John Stuart Mill)等著作為教科書。
西洋哲學-道義學、審美學。講師為費諾羅薩。以西季威克(譯者注:Henry Sidgwick)《道義學》和康德的著作等為教科書,在純正哲學的基礎上,以自黑格爾哲學至斯賓塞哲學為據,講授道義哲學、政治哲學、審美哲學、宗教哲學。
漢文學-講師為中村正直。易論。[注]東洋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委員會編:《東洋大學百年史》通史編Ⅰ,東京:東洋大學,1993年,第43—45頁。
圓了如此學習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其間,1884(明治17)年1月,得到西周、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三宅雪嶺等的贊同,作為中心人物創立“哲學會”。1885(明治18)年7月畢業,圓了是預備門及大學部第一屆學生的榜首。此后,被選為國家公費生,成為研究生、帝國大學大學院生。圓了于此兩年間撰寫初期的代表作,中間因患肺出血而不能不療養,但繼續著述出版。1887(明治20)年9月,創立“私立哲學館”。
自預備門至大學部的7年期間,圓了于東京大學以哲學為中心修習西洋諸學。教西洋哲學的是費諾羅薩,外山正一輔助他。圓了沒寫自傳,但在1887(明治20)年出版的《佛教活論序論》中,寫了被一般認為是圓了的“思想遍歷”的文章,引用如下:
雖我最近才發現完美的真理存在于佛教中,但注意發現這點并非最近才開始。明治初年早已有此意愿,爾來刻苦努力十余年,其間一心專注于這點,未嘗一日忘之。然而,我并非自一開始便相信佛教為完美的真理。尚未發現其為完美的真理時,卻相信其非真理,誹謗排斥,并無相異于常人所見。
我本出身于佛寺家庭,在佛門中長大,故維新以前完全受到佛教教育,雖然如此,我心中隱隱知道佛教并非真理,認為剃頭發、拿念珠而面對世人是一身的恥辱,并日夜渴望離其門而進世間,此時碰巧正值大政維新,其在宗教上帶來大變動,至我看到廢佛毀釋之論逐漸實際被實行,立即脫僧衣而求學于世間。
起初修儒學究其真理五年,乃知儒學未足為完美的真理。當時洋學通行于近鄰鄉村,有友人已修之,對我推薦其學。我以為,洋學為以有形事物為對象的實驗學,并不足以究無形的真理。故此一時無答應其推薦,但退一步想,佛教既非真理,儒教亦非真理,何知真理卻存在于耶穌教中?然而要知耶穌教,不可不依據洋學。于是棄儒歸洋,是在明治六年。
其后專學英文,同時欲窺究《圣經》,但僻地的書肆未有其書。即便偶有其書,因家貧而無余財可購讀。有友人已有一本中譯本。接著得到其原書,我對照原譯文日夜熟讀,稍微得以了解其意了。讀完便擲書,嘆曰:耶穌教亦不足為真理!
至此我愈加迷惑。且抱持懷疑:儒佛非真理既是如此,耶穌教非真理又是如此;但世人或信儒佛,或信耶穌教,何也?蓋因世人的智力不能發現其非真理,或因知其非真理且信之?我決不能相信非真理為真理。于是我斷然公開明言:舊有的諸教諸說中無一可信之真理。如欲追求可信的教法,不得不自己發現一個真理。
從此以后,我便進一步探究洋學的蘊奧,并闡明真理的性質,心中隱隱發誓了以后要建立一種新宗教。爾來,歲月忽忽,已過了十余年的星霜。其間我最致力于哲學研究,追求在其界內發現真理的光明,亦經歷了數年之久。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來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佛兩教中,亦不存在于耶穌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講的哲學中。此時我高興得幾乎不可計量。恰如哥倫布在大西洋中發現陸地的一端之時。至此十余年來的迷云始開,感到猶如腦中豁然開朗。
已在哲學界內發現真理的光明,之后再回顧其他舊有的諸教,耶穌教之非真理便益發明顯,又容易得以證明儒教并非真理。只有佛教可認為其說甚為合乎哲理。于是我再閱讀佛典而愈知其說之真,拍手喝彩,曰:何知歐洲數千年來實究而得到的真理,東洋則早已于三千年前的太古便有之?而我于幼時在其門,但不知真理存在于其教之中,是因當時我缺乏學識,無能力發現之。于是我放棄重新建立一個宗教的宿志,而決定改良佛教以將其當作開明世界的宗教。此正是在明治十八年之事。以上為我改良佛教的紀年。[注]井上圓了:《井上圓了選集》第3卷,東京:東洋大學,1987年,第335—337頁。(《井上圓了選集》共25卷,可在東洋大學附屬圖書館官網內“學術情報リポジトリ”下載。)
以上文章并非寫出履歷的事實,而是從“追求真理”的角度整理自己的思想問題。而從書名可知,為使佛教相關人士注意,此文章包含偏差及強調。敘述自誕生至開始修習洋學的前半部分相當于長岡時期的事,后半部分則相當于東京大學時期的事。
在此,將關注后半部分。圓了說“進一步探究洋學的蘊奧”“最致力于哲學研究”,從時期看,可視為他在哲學科第2、3學年時上過的費諾羅薩的課。其中,先學習西洋哲學史,后學習自康德至黑格爾的近世哲學。3年級時,圓了訂上2本筆記本,作成《明治十六年秋 稿錄 文三年生 井上圓了》,內容是英文書的摘錄。德國學者Rainer Schulzer分析認為圓了摘錄的54本中哲學書多達44本,判斷“井上圓了的思想中所見西洋哲學的影響,及于所有事情”[注]ライナ·シュルツァ(Rainer Schulzer):《井上圓了〈稿錄〉の研究》,《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19號,2010年9月,第289頁。。依筆者推測,圓了透過費諾羅薩的課與《稿錄》等自己的研究,“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來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佛兩教中,亦不存在于耶穌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講的哲學中”。
圓了常于著述中說“真理的標準在哲學”。吾人可認為,他以西洋哲學為前提,論評其他哲學與宗教。由上述的“思想遍歷”而言,接著論及圓了發現佛教符合哲理,便是以往其思想研究的一個潮流。現今的《百科全書》等書,仍認定井上圓了是佛教哲學家。因此,圓了往往被視為從學生時期努力研究佛教,但由其學生時期所撰寫的論文看,其追求真理的途徑并非如此單純。從此時期的論文得知,其中所論及的佛教均不超出宗教之一的范圍,圓了尚未以佛教作為專門的研究題目。對此,他在學生時期首先追究的是,儒教即中國哲學。為了厘清這點,當時的論文列舉一覽表:
第一學年(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堯舜ハ孔教ノ偶像ナル所以ヲ論ス〉(一五年六月,《東洋學藝雜誌》)
第二學年(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黃石公ハ鬼物ニアラズ又隱君子ニアラザルヲ論ズ〉(一六年五月,《東洋學藝雜誌》)
第三學年(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排孟論〉(一七年一月,《東洋學藝雜志》)
〈讀荀子〉(一七年八月,《學藝志林》)—畢業論文
第四學年(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孟子論法ヲ知ラズ〉(一七年一二月、一八年四月,《東洋學藝雜誌》)
〈易ヲ論ス〉(一八年七月及八月,《學藝志林》)
由此可知,圓了在學生時期追究西洋哲學的同時,首先追究中國哲學,闡明這點的是中國古代思想史專家佐藤將之。[注]參見佐藤將之:《井上圓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國哲學の位置》,《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21號,2012年9月,第31—32頁。
論及東洋哲學,便是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筆者剛論述圓了在日本“發現”中國哲學。那么,圓了何時自覺地認識到被稱為印度哲學的佛教中有哲學?從現有的資料看,是在寫向東本愿寺提交之呈報書的草稿之時(1884即明治17年秋,4年級)。其中一節對西洋哲學與佛教論作比較:
(哲學:作者補)有古代近世二種,有日耳曼英國二派,整體而言,除宗教之外與佛教有關系者,哲學諸科與理學中物理生物等諸科也。而哲學中與此最有密切關系者,純正哲學也。
若將其配佛教,其所謂實體哲學與小乘諸派相類,心理哲學與大乘唯識相類,論理哲學則與天臺相類;俱舍為其所謂唯物論,法相為唯心論,天臺則與物心二元一體論相同;又,英國哲學以心理學為本,故可比俱舍唯識,德國哲學則以論理為本,故可比華嚴天臺。
由是觀之,西洋哲學數百年來所研究的真理,不能跨出佛一代五十年間所說的法門之外。又,西洋哲學今日所論決的諸說,均存在于千年以前,由此來看,釋尊的活眼卓識出乎□□人的意外,誰不贊嘆!使東洋古學復興而并非只是西洋□□學□,豈有視之為野蠻愚法而廢棄之理![注]拙稿:《哲學館創立の原點——明治十七年秋、井上圓了の東本愿寺への上申書》,《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19號,2010年9月,第20頁。
如上述的“思想遍歷”所說,圓了獲得西洋哲學的核心,將其與佛典比較。由此草稿可知,在作仔細的比較前,他在某種程度上已預測到大致方向。他在《佛教活論序論》一書中說:“明治十八年廣泛搜索內外東西諸書,每夜非到深更,則不上床就寢。上床后,種種想象浮現于心內,終夕徬徨于夢里,故不能熟睡。故此,精神日夜幾乎都無安息。如此情況繼續數個月,心身均感到疲勞,但并無特別介意之。刻苦勉勵如常,昨春終于患難治病,在病床上接受醫生治療已超過了一年。”[注]井上圓了:《井上圓了選集》第3卷,東京:東洋大學,1987年,第355頁。圓了設想的哲學諸論的變遷是:唯物論→唯心論→物心二元論;主觀論→客觀論→理想論;經驗論→本然論→統合論;空理論→常識論→折衷論;可知境→不可知境→兩境;設想的佛教的變遷是:有→空→中道。換言之,他理解每個思想的發展便是正、反、合的辯證法。
關于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的如上研究,圓了在日本人所撰首個西洋哲學史的《哲學要領》前編一書中對此進行整理。《哲學要領》前編后來以單行本出版,起初是載于名為《令知會雜志》的月刊的論文,圓了從東京大學三年級時開始發表。其發表順序是:
明治17年4月 第1段 哲學緒論
明治17年6月 第2段 東洋哲學
明治17年9月 第3段 中國哲學
明治17年10月 第4段 印度哲學
明治17年11月 第5段 西洋哲學
《哲學要領》前編的特征是認為東洋哲學的歷史比西洋哲學更久遠,但此書并未論及東洋哲學家各個哲學學說,是為一缺點。然而,其內容證明圓了已能自覺地運用“東洋哲學”這一新用語。
1885(明治18)年10月27日,圓了于東京大學舉行“哲學祭”。“將哲學大約分為東洋哲學與西洋哲學二類,將東洋哲學分為中國哲學與印度哲學二種,將西洋哲學分為古代哲學與近世哲學二種”[注]東洋大學創立百年史編纂委員會編:《東洋大學百年史》資料編Ⅰ上,東京:東洋大學,1988年,第16頁。,并作為哲學發達的“樞要”,從中國哲學中選定孔子、從印度哲學中選定釋迦、從古代哲學中選定蘇格拉底、從近世哲學中選定康德以定位為哲學中興之祖,將此四位視為古今東西哲學家的代表,后來稱之為“四圣”。圓了如此表示哲學世界的具體象征以使其通俗化,并積極將東洋哲學定位于其中(圓了創立的哲學館作為重要儀式繼續哲學祭,還于晚年以哲學為主題,建設為了精神修養的公園即“哲學堂”,至今每年秋天舉行“哲學堂祭”)。
1886(明治19)至1887(明治20)年,圓了出版了3編的《哲學一夕話》,將西洋哲學與東洋哲學(佛教)融合為一體。第1編為“論物心兩界的關系”,第2編為“論神的本體”,第3編為“論真理的性質”。此著作受到首個日本人所撰之哲學論的評價。哲學家小坂國繼說:“圓了的《哲學一夕話》即為明治時期正式的純正哲學即形上學的開端。此外,其決定以后日本觀念論的方向,在此意義上也是重要的著作。其中蘊含著依據佛教思想的深奧思想,但圓了以其文才將那些深遠的、難解的思想,打造成一篇富有興趣的讀物。此著作當時受到廣泛的閱讀,故也在哲學的通俗化這點上貢獻度很高。”[注]小坂國繼:《明治哲學の研究》,東京:巖波書店,2013年,第319頁。
前文已述,近代日本東洋哲學的先導是東京大學初代綜理加藤弘之。在此教育環境中,圓了學習西洋哲學并究明其核心,進而發現了東洋哲學。其間,他過著晝夜不懈地研究的日子,甚至罹患肺結核。由此,在將西洋哲學引進日本,以及將以往的儒教和佛教等重建為東洋哲學上,圓了都扮演了先驅角色。1906(明治39)年,圓了從哲學館引退,在此之際將大學改為財團法人,以委托東洋哲學的振興給后繼者,并大學名稱為“東洋大學”[注]關于東洋哲學與西洋哲學的未來,參見新田義弘:《現象學と西田哲學——東西思想の媒體として》,《井上圓了センター年報》第4號,1995年7月,第3—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