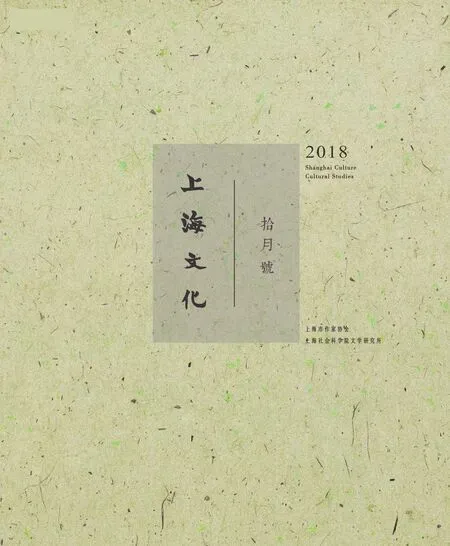“多元鏡像與當代都市文化研討會”綜述
王馨寧
(上海臨港當代美術館)
“多元鏡像與當代都市文化”學術研討會不久前在上海臨港當代美術館舉辦。上海油雕院美術館副館長傅軍、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導師姜丹丹、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副館長杜曦云、上海公共藝術協同創新中心(PACC)研究員姜俊、《上海美術》責任編輯李磊及本次“多元鏡像——2018上海當代藝術展”18位參展藝術家參與了此次話題研討。
一、關于“鏡像”的論述
作為“多元鏡像——2018上海當代藝術展”策展人傅軍認為,“鏡像”包含了幾個層面的理解,現實的鏡像、歷史的鏡像、自我的鏡像等。首先,是我們所處都市中直觀的生存體驗,高樓大廈、手機屏幕等鏡像帶來的強烈沖擊感。其次,是藝術作品和藝術家之間的關聯。某種程度而言,藝術作品是藝術家自我的一種心理投射,所以作品和作者之間存在一種鏡像關系。再次,延伸至整個中國當代藝術來看,它成為我們當下時代和都市化進程中的某種鏡像反射。
對于“多元鏡像”這一主題的設立,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副館長杜曦云指出,在策展人主觀意愿非常強的展覽中,藝術家或非藝術人的產物都將變成策展人的材料,轉化成為屬于他的話語體系,這種強策展主要突出的是策展人個人的意圖及其話語結構、邏輯等。然而,在本次展覽中,策展人很尊重每位藝術家,她的意圖是通過這個空間、平臺和機會來盡量凸顯每個人的獨一無二性。所以她沒有過分強調自己的話語意圖,而是相對低調地隱在背后,使每位藝術家的作品得以凸顯。同時,他從語言學角度提出了對于“鏡像”的解讀,認為藝術語言和真實表達之間是有差距的,藝術作品和藝術家本身不存在等號關系。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并不是我們在說語言,而是語言在說我們。從某種角度而言,人類永遠沒辦法真實、徹底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意圖,因為需經過語言這個環節,就要遵守語言自身的邏輯。這就難以說明作品表達的就是作者內心真正想傳達的,但也不能說它跟心理投射毫無關系,這是人和語言之間的關系。因此,“多元鏡像”參展作品可以被認為是藝術家日常生活所思所感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它一旦分泌出來,在脫離其肉身之后,就變成獨立的存在,這點用“鏡像”這個詞很準確。
“鏡像”在西方是一個非常久遠的話題,從柏拉圖的“模仿說”開始,后來的弗洛伊德、拉康等更是把“鏡像”作為一個哲學命題來思考。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生導師姜丹丹認為,傅軍把拉康理論用到當代藝術中提出“多元鏡像”的議題,實際上是把當代都市處境中城市這個既真實又虛幻的空間構成在鏡像和藝術中。這次展覽涉及不同的媒材,比如繪畫、攝影、裝置、雕塑等,每種藝術作為一種魔鏡透射出了藝術家在都市處境中內心的狀態及存在的一種方式,主體和他者、環境及公共空間的關系。從這個角度思考,這是很有深意的展覽,展覽中一些創作也有理論思考與省察的高度和深度。
除此之外,姜丹丹從傅軍對于策劃的思考出發,補充了有關現代性的理論,即波德萊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提出的“現代性就是流變的、轉瞬即逝的和偶然的;現代性是藝術的一邊,藝術的另一邊是永恒和不變的”。這一觀點為現代主義藝術奠定了觀念基礎。在30多年的城市建設當中,我們依然身處波德萊爾詩所描繪的憂郁情境中,城市總是在變,巴黎在變,隨之人們的憂郁也總在增長。
由波德萊爾提到的現代性理論出發,姜丹丹提到關于當代處境的思考性。當代處境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本次大部分參展作品也提供給觀眾非常有意義的創作實例,使人們延續了這個命題的思考,也可以從作品實踐回溯到理論。比如胡行易的作品提示到有關現代性的問題更加劇烈化了,那些扁平的、沒有身份的、被異化的、解構的人所揭示的矛盾沖突更加強烈了。在某種程度上它提醒著我們,實際上被使用的、消費的,甚至制造的物件,已經潛移默化滲透到我們生命,或在無形中改造、損傷著我們生命本身,從這個角度警醒我們來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李淜的作品用馴獸師和動物的例子,一種戲劇化的場景,提示我們被規訓和馴服的人與物、人與人之間被奴役化的這樣一種思考。又如韓子健的裝置作品非常有新意,也與展覽十分貼近。他會提示到都市空間中無處不在的攝像頭,所有的網絡信息也是無孔不入。在“禁止與通行”的場域,它是被所有信號穿透、打孔的身體,這是在當代處境中非常極致化的體現,讓你感受到真實和虛擬這兩者不僅僅沒有邊界,反而真實被虛擬化了。正如德勒茲所說:“虛擬是當下真實經驗的前在環境條件。”虛擬包含無窮的可能性,也呈現一種逼近真實的當代人處境,它比“現實”更豐富。
又比如魯丹做的一朵云,非常的清淡,是有霧霾透射當中的云。這些情況讓人想到法國的哲學家皮埃爾·阿多的《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他思考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歐洲,那時候城市污染非常嚴重,在心肺受到損傷的情況下,他反思我們不僅要注重保護自然環境,而且要轉化自身對事物的態度,包含我們對生活環境每一件事之間、每一個物之間的關系。魯丹的云就是從這個角度提出如何轉換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樣一個倫理問題。
再比如伊國棟的作品,你剛剛看的時候會聯想到藝術史當中的藝術典故,從圖像表面讓人想到1655年倫勃朗的《被屠宰的牛》,通過非常粗野與殘酷的畫面,讓大家看到動物被屠宰的方式,但它作為一種社會儀式來呈現,屬于日常生活當中一種儀式化的場面。英國畫家培根,他同樣用無器官身體的方式來處理這樣殘酷的場景。但是伊國棟把這種直陳的方式用于當代攝影當中,不是講述這個事情、再現這個場景,而是用一種更加直白的、呈現的方式,思考動物處境和當代生命體處境之間的關聯,也是非常有趣的切近。
另外,姜丹丹提到通過材料的運用,圖像、情感、技術的交互滲透,作者在藝術鏡像當中看到自我的形象,自我形象的撲朔迷離、不確定,甚至低微,都是自身與當代文化處境的一種省察間距。從展覽空間去看海上這批藝術家,他們的思考與創作盡管和鏡像理論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一種低調、溫和和冷靜的間距,這是一種反思的、批評的距離。
上海公共藝術協同創新中心(PACC)研究員姜俊指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德國藝術家莫霍利·納吉是對整個城市多元化空間、多元鏡像思考的先驅,他討論的正是關于柏林,和姜丹丹所說的巴黎形成一個對比。當時的柏林也存在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在現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形成多媒介同時并行的狀態。莫霍利·納吉所表達的是:我們進入一個平行時間當中,當沉浸在鄉村慢悠悠的生活狀況,我們看到的是時間線性的發展,但當我們身處城市之中,我們看到的是各種不同時間形成的網絡,一種所謂共同發生的狀況。因此,多種邏輯的影像和鏡像在我們面前出現,比如各種不同的廣告和巨大的屏幕,它在一定程度上組成了我們今天看到整個城市多元和碎片化的多元鏡像折射的關系。
此外,“都市文化”這一概念引起與會者興趣。《上海美術》責任編輯李磊覺得這是對文化語境的一個框定,即把青年藝術家置于都市文化背景中來思考。從參展作品中,可以看出青年藝術家在城市中受到的壓力和他們的思考。就都市文化而言,有廣義和狹義的區別。廣義指的是城市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是指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思想、價值觀念、信念、規范等。陳迪的《上海客廳》系列作品比較受大家關注,他的學習、生活背景很大一段時間在河南、江蘇,他到上海以后創作的作品,這么具有上海味道,這么接地氣,本身反映了這個城市的魅力。
二、藝術作品與公共空間的關系
在傅軍看來,當藝術作品安置于工作室期間,藝術家和作品之間存在著某種層面的鏡像關系,但當這個作品來到美術館中,它其實是走向了公共空間。對此,我們可通過本次展覽的很多作品,感受到上海藝術展覽蓬勃的發展,也察覺到美術館朝向娛樂性、劇場性、沉浸式發展的趨勢。
姜俊認為現在很多展覽確實充滿各種對體驗性的追求,對多元媒體、體驗性、舞臺性、參與性、表演性等方面的追求。其實從2000年開始,泰特美術館被作為一種新的美術館形式,即劇場性的美術館形式,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對古典作品的收藏和保存,它更多變成類似劇院、游樂場等場所,每天除了作品聲光電等多元媒體以外,還會舉辦各種不同的公共教育活動等。近10年來,歐洲的行為表演、行為戲劇在當代藝術中也被多次展現,幾乎每個大型的當代作品展中都存在這樣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它可以使得整個美術館有一種劇場性的效果,從而獲得更多的觀眾。而這樣的美術館,更多的和整個城市的功能轉型有著相對應的關系。
今天的城市慢慢轉化成第三產業和娛樂文化的消費場域。從60年代開始歐洲進入中產階級社會,70年代出現了大量的多元文化運動,如女性運動、族群運動、同性戀運動、環保運動等。今年也是歐洲“68”運動50周年,整個歐洲在做不同回顧。進入中產階級化的歐洲,就開始出現文化多元性,而這就是我們看到各種不同的城市景觀和城市要求,各種不同族群對于自己權利的抗爭與奮斗,同時也是一種消費升級的典型。在這個過程中,城市開始轉型,從一個原來的市場和工業聚集地,慢慢進入去工業化,出現“中產階級化”,老街區重新被改造、塑造成新鮮又光亮的新城市街區,同時把各種娛樂和消費元素注入城市當中。姜俊認為,城市其實更多需要的是娛樂,更多的消費,更多的所謂旅游族群。一些大型的都市如倫敦、柏林,都以組織非常好的藝術雙年展,非常好的各種不同的文化活動和藝術活動(當代藝術或者舞蹈各種方面)來吸引不同的族群。在這樣的趨勢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美術館和藝術越來越走向表演性、劇場性的整體特征,這也是配合整個城市的這種現代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