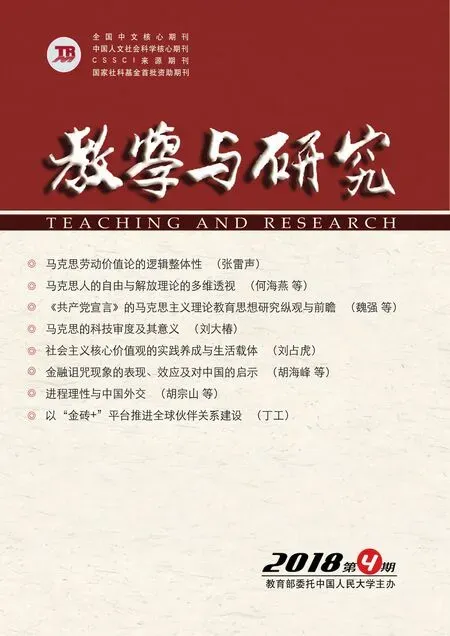論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
“國外有沒有思想政治教育”?這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較研究的前提問題,也是一些人質疑和攻擊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維度。對此,學界有個基本共識:國外(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統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名稱,但是,存在大量實質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這就是所謂的“名實之辨”。“名實之辨”為思想政治教育比較研究提供了可能,也較好地澄清了一些人的錯誤認識。然而,如果認定國外沒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那么,應該用什么指稱國外思想政治教育之“實”呢?若是翻譯搬用國外原有之“名”,那就相當于放棄了“思想政治教育”這個核心范疇;若是直接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又有削足適履、強人所難之嫌。更為關鍵的是,假如國外沒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又怎樣保證中外思想政治教育之“實”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在層次上是對等的、在研究上是可比的?顯然,如何認定國外思想政治教育之“名”仍是比較研究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本文以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為例對此作一探討,以期深化相關認識和研究。
一、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研究誤區
將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名”與“實”進行區分,肯定其存在之“實”,否定其統一之“名”,是目前普遍做法。這種做法的好處在于可以簡潔明了地解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存在的問題,弊端在于難以全面清晰地把握美國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存在的問題,而且也容易造成一些研究上的誤區。
首先,對“實”的表述較為混亂。基于“有實無名”的前提假設,人們經常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價值觀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歷史教育、政治社會化等來表述美國思想政治教育,而較少考察它們之間的內涵差異和相互關聯,鮮有追問其歷史流變和現實形態,以致這些表述相互纏繞,缺乏明確的指認對象,從而給清晰準確地認識把握美國思想政治教育問題帶來了困難。其次,對“名”的使用過于隨意。由于否認了美國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名”,一些研究者常常根據自身需要創制研究術語,提出所謂美國的“世界觀教育”“信仰教育”“人生價值觀教育”等問題。但是,較少考量這些術語與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主流話語是否相通,與其現實情況是否相符,從而使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變成了沒有美國在場、缺乏客觀對象的隨意指認。
更為嚴重的是,以龐雜的對象表述和隨意的術語使用為基礎,形成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結論。例如,一些人把“隱蔽性”看作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質和最大優勢,而事實上隱蔽性只是美國思想政治教育在正式課程之外的輔助性特征,尤其在中小學階段,標準化的教育要求、系統化的課程設置、法治化的管理方式等顯性途徑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1](P266)又如,一些人把宗教教育特別是基督教義當作美國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內容,但事實上早在1962年、1963年美國最高法院就作出將宗教教育驅逐出公立學校的判決,自此之后,宗教祈禱和圣經閱讀在公立學校和其他非教會主辦的學校中基本銷聲匿跡。[2](P44)再如,一些人將“政治社會化”等同于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甚至還比較了政治社會化與我國思想政治教育之間的異同;事實上“政治社會化”只是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學理論,在教育實踐層面并不具有廣泛影響。相反,由于其過于強調環境對個人的塑造作用、貶低個人的主體性,很快就被發展心理學的認知主義模式所替代。[3](P295)將“政治社會化”視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實”,顯然有些以偏概全。
之所以產生上述問題,主要是因為割裂了“名”與“實”的內在關聯,否認了美國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用自我之“名”衡量剪裁他者之“實”,從而造成了“名”的混亂、“實”的模糊、“名”與“實”的不符。
解決這個問題關鍵是要搞清楚“名實之辨”的“名”是名稱還是概念。名稱與概念在詞法上是兩種不同的名詞,在本質上是認識世界的兩種不同方式。名稱是用以識別事物的專門稱呼亦即專有名詞,是以經驗的方式認識世界,形成的是關于世界表象的經驗描述;概念是用以表征事物的普通名詞,是以理論的方式認識世界,形成的是關于世界本質及規律的理論闡釋。如果“名實之辨”的“名”指的是“名稱”,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國專有名詞,不具有超越時空的解釋力和適用性。但是,這樣就等于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了一種狹隘的經驗化的“地方知識”,否定了其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統治方式的普遍性和作為一門科學的合法性。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也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長足發展與巨大意義。事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當作一門科學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得以確立和發展的前提性共識。作為一門科學,思想政治教育學是由一系列概念構成的理論系統,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最為核心的概念。誠然,這個概念是由我國創造的,但是,它所蘊含的本質規定決定了其解釋范圍的普遍性。因此,“名實之辨”的“名”只能是概念,不能是名稱。當我們說“美國有沒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時,實際是在追問“美國有沒有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而不是美國有沒有“思想政治教育”這個名稱。
二、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概念指認
從概念角度考察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指認美國語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并確保其在中美兩種學術話語間的對等性?對此,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將思想政治教育翻譯成英文,然后再去美國文獻中確認其對等概念。目前,學界普遍將思想政治教育翻譯為“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結果發現美國并沒有與之相對應的概念,由此便得出“美國沒有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結論。這種方式的弊端在于:一是混淆了名稱與概念,企圖在他者的語境中找到屬于自我的專有名詞,結果只能是無功而返。二是沒有考量美國語境的特殊性,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標準衡量剪裁他者,結果也是可想而知。另外一種方式是從美國文獻出發,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概念進入美國語境時的轉譯和變形,然后結合美國語境的特點剔除其強加于這一概念的意識形態指控,進而確定與思想政治教育相對等的美國概念。大體可以分為兩步:
第一步,確定美國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指認。20世紀70年代,美國精神分析學家羅伯特·利夫頓根據社會環境控制、生存權利配給等8項條件,認為新中國初期的“思想改造”實質上就是意識形態“洗腦”。這種極端認識在當時便遭到美國蒙大拿大學的瑪麗·赫拉克的明確反對,她認為不能將中國思想改造簡單看作“洗腦”,而應該區別對待以“植入觀點”為主的“政治灌輸”和以“導出觀點”為主的“政治教育”。[4]鑒于“思想改造”是我國思想政治教育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因此,可以將“政治灌輸”和“政治教育”視為美國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指認。2008年,由英美學者共同主編的《公民與民主教育SAGE手冊》認為,與英文中公民教育概念最為接近的中國概念是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之間緊密相連,又可以合成為思想政治教育(ideopolitical education)和思想品德教育(ideomoral education)。[1](P139)在這里,“公民教育”是美國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概念指認。相較于“政治灌輸”“政治教育”而言,這種指認包含了政治與道德雙重意味。
第二步,考察用以指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在美國語境中的指認對象。首先,“政治教育”與“政治灌輸”并無二致,只是美國刻意設置的雙重標準。對此,瑪麗·赫拉克明確指出:“現實中美國人習慣于在談到自己國家時使用‘政治教育’一詞,而在談到美國以外的國家時則使用‘政治灌輸’一詞,實際上兩者往往極為相似。”[4]其次,“政治教育”與“公民教育”在美國是兩個相互等同的概念。美國著名公民教育學家沃特·C·帕克就指出:“在現代美國社會,公民教育也被稱作政治教育,但是由于政治教育含有灌輸教化的意味,所以在學術界之外不常使用這一概念。”[5](P348)再次,美國語境中的“公民教育”同樣具有政治和道德雙重意味。在政治意味上,“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相等同,都是為了培養與美國政治制度相匹配的公民,用威廉·高爾斯頓的話說:“(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呼喚富有民主精神的公民,他們的知識、能力和品格不適合非民主的政治。”[6]在道德意味上,“公民教育”與“道德教育”“品格教育”緊密相關,都是為了促進青年親社會發展(pro-social development)。甚至有學者認為“公民教育實質上就是以提供和促進公共道德、贊同公民關系治理原則和彼此間責任義務的道德教育。”[7](P26)同時,由于“道德教育”主要指涉個人道德生活,而難以涵蓋“公民教育”所需要的公共品格和行動能力,所以,也有學者主張將“公民教育”與“品格教育”相融合,稱之為“公民品格教育”。[8]
經由上述分析可見,“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都是與“思想政治教育”相對等的美國概念,亦可視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意識形態(ideology)在西方語境中是個負面概念,再加上美國人使用“政治教育”“政治灌輸”概念的“雙重標準”,所以,美國對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指認總是冠以意識形態的前綴(ideo),刻意突出政治灌輸的意味。拋開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美國所說的“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就是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概念闡釋
從概念角度考察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確認美國語境中的概念指認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并確保其與中國語境的相通性?判斷一個概念能否被稱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有兩個標準[9](P2-6):一是看這個概念是否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內涵,即“以育人為本、意識形態性、內容規定性、目的性”;二是看這個概念是否涵蓋思想政治教育外延,即“主體的覆蓋性、過程的連續性、外延的制約性”。據此,我們可對美國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進行考察。
美國公民教育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民教育是指“教育引導青年認定自己在全球社會、民族國家、地方和文化共同體中的公民身份的全部途徑,包括在家庭中的社會化、在學校教育和校外項目中的經驗、朋輩間非正式的面對面交流以及來自社會的廣泛影響。”[1](P263)狹義的公民教育是指“幫助青年獲得和學習運用公民技能、公民知識和公民態度,確保青年成為有能力負責任公民”[10](P10)的學校教育。目前,美國學界對公民教育的定義不盡相同,但主要在狹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總體來看,美國公民教育概念包括四個要件:第一,以維護發展美國政治體制為核心。美國公民教育自誕生之日起便與其政治體制緊密相連。從獨立戰爭后旨在建立統一的美利堅民族的“美國化教育”,到19世紀為應對黑人婦女爭取公民普選權開設的公民課程,從20世紀60年代“精英化”“同質化”的傳統公民教育衰落,到21世紀初新舊公民教育之爭,美國公民教育始終奠基于《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所標榜的政治理念之上,服務于美國構建“山巔之城”的政治理想,并隨著美國政治實踐的變化而變化。第二,以塑造公民身份、引導公民參與為目的。美國公民教育目的在不同歷史時期表述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圍繞塑造公民身份和引導公民參與展開。塑造公民身份核心在于教育青年明確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狹義)、具備政治生活參與的知識技能(中義)、擁有促進共同利益和參與公共事務所需的品質(廣義),[8]目的在于使青年“超越個人利益,致力實現所屬的更大群體的幸福。”[11]引導公民參與青年形成公民生活所需的動機與能力的活動,積極參與國家、社會和地方事務。第三,以傳授公民知識、公民技能、公民品性(亦稱為公民態度)為內容。公民知識主要包括美國政治體制的基本構成、民主程序和歷史演變,以及自我權利與義務、當前政治熱點事件;公民技能主要包括知識技能、參與技能和社交技能;公民品性主要包括價值觀、動機和認同等。[8]第四,以正式課程和各類活動為載體。美國公民教育載體在不同學段有不同設置。中小學階段主要以“公民學與政府”“歷史”“地理”等正式課程為主,同時輔之以校園文化建設(國旗宣誓、學生社團等)、校外服務學習等實踐活動;[1](P266-267)大學則以正式課程為輔(主要是通識課程),以社會實踐為主,先后涌現了“服務學習”“公共參與”“公民參與”等三次大規模公民參與運動。[12](P112-124)
美國道德教育概念亦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道德教育是個歷史范疇,最早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宗教教育,后在19世紀演變為以新教倫理為基準的價值觀教育,在20世紀初演變為以葆有傳統為核心的品格教育(亦稱舊品格教育),并在進步主義運動的沖擊下發生了分化,在高校分化為職業倫理教育和通識教育,在中小學分化為解決問題與社會學習兩種教育形式;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受民權運動、懷疑主義、相對主義影響,美國道德教育降至歷史最低點,甚至一度淪為“非法行為”;此后迅速反彈,出現了價值澄清、認知發展、女性主義、新品格教育等一系列影響巨大的理論流派和實踐運動,并在21世紀初成為美國最受關注的教育領域。狹義的道德教育是個理論范疇,最早于1965年由皮亞杰提出,后被柯爾伯格進一步發展,與建構主義心理學緊密相關,是“促進兒童和青少年道德認知結構(亦即道德推理階段)發展的學校教育形式”。[8]其主要內容有三:其一,以個體道德發展為中心,培養獨立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能力。其二,以道德兩難和公正團體為主要方法,前者依托青少年朋輩學習小組對開放式的道德問題和故事展開討論,后者依托小型專門的學習團體(如在大型高中設立100名學生和5名教師組成的公正團體),通過文化建設和適當灌輸進行所謂“直接民主式”的道德教育。其三,以認知主義道德發展理論為基石,富有濃厚的“理論驅動”色彩,并隨著后柯爾伯格時代諸如道德領域理論、親社會道德推理理論的興起呈現出新的實踐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廣義和狹義的道德教育雖然在內涵和外延上各有不同,但都致力于將青少年培養成為美國民主政治體制所需要的成員,用杜威的話:“民主將在每一代人那里重生,而教育是民主重生的助產士。”[13]
美國品格教育概念有新舊之分。舊品格教育興起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目的在于葆有傳統價值觀念以應對美國現代化進程引發的嚴峻挑戰,主要方式有兩個:一是“道德編碼”(morality code),即將傳統價值觀(主要是新教倫理)編碼轉述為現代性的世俗化的道德規范,用以指導學生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如1917年由威廉姆·哈德欽斯(William Hutchins)撰寫的“兒童道德編碼”就列舉了“正確生活的十條律令”,涵蓋兒童學習生活、精神衛生、道德發展的各個方面,成為當時學校品格教育的摹本。二是“團體活動”(group activities),即強調團體化生存對青少年品格發展的重要作用,在課堂內外建立了形形色色的學生俱樂部,強化對青少年道德行為的朋輩監督和成人引導。這種以傳統價值觀為核心且較少考量青少年自主性的教育方式遭到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強烈批判,并隨著后者的廣泛興起而迅速衰落。直至20世紀70年代,伴隨價值澄清和建構主義道德教育理論的興起,品格教育得以再度復蘇。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1992年約瑟森研究所發布“品格統計”報告與品格教育伙伴組織第一次規劃會議為標志,品格教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成為涵蓋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的新型教育形態,亦即新品格教育。[8]與舊品格教育相比,新品格教育在理論上將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與心理學行為主義相融合,既強調道德規范傳輸與訓練,又強調行為習慣的養成與引導;在實踐上,將理論研究與政府主導相結合,既廣泛引入心理學理論和方法以提高教育的科學性,又不失時機地利用政府對青少年品格發展的大力支持,推動品格教育成為21世紀美國教育理論和政策的主流話語。
綜合上述分析,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符合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內涵規定和外延界限,因而可以視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之“名”,三者既相互聯系又各有側重。從聯系來看,三者都致力于向青年傳播輸入美國政治理念和主流價值觀,都服務于美國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再生產,都注重通過有目的的教育設計推動青年親社會化發展,都集中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的統治需要與不同階層、不同種族的利益訴求。從區別來看:(1)在內涵上,公民教育是以共同體發展為核心的政治教化,道德教育是以個人道德發展為核心的能力訓練,品格教育則是以美國基礎價值觀為核心的規范養成。(2)在外延上,品格教育的范圍最大,涵蓋以廣義道德認同為核心的全部品格(道德品格、公民品格和績效品格);[14](P33)公民教育其次,重在處理人與共同體的關系;道德教育最小,重在處理人際關系和道德行為。(3)在形態上,公民教育貫穿美國國民教育全過程且有完整的課程體系設計,道德教育和品格教育則主要在中小學階段,沒有相應的課程體系,側重通過學校文化建設和社會實踐活動來進行。
四、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的運用原則
從概念角度考察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面臨的第三個問題是:如何運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分析美國問題或開展中美比較研究?對此我們認為,關鍵應堅持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堅定理論自信。一些人之所以糾結于“美國有沒有思想政治教育”,除了相關研究尚不充分之外,恐怕更深層的原因還在于錯誤的理論心態。主要是兩種:一是將美國奉為最高標準,認為美國沒有的我們就不該有,否則就是蓄意為之,就是所謂的“黨化教育”甚至于“洗腦”;二是搞思想理論上的極端特殊主義,過于強調中國理論的特殊性,而否認其普遍的世界歷史價值,有人甚至說: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以來提出的,不能把它向外推給洋人,向上推給祖宗。這兩種心態的要害都在于理論上的不自信。對此,我們應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大勢出發,深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增強“四個自信”的戰略思想,準確把握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的差異性和相通性,既勇于用中國話語概括中國實踐,又善于用中國概括解釋世界問題,為人類發展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
第二,增強學科自覺。意識形態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根本屬性。增強學科自覺首要之義便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準確把握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差異,探索美國語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適用邊界、指認對象和解釋原則,使之成為透視美國意識形態精神實質的有效概念工具。其次應明確概念規范,堅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學科主概念,有條件有選擇地使用美國原有之“名”和其他學科概念,尤其須警惕研究術語創制使用的隨意性,確保在學科主概念框架下實現“名實相符”。再次應遵循學科發展邏輯。大凡比較研究都須經歷“事實研究”階段,即通盤細致地掌握研究對象的實踐事實和理論事實,離開這個階段所謂的比較只能是停留于自我想象中的理論臆測。而要分析辨認他者之“實”就須首先明確他者之“名”。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之“名”研究仍任重道遠。
第三,把握概念差異。在明確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對等相通的基礎上,把握其人民中心與資本驅動的性質差異、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差異、一元主導與多元分化的內容差異。在明確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等美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之“名”的基礎上,考察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學者使用的具體之“名”及相互關系,逐步構建起名實相符、邏輯完整的概念指稱體系。此外,還需把握好概念使用的“統”與“分”。當用“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統一指稱時,應注意其各個組成部分的具體意涵及內在關聯;當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分別指稱時,應注意其作為美國思想政治教育構成部分的共同屬性和獨特作用。
參考文獻:
[1] James Arthur, Ian Davies and Carole Hahn.The SAGE Handbook of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nd Democracy[M].Los Angeles, London,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SAGE, 2008.
[2] B. Edward McClellan. Mor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chools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1999.
[3] Lyn Corno and Eric M. Anderman.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6.
[4] 高地.西方學者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評[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6,(10).
[5] Larry Nucci, Darcia Narvaez and TobiasKre-ttenauer. Handbook of Moral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ledge, 2014.
[6] Galston W.A.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1, (1).
[7] D. Warren and J. J. Patrick. Civic and Moral Learning in America[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6.
[8] Wolfgang Althof and Marvin W. Berkowitz.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Education: Their Relationship and Roles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J].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2006, (4).
[9] 鄭永廷.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10]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and Center for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on Civic Learning and Engagement (CIRCLE).The Civic Mission of Schools[M].New York: Carnegie Corporation,2003.
[11] Sherrod L. Flanagan C and Youniss J. Dimens-ions of Citizenship and Opportunities Foryouth Development: the What, Why, When, Where, and Who of Citizenship Development[J].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002, (4).
[12] Corey Dolgon, Tania D. Mitchell and Timothy K. Eatma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ervice Learning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3] Jamieson K. H. The Challenges Facing Civic Edu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J].Daedalus, 2013,(2).
[14] Scott Seider. Character Compass: How Powerful School Culture Can Point Students Toward Success[M]. Cambridge: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