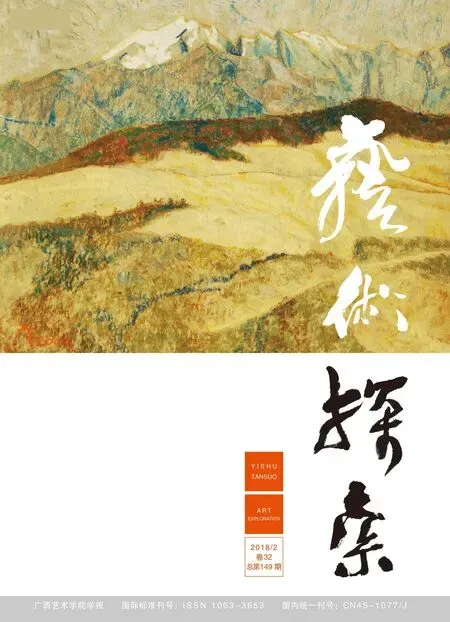壯族文化基因的影像傳承
——以電影《劉三姐》為例
熊 立
(廣西藝術學院 影視與傳媒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壯族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一個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云南、廣東等地。千百年來,壯族在生產與生活實踐中創造了優秀而豐富的文化。壯族文化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壯族獨特的文化基因不僅成就了其藝術創作,也成為其生存和保持民族特色的根源。在新的時代背景中,如何激活少數民族文化基因,使其成為當代新的文化背景之下民族藝術發展的因子和機緣,同時,如何挖掘少數民族的特色,利用現代藝術方式進一步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推動民族地區的文化傳承與發展,這是當下民族藝術包括影視藝術創作必須思考的問題。
一、地域環境、生產方式與壯族的文化基因
在我國,壯族主要的聚居區在嶺南西部。這里地形奇特,山陵廣布,江河縱橫交錯,四季氣候溫暖,雨水充沛,自然環境優美,自然資源豐富。在地域上,廣西三面臨南海,并與越南接壤,往來頻繁。顯然,廣西的奇山秀水不同于溫婉的江南水鄉,也不同于遼闊、雄壯的北國平原,其特有的自然條件、生態環境與對外交流的特殊性,滋養著生長在此的壯族人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個地域的自然環境與民族的生理基礎及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關系。“少數民族是最能釋放自我天性的群體,他們的生境決定了其自由自在的天性。”[1]30廣西地區獨特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壯族自由自在的個性特征,他們熱愛自然與生命,追求自由的生活及樂觀向上的精神。壯族一直以來就有“倚歌自配”的婚戀民俗,壯族的“山歌”不僅是他們溝通和交流的方式,更是他們抒發情感進而自由選擇配偶的方式。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歌圩文化”更是壯族追求個性和自由的充分體現。在歌圩——這種集體的歡樂對歌活動中,人的天性得以釋放,呈現出自由自在的生命本真狀態。這種山歌和歌圩的民俗不斷傳承,對壯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劉長林教授認為:“決定每一民族文化基因結構的始因并不在社會系統的內部,而在社會系統的外部,即民族的生理基礎和民族生存的自然環境。”[2]31可見,南方獨特的自然環境不僅為壯族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也為壯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豐富、厚重的物質基礎。經過歷史不斷的錘煉與沉淀,這些自然環境最終成為影響壯族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性因子。
與地理環境相適應的是壯族以稻作農耕為主導的生產方式。長期與大自然打交道的稻作生產方式給壯族文化打上農耕文化的深刻烙印。壯族自古就有著敬畏神明的習俗。他們的信仰中摻雜著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形成信奉多神的宗教觀念。“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3]487相應而言,壯族民間故事大多表現了壯族人民對神靈的頂禮膜拜,流露出信仰和依靠神靈的心態。這種宗教信仰的習俗體現了壯族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蘊以及獨特的世界觀。同時,在長期農耕生活中,壯族形成了善惡分明的倫理道德觀念。壯族民間關于“惡”和“善”的故事,大多以惡人遭受懲罰、好人得到應有的回報而告終,這反映了壯族人民的是非觀和倫理觀,體現了壯族“好善鄙惡,愛憎分明”的倫理道德觀。[4]39覃德清教授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認為:“基于水稻培育和種植基礎上形成的‘那文化’和‘弄文化’,是壯族文化衍生的根基,是壯族文化開放性與封閉性特征的基礎,是壯族‘堅忍聰靈,寬和明達’的文化心理與民族性格形成的物質條件。”[5]23可見,以稻作生產為主的“那文化”和“弄文化”為壯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條件,進而成為壯族文化發展與衍生的根基。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地理環境與生活方式相融合往往催生出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6]“所謂文化基因,就是決定文化系統傳承與變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結晶在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系統中、升華為哲學核心理念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7]134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文化基因長久地、穩定地、普遍地發揮著作用,對各個民族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的作用自始至終都存在著,它體現在各民族不同的思想、信仰、道德以及文學藝術之中。廣西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和在其中生成的歌圩風俗、多神崇拜的信仰習俗、“好善鄙惡”的道德倫常、山歌的藝術形式等構成壯族文化的原始因子,經過后世的不斷傳承,逐漸積淀成一種深沉而穩定的心理模式和行為規范,影響著生存在這一區域中的壯族人民,使他們呈現獨特的民族品性和精神特質。因此,壯族文化的形成反映了廣西地區的地理環境與壯族的生活方式相適應的普世性規律,同時,在其文化形態和內涵上往往又折射出地域性,并體現出壯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一個族群的文化基因往往通過藝術或者其他的媒介來呈現或傳承。一方面,藝術的生命力來源于多彩本真的民族生活,其汲取了民族生活土壤中的文化元素,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信息,因此,作為一種特殊文化樣式的藝術薀含了文化的全部基因;另一方面,文化又必須借助藝術載體進行傳承和傳播,二者相互聯系,不可或缺且相互印證。長期以來,由于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環境相對封閉,文化的傳播與傳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范圍僅限于本地域或者臨近的民族之間,并且人們對于一部分原生態文化的意義認識不足,對優秀的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處于原始、靜態的階段,少數民族文化的活力日漸衰減,面臨著逐漸消失的威脅。到了現代社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影像成為當代民族藝術表達與傳播所采取的較為普遍的形式之一。電影兼具記錄、審美與傳播的多重功能,為民族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傳播、傳承提供了有效的平臺和途徑,極大地加強了傳統民族文化傳播的力度,加快了其發展的進度。因此,在影像時代如何對電影傳承民族文化的優良基因進行研究是一個重要且迫切的課題。
二、《劉三姐》與壯族文化基因的傳承
劉三姐的傳說流傳悠久,民間也有不同版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加強了文藝戰線宣揚民族團結、共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力度,毛澤東主席號召搶救國家民族文化遺產,全國掀起了搜集、挖掘民族瑰寶的文藝運動。電影《劉三姐》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應時代而生的產物。在制作之前,《劉三姐》的導演和編劇深入到廣西地區采風和調研,充分考察了壯族的風土人情、生活習性和民族性格。在此基礎上,創作者采用了民間廣為流傳的劉三姐傳說為素材,采取了以壯族山歌對唱為主的形式,進行凝練和加工來構建故事。據統計,在電影《劉三姐》的編劇過程中,“從民間搜集了340本民歌,加上群眾口授,共搜集了182 500多首山歌”[8]116。《劉三姐》所采用的山歌,正是從民間積淀形成的18萬多首山歌中篩選出來的。同時,它又借鑒了西洋歌劇的精華,創造出“中國式歌劇”的山歌。“民歌文化既是劉三姐文化最本質的特征,也是廣西少數民族最鮮明奪目的文化符號。”[9]54《劉三姐》將經過現代編劇、導演再提煉創作后的山歌對唱貫穿于全片,影片對生活場景的描繪、壯族兒女形象的刻畫和故事情節的營構,都通過山歌這一最具壯族藝術特色的形式展現出來,這種創作手法既是對壯族傳統文化藝術的繼承與發展,也融合了現代藝術的開拓與創新,具有極高的藝術性和思想性。
另外,《劉三姐》將故事的敘述背景設置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影片中桂林地區的秀峰碧水、茶嶺農田、竹筏鸕鶿,展現出具有靈性和生命律動的南國風景。撒網捕魚、對唱山歌、縫制繡球等富有壯族特色的生產、生活場景,構成了自由自在的生活景觀和民族風情圖,呈現了與其他地域不同的壯族文化特征,給觀眾帶來清新自然的美感。除此之外,桂林山水不僅作為影像奇觀和地域特色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還對壯族的民族識別以及民族文化進行了有力的詮釋。“桂林山水作為壯族文化的地理因素,它具有不可公約的唯一性、堅固的理據性與大地的包容性,這可以修正現代品格的抽象性、片面性與無根性;它所呈現出的恬靜、純潔、祥和不僅僅是壯族文化品質的最好詮釋,更是讓一個美好世界有了大地的依托與賦形。”[10]184《劉三姐》中塑造以“劉三姐”為代表的在風景秀麗的南國邊遠地帶,在純凈秀美的自然山水中生活的壯族兒女的故事,不僅體現了壯族生活對廣西獨特的自然環境的親附性、依托性,更折射出壯族文化自然淳樸的原生生發模式以及壯族性格本真向善的深層緣由,這使得觀眾在被影片視聽語言吸引的同時,也在情感和身份上對壯族文化產生認同。
藝術作品的成功很大部分取決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電影《劉三姐》首先讓人物形象符合壯族的性格特征,在此基礎上再賦予人物以時代的內涵。劉三姐的形象在壯族民間傳說中是變化不定的,“但是萬變不離根本,最能代表劉三姐本質特點的能歌善唱和聰明智慧,在每一種類的劉三姐形象中都占據主要位置”[11]65。電影《劉三姐》汲取了傳說中劉三姐“能歌善唱”和“聰明智慧”的典型人物特征。其中,山歌是劉三姐人物的血肉和精神,也是壯族文化中具有標識性和生命力的部分。電影中,劉三姐的歌聲不僅顯示了“歌仙”的才能,更是充滿了智慧和力量。“你歌哪有我歌多,我有十萬八千籮”,“山歌能把海填平,上山能趕烏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唱出人間不平事,唱出窮人一片心”。與民間故事中劉三姐形象不同的是,影片經過改編淡化了劉三姐傳說中的“歌仙”形象,突出了她作為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性美。“著重展現她作為‘人’的一面的特征,剔除神秘色彩”[12]235,因此,劉三姐的形象帶有新時代的平民色彩和民間情懷,她唱出了老百姓的理想與愿望,得到了觀眾的同情與喜愛。同時,在影片中劉三姐與財主及走狗們堅決的斗爭充分體現了壯族特有的“智慧”與“機巧”。“莫夸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劉三姐和莫財主等人的對歌既顯示出壯族傳統的“好善鄙惡,愛憎分明”的精神,又富有戰斗性,對邪惡勢力進行了揭露。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作為嶺南最古老的少數民族——壯族具有鮮明的南方文化特征,這種文化特征來自于崇智的文化根系。所謂崇智文化根系是指在一個民族的思維中體現出較多的智慧性,在民族的心理中體現出較強的對智、巧的企求和崇拜。”[13]25可見,影片通過劉三姐的形象忠實而原生態地再現了剛直、充滿智慧的民族性格。除此之外,影片還塑造了劉三姐大膽能干、火熱多情的壯族妹子的形象。她既會捕魚,又能做一手好針線,對生活和愛情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她對阿牛哥的情感在與地主老爺做斗爭的過程中,逐漸建立并日漸堅定。她暗地里為心上人縫繡球,唱著山歌表達對心上人的情思并鼓勵阿牛接受戀情:“竹子當收你不收,筍子當留你不留,繡球當撿你不撿,空留兩手撿憂愁”,壯族兒女勤勞勇敢、大膽追求愛情和幸福生活的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劉三姐這個人物形象達到了個性與共性的完美融合,是壯民族反抗階級壓迫和剝削,爭取政治、經濟和文化自由解放的理想化身,是壯民族正直、勇敢、智慧、善歌品質的縮影”[8]115。因此,經過藝術加工后的《劉三姐》不僅體現了壯族特有的思想意志、文化素養和審美情趣,也具有時代色彩與現代魅力,贏得了觀眾的認同。
當然,與同時期的其他文藝作品相仿,電影《劉三姐》不可避免地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在特定的歷史年代,電影被置于國家意識形態的整體格局與規劃之中,政治訓誡和思想教育功能凌駕于電影的藝術形式和娛樂作用之上,“把本來體現了少數民族民間生命精神的傳說轉換成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同時也使之納入到民族國家文學話語系統”[14]62。“一人唱來萬人和”的《劉三姐》也同樣如此,“這無論是從影片的改編、攝制還是接受上都可以得到明證”[15]9。但是,影片中劉三姐并沒有完全變成“土改斗爭”中的革命領袖,壯族山歌也沒有演化為所向披靡的革命武器,劉三姐和阿牛哥在戰勝莫懷仁后,并沒有繼續投入革命斗爭,而是泛舟于秀美的大自然之中,駛向自由幸福的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因為山歌保存了壯族人民所具有的幽默、睿智與浪漫、抒情的品性,柔化了意識形態的剛性色彩,以劉三姐和阿牛哥為代表的壯族人民大膽反抗、追求自由幸福的樂觀精神,超越了彼時時代的局限,給予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壯族文化質樸、純真與柔情的品質賦予影片人文關懷與藝術情感的補充或修正,才使影片呈現一種“張力”,在建構具有革命意志的現代社會的同時,為世人敞開了一個獨具民族特色的歌美、景美、人美的藝術世界。
電影《劉三姐》在1961年上映后,獲得巨大轟動,風靡了全中國。據統計,此后《劉三姐》曾在香港重映三次,在世界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后上映,受到國內外觀眾的喜愛。《劉三姐》之所以一問世就震撼中外,并且保持了經久不衰的魅力,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融匯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超越了時代思想意識的束縛,通過影像傳承了壯族文化基因,使壯族文化精髓得到深刻的藝術呈現。在藝術作品琳瑯滿目的當下,《劉三姐》仍然能以歷史記憶和影像魅力在海內外擁有眾多觀眾,享有聲譽,“歌仙‘劉三姐’作為廣西旅游和文化的品牌,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一樣鐫刻在了人們心中”[16]108。可以說,《劉三姐》不僅是電影中的經典,也是壯族文化傳承的藝術杰作,劉三姐的形象已不僅僅體現了具有地域性與民族性識別和認知的文化民族品格,更成為廣西的民族符號,以及中華民族的情感體現和文化象征。
三、文化基因的激活與傳承
中國地緣遼闊,有56個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中都創造了獨特的、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民族文化中凝聚、積淀的思想精華,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不僅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也為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獨特貢獻。”[17]民族傳統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創造的“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不僅僅是民族文化發展的珍貴歷史遺產,更能作為有生命力的精神基因,為當代社會文化、藝術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養料。另外,文化基因不僅是民族文化的特色,也是民族的標志。“文化基因使文化得以傳承,因而也使一定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具有了相對穩定的特質,即人們常說的保持了文化的民族性。”[18]51在歷史長河中,民族傳統文化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在發生著主流或非主流的變化,不同的文化元素被淘漉和篩選,經歷著重組與再生,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傳統文化始終不變的是其文化基因和遺傳密碼。“說到底,民族就是文化基因的產物,是一定人群在文化基因作用下反過來認同和歸屬于文化基因的共同體。如果丟掉了民族文化基因,那么民族也就消亡了。”[18]52可見,“文化基因”不僅是我國民族文化多樣性與文化創造力的充分體現,更是區別不同民族文化的識別碼,是民族歷史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的紐帶。隨著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增強,“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19]。然而,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語境中,民族文化只有經過傳承和發展才能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中,激活民族文化基因,傳承民族文化精神,同時使其成為當代民族藝術發展的因子和機緣,對文化發展和民族認同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電影逐漸成為現代社會中深受人們喜愛和認可一種重要的媒介傳播形式,成為記錄民族生活和展現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這也為我國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平臺。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電影不僅僅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而存在,而是被置于整個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中的“核心地帶”。這樣,我們就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我們在發展作為產業的電影時,應如何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美學與藝術韻味并在國際上有競爭力、體現中華文化深厚底蘊的電影產品;如何激活民族文化的基因,使之在現代語境中,煥發出新的活力,成為電影產業文化的核心與靈魂。另一方面,隨著當前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相當多的傳統文化瑰寶在逐漸走向消亡。而在現代語境中,傳統文化精髓作為隱性基因只有經過激活,才能夠實現它的潛在價值。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又面臨如何對民族傳統文化遺產進行傳承與生產性保護,以及如何加強對民族文化身份的確認,以使其在多元共生的當代文化景觀中彰顯自身價值。這兩個問題歸結為一點,即我們的藝術包括電影都面臨著如何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如何激活民族文化基因進行現代創新,從而在傳承民族文化的同時提升產業競爭力的現實問題。在這方面,電影《劉三姐》為我們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如上文分析,劉三姐傳說是民族文化的寶貴遺產,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廣西民族民間文化的挖掘整理與推陳出新境況下所創作的電影《劉三姐》借助電影藝術的影像形式傳承與傳播了壯族的文化精髓,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劉三姐傳說和山歌雖然是是農耕文化的產物,但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農耕時代偏遠的邊界走向現代化的工業社會,從嶺南走向全國乃至走向世界,存在著多種原因。從《劉三姐》作為藝術作品的角度來考察,我們會發現,劉三姐的主題并不限于男耕女織的農作生活,而是反映了壯族文化中對自由、平等、樂觀、浪漫等的追求,這種普世性人文精神有溝通傳統與現代、地方與全球的功能,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這是《劉三姐》能夠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同時,由民間人物經過影像藝術轉換與創新而成的劉三姐形象不僅是充滿智慧、富有正義感、不畏強權、向往自由的壯鄉兒女的典型寫照,更反映了中華民族崇尚自然、追求生存與愛情自由的民族品性,“是一個階級、一個民族的精神”[8]115。雖然在“十七年”特殊語境下,《劉三姐》還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電影藝術家自覺運用民族文化資源進行創新,用電影呈現壯族的歷史記憶、文化傳統、人文精神和道德追求的努力,對當下的藝術創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傳統文化日益衰落的今天,在大力提倡文化軟實力的今天,我們應該自覺挖掘傳統民族文化資源,借用電影影像藝術激活與傳承傳統民族文化的因子,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的優秀的藝術作品。同時,電影要想獲得持久的發展和保持充沛的生命力,必須要有源源不斷的活水和能量的補給,而這活水和能量的源頭所在正是傳統民族文化中最深層、最本質、最鮮活的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基因不但可以為當代電影藝術發展提供靈感和源泉,更是我國文化藝術持續繁榮發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因素。我們只有用現代意識從整體上來認識民族傳統文化,將優秀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握民族文化基因與人民心靈共顫的規律,才可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把民族文化基因的生命活力注入文化藝術之中,把當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產業發展推上一個新階段。
參考文獻:
[1]龔麗娟.民族藝術自由理想的典范生發——影片《劉三姐》與《阿詩瑪》的生態批評[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2]劉長林.宇宙基因·社會基因·文化基因[J].哲學動態,1988(11).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李一鳴.試論壯族民間故事所體現的壯族人民的倫理道德觀[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4).
[5]覃德清.壯族文化的傳統特征與現代建構[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
[6]習近平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N].(2014-05-05)[2017-01-09].http://www.gov.cn/xinwen/2014-05/05/content_2671258.htm.
[7]王東.中華文明的五次輝煌與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學刊,2003(5).
[8]覃忠盛.《劉三姐》的民族藝術審美[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1).
[9]羅傳洲.廣西民族文化基本元素與核心價值的詩意展示[J].當代廣西,2010(11).
[10]周飛伶.壯族題材電影的民族符號意義:建構現代之夢——以《劉三姐》與《尋找劉三姐》為例[J].當代電影,2014(7).
[11]楊寧寧.劉三姐形象演變探微[J].民族文學研究,1998(1).
[12]張維.劉三姐[M]//鄭雪來,主編.世界電影鑒賞辭典(1).增訂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13]牛永勤.劉三姐與壯族山歌文化[J].中國教師,2005(11).
[14]李曉峰.論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發生[J].民族文學研究,2007(1).
[15]章柏青,賈磊磊,主編.中國當代電影發展史(上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16]林進桃,劉紀新.時代背景下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奇葩[J].四川戲劇,2009(10).
[17]徐向紅.萃聚傳統精華涵養民族精神——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孔子研究院重要講話精神的體會[EB/OL].(2014-01-30)[2016-05-22].http://www.qstheory.cn/zl/bkjx/201401/t20140131_3179 47.htm.
[18]趙傳海.論文化基因及其社會功能[J].河南社會科學,2008(3).
[19]滿運來.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EB/OL].(2009-11-27)[2016-05-25].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0464507.html.